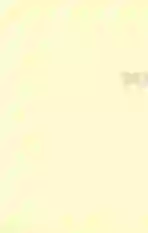别逃了,活下去
2014-08-19杨庆祥
杨庆祥
在去往锡林格勒草原的路上,发生了一场并不严重的车祸。我们年轻的女主人公因此受伤——腰椎骨折。在医院里休养了快三十天之后,她向亲人们隐瞒了自己痊愈的事实,选择继续躺在病床上,做一个“非正常的病人”。小说是这样描述女主人公此时的心理的:
我点点头,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可以站起来的事情。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我可以站起来的话语,也不期待恢复正常后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灾难。
两个星期后,褥疮并没有长在后背或是腰上。它们长在了我的脑袋里,慢慢腐蚀了我的意志和思维。
我没有再次尝试走路的想法,也没有想到外面走走的冲动。没有什么地方比被窝里更让我觉得安全的地方。我把被子裹得紧紧的,这样使我安心。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没有认真地去想过,也想不明白。前面的路像是一片在黑夜中的汪洋大海,没有船只,没有灯塔,没有月光。只是一片无际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正如二狗所说的,我们每人都是这片大海中一座冰山,一座孤岛,我害怕被淹没。
这是青年作家孟小书的中篇小说《锡林格勒之光》向我们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尾奇崛有力,它让我想起卡夫卡的经典之作《变形记》。在《变形记》的开篇,卡夫卡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一开篇可以和《锡林格勒之光》的结尾进行互读。《锡林格勒》中的女主角“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另外一个格里高尔,他们共同面对日益商品化和科技化的社会事实,在被资本组织起来的残酷竞争中被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但稍有不同的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似乎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他甚至没有太多的意识,而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了奇异的变形。而在《锡林格勒之光》里,这种变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系列事实的打击下,主人公最终自觉并有意识地选择了做一个“永远的病人”——虽然这个病人比起其他人来说显得如此正常。《锡林格勒之光》由此具有了某种症候性,一场意外的车祸导引出了沉重的社会现实,虽然孟小书的叙述还稍微显得有些单薄,但是,她分享了一代人共同的幻灭体验。宏大的历史已经远去,父辈的旗帜已经褪色,在资本的汪洋大海中,个体的孤岛似乎注定要被无情地淹没。
这是孟小书的小说呈现的一种特质,她善于在日常的、看似非常“现实主义”的叙述中嵌入后现代的元素,在故事的扭转和变形中展示生活本身的荒谬和非逻辑性。在《爸爸不是我杀的》这部短篇小说中,故事的核心要素其实相对简单:一个执着于电影梦的年轻人和他的父亲发生了争执,并在一场冲突中失手将父亲推下了悬崖。但孟小书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连环套”的叙述方式,通过李嘉华的梦——在他的梦中还有另外一个梦——也即“梦中梦”的结构来展示其与父亲的冲突以及陷入迷乱后的精神状态。这个短篇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对于主人公来说,他混乱的内部只能通过混乱的、不合逻辑的梦境予以呈现,这种梦境同时又因为描述得过于真实而呈现出本来的“非真实性”。在这种梦非梦、真非真、假非假的叙述的最后,“北京西城区,一名青年男子从21层楼顶跳下,身亡。”爸爸是谁杀死的?我们不知道。“我”又是被谁杀死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了解到的仅仅是,“电影梦”变成了一个死亡的诅咒。如果我们的联想能稍微丰富一点,也许会想起大卫·林奇的经典电影《穆赫兰道》,好莱坞寻梦最终不过变成了一场“梦中梦”,资本生产的幻觉像麻醉剂一样俘获了生在其中的许多人。也许,孟小书所极力想要做到的,就是刺穿这个梦,展示生存本来的真相和生命本来的破败。
在另外一篇小说《擒梦》中,男女主角拥有非常文艺的名字:擒梦和思远。一个暗示着实现梦想的愿望,一个暗示着追逐远方的梦想。这两个年轻人在一次邂逅中认识——记住,在大都市中,这种偶然的邂逅往往被视为日常生活的缺口,由此可以探求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但是,孟小书摒弃了这种通俗小说式的想象,她几乎是展示了一种原封不动的、可以从我们的新闻报道里检索到的故事。他们相遇,但并没有奇迹发生,他们之间甚至都没有发生爱情,这是多么乏味而无聊的现代相遇和现代生活。故事最后的结局是,男主角死了,因为他为自己的淘宝店操劳过度(这其实来源于一个新闻报道)。而我们的女主角,她大概小有悲伤,但是,她不过是“呆呆地望着天空”,并问她身边的小狗:“你觉得烟花像什么?”
这种情绪上的无力、空虚和百无聊赖是孟小说中的普遍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都市精神疾病——我所读到的孟小书的全部作品,其背景都是大都市。西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或许,没有像厌世态度那样无条件地属于大都会的心理现象。厌世态度首先产生于迅速变化以及反差强烈的神经刺激。……无限地追求快乐使人变得厌世,因为它激起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中,以至于最后对什么都没有反应。”我在其他青年作家——比如张悦然的作品中——也感觉到了这种情绪的存在,在《好事近》里,张悦然就借女主角之口这样陈述其感情观:“爱不要那么用力,恨也不要那么用力”。在这一点上,孟小书和她的同代作家似乎分享了共同体验。在短篇小说《逃不出的幻世》中,女主角秦梦(这是另一个擒梦)从北京“私奔”到苏州,并在此遇到了男主角白慕云,他们几乎重复了《擒梦》的故事结构,相遇,然后似乎发生了一点什么,似乎又没有发生什么,因为对于我们的女主角来说,她的人生哲学不过是:“事事皆是命中注定,我不决绝,我不反抗,随遇而安。”最后她发现,白慕云的境遇和自己极其相似,原来,我们所寻找的,不过是另外一个自己。这里的潜台词似乎是:既然如此,何必寻找?既然一切都是逃不出的幻世,又何必出逃(私奔)?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主要在于它题目中的一个“逃”字。如果要严格要求我们的作者,也许她的小说并没有将这个主题演绎得让我十分满意。但即使如此,“逃”依然升华了这部小说。不必提到门罗那篇著名的《逃离》,即使是看看我们当下的许多创作——比如青年作家蔡东的小说《净尘山》——都涉及“逃离”的主题。当梦想遭遇现实,当有限的人生遭遇无限的时间之流,最重要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当无力的个体遭遇强大的社会机器的时候,也许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逃”。有人逃往“净尘山”,虽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有人逃向“地震”的现场,虽然这种历史的偶然并不能完成最后的救赎,而孟小书干脆就指出,别逃了,因为一切皆是幻世。
我们真的只能就此止步吗?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当然觉得不应该如此,我总是试图重新激活宏大的东西,来刺激我的同代人摆脱这种无处可逃的历史境遇。但对于1987年出生的双鱼座,并可能有点小小的强迫症(她作品中的主角都会执着于抠死皮之类的动作)的孟小书来说,她的故事就是她全部的表达。所以,她的任务可能仅仅是——也只能是——将故事锤炼得更加精彩有力。同时她也需要明白,讲述故事其实是危险的行为,很有可能就像《雕塑师》中所说的那样,因为对于艺术的迷恋,最后将生命都搭进去了——从这个角度看,《雕塑师》是关于我们的时代里艺术与生命关系的残酷隐喻。
最后,还是回到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锡林格勒之光》上来,这部小说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梦里,我变成了一条在寒风中的橡皮泥,硬得开始干裂。我随着寒风不停滚动在跌宕起伏的街道上,像是在坐过山车般地乐在其中。一觉醒来,动弹不得,我面带微笑,仿佛看见了锡林格勒上的日出。
这个结尾让我想起很多——曹禺的《日出》,契科夫的《樱桃园》。正如竹内好所言:文学不是要人死的,而是要人活的。因为有了这锡林格勒的日出以及对它的叙述,我们由此得到信心,即使一切无处可逃,大概也可以勇敢地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