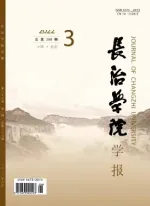论巫术与禁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2014-08-15肖发荣
肖发荣
(西安石油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陕西西安 710065)
女性社会地位的形成是众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巫术与禁忌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文化传统中遗留下来的社会控制力量①张光直先生在研究古代中国的权力竞争者问题时,就从控制手段着眼。他认为,“以控制少数几项关键资源的方式,以积聚手段的方式来达到占有手段的目的”,这是权力竞争的“决定因素”。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页。,在两性社会地位初步分化的过程中,巫术与禁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巫术对性别的选择
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巫术是部落社会里十分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造者。
巫术与两性社会地位的关系非常密切。巫术作为一种由文化传统遗留下来的十分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因而对巫术的控制和掌握也就成了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马林诺夫斯基报道说,在多布人中,妇女之所以具有比特罗布里恩德岛妇女更高的地位,是因为她们掌握了生产活动中的巫术手段,而且呼唤神力、惩罚过错的特殊权力很大程度上也操纵在她们手中。[1]31-34普理查德的研究也表明,在努尔人中,女人有时也可以成为预言家或巫师,从而获得很好的社会声望。[2]203相比而言,巫术对于提高男子的地位表现得更加突出。在大多数部落社会里,巫术都是男性的特长,尤其是男性酋长的特长。在特罗布里恩德岛,酋长就通过巫术强化了他控制民众的力量,这是因为在他的麾下有着最好的巫师。当有人开罪他或损坏他的权威时,他便召唤他的巫师,用黑巫术(blackmagic)把对方置于死地。由于他能够公开进行这件事,因而土著人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恐惧。酋长还可以施法造成长期的干旱,以此表示他对子民的不满,从而提高他个人的权威,从而逐渐培养了部落成员对其运用巫术能力的依赖,以及对其权威的顺从。因此,由谁掌握巫术力量也是制约两性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人类学史上,弗雷泽最先将巫术区分为“个体巫术”和“公众巫术”两种。“个体巫术”即为了个人的利害而施行的巫术仪式或法术,“公众巫术”则是为了整个部落里的共同利益而施行的巫术。从“个体巫术”到“公众巫术”的分化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是“个体巫术”并未被“公众巫术”完全代替,只不过“公众巫术”在社会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个体巫术”的影响尽管存在,但已微乎其微。至此,巫师已不再是一个个体巫术的执行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公务人员。当部落的整体利益被认为是有赖于这些巫术仪式的履行时,巫师就上升到一种更有影响和声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容易地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份和权势。因而,这种专业就会使部落里一些最能干的、最有野心的人们进入显贵地位。因为这种职业可提供给他们以尊荣、财富和权力的可能性,而这是任何其他职业所难以提供的。[3]48弗雷泽总结说:“就巫术公务职能曾是最能干的人们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之一来说,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作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决非微不足道。”[3]50很显然,“公众巫师”是在掌握了“公众巫术”之后才成了社会权力阶层的一份子,他们对“公众巫术”的掌控不仅是其个人权力地位上升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为部落的安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从传世文献来看,中国上古社会中也确曾有过一个时期,巫术在社会生活中达到了一种十分活跃的地步,甚至影响到当时的社会稳定。《国语·楚语》中,保存了一段观射父对上古社会中巫术发展情况的追述,其云:
古者民神不杂,……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4]595-5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少昊以前,女性在巫术活动中十分活跃;第二,少昊末世,巫术在社会中泛滥,已经普及到社会的每个成员,宗教目的不必再通过富有宗教经验的巫师就可以实现,人神交通极为随便;第三,颛顼时进行了严厉的巫术整顿,命重、黎“绝地天通”,垄断了巫术的使用权,恢复了以前“民神不杂”的宗教秩序;第四,尧舜之世,巫术似乎又一次死灰复燃,于是发生了对巫术的第二次打击。在前面引述的人类学材料中,我们已经指出,巫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对巫术的掌握与否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关,张光直先生正确地指出了巫术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作用,他将取得这种知识和技能与谋取政治权威联系在一起,他曾说:“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5]29这恰好说明掌握公共巫术具有获得权力的重要意义。
然而,上古时期对巫术的两次沉重打击并没有完全摧毁中国的巫术,女子在巫术活动中仍然扮演着一些重要的角色。《周礼·春官》就专门讲到女巫,她们的职责在于“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若王后吊,则与祝前;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6]816-817。可见,女巫的主要任务只保留了求雨、免灾。如果说,《周礼》对女巫的记载只是制度上的说明,那么《左传》、《礼记》等书中则为我们保留了一些女巫真实存在的事例。如《左传》鲁僖公二十一年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郑玄注说:“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人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7]390《礼记·檀弓下》载:“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8]157-158这是说鲁穆公欲通过暴晒女巫(巫婆)以求雨抗旱。
结合郑玄注来看,“尪”即仰面不能俯身的残疾病人,而此处之“巫”在县子看来只不过是“愚妇人”而已,其为女性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不难看出,巫、尪均为女巫,其承载的社会功能即在祈祷请雨;而焚烧或暴晒女巫、残疾之人乃是中国上古社会中遭遇旱灾时的应对方式之一。
实际上,使用女巫求雨抗旱的事例至少从商代就已经开始出现。陈梦家先生曾说:从卜辞来看,当时王者的地位已极巩固,政治、武力与宗教巫术的执掌都已为男性占有,在各期卜人中都无女性,用女巫的情况只是在求雨时才可见到,“商代的女巫已仅为求雨舞雩的技艺人才,不复掌握宗教巫术的大权。”[9]533陈来先生也说,商周的古巫虽带有上古巫觋的余迹,却已转变为祭祀文化体系中的祭祀阶层,其职能也主要为祝祷祠祭神灵,原来的公共巫师已转变为祭祀文化结构中的一个角色。[10]32裘锡圭先生《说卜辞的焚巫尪与做土龙》一文对卜辞中所记“焚”字和一些女巫的名字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商代有焚巫求雨的习俗”,“焚尪求雨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习俗,其产生也许早于焚巫”。[11]23《史记·滑稽列传》说西门豹曾在邺地打击女巫[12]3211-3213,这正好说明女巫已完全融入祭祀阶层中;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女巫掌握了公共巫术从而形成了大众对她们的依赖。尽管她们遭到了打击,但她们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则是不争的事实。掌握了“公众巫术”使女子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和巫术联系较为密切的禁忌又会对女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二、性别视域中的禁忌
根据人类学家的调查和研究,我们看到,在部落社会中,对女性的禁忌主要包括经期禁忌、孕期禁忌和产期禁忌,这在世界各地的初民社会甚至文明社会中都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而这些禁忌的结果便是对两性的隔离或限制。
弗雷泽很早就在《金枝》中提到,在许多部落社会中,人们把经期、产期的妇女看作危险人物,严禁她们与别人接触,并常把她们赶到偏僻无人之地隔离起来。普韦布洛人周围的其他部落就在住地为经期妇女准备小小的房间。在此期间,她必须自己烧饭,用自己的餐具,彻底同外界隔开;即使在家庭生活中,她也不许接触任何东西,否则就是亵渎,尤其是她若接触了猎手的器具,人们就认为它们的功效将被毁掉。将禁忌期的妇女同男性相隔离的现象在科维奥人中十分突出,男子在家族住宅与男子宿舍间往来;女子则在家族住宅与位于更低下处的月经小屋间来往。男子在进行神圣的祭供之后,消除其神性回到居住空间;女子由月经小屋回归时则需要进行清洗。分娩时,女性进入较月经小屋更低的森林中的小屋,不能同男性接触,由少女进行照料。主持祭祀的祭司在男子宿舍中闭门不出,避免同女性的接触,接受少年男子的照料。这种对禁忌期女性的隔离现象也见于美国西北部阿拉斯加附近卡迪亚克岛人、布赖布赖印第安人、南非班图人、巴佩德氏族、澳大利亚土著、新几内亚阿拉佩什人中。②关于部落社会性别禁忌的记载,可详参:弗雷泽《金枝》,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310-334页;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4页;吉田祯吾《宗教人类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0-131页;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禁忌在文明社会中同样是较为普遍的。黄石在《关于性的迷信与风俗》中写到:“印度的妇女一入定期不洁的状态(笔者按:即月经),便立刻退居于孤僻的地方,不得与常人相接。”在此期间,“仅仅发生同丈夫同居的年头,也算是重大的罪恶”。[13]18希伯来《旧约圣经》中记载:“妇人行经,七日不洁……妇人在不洁的时期,她所睡的寝具也是不洁的,所坐的东西也是不洁的。”[13]54-55
在有些地方,不仅保留了女性禁忌的形式,而且还保留了它的功能;而有些地方仅仅保留了功能,形式已发生了变化。对于前者,我们看到在中国先秦社会中的“居侧室”之礼即是如此。《新书·胎教》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寠室。”“寠室”,《大戴礼记》作“宴室”。卢文绍曰:“宴室,夹室,次宴寝也,亦曰侧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晨,女史皆以金环止御。王后以七月就宴室,闭房而处也。”[14]390《礼记》中也有记载,如:
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斋,则不入侧室之门。[8]390
妾将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问之。
公庶子生,就侧室。[8]395
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396
可见,不管是贵族妇女如王后,还是普通人之妻妾诸类,产期将近,都要从正室移至侧室居住,一直到孩子降生,不能与丈夫见面。即使丈夫不顾俗忌来探望,她也自称“不敢见”,断然拒绝。如果男子正值斋戒,更不能跨进侧室半步。这显然是对以前禁忌期隔离妇女习俗的沿袭。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产期禁忌的习俗在战国以降的社会中仍有很大的影响,即使到汉代还很流行。例如,汉代江南人对分娩之事尤为忌讳,产妇本家也不敢让妇女在家分娩,而是让她住到远离人群的空墓或道旁茅舍中待产。等到生子满月后,才允许她进入家门。不仅如此,汉代人还把对妇女禁忌的观念延伸到其他一些领域。王充即说:“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恶之。”[15]228对于后者,笔者所说的功能的保留就是指对女性禁忌观念的存在,因为古人认为女人不洁、女人不祥,而这种观念在军事活动中的影响就更为显著,如《左传》所谓的“戎事不迩女器”[7]399。
人类学家大多将这种禁忌的原因归于原始人的迷信心理,认为其根源在于这些非常时期中的妇女是“不洁的、污秽的”观念,而这种不洁恰好构成了对神圣事物的挑战和威胁。罗维报道说:“带有神圣气味的种种活动之所以禁止妇女参加,就是怕被月经玷污了;有时不准妇女接触某种圣物,也以此为理由。”他还强调说:“在蛮族女性观之形成中,月经的影响是未可小视的。”[16]243大量关于原始部落的调查材料表明,男性确信他们在狩猎或种植方面的成功与自己从男子会所里继承来的巫术有关,而行经期、妊娠期的妇女对这种巫术的效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对月经来潮或怀孕妇女必须进行隔离。前面我们提到的“居侧室”之礼,毫无疑问,就是分娩期隔离的遗俗。[17]65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尚书·舜典》所谓的“百兽率舞”[6]131,《吕氏春秋·古乐》所谓的“帝尧立,乃命质为乐……以致舞百兽”[18]285,这些都可能是集体狩猎之前用舞蹈形式去表演与野兽搏斗的过程,以期捕获更多野兽,这是典型的原始巫术。这些历来为人们疑信参半的传说告诉我们,中国的先民确实有过关于狩猎巫术的信仰,为了保持这些巫术的纯洁和效力,实行妊娠期的隔离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早期社会中,对女性的禁忌的确是制约女性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由禁忌所导致的对女性的隔离给女性社会地位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禁忌”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神圣性的和危险性的。人类学家在研究禁忌时经常使用这两个概念,二者之间的转换十分微妙。吉田祯吾曾说:“神圣就是危险。”[19]197-198本尼迪克特也认为,神圣之物常常有两种可能的方面,它可能是危险的源泉,也可能是赐福的源泉。[20]19、94因为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来看,在上面所说的以女子为不洁、不祥的大量事例之外,还存在一些部落社会把月经视为危险的同时也给予了它神圣的意义。例如在易洛魁印第安人社会里,月经中的妇女被隔离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在月经中神秘的力量达到了顶峰;北美的阿帕契人则从来不把青春期的女孩当作危险之源而隔离,他们认为女孩初潮是一种有力的超自然祝福;在普韦布洛人社会中,妇女不仅没有经期小房,而且也不在此时防范妇女,月经期的妇女生活与日常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些社会尤其是易洛魁社会中,禁忌的二重性都得到了发挥,女子的社会地位较高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早期社会中对女性的禁忌并不局限于经期、孕期和产期。在中国上古社会中,我们还存在许多丧期中的性别禁忌。如《礼记·杂记上》载:“子羔之袭也,……曾子曰:‘不袭妇服。’”[8]584曾子批评子羔死后穿女人的衣服。《杂记下》载:“妇人非三年之丧,不踰封而弔。”这是说,除非有父母之丧,否则妇女不能越过国境去吊唁。又说:“嫂不抚叔,叔不抚嫂。”[8]619据周礼,为死者进行小敛和大殓的时候,死者的男女亲属都先后抚尸而哭,但例外的是,嫂子不能抚小叔子尸体而哭,反之亦然。《丧大记》说:“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8]630伺候死者更衣诸事的人必须是和死者性别相同,不能为异性。丧期中对性的禁忌同样是非常严格的,如《丧大记》所谓“覃而从御”[8]656,即是说主人行过覃祭后才可以到燕寝和妇女过夜;“期,居廬,终丧不御于内者”[8]657,服齐衰周年而守丧在倚廬之中,并且一直到终丧也不到内宅和妇女过夜。
另外,性别禁忌还涉及到寡妇这一特殊的人群。《礼记·坊记》曰:“寡妇不夜哭。”[8]771是说寡妇不要在夜晚哭泣,免招非议。对寡妇的禁忌,甚至还波及到她的孩子,如《坊记》所谓“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③《礼记·曲礼上》也说:“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16、771页。
当我们回到中国的上古社会时,我们发现:禁忌对女性来说体现的大多是“危险”的一面,而缺乏“神圣”的一面。这就使经期、孕期、产期甚至是丧期的女性和整个社会秩序处在了对立的关系中,甚至由此引发的女性不洁、女性不祥的观念,也使女性在其他的社会活动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这就说明,当人们把神圣与危险统一起来时,性别禁忌可能不会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片面强调它的危险性时,禁忌则会对女性社会地位构成严重的制约和限制。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是从巫术与禁忌两个方面初步考察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形成。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巫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如果能够被女性所掌握,那么这将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而对女性的禁忌,则往往造成女性与社会的隔离,这就使得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1][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英]普理查德.努尔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英]弗雷泽.金枝[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4]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6]阮元.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J].燕京学报,1936.(20):533.
[10]陈来.陈来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裘锡圭.古文字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高洪兴:黄石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4]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5]王充.论衡[M].诸子集成(7)[C].上海:上海书店,1986.
[16][美]罗维.初民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7]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
[18]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19][日]吉田祯吾.宗教人类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0][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