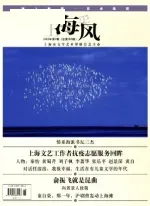观点集粹
2014-08-15
腐败与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刊文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各国外交官——这些外交官来自拥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他们的行为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这两位教授从纽约市政厅获得了所有外交官的违章停车信息。在纽约,尤其是繁华的曼哈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停车,是件很困难的事。外交官在违章停车上有一个便利,即外交豁免权,他们违章会被记录,却不用交罚款。面对这样一个制度“特权”,各国外交官的违章情况却有天壤之别。来自北欧的外交官相当自律,十年间的违章记录为零;而来自中东某国家的外交官一年违章超过400次,平均算起来,就是每天至少有一次违章。
该研究发现,一名外交官违章停车的次数与其所在国家的腐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可见,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文化对个体行为有重要影响。
创新是一种价值观
中国青年报刊文说,《驱动力》作者丹尼尔·平克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思考方式,第一种是功利的,让我们不择手段地追求短期利益。第二种是无私的,在使用这种思考方式的时候,我们很看重人际关系,会争取去理解、同情他人,而且会有意识地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
以色列有一个幼儿园因为家长来接孩子时经常迟到而困扰,于是有一个经济学家帮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罚迟到的家长的款。我们可能觉得为了逃避罚款,迟到的家长数量会减少,可是实际上在执行罚款制度之后,更多的家长开始迟到了。这是因为,在执行罚款制度之前,家长觉得他们和老师是朋友,迟到时会感到后悔和歉疚。而执行罚款体系之后,家长感到老师是在给他们服务,即使迟到也不用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已经用钱弥补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说,一旦人用功利心态面对某件事之后,就很难再让功利心态消失。现在的精英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结构,其实都在鼓励我们使用第一种功利的思考方式,但是科学研究证明,创新能力和情商都是由第二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因为创新本身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重点或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要带着好奇、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跟很多不同的人接触。只有从和自己不同的人身上学习,珍惜他们的才能,并和他们相互帮助,才能最大地激发创新的潜力。可是当我们带着功利心态的时候,就很容易相互怀疑和排斥,让交流合作变得非常困难。创新是一种价值观,它与功利相矛盾。精英教育体系最失败的一点,是鼓励相互竞争,学生们太相信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知道其实生活并不应该是一架通向成功的梯子。
院士的科学三问
文汇报刊登中科院院士汪品先的来信,从三个问题谈科学创新。
一、科学究竟是生产力还是文化?原创性的科学,往往是出于精神动力而不是追求物质目标。布鲁诺为“日心说”献身并不涉及生产力,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也没有考虑提高产量。创造需要激情,单纯的物质目标很难产生“吃力不讨好”去做原创性研究的激情,而只会去寻找“成功”的捷径。
二、汉语在科学创新中是什么地位?现在我们最好的研究成果用英语发表,学生学习科学最好用英语教学。展望未来,汉语是不是只能在一般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保留,而应该逐步退出科学舞台?历史上通用语言都是随着国家兴衰而变化,科学同样如此。英文的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势的产物。而当年牛顿写论文用的是拉丁文,爱因斯坦用的是德文,都不是英文。
三、如何弥合科学和文化的断层?现代科学是在文艺复兴中产生的,甚至有人说创立现代科学的不是牛顿,而是达芬奇。许多国家设有“科学与艺术院”,两者放在一起。我国不然,从今天的科学院到高考,都是文理分鲸,中间有个断层,断层的牺牲品是创新。《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两年前用自费建造的深潜器下到深海一万米,创造了单人下潜的世界纪录;译成四十种语言的《万物简史》,作者布莱森不是科学家,但能生动细致地告诉你大科学家们当年怎样创新。相比之下,我们恐怕缺了一类为科学和文化构筑桥梁的人。当然还有政策,发达国家评估大型科学计划或研究机构,有一项标准叫“教育与普及”,要向纳税人交代自己的工作,我国是不是也应该引进,去弥合科学和文化间的断层?
女排重振的背后:放权与不折腾
澎湃新闻报道说,中国女排在意大利获得世锦赛亚军,取得16年参赛最佳战绩,而带来这一切的,不仅仅是郎平和姑娘们的努力,还有排管中心主任潘志琛的放权与“不折腾”。郎平说潘志琛最打动她的是一句话:“我是门外汉,队伍的一切你来负责,其他的我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潘志琛不揽权,不越位。在各种赛前动员会、赛后发布会,以及队伍备战的各个场合节点,都没有他的身影。而在郎平的实验遇到一些非议时,他又主动屏蔽了这一切。
在被定义为某种精神的女排项目中,郎平的实验确实有点过于前卫,甚至是反女排精神式的。训练中,以往的魔鬼训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单位时间内的高强度和质量。而在赛后,查房、没收手机等军规没有了,队员们可以和她聊聊人生、未来,包括一些诸如美容等女性话题。针对人才流动性差、队员基础不扎实的特点,她启用了一个大国家队的概念。一批批队员,被走马灯式的在国家队训练,并出现在各种关键的比赛中,不惜本钱。包括朱婷、袁心玥等新锐,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掘出来。
郎平精准地把握了女排现状,将国外一些理念移植到国家队身上并和传统的训练思想相融合。她总是要求自己比队员提前半个小时来到训练场,在如此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加上郎平独有的大赛调节能力,队伍迅速拧成一股绳。从决赛赛后姑娘们玩自拍的主动,以及各方面的评论可以看出,郎平式的思维已经植根到队伍的各个角落。在体育总局各支运动中心,这种中心领导+主教练的合作模式就好比美国体育联盟中的总经理和主教练的关系,具有普遍推广价值。在中国三大球遭遇困境,主管部门“昏招迭出”时,潘志琛和郎平的模式也许能为前方照亮一条路。
发达国家的新定义
凤凰网刊文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长前阵子的发言“一个发达国家,不是穷人有车,而是富人搭公交”,如今已成了发达国家的流行新定义,也成为全球城市的愿景。
富人宁可牺牲隐秘的个人空间,放弃豪华的私人交通工具,跑去跟大家挤公交,代表了社会治安良好,大众运输系统安全可靠,接驳方便准时,而且舒适洁净,人潮流量紧疏合宜,即使高峰时间也不会挤不上车。同时,富人自愿不开车,也显示了素质,为了节约能源,能不开车就不开车。发达并不仅指有钱,还有思想的觉醒、道德的进步。亚洲许多城市已经做到这点,譬如香港,譬如东京。比起美国其他城市,纽约算是“发达”,曼哈顿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家庭不养车。虽然纽约的大众运输仍有改善空间,既不准时可靠,且恶臭脏乱,周末经常停驶,但纽约仍逐渐增建改善公交系统,从去年开始,甚至提供自行车网,供市民使用。私人轿车对城市来说,其实是负面的暗示。一条街,应该是人来人往,老弱妇孺无须人陪伴,而不是因为治安不好或空气污染,而人人只能坐在车里,徒留街面光秃秃,一点人气都没有。
一座城市的市政究竟办得如何,且看他们的市长自己愿不愿意天天搭公交上下班。
被滥用的道德问题
南方朔在《读者》上刊文说,当年我初进大学时,台湾依然贫穷,台大学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学生搭车都不排队,只要车一来,大家就一拥而上。这种情况被一个美国留学生写成一封读者来信登在报上,文章认为台大是台湾的最高学府,而学生连排队乘车的公德心都没有。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台大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发起了“台大学生自觉道德运动”。运动的压力的确使学生在等公交车时排队了,但公交车一来,排的队立刻大乱,大家还是一拥而上。
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供需不平衡的经济问题。当时公交车的供给少,等一班车要十几二十分钟,错过一班就会误很多事,拼了命地抢上公交车当然会成为常态。就像今天,台湾的交通工具选择已多,坐公交车的已少,没人叫他排队他也会排队。这并不是现在的人变得比较有道德,而是整个交通工具的供需关系已经完全改变。
道德虽和许多问题有关,但它不是每种问题的根源,用道德谈问题,通常只会愈谈愈糟。贪污问题就是一例。西方认为贪腐乃是政府的秘密所造成的,这也是西方的反贪特别强调政府必须透明的原因。北欧的瑞典之所以贪腐率低,就是因为瑞典的政治透明度举世第一。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以透明度来思考贪污问题,自古以来,我们是以道德来谈贪污问题。我们认为要防止贪污,就必须提高官吏的道德水准,使他们有一种清廉如水的节操,才可以一介不取。这些都是道德性手段,而不是制度性手段,所以才出现大家都说自己清廉,但总有人阳奉阴违的现象。
更名的纠结
人民日报刊登陈效卫的文章说,初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市,对该市名称叫法颇感疑惑:机票上明明清晰无误地写着伏尔加格勒,但当地人却言之凿凿地称之为斯大林格勒;媒体报道时今天用伏尔加格勒,明天又用斯大林格勒;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个名字都是官方正式名称。
据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规定,除了涉及民族、种族、宗教、性别等带有歧视、亵渎、侮辱性质的地名外,最好从一而终。频繁更改,容易丢失自我。地名的更改是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据专家估计,伏尔加格勒更名耗费约合人民币15亿元。更为遗憾的是,每次更名,实用主义者、没有政治倾向的普通民众都表示反对,最终或再次改回,或另起新名。一座城市的历史价值、固有内涵属客观存在,不会因名称改变而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受到德国无限制潜艇战而“恨屋及乌”,来自密歇根的国会众议员史密斯遂提出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议案:将那些含有“德国”“柏林”等字眼的地名统统改成“胜利”“自由”等。尽管这一议案最后未能通过,但多座城市闻风而动。全美60多个城市,几乎在一夜间完成了地名转换。更名潮带来了很多问题。在德裔比较集中的五大湖区,地名的更改导致当地人不胜其烦,在战后旋即恢复了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