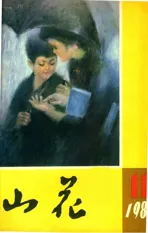沧桑之石:淳朴的栖居
2014-08-08人邻
人邻
余平,或余平们,对这些民居起这些意念,日趋喜欢且惋叹的时候,已是到了反刍人生的年岁。所谓落花流水、人面桃花,在余平是必定有些感触的。
牛的反刍,是为了消化,虽然也历经了漫漫长夜。而人的反刍,大率是微微苦涩的黯然咀嚼,即便内里偶尔也会隐含着的一丝杳远的温热和暗香。
余平面对的这些正在消亡、终将最后全然消亡的古老石头民居,心下的反刍,不仅仅是为了大叹一口气,“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样,灰了心。而是,他要在反刍之后,以磐石之心,思想而且力行,要这在愚蠢的所谓的现代化潮流之下“倒行逆施”——他苦心孤诣在当下时间里摸索的“瓦库”,即是一证。
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族群,会一直往前走,永不回头。至少其中的某些人,上苍赐予他们使命似的,他们会留恋,会徘徊,会反刍,会对“磨蚀”了的过去时光留恋、凝神、沉浸。余平即是这样的人之一。
余平和余平们,去跑那些古老的镇子,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追寻时间和空间之“慢”,追寻“慢”所保留着的更多的人性温暖?是为了抵御现代性的“快”的冷漠,那些水泥、钢铁和玻璃、塑料的冷漠?是为了安妥要“诗意地栖居”的自己的心?
是的!余平的回答是坚定的。
我们日渐生存于现代建筑,甚至后现代建筑之中——它们复杂,精巧,不乏微妙,但是它们从来不会让我们感到亲切,不会有人愿意让温热的皮肤挨近这样的建筑。
而这些至今依旧存在的石头民居,它们随意,简单,甚至有些简陋。它们没有埃及金字塔那样的高大雄浑,充满神秘意味;它们也没有希腊建筑无与伦比的力学结构和精美得令人咋舌的雕刻;它们也没有伊斯兰建筑上那些迷人的植物的花纹——一切都没有,但是,它们拥有几乎和人类自身一样的质朴、温暖。它们,几乎就是我们自己,这自然的石头和自然的我们的肉体。
这种“慢”的美,余平欲“倒行逆施”的,是大地赐予我们的安然,是令人安然的美。好些年前,我曾去过甘肃最边缘的临近四川的武都。《武都志》记载,武都始设于汉,武都颇为古老了。下车时正值傍晚,夜色浓重,沿街两溜小店,灯火初上,几分热闹,猛听到老板娘招呼,声音炸炸的透着热辣,恍惚就是从前什么时候古人行旅路上的一个小镇。
放下行李出来。沿一个斜坡下去,见小小的古旧城门。城门下陷,矮了许多,似乎过去的人也一律都是那么矮。从城门透过去看,那边,一溜几百米古老的青石板铺就,黯淡的光微微泛着生硬冷色。石板什么时候铺的,也许是在清代吧。磨蚀的痕迹看,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死,就从这青石板上过去了。
余平收入镜头里的这些石头民居,看似平凡,其实亦是有其玄机的。比如,这些石头民居地基的基坑就有玄妙处。通过考古,考古学家们发现埃及的金字塔,它的基坑是微微向内倾斜的,也就是说,所有石头的力量除了向下压之外,还有向内压去的力量。这些石头民居的地基,也采用微微向内倾斜的基坑的方法。
这些石头民居的建造,并没有图纸,没有多少算计,只是大略,结果却是准确精微的。大量的不规则的石头,在正式使用之前,没有人,包括具体建造的工匠,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每一块石头将用于哪个位置。只是到了具体建造的时候,看似寻常的工匠才开始显现他卓越的才能,他们,甚至是未卜先知:
这个人站在一边,叼着自家卷的旱烟,乜斜着眼角。小伙子们兜抬着一块石头,抬到地基一角。他们看着这个人,等着“起”或是“落”这样的话从他的嘴角飘落。建造屋子的第一块石头,一定要放在屋角的地基位置。这一块石头的奠定,极其重要。之后,一切由此蔓延开去。这样的砌筑,需要非凡的眼力,甚至石头的哪一个面,朝上朝下、朝里朝外,都极准确,绝无失算的。一二百斤的大石头,不会贸然搬上去,尔后又卸了下来。这人不动声色看着:“挪,挪,下,下,停,好,落!”那块石头就准确无误地落下。这人过去,用脚踢踢,偶尔也会弯下腰去拍拍,抚弄一下,似乎是对那块石头说了些什么。这人有些时候并没有将石头的位置做一丝一毫的改变,只是随意的絮叨,抚弄,而那块石头就如同给施了魔法,磐石一般安稳。
几乎所有石头,都各尽其用,没有一块会给废弃了。石头的多少,看来有随意性,却奇怪地将好。个别的时候,到了最后,还有很少的一两块,或三几块,也会给人收拾了去,安妥地放在某一个地方,人们会奇怪地发现,那儿是将好需要的。
数年前,我去过河北井陉的于家石头村。我不知道村里人如何从山上开采那么巨大的石头,如何运送到村子里,又是如何把它们堆叠起来。我尤其难以理解的是,石头村的房子,除了门窗,其他完全是用石头建造的。在一家的屋子里,我仰头看着那座石头房子的拱顶,觉出某种力量的自下而上,缓缓升到了屋顶,在那儿汇合。屋子的拱顶位置,我感到那种温和安逸的力量,悄然而坚固地笼罩在那儿。那个拱顶,和四围的石头墙,甚至和空出来的门窗,浑然一体,坚不可摧。在那儿,我还看到了三百多年前的几间屋子,堆叠起这间屋子的石头,任何一块都毫无松动,甚至叫人觉得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过是凿去了其中一部分石头而已。
更叫人吃惊的,是村口一座三层的亭子。亭子用大小不规则的石头砌筑,其中竟然有很多未经凿制处理的原石。石头与石头之间,亦不用泥土黏合,似乎只是随意堆叠起来的,叫人疑心会在什么时候轰然坍塌下来。然而,这座看起来松散随意的亭子,在力学上却达到了奇妙的均衡,三百年来固若铜浇铁铸。也正是因为这亭子的不可思议,村里有一个传说:当年建造的时候,出了银子的大户,说让村里的人把自己家的牛喂饱、备好,等着拉运石料就是。一夜过去,却没有人来各家各户牵牛运送石料。天亮了,人们惊讶地发现,亭子建起来了。人们更惊讶的是,各家牛圈里的门都拴着,每一头牛的身上却都是大汗淋漓。
早年的黑龙江的猎人,甚至会借助石头的神奇垒砌方法猎熊。猎人利用若干块大石头和很少的几根木头,建造起猎熊的石屋。熊进入石屋,只要稍稍触动猎人布下的诱饵,石屋就轰然坍塌下来,把熊死死压住。
余平亦曾在大地震之后,迫不及待地跑去看那些羌人的碉楼,却欣慰地发现“正是这样由不规则的石头、石片和黄泥叉合交错在一起的方法,使得每一部分都如同是木架构的榫卯结构……”。
先人的某些智慧,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人类究竟是愚蠢了,还是更加聪明了,难说?
余平先生也一定去过古徽州的渔梁坝(这个坝,先前的繁体是写作“壩”的,何等霸气),一定会惊叹于几千块青石条,力量无比地勾连封压在山坡上,桀傲不驯,横绝千古,霸气冲天。那些自觉大气的,去渔梁坝看看,看那几千块重千百斤的巨大青石条勾连在一起,压住半面环水的渔梁坝,再去论自己的气度如何吧。
霸气冲天的青石条,只是粗粗凿出的毛坯,就像未经调教的小马驹,显露出野性的筋骨。几百年过去,这些当年野性的粗糙青石条,已经满是天地沧桑,而那些在渔梁坝上游走的人,真的,轻若鸿毛。
作为设计师的余平,自然不会如同我等一般观察——他一定会观察体悟到远比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东西。这上苍赐予他的,是他的福祉,也是他毕生难破之“执”。
对自然赐予人类的,诸如石头之类建造的民居舍身饲虎般的迷恋,在余平,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遥遥二十年了。这种迷恋的缘起,在余平,初起该是自然的。继而的执着,是这些古老朴素建筑在引起某些人(包括环保主义者)目光关怀的同时,更加迅疾地给所谓的现代化携裹着的匆匆人流抛弃着。不仅如此——这是矛盾的世界,甚至那些古老民居的拥有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自己也迅速地放弃了,而绝不会以“盾”的形式抵御。依然存在的或正在衰老、坍塌的古老民居,迅疾转为水泥、玻璃和塑钢的简洁而便利的构成。在它们的“原地”,没有人至少是很少有人想要留住过去,留住它们。
余平苦心“留住”,展示在这儿的这些石头房子,是过往尘光延续下来的生命痕迹,看见且试图“留住”它们的人,惊讶、留恋、惋叹之余,即有余平或余平一干人命定般的矢志苦行,要为了它们的“存在”而身体力行。衣食,是我们常说的话,其实,居所也是我们的“衣”,人们劳作之后的得以安歇的“衣”。
作为不断行旅的人,余平或者我,每一次的出行,都会疑问,我们要去哪里,要看些什么?途经的每一座城市都是相仿若的,即便是所谓的挖空心思的追逐时光的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也至多不过是在审美上完成了建筑师的自家苦心冥想,完成了建筑师试图建立新感受而对过去的巨大破坏力,是结构,解构,再解构而已。
人们置身其间的时候,建筑师即便设计了似乎足够开阔的内部空间,饰之以木石,甚至皮草、棉麻,温暖其色调,游走其间的我们依然会觉出疏离感,觉出冷漠和压迫。这些水泥、玻璃和塑钢,在日落之后,它们瞬息间的冷,生硬,是近乎残酷的,即便有似乎温暖的灯光,于我们的内心也是隔膜的。那些灯光,随着巨大的玻璃窗向外漫延,更加深了黑夜的冷。
那些材料的非自然属性,不是我们曾经安身立命的自然之物——土、木、砖、瓦、石,不是曾经厚厚铺在我们屋顶的秸秆和茅草,不是在日落之后,能够在漫长寒夜慢慢散发着整个白天吸收的温煦阳光,让我们在持续的睡眠中,感受如同亲人一样的绵延温暖。
如今,那些蜡烛和油灯的温暖,带着自然之物的温暖,哪里去了?而人类究竟是为了什么,建造了这样的建筑,栖身其间,而且,还沾沾自喜。
——真的,我们要想起大地。我们已经忘却了它们。我们是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中长大的,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内心偶尔脆弱的时候,才会想起。可当我们想起时,大地已经千疮百孔。
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即便是对于释迦牟尼来说——他首先是拒绝极端的禁欲主义,认为那是对“对苦难的终极解脱”(涅槃)的阻碍。他在奢侈与纵欲之外,找到了另一条满足肉体需求的道路,这就是为人所知的“中间道路”,这佛学中的核心原则,也应该成为当下人类的生活准则。
我们甚至也不必像梭罗那样,林间栖身的简陋小木屋里,仅设一桌一椅一榻,甚至连喝水的杯子也只有一只,来了客人,是两个人轮着喝水的。
余平“对焦”的这些静静伫立在山河大地上的民居,这些穿越了时光的山坳和海边的石头房子,历经了无数尘世的悲欢离合,在山河大地上也在余平的镜头里与世无争地存在着。那些出入于石头房子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他们婚丧嫁娶,繁衍不息,不知何为道,却自然地合于大道。
迷恋于这种长久的美和温暖的余平,有如发愿一般,这二十年来,一而再,再而三,以田野考古的方式,跑遍了他所能知道所能去到的古老镇子。
余平,这个试图在现世空间里留下这些“石头”的人,也许会知道曾经有人写下的这样的两句诗:
就连上帝也不能
拯救一朵玫瑰。
他知道,但是,依旧。
这些古老的镇子:四川的桃坪、上里和扎坝,福建的东庠,安徽的南坪,贵州的培田、本寨、大同、青岩、天龙,江西的婺源、楠溪江,浙江的前童,重庆的宁厂,陕西的党家村……还有更多的古老镇子,余平还没有整理出来——比如我去过的河北井陉的于家村、北京门头沟斋堂的爨底下村和福建崇武古城,余平不会没有去过。
在这里,且让我们随着余平的带着风霜雨雪和汗水的镜头,稍稍做一番神游吧——
四川桃坪古镇,所居为羌人。这里的羌人一定是在过去某个血腥的年代,给强大的暴力逼迫着,不断迁徙,而隐匿在这荒芜的崇山峻岭中的。栖身桃坪的羌人,为了族群繁衍,凭高居险,聚众结寨,用这荒芜之地所能给予的石头,以血肉之躯、泥汗之手,用石头和石片砌筑了他们得以存身的寨子。
这样的几乎是随意砌筑的没有设计图的石头建筑,却奇怪地坚固。数十米高的碉楼,都是先建造一层,放置一年,来年再建筑上一层。而余平在自己的观察中也发现:“石块间的缝隙和黄泥,成为天然的物理伸缩缝,使坚硬的石头建筑成为一个柔性结构体,分散和消解了相互挤压的力量”。这些石屋的建造者,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秘密规程,并将这种规程永久坚守。这种规程,心手相传,表面看来几乎是任意的,但是确乎有其难以言喻的秘密。这种巧妙的建筑方法,一如某些原始部落的先民对某些工具的制造,一旦形成,就永久不变。他们甚至会以为稍有改变,这些建筑方法就失去了效力。石屋的建造,看似简单,但是交由一个现代的建筑师,面对那些杂乱无章的石头、石片,他一定是束手无策。
地域偏狭,为了利用山坡上难得的任何一块平地,每一户人家的屋顶,即是上一户人家晾包谷、说话歇息的院子。最有意思的是,桃坪的羌人选择的这处地方,甚至有山水从高处流下,蜿蜒到各家各户,甚是方便。
再封闭的地方,也会有人外出,会有人回来。沈从文在《边城》的结尾这样写道:“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得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余平镜头里那个在屋顶上晾晒了衣服的女人,在眺望什么呢?也许,她家里的男人已经出去了很久了。
余平的镜头下的福建东庠古镇,则是在海边了。
这些石头的民居,居然全都是用海礁石建造的。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天不绝人。在海上讨生活的打鱼人,岸上的造房子,没有山石,更无缘砖瓦,然而海边却有取用不尽的海礁石。甚至,亡人的坟茔也是用海礁石建造的。生于海礁石的居所,死亦是与海礁石相伴听涛而眠,从兹来,亦从兹去,该是不悲哀的。所谓“叶落归根”,身心之归,即是如此吧。
海礁石建造的石屋大多极朴素。寻常渔家唯一的奢侈,只是在门柱和门楣上用了略略凿制的条石。只有很少的大户人家,才在个别处有一些讲究,如将女儿墙上的排水口做成一只鱼形的浮雕,或者在某一面墙上镶嵌了一块雕成了莲蓬荷叶的浮雕。在临海地方,海风肆虐,似乎精细的雕刻是并不需要的,坚固才是最要。精细的雕花不仅是奢靡,也给人不沉稳的感觉。只有坚实的石条砌筑的屋子,才是叫人内心安稳的。尤其,男人出海捕鱼,留在家里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安然无恙才是最为要紧的。
我喜欢余平镜头里的一间石屋,尽管太有些简陋。因为石头外墙的要求整齐,朝里的一面墙就参差不齐。全然裸露着的石头内墙,高低不平,甚至都没有考虑到用什么去填实、抹平。裸露的石头墙面,石缝之间的任何一处,都可以将一根树枝、铁钉什么的插进去,在上面便利地挂上任何东西。
石屋的门开着,木板的窗子也开着,外面的光线透亮地照射进来。屋里,一个孩子在低矮的小板凳坐着,就着一只高板凳写作业。地上,有鸡和狗闲闲走着。叫人惊讶的是,屋里四处竟然是格外干净。
这样的屋子,叫我想起曾经去过的福建崇武古城里的一家。一位老妇人静静坐着,迎门的八仙桌背后的墙上,是六七个油漆斑驳的小镜框,里面一律是男人的黑白照片,有年轻的,也有老年的。也许,这些男人是在出海打渔的时候殁了的。留下来的,只有这些已然泛黄了的旧照片。
面对海洋,风大,石屋都不甚高大,不惟门,就连窗子也是木板的。我在北海的涠洲岛上,见到过这种木板的窗子。无风的时候,打开;起风了,关上就是。经常刮台风的地方,哪里敢用玻璃,更不要说用纸糊了。
海风的大,东庠古镇的石头民居,屋顶上的瓦,每一片都是压了沉甸甸的石块的。那些压在屋瓦上的石块,白日间吸收着阳光的炽热,清凉月夜下,阳光的炽热慢慢散尽了,但还是有一些什么积蕴下来,泛出的黄色、褐色、红色。那些沉实的色泽,是应该叫做“阳光色”的。看着这样的石头,人心里是温暖暖的。
于山民、渔民那种粗犷坚韧的生存之外,余平亦会迷恋江南前童古镇那样的地方。前童古镇毕竟是江南富庶之地,有所谓“书香门第”、“诗书传家”,也有退而求其次的仕途失意或隐士般的“耕读人家”,有这样的人家,人们才会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致,即便是面对残山剩水,吴侬软语、温文尔雅也是不会丢了的。
前童气候温润、树木繁茂,并无山,亦并无建造房子的可用的坚固的石头,但奇妙的是,白溪河畔却天赐般有着取之不竭的大小鹅卵石,也有着可以用来錾刻的相对松软的褐红色的茶盘石。
肉身的人,却是奇怪地谙熟石性。坚硬耐磨的鹅卵石,大的用来砌筑墙基,小的,填塞那些大鹅卵石的缝隙,更小的,拼花镶嵌于小街小巷的地面。而相对松软的茶盘石,这儿或是外来的匠人,则将它解成片状,錾刻出透雕的窗花——荷花、牡丹、石榴、佛手、蝙蝠……镶嵌在窗子上。精细的纹饰装点着小镇的悠闲静谧,这纹饰也有如文字一样,历经了风雨岁月,有依旧清晰,也有漫漶的,细心的人,是可以在这清晰和漫漶里读出些什么的。
鹅卵石砌筑起来的墙基,浑然大气,而镶嵌在墙上的赭红色的透雕的花窗,不仅让坚固厚实的墙忽地有了透气的感觉;同时,这些青灰色的鹅卵石和赭红色雕花的茶盘石,冷暖相映,在用色上也竟然是极和谐的搭配。
前童古镇亦有小小的僻静小门——后门。这是那种悄无声息的门,极窄小,不经意就不会注意到的角落里的小门。若昨夜有雨,滋润的泥地,早早有人出来,是要留下泥泞屐痕的。小门若在半山僻静处,几乎是“山中无岁月”的那种门,推开门,负手一径走去,云溪头上,真是可以“坐看云起时”的。
这样的小门,进出,一律静悄悄的。小门历经的事,有些是淡到无法再淡的,后院一扫,就连那几片落满了灰尘的枯叶也不知哪儿去了。可就是这样的小门,偶尔会有极隐秘的事。深更,小门悄悄开了,又悄悄关上,似乎什么也没发生。天蒙蒙亮时,小门又开了,有人悄悄离去。在山西某处一个老宅子,我就曾见过一个后来砌住的小门。因什么砌了起来,没有人愿意告诉我。
这样的石头民居,也都是近水的。这里的女人们依旧在小溪边洗衣,两两相对,似乎也并不是在洗衣,要紧的是聚在一起说些什么。这里做饭,用的是井水。井都极妙。有井口小的,仅容一桶。桶稍大,就不便进出。这井也许是专供女人和半大孩子使用的。亦有井口是用整块石头凿出,墩在井上,高出地面一尺多,大约是为了不让地面的雨水流入,为了干净的。这些井,各各样子不同,有外方内圆,有内外皆方,有六边形者,也有两个或三个眼的井。
院子里有马槽,相当大,用几百斤的整块石头凿成,槽沿已经豁豁牙牙,磨蚀下去好几寸了。这样深的磨蚀,不知有多少匹马在这儿吃过草。
在这样的街上,闲来走走,走走停停,卖布的,卖茶的,有那么多可以让人留恋忘返的人家的营生。街后面的僻静小巷,偶尔才有人走过。巷子,也是不断拐着的,拐来拐去。原先大约是会宽一些的,一家人在这里盖了房子,住下,增添人口;又一家人来了,盖了房子……不断有人盖房子,巷子也就挤成了现在的样子。
黔北大同古镇,原名大洞场的地方,也是余平所留恋的。这儿靠近山岩的地方,有巨大的天然岩洞。不仅可以在岩洞内部居住,甚至还可以在靠近外面的岩洞部分,用石头分隔出一间间屋子。这些山岩下面深浅不一的岩洞,有明显的海水冲刷蚀痕。若干万年前,这儿应该是海底。在甘肃天水的仙人崖,我也曾经见过这样的沧海桑田的岩洞,道士们就是借助这样的地貌,建造起“道法自然”的修仙之地。
余平对大同古镇的探访,也许是从水路,先到古镇的渡口而后到山门,再到下码头街的。从下码头街到渡口,这一段路一共铺砌了2070块石条。这些石条,上面是路,下面却是排水沟,其双重用途,在雨水极多的古镇,尽显了前人的智慧。
编了号码的石条,一条条排过去,密码的组合一样。石条亦随着过往的岁月,每一条都和地面的坡度严丝合缝,默契而相安。偶尔损坏了的一块,若要更换,虽然有表面的相像,但是要磨合很久时间,才能安妥下来。
古镇的渡口,是过去的所谓“官滩”码头。官滩,过去应该是有税收的。凡停经的船只,上货下货的船,各样的交易,桐油,茶叶,丝麻,白米糙米,布匹蜡烛……都要一一交税。可以想象当年水路旱路的繁华,大小船只,商人,船工,乡绅,地痞无赖,各路正规不正规军人,烟馆,酒馆,戏楼,烟花女子……入夜了,沿河各样灯笼都亮了起来。
现在呢,萧条了。可是萧条没有影响到古镇人的悠闲安逸。人依旧会在朴实的石头之外,想着再弄点什么点缀生活。沿着街道的排水孔,本来不过留一小孔即是,而古镇的人们,却希望有点什么喜庆的点缀一下,遂琢磨着让石匠錾刻些什么,这些排水孔,也就錾刻成了铜钱样、荷花样、云纹样。人走过的时候,低头看看,寻常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别样的意思,喜庆的意思。若是铜钱的排水孔,生了绿苔,也就仿若铜钱那样;若是荷花,生了绿苔,也就仿若是碧绿的荷叶了……
这些石头的民居,与官府的样式各异,绝不会雷同。官民官民,官与民在这里是相对的关系,不过是和谐不和谐罢了。百姓与官家的想法,只求有好官清官即满足,只求风调雨顺,相安无事。
游走在这儿的小巷里,也还能见到随意放在墙角的沾满了灰尘的小石磨。街巷里,“店铺不挂招牌也无吆喝,摆着什么家当就是什么店。有椅子、镜子的是理发店,炉火上摆着蒸笼的是饭馆,挂满铁器竹器的是卖农具的……”。余平如此写道。
店是自家的,东西是自家的,手艺是自家的,没有买卖,一切也都还在。过去了的一天辰光,一毛钱的买卖也没有,可是,有什么呢。日月还在,流水还在。
这样的地方,就连街边或小院门里雨水洗淋干净的一把扫帚,也是要叫人多看一眼的。
住在这样石头屋子里的人,白天,他们辛苦了一天,汗流浃背……而夏夜里,在蝉鸣的院子里,一盏灯,小桌小凳,几个人清茶淡酒,谈古论今,说说闲话,才真正是安适的。
……可以了,不劳我絮叨多说了,还有更多的,更美好温馨的,随着余平的镜头,一起慢慢流连,慢慢行走着看吧
中国古民居观察·石
山花艺术馆
2014年 6 期
策展人:沈 奇
本期参展人:余 平、董 静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石砌民居
聚落的成因及特点,编号:13YJC760012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陕西省五个
古镇的用材与修缮研究,编号:2013Jk0464
余 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工业设计系 副教授
董 静:西安财经学院 艺术系 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