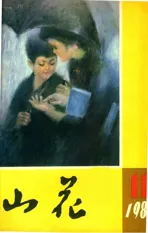在志成该做点什么
2014-08-08丰一畛
1
赵晓阳所在的学校有两座标志性建筑。一座是桂园宾馆,学校的公共接待处,赵晓阳帮导师的朋友安排住宿时进去过一次,里面的装潢传说是四星的标准,但除了稍精致点外,赵晓阳并没看出客房有什么特别的,倒是结账时吓了他一跳。另一座便是志成大厦。志成大厦位于宿舍园区旁,以前也是学校的财产,后来不知怎么转卖给了私人,不久又被按层或按间承包出去,当然大部分还是被布置成了廉价客房,只有顶楼的两层,装成了个可以搓麻和打桌球的休闲会所。由于房价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学校源源不断的校园情侣成了志成大厦最主要的顾客。每天下午或傍晚,志成大厦的门口总有十几个重庆大妈肩上挎着包边聊天边在那招揽生意。“帅哥,住宿不?”“妹儿,进来住撒,这里有葩火。”……渐渐地,志成大厦就有了更贴切更如雷贯耳的名字——炮楼。有一次,赵晓阳匆匆从志成门口经过,一大妈还硬塞给他一张红色传单,他在将传单扔进垃圾桶的瞬息瞥见了上面的四个艺术字,初夜八折。一霎时,他都想伸手将那纸片从垃圾桶掏出来看个究竟了,他鼻孔哼着气,终究没有止步,但脑子却热火朝天地滚起来。初夜?怎样才算是初夜?大妈们又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初夜呢?难道别人做完了,她们会去查房,看处女膜有没有破?
想到处女膜,赵晓阳的心头一紧。有那么一段时间,像是一句口头禅,氲儿总是冲着他嚷:“你还我处女膜。”“赵晓阳,你还我处女膜!”氲儿努着气嘟嘟的嘴,如一个索债的,拿大眼睛瞪着他,他缩着头,心里嘀咕,怎么还?但他说出口的永远都是一堆堆的道歉,永远都是空头支票似的许诺,他承诺用他的时间来还,用他一辈子的时间。可那个平安夜的晚上,氲儿歘地从床上跳起来,眼里打着泪花,指着他的鼻子骂:“赵晓阳,你他妈的还我处女膜!”他足足看了她两分钟,像是用眼光在她身上挖着什么,后来她的眼仁都被凿穿了,他才脱口而出,还你妹!声音大得他自己都浑身哆嗦了几下……那是他们第一次去志成,也是唯一的一次。他软磨硬泡了很久她才勉强同意去的,她说她不想赶那个时髦。“志成有什么好去的,脏兮兮的不说,还有蟑螂和老鼠。”她说这话的语气好像她去过好多次了似的……可这一切都真实发生过吗?
重新回忆起那个诡异的夜晚,电梯旁的巧合就恍如一把利剑,将连贯的夜劈成了两瓣儿,一瓣糟糕,另一瓣更糟糕。氲儿彻底生气了,刚才还泛着泪的眼里蹿出了火星,她靴子敲击地板的声音也打出了火星,咣咣的,她走得迅疾,他在后面追着,脸上和心里死灰一片。电梯还没停稳,只抻开了条缝儿,她就横着身子钻了进去。他紧随着,也要一脚往里迈,迎面呀的一声,他撞在了一女孩的身上。“赵晓阳!”他脸上的死灰还没来及换成惊讶或惊喜,楚楚的尖嗓子就针样扎过来。他嘴角咧了咧,生疼生疼的。“……呃,楚楚,幸亏是你,要不然就被讹上了。”“谁会不长眼睛讹你,看你的样儿长得像有钱人吗?”楚楚大咧咧调侃着,眼睛吊下来,身体侧了侧,她在乜氲儿。楚楚的头又斜了斜,电梯的缝儿越来越窄,氲儿不见了,他脸上伪装出的笑如一层蛇皮般,秃噜噜掉在地上。“我走了哈。”楚楚提了提包,一身轻松样,小眼睛蝴蝶似的眨出了蜜。他杵在电梯口,脑袋里空空如也,却又仿佛有呼呼的声音响个不停。“我走了哈。”楚楚顺着走廊走出去很远,忽然折回来,摆着手笑眯眯地又道了个别。他转头尴尬地回应了下,呼出的气里满是愤懑。
他还是追上了她。但他不敢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只默默跟在她身后。冬夜又敷了一层冷,他们陷进薄雾里,沉默混杂了夜的呼吸,苍茫茫的。脚下落叶的吱嘎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而远处操场上隐隐升起的欢叫又像是近在耳旁。他的心伴着脚步咕咚咕咚响,里面的委屈涨潮似的止不住泛滥。他不想追出来的,可他还是追出来了。操场上有人在放孔明灯,他抬头看天,几个大小不一的亮点游弋在某些吵嚷声的尽头,他闭了闭眼,泪却不争气地滑下来。他无声跟着,任着泪流进嘴角,牙齿咬得紧紧的。沉默大起来,像一种原因,又像一种过程,直到她走进寝室,面无表情说了句“你回去吧”,然后砰的关上门,那沉默才果实般沉甸甸砸在他头上,他醒了,又像睡着了,木讷讷地出了楼门。
去志成的路上氲儿还好好的。一个大苹果,她咬一口,又喂他一口。她抱怨着说他咬的太小了,命令他张大嘴。她将苹果抵着他的牙齿往嘴里塞,他猛一使劲,她又倏忽间拔出了苹果。他咬了个空,牙齿打着颤音。她就放肆地笑。笑得他的小和尚都一动一动的。她来了信息,要从包里掏手机,让他先拿着苹果。他躲闪着,苹果不剩多少了,她紧吃两口就可以丢了。她非要他拿,他又躲了,她一转身就把没吃完的苹果囫囵扔进了垃圾桶。……躺在志成大厦十五楼的软床上,她的表情似乎就有了异样。他吻她。她没什么回应。他手试着往她的内衣里伸,还没摸到什么,她就挣脱了。“师兄太坏了,说好了今天晚上什么都不做的。”他比她高一级,平常时候,她都喊他师兄的。他就道歉,一迭声地说:“都是师兄不好,不知怎么就惹氲儿生气了。”“那你向我保证,今晚不许碰我。”氲儿气呼呼的脸总那么好看。他嘿嘿笑着,逃也似的,说先去洗个热水澡。
莲蓬头里的水漫在赵晓阳的身上,舒服极了。人在洗澡间里总习惯于盲目乐观,赵晓阳揩着身上的垢,小声哼着跑调的歌,并没把氲儿的变脸当成多么不好的预兆。氲儿一直都这样的,心里仿佛总对做爱这事儿存着不必要的偏见。所以,每次他想做那事,他的哄都格外地漫长,也格外地耐心细致,俨然如一个拆弹专家的工作。他曾经跟她探讨过性的必然性问题,甚至有时还夸大性在爱情里的作用。她都没怎么反驳,可她就是不自控地觉得他的小和尚脏兮兮的,做爱这事儿脏兮兮的。刚跟他在一起那会儿,她喜欢抖弄老古董般一本正经地跟他说,只有结婚了才可以上床的。“真的,只有结了婚才能上床,不管这个观念多么陈旧落伍,它已经烙进我心里了,你千万不要试图改变我,你改变不了我的,我自己都改变不了我。要是可以的话,也就轮不到师兄宠氲儿了。”他点着头附和,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心里却暗暗趸着不屑。她之前谈过恋爱的,还不止一次,用他跟她开玩笑时的话说,也是劣迹斑斑了,做过就做过嘛,这样端着,就有一点装了。直到那天,灯光下,他看着她私处流出的殷殷的血,心像漏气的球似的一点一点软下去……
2
赵晓阳裸着躺在床上。氲儿去洗澡了。从卫生间出来,他就这么裸着。氲儿扫了眼他赤条条的身体,没说什么。他裸着去烧开水,裸着帮她脱衣服,裸着往她身上蹭,她推攘着,哄孩子似的说,师兄别闹。她脱得只剩胸罩和内裤了,又若无其事地说,大叔下午打电话了。他搭在她后背上的手怔了下。“是吗,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随便聊了聊。”“哦……这样的。”他想拍拍她屁股的,手张了张,犹豫的半瞬儿,那屁股一扭一扭晃出了他的眼眶。它圆圆的,翘翘的,他听到他的呼吸莫名地停了会儿。
大叔特指一个人。遇见他之前,她曾做好了飞蛾扑火的准备迎接那个人。大叔大氲儿八岁,早年没读过多少书,现在广东谋生,兼做户外领队,而她,她自己说她只是个四川的学生妹。在这个男女关系异常迷乱的时代,在这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娶二十七岁的姑娘被当作完美爱情连篇累牍的当下,他们间这点客观的距离算不得什么问题的。可她却固执地认为,问题大了。很不幸的是,大叔好像也认为这是个问题。于是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暑假里,大叔带着氲儿去了一趟草原。她渴望着发生些什么,又害怕着真的发生了什么……天空高远,草原辽阔,他们的帐篷里一豆灯火在翩翩摇曳,那到底是一次怎样的奇幻之旅呢?
直到赵晓阳的加入,两个人的复杂又变成了三个人的更加复杂。他是一个后来者,这几乎成了他的原罪。他该怎么面对氲儿的大叔?怎么面对在心里始终为大叔留着位置的氲儿?又该如何面对氲儿跟大叔持续至今又会绵延至明天的情感过程?他确信,氲儿是喜欢她的,或者爱,但她更确信,氲儿喜欢大叔,或者更爱。他一直有一个宽容的姿态,也用理智化解着嫉妒,但记忆深刻的,还是她坐在电脑前展示草原之行的照片时他内心里那无法描摹的感受。草原太美了,她浏览照片时的笑太澄澈了,可身旁的他轻触着她干净的笑,笑里分明就长出了毛茸茸的刺儿,那密密的刺儿仿佛是针对他的,他抿了下嘴,想碾碎了品品那刺儿的味儿,那刺儿就忽而全不见了,他眼望着一撮一撮的黑暗渐渐从心里冒出来,宿命似的——她花朵般肆意飘香的笑不是他给的。
氲儿你说我是第三者吗?他跟她第一次睡在一张床上时,他问。
不是。氲儿说。
氲儿你说大叔现在是第三者吗?他跟她粘腻到彼此都觉得不可思议时,他问。
不是。氲儿说。
有时候,氲儿也会调皮地问他,或者迷惑地问他。
师兄,我去广州玩可以跟大叔见见面吗?
不知道。他说。
那我们见了面可以牵牵小手吗?
不知道。他说。
接吻呢?
不知道。他说。
他确实不知道。虽然,随着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拉越长,她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她对大叔的情感正一步步往亲情的方向发展。他相信她说的。他也不想去怀疑。但那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自负到完全无视他们三人之间那情感枝杈的蔓延。说到底,他掌控不了什么,预测也仅只是预测,他也不能轻易地将某种行为视为爱或不爱的表征,于是,他只能反问。
有了师兄氲儿该不该在大叔那里稍加节制?不见大叔算是一种节制吗?
牵手和爱情的关系是怎样的?接吻和爱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氲儿怎么看待牵手和接吻?氲儿又怎么在言行的表达上区别大叔和师兄?
氲儿皱着眉头,忽然亲他一口,撒娇似的莞尔,反正我还是会去广州见大叔的,师兄就等着到时以泪洗面吧。
她没有去广州。大叔来重庆了。他们一块去接的。住宿就安排在志成。他问是不是太寒碜了,她倔强地说,她想跟大叔住得近一点。他有玩笑含在喉咙里,攒了会唾沫咽下去了。现在,他对大叔的印象已不甚明晰。只一个场景,湖面上的水鸟似的,偶尔闪过。吃了火锅后,氲儿不知为了什么要回趟寝室,他就先带大叔去志成。他是热络的,大叔也是善谈的,场子并没有冷下来,但两个陌生人之间要始终维持这场子的热度,就如反刍的牛要时不时倒草似的,两个人的脑子就不得不间或往外吐话题。可他们能言的话题又确实不多,这不多里,大部分又都跟氲儿有关,他们又要回避。为了使两人的谈话不至于显得那么刻意,来到房间后,他们几乎是抢着去开电视的。开着电视,他们名义上的主要的事儿就变成了看,看会提供彼此沉默的合理理由,制造毫无危险性的公共话题,并掩盖话题转换时必然会产生的突兀感。他们打对了如意算盘,但电视却一时开不了。房间里是有电的,电源插座的指示灯也亮着,但电视机的电线插头插上去却毫无反应。他们如两只无头苍蝇,按按这里,敲敲那里,后来他就记住了那张画面,电视屏幕忽的蓝了下,他看了看他,他也看了看他,都笑了。
除了那客气的对视,他们还有一点挺默契,是氲儿告诉他的。她先问他觉得大叔怎么样,他说大叔挺好的。她又问他是不是真心话,他说是。然后她脸上的酒窝就溢出来了,志得意满地说,她问大叔觉得师兄怎么样,大叔也说师兄挺好的,她也问大叔是不是真心话,大叔也回答是。
莲蓬头哗哗的,氲儿的话隔着水声和玻璃门传过来,“志成没有吹风机,我不洗头发了。”他含混地应着,想着氲儿忽然的不高兴是不是大叔打来电话的原因。他没有那么肯定,只忧郁地想,如果是的话,那他刚才低声下气的哄就真的下贱了。他有一点悲伤,为了避免在纠结中继续悲伤下去,他拿出手机来刷屏。以前的话,他会玩玩微博或微信,但她让他染上了没事翻QQ好友说说的毛病。他打开QQ空间,第一条更新就是她的。时间显示的是几分钟前。“大叔的声音听上去为什么那么憔悴呢?”他瞪着屏幕上的字,很久,字都变花了,他还空洞洞地瞪着,后来他的胃猛地痉挛起来,他忍着,身体在缩,肚子也在缩,手握成拳头顶进痛里。就在他洗澡的眨眼的工夫,日月悬置,黑白颠倒,现实伸出它狰狞的獠牙,只轻轻一碰,就戳破他自己用时光作原料织就的捆缚自己的那层厚厚的茧。他以为过去的都不曾过去,大叔从来都没有被完成,他如影随形,洗澡间里的镜子似的,照着他一丝不挂的身躯。他洗不净他的小和尚的,他也不可能洗净他的小和尚的,她的眼里,它生就是令人作呕的……他把眼神搁在虚空中,呼吸又停滞了会,白炽灯的炸响噼噼啪啪的,迷蒙里,他终于看出了从未觉察的另一种事实,她也是脏兮兮的,还猥琐,也包括大叔。他们耽于算计,徘徊不定,从未有勇气径直走向对方。他们又自私有余,贪心无度,舍不得放开手来成全彼此。他们就那么牵绊着,将所谓的爱情生生拖入泥淖,满足于自我幻想的不完美。而他,竟然在无意间成就了他们,有了他,他们的无能变成了不能,他们的市侩精明也顺理成章被罩上了一层梦想的光影。他恨他们了,更恨自己了……事情是怎么一点一点坏下来的呢?
他赤裸着背对着她。她穿着睡衣睡裤背对着他。
他给她发了条短信。
“我在你说说下面留了言。”
“你转过身直接问我不好吗?”
他转身了。扑在她身上。撕扯她的衣裤。她从没见过他如此的野蛮,一时错愕,反应过来,抓挠着他的脸。玻璃墙外,几束平安夜的烟火载着美好的祈愿飞向天空,有那么一道红光,划错了地方似的透过帘隙落在他们扭动交错的腿上。冰凉冰凉的。
3
房间是退不了的。很快,短信提示音响了。“女朋友怎么让你睡跑了?”楚楚的短信。他心里恓惶得很,懒得听风凉话。一会儿,手机又嘟嘟了两声,“不方便回?在哪呢?”他丢了电脑包,仰躺在床上,“志成。”“一个人?”“你说呢,两个跑了一个。”“哈哈,干嘛呢?——看A片?”她发了一串笑脸,他的脸都被憋青了,嘴里骂着脏话,正要回一串怒脸,突然的敲门声惊了他一激灵。他以为听错了,当当当,真是他的房门。
“谁?”
“扫黄的。”
楚楚的坏笑。他打开门,疑窦写在脸上。
“是不是以为我在跟踪你?”她说话的气流喷过来,像只红笔胡乱划着叉。“做贼心虚了吧。”她边说边往房间里走。“以前我邀你来志成那么多次,你都不来,现在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出了什么事,后果自负哈。”他将他失落的情绪收好了压在心底,深吸一口气,恢复了跟她一贯的说话方式。
她摇着头环顾了房间一圈,没脱鞋子,检测床的承载能力似的,一努劲儿,将身体摔上去。
“这是玩的哪一出,真要跟我上床?”他也纳闷了,还发怵了,自从他们很久前过了那段暧昧期,他们的谈天是变得非常随意了,举止也轻佻,但像这样的架势,孤男寡女,躺一个房间里,还是志成的房间,无论如何都越雷池了,他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仿佛是不期而遇的,荒谬的现实一下子就触到了他深藏的某个秘密的阀门。他的后背被什么击中了似的,一凛。
“你想的美,一个你都搞不定,还想搞两个。”她甩了甩头发,侧起身,言语里都是挑逗的意味。“我要是在师妹那里随便说点什么,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们同级,又算是好朋友,他跟氲儿刚确定关系时请她吃了顿饭,那次以后,她就管氲儿叫师妹。
“不就是楼梯口撞了下嘛,真要讹我?”他嗅到了房间里四处游荡的荷尔蒙的气息,但他绷紧的神经却在慢慢松弛,床上躺着的女孩是楚楚,那个小宠物似的傻姑娘,他没有必要害怕的。
“不跟你闹了,师妹过会会不会回来?如果看到我们现在这样,那可真就说不清了。”
“看来你自私的毛病一点都没改。”他的话顺着惯性蹦出来,心思却绕着楚楚的担心转,氲儿回来就麻烦了,可氲儿当然不会回来了,他沉潜着的愁苦倏地水泡般冒上来,他咂了咂嘴,满嘴不是滋味儿。“咦,你怎么知道我住这个房间的?”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你不会真跟踪我吧?”他的脑子开了窍般,问题连上了问题,“你平安夜来志成做什么?”问题荒草似的燃起来了,“不要说你玩的是一夜情?!”
楚楚是重庆本地的姑娘,个不高,单眼皮,白白的,听别人讲话时喜欢将眼皮冷冷地吊下来,一副心不在焉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认识氲儿前,赵晓阳曾在楚楚身上花过不少时间和心思。有人说,男女的感情就像抛物线,顶点的时候捅不破那层纸儿,关系也就会眼睁睁淡下来。他那时是翻来覆去地想过要不要跟楚楚谈场恋爱的,她也明显觉察了他对她的好感。他去过她家玩。他们在一个脚盆里洗脚。他还拍了张照片,四个脚丫子摞起来的照片,像个特别的寓言似的,一直存在他手机里。但也是在她家客房的床上,他辗转反侧,最终做了个艰难的决定。他不要跟楚楚谈恋爱。他发现感性上他越来越亲近她,而理智上他又越来越排斥她。她太像个小动物了,她会为了所谓的感情或随便什么忽然打来电话,哭得伤心欲绝,又会迫不及待把他找来只为抱怨跟某人不值一提的摩擦。她仿佛只活在生活的表层,也只需要他的表层,他们更像彼此的宠物。他受不了这一点,他不能跟她谈恋爱,可他的欲望已被自己撩拨起来了,他又想跟她做爱。这是个多么荒唐的境地啊!他费尽周折最后确认的只是想当一个嫖客!嫖也不能真嫖,他的行动在暧昧的当口停下来,但他们毕竟暧昧着,他的嘴就口无遮拦了,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去趟志成?她开始还挺反感这样轻浮的玩笑,后来明白,他玩笑开得越大,他们关系中爱情的成分也就越少。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主动,不打她的主意了,因此,像一个固定的话题似的,哪怕有其他的朋友在,他偶尔也会随口说道,一会散了咱们去志成?斗地主吗?她也随口应道。
4
楚楚变回了她小动物的本来面目。她坐在床头,怀里抱着枕头,目光哀戚。赵晓阳则坐在床尾,腿盘着,低头听她说话。他有些走神,想起以前,也是这样,电话里,她讲着讲着就带哭腔了,越哄,她的声音就越湿漉漉的。她入住登记时在信息表上看到了他的名字,顺便记下了房间号。她绕了很大的圈子才告诉他来志成的目的。她说她要跟他道歉的,她把他当成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她骗过他,其实也不能说是骗,应该是误导。他们相熟了之后,曾交换过一些隐私。她说她只看过一次A片,还是本科时,她看着看着竟睡着了。她说她虽然谈过一个男朋友,但直到他告诉她之前,她完全不知道女孩子也可以自慰这回事儿。她说的都不假,但她看出她的话误导了他,但她却没纠正。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往外说!”这是楚楚的惯用伎俩,以前也总是这样,“你保证,也不能跟师妹说。”
“那还是算了吧,你还是别说了,万一……”
“不能万一,你快保证!”
“那我保证。”赵晓阳无奈地笑了笑,看来楚楚真的长不大了,她连说话的口吻都跟以前一模一样,每次,她告诉他点什么,让他当个秘密听着,鬼鬼祟祟的,可回头她又跟别人说了。后来他不想听她的秘密了,可她偏要说,还让他保证,说出去就天打五雷轰。
“我是做过那事的。”楚楚两手抱紧了枕头,很痛苦似的。
“做过就做过呗。”
“是那事。”
“我知道,不就是性交吗?我也做过。”
“你怎么那么恶心,当你朋友才跟你说的。”楚楚的泪说来就来,她拿枕头沾了沾眼角,“就在志成,大四的平安夜,那时你还没来读研,”楚楚的泪大颗大颗冒出来,琥珀般晶亮,“我以为别人都不这样的,真的,我心里面愧疚极了,不知道愧疚什么,我不后悔的,是我自己要做的,可我还是愧疚,愧疚得要死。”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时你们彼此欢喜,两厢情愿,然后水到渠成做那事。”赵晓阳似乎不太明白她的愧疚指什么,但他还是安慰着。
“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吗?就是……我也说不清楚,我不后悔的,但是……”她说不下去了,抱着枕头抽泣起来。
他挨过去搂住了她,她的哭声大起来,泼染成一片混沌的海,他在海浪里浮浮沉沉,重重的脑袋忽然不合时宜地闪过了四个字,初夜八折。那是楚楚的初夜吗?他的心孤独地叫了声。他眨了眨眼,那唤叫更像是氲儿的,氲儿一面眼泪河水似的淙淙往下流一面又笑着似的喊,“师兄,你还我处女膜。”……那是他跟氲儿的初夜吗?哪次算是他跟氲儿的初夜呢?他想也许这辈子他都不会忘记那一小滩血液了,他盯瞅着它们从氲儿的私处流出来,就仿佛一个全新的世界轰隆隆碾过,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恐惧是漆黑的,还缠着凄厉厉的哀鸣……那几天,氲儿的周期迟迟不来,他们都害怕怀孕了,可他们根本就没做过,怎么可能怀孕呢?他们没做过吗?他的小和尚那么多次亲吻着她的私处,她不允许它进去,可它却在一点点试探着深入着。到底是哪一次试探又是哪一次深入可以被命名为初夜呢?直到血液流出来那次吗?可它们刚渗洇着时,他们以为那只不过是经血呢。他们还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般傻乐呢……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他喃喃地劝慰着,内心的失败感愈发强烈,不要哭了,他抚摸着她的背,她的裙腰,她的大腿。“不要。”他听见她说,又像是他自己说的。他把她放倒,手伸进她的裙子,她的丝袜滑腻腻的。他亲吻她。她闭着眼。他听见他说想要上她。他听见她说不要。他的手扯了扯她的内裤,他的手寻觅到那汪黏嗒嗒的湿地。他又听见自己绝望地说,“你之前怎么不跟我来志成呢?你可知道我在这里给你留了秘密的。我看到我们的距离了,沟壑纵横,可来志成就是我搭的桥啊,你该迈过来的,迈过来,我就会告诉你,来志成不是为了上你,是要在这里跟你表白,是要跟你表白啊。”他又听到她的哭声了,嘤嘤的。“可我现在想上你了。”“想上你了。”“求求你了,不要。”“真的不要。”他解开了她的裙子,褪着她的丝袜和内裤。“你怕什么呢,你不是做过吗,你不是在志成连初夜都给别人了吗?你个贱女人。”她突然过了电似的,警然一惊,浑身着起熊熊的仇恨,冷不丁一脚踹出去,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头就磕地板上了。他趴地上张着嘴望她,她草草穿好衣服,看都没看他一眼,小跑着撞开了门……
5
赵晓阳一丝不挂地站在志成1505号房间里,他刚又去冲了个澡,他把电脑打开了,房间里充斥着波多野结衣的呻吟,他本想跟氲儿一块看波多野结衣的,氲儿曾说,从某个角度上看,波多野结衣很像林志玲。他只带了两只套套,他从电脑包的侧袋里找出来。他手里捏着套套,却又不知做点什么了。他读套套上的字,durex,1 natural latex rubber condom,天然胶乳橡胶避孕套,内含1只,批号0010836838。他拆开,对着嘴吹起来。他像个小孩,追逐着房间里的两只气球。他拉开窗帘,赤裸裸站在玻璃墙前。正前面是几栋宿舍楼,楼里的人影清晰可见。再远处,灯火璀璨的地方是桂园宾馆。平安夜,桂园宾馆前竖起两个硕大的布满彩灯的圣诞老人。桂园宾馆依山而建,两座主体楼交并于空中,赵晓阳惊奇地发现,从志成的这个房间望出去,桂圆宾馆活像个叉着腿的女人。他正对着桂园宾馆,小和尚抵在玻璃墙上。身后的波多野结衣要叫床了,他握着小和尚的手快起来,一下一下一下,桂圆宾馆好像随着他的节奏也动起来了,他感到了内心的欢畅,他想象着他在强暴的是林志玲,他感觉他快要飞起来了。
玻璃墙上的精液污渍似的滴着,他躺床上,恍惚瞅见自己拿着张纸巾走过去擦了,可他明明躺在床上一动未动。他蜷着身,用食指划拉手机屏幕,氲儿回复他的评论了,他在她的说说下面留言,刚才的不高兴跟这条说说有关吗?氲儿说,谁知道呢,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他又起身站在玻璃墙前,精液确实没有了,他什么时候擦的呢?他又不知该做点什么了。他想起两个多月前的国庆节,一个女孩来这个学校找他的男朋友,结果他的男朋友已经背着她觅得新欢。那女孩就从志成的十二楼跳下去了。他从同学上传的手机图片里看见过她孤零零的一只臂膀。真是傻呢!很多人议论纷纷,为什么要跳楼呢?他的思绪凝滞了一会儿,像死过去般闭着眼睛。说不定呢,说不定她只是待在房间里实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死神敲了下她的头,她就跳下去了。是的,她跳下去跟一个劈腿的男人毫无关系,她只是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而已。他突然想哭,嚎啕地哭,他快步走回床前,用被子蒙起脸……多年以前,那个刚上初中的他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他被会匪夷所思的时间裹挟着押入一小块名为志成1505号房的空间,并因为一个陌生的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而去跳楼的女孩嚎啕大哭,他哭得如此掏心,如此入情,像在哭当年挂着泪水的自己——
那时他真年轻啊,才上初中,新的环境让他惊恐又让他兴奋。一个女孩,他小学隔壁班的同学,他甚至都无法确认是哪一个,从进校第一天起,就频频递来情书。一封又一封署着她名字的情书从一个又一个认识不认识的同学手中传来,男生寝室议论开了,女生寝室也议论开了,整个班级都议论开了。他仿佛无处遁逃,他不知怎么就无处遁逃了。那个夜晚,灯熄了,他溜出寝室,偷偷爬上教学楼的楼顶,他想到了死,他又不太明确他想到的是不是死,他坐在楼顶,苍穹浩瀚,繁星斗艳,他泪如雨下。
作者简介:
丰一畛,原名孔瑞,1987年生,西南大学在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