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若干次渴求的慌乱
2014-08-06

当诗歌中我的玉带河已经泛滥成灾时,我想,的确应该用散章再去为她梳理一下流散的族谱,用我记忆中的感受去添砖加瓦,尽管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乡人们也看不到这些稚嫩的文字,它们没有老茧耐人寻味,不分三伏九秋,它们有的只是我,一个叛离者工工整整写下的认罪书,仅此而已。
相比于天干物燥,我更加倾向于多愁善感的雨季,而玉带河几乎给予了我所需的所有养分,恰到其处:疼痛,喜悦,心慌,留恋……当我再次列出这一长串令人敬畏的字眼时,我已经离开她多日,没有河流相伴的日子里居无定所。因此,有时我在怀疑自己的恐惧是不是源自于渴求,我害怕失去,分离,聚少离多,害怕秋季里缺山少水,把使用娴熟的家乡话压在箱底,看着她发霉却置之不理。
令我引以为豪的是我的家乡位于秦巴山区深处,汉江的源头——宁强(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套用范晓波在《田野的深度》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湿的发绿发腻的地方。这种地势地貌满足了我封闭自守的性格。我想,古老的羌族先辈定居在此的原因也差不多如此吧,他们遗留下来的高高的碉堡便是这样一个见证,自给自足,以防御为主的习性显示出他们内心对于安定的向往,看似松散却又密不可分;而充沛的降雨量和温润的气候适宜于农耕牧养,至今金山寺一带仍旧以放牧为主,闻名内外的宁强矮马充当了历史的载体。当它们被凶悍的皮鞭驯服时,一段属于我们的历史也就这么被开辟出来,有了炊烟从此便有了人间。
本土散文作家李汉荣特地为故乡的河流开辟本纪。他沿蜿蜒曲折的河流行走,这一走便是半个多世纪,走出了江湖冷暖,从现在逆流到过去,走到历史的拐角处,一转身遁入流水,又从过去流回到了现在。有时,静下心来想想,河流真是个神秘的栖息处所,纳酸甜苦辣,容肮脏洁净,她在家乡人心中已然化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暴雨过后的汹涌澎湃还是素日里的安静贤淑,似乎都在昭示着自己变幻莫测的脾性,从不隶属,哪怕把自己一寸一寸流尽,流到只剩下坚硬的骨头和黄昏的光阴,也要一吐为快。这像家乡人的性情,农村人秉承的开朗、豪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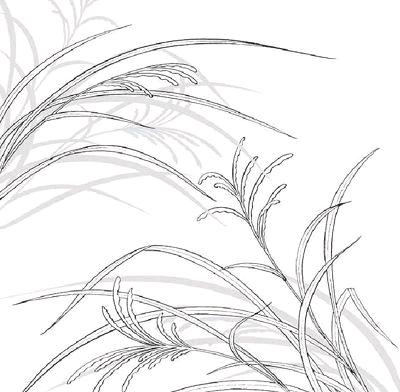
而在玉带河的另侧老代坝村,我家门前的一条河流,父亲曾说过她的身世,发源于群山大湾,荒野之地,祖辈们取名为金溪河,我对河流的认知大概也是来源于此。八岁多时我在堤坝上摸鱼,一场不期而遇的暴雨加剧了河流的愤怒,我的撕裂远远比不上流水的荒蛮暴躁。在一块并不算庞大的突兀的花岗岩上我总算学会了低头哭泣,学会了绝望,小心翼翼地与命运挣扎,准备随时被荒蛮的岁月冲走。幸运的是一位放牛归来的老农将我从漩涡中救起,他的出现改变了我对河流的理解。像一出荒诞剧,彼此建立起来的信任竟然靠矛盾来加以维系。
在自然的引诱下我慢慢学会了亲近它们,也许正是这种自闭塑造了我在诗歌中的角色。我不止一次说到石头、水草、河岸,它们都是人性另一面静默的主体,在我的视线里从未逃离过它应有的宿命。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是一个见证者,又是一个失败的体验者。在同学外省务工归来的某天,突然会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这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我守旧、闭塞,更愿意把开口的机会交给笔墨纸张,而他们的命运里已经混合着南方的燥热,像炙热午后突降的一场暴雨,他们习惯了暂住证与身份证的角色混演,正如我习惯了难以避免的疼痛,我从没有想过我们的不同何时能够得到时间的化解,当然,在我选择诗歌那一刻这也就无法避免,与其说我住在玉带河畔,还不如说我住在我的体内。
而后,二十年转瞬即逝,渐渐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秘密,深浅不一。譬如流动的风景,天空,大地,山峦,乔木,动物,庄稼,它们的远去永远是一个未加雕琢的谜团。像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如蒲公英般被可恶的狂风通通吹散,灰飞烟灭,半新不旧,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扎根,采花,酿蜜。当故乡已经越来越远,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号时,我只能从稀缺的梦境中返回村小那棵硕壮的月桂树下,折一枝献给早逝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坟比死亡更令人恐惧,遮天蔽日的椿树、刺藤掩盖了他们的痕迹,我担心他们的存在是否在若干年后也会作为一个谜:从未生那么也就从未死去。
作为那份遗迹的幸存者老屋,沧桑已言过其时,生命紧促而踉跄,没有多余的念想可供凋零。而庭院深深,蓬勃的车前草将她包围的密不透风;早年枯萎的木竹沿天空的方向展开翅膀;丝瓜藤、冬瓜架各得其所;老式石碾卧在柴草丛中继续着一场永无止境的美梦。熟悉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空的只是一份不复存在的心情。我曾在故乡一个黏稠的午夜写道:
现在,她空着,剩不下阳光和温暖
硕大的霉味包裹着她的骨架,皮毛焉在
仿佛从未臆测过她的过去以及将来
她的存在只是为了祭奠一份逝去的感情
如同坟墓一般活着,不靠天,不靠地
孤独地挣扎在地平线上,荒诞而又真实
如今树倒猢狲散,所谓祭奠莫过于痛恨,造成这一切的又是谁。二十年的光景,思念早被一网打尽,我渴求玉带河能够破镜重圆,弯腰的父亲不再担心光秃秃的冬天柴火劈的不够,我唯有一家人,只求温饱,不怕夜里做梦,清晨赶赴雾色掩盖的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