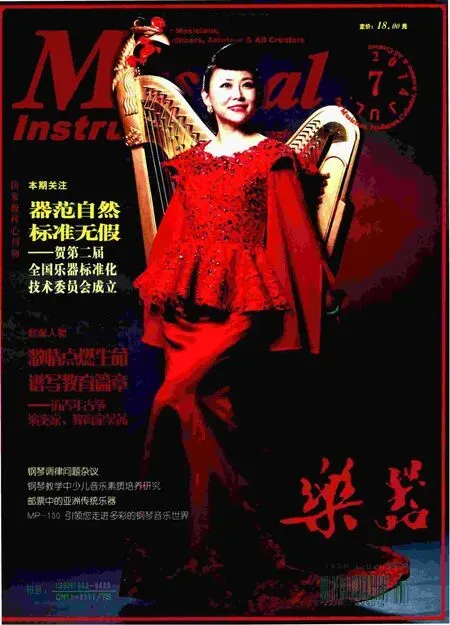邂逅王晓明
2014-07-30
本刊记者/柳 蕾
4岁学习小提琴,9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师从徐律教授。1997年获得第一届中法咪哆小提琴比赛第一名。2002年考入世界著名音乐学府——维也纳国立音乐表演艺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曾获得维也纳国际“史迪芬”小提琴比赛第一名以及国际知名重奏比赛。2008年,26岁的他成为苏黎世国家歌剧院乐团首席职位,并在近年的国际小提琴大师班中担任主讲。
与小提琴演奏家王晓明的交谈是记者本次采访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第二届校友艺术节”的意外收获。拿到厚厚的一本艺术节介绍册,记者一下子就看到“斯特拉迪瓦里弦乐四重奏(The Stradivari Quartet)”这个名字,众所周知,斯特拉迪瓦里是世界公认的制琴大师,以他的名字命名弦乐四重奏,这里面必定有故事。
这天下午是该乐队成员分别给学生上重奏课,一组是弦乐四重奏,一组是钢琴三重奏。王晓明负责钢琴三重奏这组。在记者听课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是站着教课,并经常给学生讲解如何相互配合以及一些演奏方面的处理技巧,学生们领会之后明显就有改观。在王晓明的举手投足间,也流露出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职业演奏家。
组合的由来和情况
当记者问道“斯特拉迪瓦里弦乐四重奏”这个组合的名字的时候,王晓明说道:“我在2002年到维也纳国立音乐表演艺术大学留学,跟随小提琴大师Gerhardschulz(阿班贝尔格四重奏成员)学习。六年前,从维也纳去苏黎世,考入苏黎世国家歌剧院团,并成为剧院的终身首席。重奏组合的成员目前都定居在苏黎世,我们是在音乐会上相识的,大家在艺术上有相同的出发点,想一起合作成立一个组合。我后来找到了苏黎世哈比斯罗特恩斯特拉迪瓦里基金会,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基金会,他们的思维很开放。当然我们提出了想法,基金会很认可我们的创意。基金会在瑞士圣加仑这个城市,有六把斯特拉迪瓦里琴: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两把大提琴,除了资助给我们,另外两把还资助给了其他音乐家。瑞士是个开放的国家,虽然小,但是他们讲多国语言。英、德、法、意语,在全面衡量我们的艺术资历后,我们得到了演奏这些名贵琴的机会。”

“听新闻说在香港的拍卖会上,斯特拉迪瓦里的一台中提琴卖出了四千五百万高价,而斯特拉迪瓦里一生只有九把留世的中提琴,现在一把在我们的重奏组里,这把琴是斯特拉迪瓦里在90岁高龄时的作品。有这样的绝品在我们的组合里,可想而知这个组合的份量了。这个基金会还曾经赞助过瓜奈里四重奏,同样将瓜奈里名琴捐助给四位艺术家,他们演奏了30年,已经退休了,能在那些前辈之后光荣地接过这样的工作,也是我们这个组合最大的荣誉和荣幸。”
荣誉和机会像一根皮鞭
王晓明的谈吐很清晰,对问题回答的很全面。面对这样令全球音乐家都艳羡的机会,在背后还需要艺术家负担和付出很多。
他说道:“听起来是资助,但同样有竞争机制,这个资助并不是终生制的。基金会要看音乐家持有琴后的表现,包括音乐家的状态、演奏质量以及活动能力等。包括我们全球各地演出的信息,包括来北京,都要反馈给基金会,让基金会知道琴的走向,是否发挥了琴的艺术价值,以及我们的艺术行为是否跟琴匹配等等。目前,我们每年有35到40场音乐会,每年都在中国巡演,每隔一年要去美国巡演,明年还要去韩国和日本。基本是在全球地区演出。”
重奏是音乐表现形式中最有难度的,也是最富有变化的。看得到的是头顶上荣誉和责任,看不到的是对音乐的慢工细活。用王晓明的回答就是经得住“熬”。
他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是盲婚哑嫁的夫妻,相互之间就是要磨合。我们平时在苏伊士运河边上的排练厅定期排练。四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会出现因为不同理解而吵架的情况。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母语,其实音乐是最直白的语言,在音乐中最好沟通。从一个组合能够成型的几点要素来说,需要音乐基础,音色、音准、音乐理解等都要统一。‘熬’一部作品,经常一年不演出。我们曾经为了演奏巴托克的四重奏,8、9个月没有演出,一直在磨合。重奏组合起步很艰难也很漫长,只要熬过去,回馈给你的绝对是值得的。”
除了在艺术上着力打造自己的特点,还有实际的经济问题。王晓明说:“我们的乐器的保险很高。一把乐器保险一年缴费在15万人民币左右。也就是在手上多少年,就要交多少年的保费。大提琴出行一定要买两张票,经常在机场值机的时候,工作人员要弄清楚是大提琴先生还是女士的问题。而且我们四个人也是尽量避免坐同一班机,这个也是国际乐团出行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王晓明的确是年轻一代音乐家中比较幸运的一位,但这份幸运背后是他马不停蹄游走在世界各个的舞台间的辛苦和汗水换来的。
西方音乐会宠儿在国内撩起面纱
谈到中西方音乐会上演出四重奏有何不同时,王晓明说:“其实在中、西方的舞台数量上相差不多了,但国内舞台通常感觉有点无聊,毕竟重奏的气场小。不同点主要在质量上,也是因为观众的原因。在欧洲每场室内乐音乐会都爆满,还有在楼梯站着听的。乐迷们特专业,有次我们在美国演出,排练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拿着总谱在听我们演奏,可想而知我们的压力有多大。另外是曲目的选择,我们去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奏的是舒伯特《死神与少女》,今晚我们演奏斯美塔那的《我的一生》,这些都是四重奏演奏最多的。我们还想带来新鲜的音乐,演奏的是沃尔夫的《意大利小夜曲》和亚纳切克的《私密之信》,我们今后会在曲目上给中国观众更多的新鲜感,这也是继续努力发展的方向。”
一份宽广的事业
王晓明说:“我其实并不只演奏四重奏。我的本职工作是乐团的首席,除此之外我还有个人和室内乐音乐会。的确,国内教育跟国外不太一样,国内是比较突出个人的发展,这并不是错误的,但应该更立体化。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独奏家、室内乐家,也不一定是首席,需要上学期间多元化学习和感受。我当时在维也纳上学,独奏、乐团、室内乐我全都拉,三条路我都走过,丰满了自己的羽翼。我是个职业的演奏者,但是我的事业很宽广,不要束缚在一个上面,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很多选择的。”
驾驭这样的古典名琴,记者不禁要问他们艺术风格是如何定位的。他说:“虽然我们用的是古老的有名气的乐器,但我们不想做的老气横秋。我想用古老的乐器,焕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音乐。我们四个成员是70、80后。我们的思想很活跃,想给观众演奏最新鲜的音乐,至于细化到每场演出的曲目要根据观众和主办方的要求来制定。”
采访中,王晓明的附中恩师徐律一直在旁边帮他打理一些琐事。看到自己昔日的爱徒成为了艺术家,并为母校出力,这也是老师最大的欣慰。在大师课上,徐老师一直目不转睛地坐在台下听课。采访后徐老师对记者说:“看不出来吧,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留学的经历让王晓明迅速成熟起来,无论在生活还是艺术上,他还在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