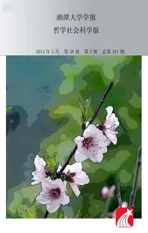中国法医学期刊的先锋
——《法医月刊》初探*1
2014-07-30章育良
章育良,许 峰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80年前创刊的《法医月刊》是中国第一本专业的法医学期刊。它是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产物,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司法改革尤其是法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壮大。最早注意到《法医月刊》之价值的是黄瑞亭先生,他站在林几的角度简要论述了《法医月刊》的创办经过。[1]37-38本文通过研读《法医月刊》及相关史料,拟对《法医月刊》的创刊背景、发展历程、基本特点及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法医月刊》的创办背景
现代法医学是伴随着现代司法制度的兴起而发轫的学科。民国伊始,中国法庭的刑事审判方式由纠问式转向控辩式,这就要求诉讼证据在案件公开审理的过程中在法庭上当众出示、展现。鉴定人要出庭宣读鉴定结论,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辩驳与质询,由此派生出法医学这门研究法律医学证据的科学。
1912年颁布的《刑事诉讼律》及次年制定的《解剖规则》明确规定,为查明死因,准许解剖尸体。然而,由于法医人才匮乏,虽然法医学的发展有了法律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仍由“仵作”承担,以《洗冤集录》为代表的旧法验尸依然盛行于中国,导致冤案频发,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思,其中以林几为代表。
林几堪称中国现代法医学创始人。1918年,林几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留校任病理学助教,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受北平大学医学院之聘筹建法医教研室。1932年受司法行政部委托,到上海筹建法医学研究所,并出任所长。
早在1924年底,林几就从国家大义的角度,撰写了《司法改良与法医学之关系》。他认为,目前国家正在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进行司法改良,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免除去旧式的仵作式的鉴定,而代以包括有医学及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法医学来鉴定并研究法律上的各问题”却始终进展不顺。[2]49环观世界,“法医学的进步,在今日已有一日千里之势,安能不急起力追,以补助司法的改善呢?”林几相信,在教育界和司法界的共同努力下,推动法医学的进步,“则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日期,亦非远了。”[2]53
1935年,在第一届研究员毕业之际,林几感慨良多:“吾国法医,向乏专门研究,墨守旧法;然人类因世界之物质进步,思想发达,而犯罪行为,则奇妙新颖,变幻莫测;是以吾国司法检务,犹如以稚子之制强寇,其不反被制于强寇而频兴冤狱者几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传统检验方法,却“毫无科学根据”,中国法医之改良“尤属当务之急”。[3]
林几的呼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纷纷撰文声援,如姜成勋的《调查司法声中应注意法医之吾见》,署名“汶”的《致司法部之呈文》等[1]22,国民党高层戴季陶也认为,法医学是“法谳之要术,人道之保障”,希望“政府对于法医人才之造就当视若急固焉可”。[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几才毅然南下,接受司法行政部的邀请,继续筹建几度难产的法医研究所。1932年8月,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在上海真如(今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正式成立。法医研究所对自己的定位是“掌理关于法医学之研究编审,民刑事案件之鉴定检验,及法医人才培养事宜”。[5]在林几的带领下,法医研究所紧紧围绕自己的定位开展工作,成效显著。1933年7月,第一届研究员入学后,林几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这些年轻人将来都是法医界的栋梁之才,如何在短短的一年半之内让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除了检验各地送来的疑难案件可以一定程度传播法医学知识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普及法医学常识?法医研究所作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法医学理论与务实的机构,如何扩大影响并增强与同行的联系合作?林几想到了一个“一箭多雕”的好办法——办刊物。当时,国内的医学刊物和法学刊物颇多,但尚无法医学方面的专业刊物,创办这样一个刊物,也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于是,《法医月刊》应运而生。
二、《法医月刊》的发展历程
《法医月刊》于1934年元旦创刊,至1936年1月30日出版最后一期,历时2年,共刊行21期。除用6期发为2个专号外(其中8~11期为鉴定案例专号,12、13期合刊为第一届法医研究员毕业论文专号),其余15期共载文162篇,平均每期刊文10.8篇。计上2个专号登载的100个案例和17篇毕业论文,则合计刊文279篇,总版面为2255个(含广告页)。开始设有论著、检验、化验、问答等栏目,随着刊物的发展和稿源的逐渐丰富,先后增设鉴定实例、医药、消息、综说、译述等栏目。
《法医月刊》以“图得着真正而科学化的洗冤录”[6]为办刊宗旨。林几在发刊词中详细阐述了办刊的具体设想:“法医研究所有研究班之后,集教授、学员平时研究所得,发为月刊。举凡学术事例之足供研究参考者,公开登载。学术则包括法律、医药、理化、生物学、毒物、心理及侦察各科。事例则分民事、刑事各案。有意见之商榷,或事实之鉴定,但求真实,不涉虚夸。深愿法政界、医药界之有志于斯者,共同讨论,而期进步焉。”[7]陈安良在“编前言”中也呼吁道:“因为它是刚出世的婴孩,希望各界能以同情的态度爱护,并用科学的眼光研究的精神加以指导。”[6]
陈安良仅仅是法医研究所第一届研究员中的一员,“编前言”何以交由他来撰写?不仅如此,《法医月刊》的整个编辑队伍大都出自这届研究员中。这正是林几的过人之处。放手让学员去办刊,让学员始终在第一线,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有裨益。因为办杂志是个系统工程,能全方位地锻炼人,组稿、编辑、印刷、发行、广告、财务等每个流程,都是需要智慧和汗水的。
第一届研究员,林几精心挑选了17人。从下表可以看出,这批学员有着良好的知识背景,全部是医学专业出身,毕业于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医学院等名校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段,入学时平均年龄28.5岁,最小的25岁,最大的39岁。

法医研究所第一届研究员花名册
来源:《第一届法医研究员姓名一览》,《法医月刊》1935年第10期,前言页。
学员入学后,即组建第一届法医研究员研究会,再从研究会会员中选举9人组成出版委员会,负责《法医月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所长林几兼任总编辑。其中,编辑组2人、文书组1人、财务组1人、校对组2人、印刷组1人、交际组2人。出版委员会成员是:陈安良、陈康颐、汪继祖、张积钟、蔡炳南、于锡銮、吕瑞泉、王思俭、连耕南;除连耕南(其身份不详,或为教师代表)外,其余8人均来自第一届研究员班,具体分工不详。
从第七期开始,除总编辑一职不变外,改由陈安良、张积钟任编辑,汪继祖、陈伟任校对,蔡炳南负责出版(发行)事宜,于锡銮、吕瑞泉负责广告部的工作。
1934年12月第一届研究员班毕业后,研究会的工作不能继续,法医研究所决定对该会进行改组,会员由原来的仅限于研究员扩大到该所教职员、名誉技术专员等,组成法医研究会,负责研究、出版等会务。由是,自1935年1月起,《法医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就由新的编辑部负责了。与创刊时由第一届研究员担任编辑出版工作不同,新编辑部的成员均为法医研究所的教职员,其中,林几兼任编辑主任、张平任总务主任、祝绍煌任广告主任、杨尚鸿任校对主任、范启煌任财务主任。这一调整,或许是考虑到研究员毕业后的流动性太大,不利于形成一支稳定的编辑团队;直接原因则是第一届研究员毕业后,第二届研究员的招生工作迟至1935年9月才启动。
不幸的是,新的编辑班子组建没多久,林几就患了十二指肠溃疡,必须赴北平接受治疗,司法行政部遂任命孙逵方继任所长一职,并自第15期开始兼任《法医月刊》的主编工作。
鉴于法医研究所工作日趋繁重,无暇顾及法医学论文的写作与编辑,故自1936年4月起改月刊为季刊,更名为《法医学季刊》,孙逵方重拟发刊辞,卷次期号另起。惜乎出版3期后即终刊。虽然《法医学季刊》脱胎于《法医月刊》,但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前者均迥异于后者,故对《法医月刊》的考察,并不涉及《法医学季刊》。
三、《法医月刊》的基本特点
《法医月刊》创刊伊始,就以创新、专业、特色而让人眼前一亮,两年下来,它慢慢地积淀出自己的风格。
从办刊理念来看,以培养年轻人为目的。首先,大胆启用年轻人办刊。在招收的第一届研究员中成立出版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医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这些刚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大学生编辑出版一本杂志,并且是刚刚创刊的全国公开发行的杂志,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其次,大量刊登年轻人的论著。在1—7期杂志中,90%以上的论文都是由这些学员撰写的。通过《法医月刊》,人人都得到了练笔的机会,有的甚至每期都有文章刊出。再次,在第一届研究员毕业之际,将他们的毕业论文作为《法医月刊》的一个专号刊出,林几亲自作序,称赞这些文章“对于各种法医学术之探讨,尚颇有见地”。[3]可以说,《法医月刊》就是特意为培养锻炼年轻人而创立的。林几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第一届研究员毕业之后,还有不少学员投稿《法医月刊》。

法医研究所第一届研究员毕业论文题目一览表
资料来源:《法医月刊》1935年第12-13期合刊。
从编排体例来看,栏目设置科学合理有持续性。作为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刊物,《法医月刊》以彰显专业特色为鹄的。而栏目的设置则能较好地体现一本刊物的水准和特色。在林几看来,法医学无非是“检验一切关于法医学事项”,“研究一切关于法医学问题”。[8]故林几把检验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在《法医月刊》中,检验栏所占比重最大,每期所占篇幅在1/3—2/3之间。以第二期为例,该期共刊文14篇,“检验栏”独占8篇,比例为57%。同时,《法医月刊》也没有忽视对法医学理论的研究。这主要集中在“论著栏”中,以刊登法医学研究者的研习成果为主。林几的《实验法医学》、《法医学史》等就是在“论著栏”首发的。后来,又开设“译著栏”,登载国外法医学最新理论成果,如陈康颐翻译的日本学者撰写的《关于安眠剂在法化学上的证明法》等。林几特别重视案例的作用。的确,对于一个现代法医学刚刚萌芽的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案例更有说服力的了。因此,“让案例说话”就成为《法医月刊》的一大特色。法医学研究所每年要检验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案件,《法医月刊》就地取材,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自第二期起,开设“鉴定实例栏”。然每期一两则案例似乎不能满足社会之需求,故该刊计划从2300多个案例中选择100个案例,分3期作“鉴定实例专号”,最后实际用了4期的篇幅,形成煌煌4大本“专号”,“实开法医鉴定实例之纪元”[9],引起较大反响。以至于《北平医刊》、《中华医学杂志》、《新医药》等杂志纷纷仿效,也开设类似专栏。
此外,“为普及法医学术起见”,特别开设“问答栏”,“如对法医有疑难问题时请函寄本会,当据科学原理详细答复。”[10]为了更好地“讨论学术问题及改良检政”“谋法界医界之联络”[11]自第14期起特设“消息栏”,刊登法医界的新闻,以加强法医界的交流合作。为增强刊物的可读性、趣味性,增设了“艺苑”栏目,专门刊登以文学手法阐述法医学知识的文章,如张平的《从童年绝食的故事来猜度一个伪伤者的心理变态》等。
《法医月刊》的栏目一经设置,即固定下来,不曾取消或中断,这体现了一本刊物的严肃性和可持续性。
从编辑策略来看,主打本土化、通俗化两张王牌。为了让现代法医学知识更好地被国人认知和接受,《法医月刊》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策略。一方面,将西方语境下的法医学本土化。编辑们从各地送来鉴定的案例中发掘国人对法医学的“关注点”和“兴趣点”,重点刊登相关论著。如亲子鉴定、中毒鉴定、血迹鉴定、强奸鉴定、指纹鉴定、尸体鉴定、自杀他杀鉴定等话题,就占了《法医月刊》相当篇幅。以中毒鉴定为例,该刊先后讨论了砒霜中毒、氰化钾中毒、煤气中毒、鸦片中毒、硫酸硝酸中毒、磷中毒、河豚中毒、吗啡中毒等常见的中毒现象及在法医学上的检验方法。这些以现代法医学知识为支撑的论证,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另一方面,将复杂深奥的法医学知识通俗化。主要是以摆案例、讲故事等形式让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一是“以案说法”。这就是上文讲到的“鉴定实例栏”、“鉴定实例专号”,此处不赘。二是“以事说法”。这以“艺苑”栏为代表。试举一例。该刊第4期“艺苑”栏刊登了一则关于煤气中毒的文章。文章首先讲述了一个寻常百姓家冬天因门窗紧闭导致父女俩煤气中毒的故事,然后引出煤气中毒的原因、中毒的症状、中毒后的治疗方法和预防中毒的措施等问题。[12]该文写得通俗易懂,用语生动活泼,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认同。
从发展环境来看,始终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重视和支持。近代中国的几千种报刊,大多数都是在夹缝中生存,而《法医月刊》的境遇则令人艳羡,这与国民政府高层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从诸多高层人物为《法医月刊》的题词可以看出。在《法医月刊》出版期间,两任司法行政部长均为其题写刊名。1934年1月,罗文干为创刊号题写刊名,并沿用至该年年底。1935年2月,罗的继任者王用宾也为其题写了刊名并沿用至终刊。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王用宾,司法行政部次长郑天赐、石志泉、谢健、谢冠生、潘恩培,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上海特别市高等法院院长沈家彝等均为《法医月刊》题词。如居正的题词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不可谓仁乎”[13],王用宾的题词是,“洗冤有录,释冤有医,考古证今,实验为宜,学术医术,启发应时,悉心精研,治平之基。”[14]这些题词,对法医学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同时也显示了高层和法学界达人对法医学的重视和支持。另外,遍翻《法医月刊》,并未看到编辑部对经费问题的抱怨,且还能出版两个厚厚的“专号”,可见该刊的经费是充裕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行政部对《法医月刊》的大力支持。
四、《法医月刊》的历史影响
《法医月刊》的创办,是中国近代法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诞生,凸显了法医学的学科属性和专业特性;它的成长,为法医学的发展壮大、为法医学人才的培养成长、为法医学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平台。
首先,传播了现代法医学观念。林几和《法医月刊》的编辑们,试图通过《法医月刊》传播现代法医学知识和观念。比如,用现代遗传学知识讨论亲子鉴定问题,证明传统的滴血认亲的方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用现代毒物学知识解释“银叉验毒”是不可靠的;用现代免疫学的知识论证人学和动物学的区别;用现代解剖学和病理组织学的知识呼吁重视尸体解剖和病理学检验,而不能仅仅检验尸表,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告诉大家:法医学并不只是专业人员需要掌握的知识,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这与林几坚持“把科学当做揭示真相的唯一根本标准”[15]205是分不开的。
其次,培养了一批法医学人才。如前所述,林几将《法医月刊》设置为法医研究所招收的研究员施展才华的舞台,采、写、编、发各流程均由学生负责。尤其是大胆地刊登学生的习作,让学生在检验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得以充分表达。这种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终生受益。法医研究所招收的第一届研究员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快就成为行家里手,为民国后期法医学的发展和新中国法医学的建设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这批学生毕业后,由司法行政部发给法医师证书(这是中国的第一批法医师),除部分学生另有安排外,其余均分发各省服务,“嗣后各法院遇有疑难案件,均由分发各员负检验或鉴定之责”。[16]后来,他们有的赴国外继续深造,有的转入高等学校任教,成为法医学各领域的专家。如陈安良先后赴德国符兹堡大学医学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广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市卫生局副局长、广州市副市长等职。[17]张树槐于1940年回北平大学任教,1943年赴日本长崎医科大学深造,专攻法医血清学、指纹学和血型的研究,回国后从事法医人证及物证检验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法医学教研组主任,兼任公安部法医师、北京市公安局法医学顾问等。[18]而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法医学教材就是由陈康颐主编,汪继祖、张树槐参编的。[19]
最后,促进了法医学学科形成。某一学问能否形成一门学科,一般包括几个要素:完整的理论体系、一定规模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权威的专业期刊等。《法医月刊》从上述方面均作了努力。培养专业人才已在上文讨论,兹处不赘。在构建理论体系方面,《法医月刊》发表了一些对法医学学科建构颇有价值的论著。比如林几所著《实验法医学》就在该刊连载。在该著中,他这样定义法医学:“法医学者,是以医学及自然科学为基础而鉴定且研究法律上问题者也。”据其研究,法医学可分为法医检验学、法医精神病学、法化学、社会医学、保险医学、灾害医学等。[20]祖照基也探讨了法医学的定义及在医学上的地位,他认为,重视法医学的国家,也就是“文化进步之国家”。[21]林几还从学科史的角度梳理了世界法医学的发展史。[22]《法医月刊》对学科建设最重要的贡献则在于,让法医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业刊物;它的诞生,是法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法医月刊》还为法医学界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这就是“消息栏”的创设。“消息栏”主要刊登“有关于检验及其他与法医学有关之消息”[11]。如第15期就发布了浙江省高等法院培养法医人才的消息。[23]
五、结语
诚如《中国医学通史》的评价:作为“我国第一部公开发行的法医学杂志”, 《法医月刊》“对现代法医学的引进、介绍、应用与传播做了很大的努力”。[24]442煌煌《中国医学通史》能注意到并专用一段来讲《法医月刊》,可见该刊在中国医学史上尚有一定的地位。遗憾的是,随着《法医月刊》灵魂人物——林几的北上,《法医月刊》的办刊方针逐渐偏离初衷。后来,一个新的刊物《法医学季刊》取而代之,而新刊也仅出版了3期就中止了。但是,《法医月刊》的终刊,并不意味着法医学在中国遭遇了困境。相反,它已经被装进近代司法改革的汽车里,随着车轮滚滚向前。因为它传播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观念;它影响的,不仅是个体,更是时代。
参考文献:
[1]黄瑞亭.法医青天——林几法医生涯录[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
[2]林几.司法改良与法医学之关系[M].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 北京:晨报社出版部,1925.
[3]林几.序[J].法医月刊,1935(12-13).
[4]万友竹.法医论[J].医药学,1931(11).
[5]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暂行章程[J].司法行政公报,1932(13).
[6]陈安良.编前言[J].法医月刊,1934(1).
[7]林几.发刊辞[J].法医月刊,1934(1).
[8]林几.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成立一周年报告[J].法医月刊,1934(1).
[9]法医研究所成立二周年纪念刊物预告(鉴定实例专号)[J].法医月刊,1934(7).
[10]问答栏启事[J].法医月刊,1934(2).
[11]消息栏启事[J].法医月刊,1935(12-13).
[12]百渊.一氧化碳的中毒——煤毒[J].法医月刊,1934(4).
[13]居正.题词[J].法医月刊,1934(9).
[14]王用宾.题词[J].法医月刊,1935(14).
[15][荷]冯客.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M].徐有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6]法医师分发各省服务[J].法令周刊,1935(242).
[17]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开拓者——记著名公共卫生专家、法医学家陈安良教授[J].广东科技报,2008-12-09.
[18]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卫生年鉴1991[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19]中国法医学家——陈康颐教授.法律与医学杂志,1996,3(1).
[20]林几.实验法医学[J].法医月刊,1934(4).
[21]祖照基.法医学之定义及其在医学上之地位[J].法医月刊,1935(15).
[22]林几.法医学史[J].法医月刊,1935(14).
[23]医界消息[J].法医月刊,1935(15).
[24]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