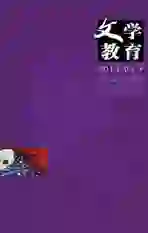《沉沦》和《田园的忧郁》中忧郁症成因分析
2014-07-24覃瑶
覃瑶
内容摘要:《沉沦》和《田园的忧郁》都是剖析忧郁症的小说。同时这两部小说又带有极强的自传色彩,大部分内容都取自作者的真实经历。从相似的忧郁症状出发,(包括:孤独寂寞的心境、情绪行为上的消沉倦怠、神经过敏症、生理上的虚弱乏力),基于两篇文章极强的自传性,本文根据作家相关的传记材料探析两位小说主人公相同病症的不同成因即:1、不同的社会背景;2、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
关键词:《沉沦》 《田园的忧郁》 忧郁症
一.相似的病态心理
《沉沦》和《田园的忧郁》都是典型的剖析忧郁症的小说。《沉沦》讲述一个民国时期的男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因国运衰微,遭人冷眼。抱负不得施展和青春活力不得释放的双重挫折诱使他以错误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欲和痛苦,可是随之而来强烈的自责羞愧和挫败感让他精神崩溃,最终自杀。《田园的忧郁》讲述年轻作家因不堪忍受城市的喧嚣和事业挫败的压力,携妻子和猫狗迁居乡下,可乡下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又使他厌倦,精神上的根本问题不得解决,反而越来越压抑暴躁,甚至常常出现幻觉,小说到此为止。
从文本来看,两位主人公的忧郁症症状十分相似。首先,二者都感到孤独寂寥。留学生在读期间感到“孤冷得可怜”,作家则心生“缺乏生机的寂寞无聊感”。这种孤独来自对被理解的渴望,当两人试图从人际关系中获得理解时,他们很快就感到厌倦,深感交流的无力和被动,最终又落到郁郁寡欢的境况当中。然后,两人在情绪和行为上都表现得消沉倦怠。对于留学生来说,不仅教科书“味同嚼蜡”[1],历来钟爱的小说也“早有一些儿厌倦”[2]。作家对生活的厌倦更为明显“不论读着什么书,他都会产生一种‘一切书籍全是无聊的感受”[3]。虽然他们各有理想,可是两人都迟迟没有行动。对于人生和自我的价值,一个觉得自己是槁木,死灰,人生的热望已然消灭;另一个甚至怀疑人生的价值是否真正存在:“人生真有值得一活的价值吗?死了?也有值得一死的价值吗?”“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4]其次,相似的忧郁症状还表现在神经上的过于敏感。一方面,两人都多愁善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就流出“两行清泪”来。另一方面两人情绪都易激动。留学生容易产生亢奋的复仇心理。作家则易怒,他曾多次因小事对妻子发怒,甚至大打出手。此外,神经敏感还表现为多疑,只要同学在一旁说笑,留学生就感觉别人是在嘲笑讥讽他。作家常疑心别人要杀掉他的狗,他明知不用担心,可每到夜幕降临,他又充满焦虑。最后,随两人神经过敏而来的是经常性的浅睡眠甚至是失眠现象,而伴随着睡眠质量下降和持续的精神紧绷,两人都出现了记忆力、体重下降,体质的逐渐衰弱和幻听、幻视等现象。
二.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沉沦》和《田园的忧郁》
《沉沦》和《田园的忧郁》都是自传性很强的小说,二者都迎合了当时风行的私小说“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的暴露出来”的艺术风格。
1919年,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肄业并于该年十一月进入东京帝大经济部就读,《沉沦》完稿则是在1921年。从内容上看,《沉沦》主人公的经历与郁达夫自传的内容十分相似:1、主人公留学以前的成长经历,与郁达夫在自传中的讲述基本一致;2、留学期间,两人除了身份地位相同,在日应试留学的经历也相似;3、从细节上看,小说里留学生同长兄发生矛盾后选择从经济部转到文学部,然后搬入梅园等事件在刘保昌先生的《郁达夫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4、郁达夫在1915到1916年间确有忧郁症病史。郁达夫曾谈及自己“对于创作,有如何的一种成见”时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所以我对于创作,抱的是这一种态度,起初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5]就以上几方面,我们可以推断《沉沦》是郁达夫以他在名古屋八高和东京帝大的生活为题材写成带有自传性的小说,留学生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自己。
《田园的忧郁》,其自传痕迹也很明显。从《田园的忧郁》的序言中我们得知佐藤春夫在1916年四月到十一月期间曾离开和歌山县东牟楼郡新宫町移居到武藏野的南端——神奈川县的乡村,同行的只有他的妻子,两只狗,两只猫,那儿浓郁的乡村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田园的忧郁》便是他根据这段时期的经历,加之后来在艺术、情感上的遭遇从1916年到1918年经历《田园杂记》《病了的蔷薇》再到《田园的忧郁》历时三年完成的作品。《田园的忧郁》算得上是他这三年经历和感悟的诗意式的沉淀。
三.相似忧郁症状的不同成因
虽然两位主人公在忧郁症的症状上非常相似,但仔细分析这两种忧郁即“孤冷得可怜”与“缺乏生机的寂寞无聊感”,其中确有内在性质的差异,也就是说导致这两种相似忧郁症的原因是不同的。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两部小说都具有极强的自传性,主人公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自己。所以接下来文章就从作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两个主人公相似忧郁症的不同成因。
(1)社会历史背景
不同的病因首先源自二人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郁达夫笔下的留学生同他一样,其忧郁根植于“祖国的劣弱”。郁达夫在自传中谈及《沉沦》的创作背景时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力气,毫无勇毅,艾艾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6]郁达夫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一年,而“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7]。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一代人,他的出生就是“一个悲剧的诞生”。这样的出生为后来的忧郁埋下了毒根。长于社会动乱,民族危亡之际,郁达夫从小被灌输“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的观念。少年所读也促使他铭记国耻,义愤填膺,拯救百姓和国家于危难之间,报家国之血恨的理想,是深入骨髓的。可现实却是残酷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如同晴天霹雳;八国联军侵华后清王朝完全沦为外国人统治中国的工具,多少志士仁人满腔救国图强的热血被无情抹杀;《巴黎和约》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轻视更是让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抬不起头来。这样的惨况常人都难以忍受,更何况是郁达夫这样格外敏感的人。在自传中他说道自己所感受到的“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到过日本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出的。《沉沦》中留学生之所以苦闷抑郁,敏感多疑,根据郁达夫的景况就可以明白得十分透彻。在祖国劣弱背景下,留学生在日本长期生活在别人的侮辱、轻蔑、谩骂之中,因此情绪日渐低靡,日益感到自我价值的缺失,陷入对生活的极度厌倦、对现实的无力是从之中。
而佐藤春夫笔下作家的忧郁根植于安泰环境中青年对人生与价值的哲学性的迷茫和困惑。在佐藤春夫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日本从多次对中及对俄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了巨额资本积累,这促使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国内经济繁荣,局势稳定,与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一战后美国民主主义思潮兴起,开放的日本迅速接受了该思潮的影响,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各个文化领域。郁达夫在为戏剧《出家及其弟子》的中译本写序的时候,曾回忆了当时日本青年的思想状况:“当时的日本,政治入于小康,思想纵横错乱之至。大家觉得旧的传统应该破坏,然而可以使人安心立命的新的东西,却还没找着。所以一般神经过敏的有思想的青年,流入于虚无者,就跑上华严大瀑去投身自杀,志趋不坚的,就做了颓废派的恶徒,去贪他目前的官能的满足。”[7]这种颓废萎靡,消极悲观厌世,虚无的社会思潮影响是极大的,佐藤便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之家,处于这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他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已经远远地游离于自明治时代以来、青年立志投身于社会发展建设的浪潮中。他感觉到的是一种近代社会,安逸生活中的人生的虚无,对人生产生了倦怠颓废的情绪。“与人应该如何渡过自己的人生这一问题相比,倒不如说首先被他们看重的是怎样才能排遣人生中的无聊与厌倦这一‘近代的忧郁。”[8]佐藤春夫笔下的作家所经历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近代的忧郁”。
(2)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
从个人方面来看,需要重点提出的是关于郁达夫之忧郁的直接诱因。1915年的冬天,郁达夫时值20岁青春,正如《沉沦》里面的留学生一样,“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9],而这不可抑制的性欲加之精神上的压力最终导致了他的犯罪——这一年的冬天,12月19日,他第一次嫖妓,失了“童贞”。作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郁达夫,本来是非常洁身自好的,而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他深深的自责和悔恨心理,这种心理与他空有报国热情而无报国之门的失落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他严重的忧郁症的病发。郁达夫在小说中所解剖的循环性,不断恶化的忧郁症,其直接原因正在于此。
而在《田园的忧郁》的故事背景中,这时的佐藤春夫正经历艺术之途上的失意。他出生于一个有着九代行医历史的医学世家,这也是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及父亲都长于传统文体如俳句、狂歌、汉诗等的创作。“在这种中产阶级的文学氛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佐藤春夫,对自己得天独厚的文学天赋是深信不疑的。”[10]基于这样的自信,佐藤春夫也相当自尊。他在晚年的《自负之鉴》中说道“假如我没能够成为艺术家,那么我没有资格在这个社会的任何一隅立足(请不要误认为这是种自卑,这是我的自尊)。”可是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艺术之途受阻时,他就“把批评的目光转向内在的自我,在坚信自己的艺术才能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不安。”[11]在这种内省中,佐藤春夫作为自尊的艺术青年,敏感过度的自我意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自虐性。沉重的压力致使他倦怠颓废,焦虑不安地从城市“逃到”了“被世界遗忘,被文明舍弃”的田园。作家在田园中表现的病态正是这高度自尊和巨大压力的产物,是佐藤春夫个人情感的投射。
注释:
﹝1﹞郁达夫:《沉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5页
﹝2﹞同上,第7页
﹝3﹞[日]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吴树文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年5月版,第63页
﹝4﹞《圣经和合本·传道书》,第643页
﹝5﹞郁达夫:《郁达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83页
﹝6﹞郁达夫:《郁达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85页
﹝7﹞同上,第3页
﹝8﹞刘保昌:《郁达夫传》,崇文书局,2010年6月第一版,第41页
﹝9﹞姚继中:《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02期
﹝10﹞郁达夫:《郁达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65页
﹝11﹞曹永洁:《佐藤春夫“忧郁”的精神构造》,见《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06期
﹝12﹞[日]佐藤春夫《自负之鉴》,转引自曹永洁:《佐藤春夫“忧郁”的精神构造》,见《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06期
参考文献:
①郁达夫:《郁达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②刘保昌:《郁达夫传》,崇文书局,2010年6月第一版
③郁达夫:《沉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④佐藤春夫(日):《田园的忧郁》,吴树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年5月版
⑤姚继中:《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⑥曹永洁:《佐藤春夫“忧郁”的精神构造》,见《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06期
⑦童晓薇:《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02期
⑧陈延:《私小说和社会意识——从郁达夫、葛西善藏作品的自我形象》,《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⑨辜鴹主编:《怎么就是高兴不起来》,贵州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