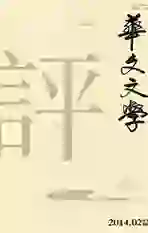恋物、悼亡与家国寓言
2014-07-22汪荣
汪荣
摘 要:黄锦树是马华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他创作于1995年的短篇小说《鱼骸》是其写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鱼骸》用浑厚沉郁的文字风格,讲述了一个旅台马华学者的现实境况与往事追忆,对离散华人的原乡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鱼骸》全篇散发着热带的气息与神秘的中国氛围,故事怪诞且意象充盈,将文化政治寓于美学的经营之中,在表面的情节背后潜藏着浓郁的象征意味,构成了独特的“离散诗学”。而《鱼骸》表述中的种种暧昧与悖论也是黄锦树自己的困惑与危机。
关键词:黄锦树;《鱼骸》;家国寓言,离散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101-06
在汉语写作的文学版图中,马来西亚的华文创作别具一格,构成了自身的体系与脉络。尽管有客观环境的种种设限,但马华文学依然以独特的美学风格、复杂的历史向度引人瞩目。近年来,李永平、黎紫书等人的作品纷纷引进大陆,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而仅就马华文学场域而言,黄锦树无疑是马华新生代文学的代表人物。
黄锦树,196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是在台的马华离散作家。作为一个栖身学院的批评家,他的论述与创作并行,“以实验性的小说创作和尖锐而不无偏激的文学批评强力挑战冲击马华文学的既有格局和美学成规。”①而他创作于1995年的短篇小说《鱼骸》则是其写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获得台湾第18届时报小说首奖,还被选入多个文学读本,是马华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经典。
《鱼骸》用浑厚沉郁的文字风格,讲述了一个旅台马华学者的现实境况与往事追忆,对离散华人的原乡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小说集中体现了黄锦树的创作特色:“铺陈中华性意象,逼视离散性现实,体现创伤性历史”②。《鱼骸》全篇散发着热带的气息与神秘的中国氛围,故事怪诞且意象充盈,将文化政治寓于美学的经营之中,在表面的情节背后潜藏着浓郁的象征意味,值得我们重新进行寓言式阐释和症候式解读。
一、文本的两个世界:
细节的对照与主体的镜像
《鱼骸》的结构十分严密,以“时间”为标准可以区分为“回忆”与“当下”两个场景,是一个交错并进的双线结构。然而,作者黄锦树在结构上的独具匠心不仅体现在文本内部,还体现在文本与历史的对话上,他借由一个虚构的文本,将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历史重新讲述出来,也由此凸显了文本的政治向度。上述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双向互动,同时也提醒我们:黄锦树深谙张爱玲“参差对照”的美学。事实上,《鱼骸》在结构内部充满了对称与并置,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紧张感的文本。回忆/当下,文本/历史抑或只是一系列“参差对照”中的核心环节,表现在内容上,还有诸多悖论性的对照。作为一个后现代语境与学院背景的创作者,黄锦树的作品在形式上十分饱和,充满了悖论与反讽精神,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本的开头,黄锦树用大量的引文展示了考据学中关于龟和甲骨的记载,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伏笔。之后,就是少年时代的主人公“他”进入沼泽探险的故事,在其后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他去沼泽的目的是寻找大哥的踪迹。这两个自然段中,黄锦树铺展了热带的感性细节,充满了南洋的在地风味:赤道上烈阳曝照的正午,安静的四野,“沼泽深处有鸟鸣蛙叫,大爬虫的腹部窸窸窣窣地摩擦着草茎,猴群次第跃过稀疏的树。”随后,在沼泽中,他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龟壳。这是一幅生气勃勃的热带风景,充满了生命的蛮荒气息。但接下来的情节,则从回忆转入现实,他在台大研究室接到弟弟寄来的信笺,被告知他大哥死亡的消息。与此同时,灼热的赤道风景也迅速变更为台大老旧颓败的图书馆和研究室,气氛变得深邃诡秘起来。热带的狂暴与台大的阴凉、文字节奏陡然的降速、整体氛围上的由热转凉——黄锦树用精细的笔触描写了截然相反的两幅图像。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后描写研究室内景的一个自然段:书架上的旧籍、神话造型的古董、泛黄的相片、陈旧的龟壳,即使安置了现代的用品如计算机和办公用品,都被“残阳镀以一抹远古的辉煌”。这是一幅怀旧视景下的图像,台大的场景被有意地做旧,主人公“他”虽然置身于现代文明之中,室内的空间却错位地充满了上古诡秘的气息。这也与“他”其后在深夜的研究室杀龟取甲的鬼祟行为形成了互文,抑或,正是他个性的怪异和对上古的迷恋才使得他的研究室布置成这幅模样。
在开头的这几段中,黄锦树已经显露了他标志性的美学风格:南洋地景、中国符号与繁复的修辞。《鱼骸》的文本充满了各种伏笔,开头的几段已然讲述了故事的泰半,后面的故事则是对开头几段的展开:结尾处重回“他”的少年时代,信中大哥之死的故事在讲述中展开,研究室的龟甲暗示他其后的杀龟取甲。而其间的种种参差对照也铺陈开来:时间上的回忆与现实、少年的狂热与中年的颓唐、空间上的大马与台湾、热带的灼热与亚热带的阴凉、野外的开阔和室内的狭隘……这些文本表层的细节,构成了非常有张力的对照。
而这些细节的对照抑或不足以说明文本内部的深层结构和寓言层面。事实上,《鱼骸》的深度对照在于主人公“他”与其大哥之间。全文读毕,我们就知道失踪的大哥其实早已葬身在大马幽暗的沼泽之中,尽管他死亡的消息直到40年后才得以证实,但主人公“他”在离开大马之前就已然知晓。那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他追踪一头大陆龟,潜入沼泽深处为水草所隔离的水域,骇然发现了一副仰卧的尸骨,他暗暗地觉察那是大哥的骸骨——“原来你在这里。”大哥受到“中国”革命的激励,参加马共而被政府追踪,最后葬身沼泽;而主人公“他”却由此离开大马,在台湾求学直到在台大就职。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主人公“他”与大哥两人不同的命运轨迹,大哥死在鲜活的17岁,而“他”则安度人生,以研究上古为依归。大哥一度想回到中国而最终死在大马的沼泽中,“他”能回中国却故意不回,在台湾恋物龟甲,狂想上古世界。
但上述的对照或许太过表面。历史的种种吊诡与暧昧之处才是黄锦树意图剖析的物件,而他念念不忘的则是关于“本土性”/“中国性”的辩证。回到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主人公“他”与大哥之间,其实构成了文本意义上的镜像关系。在文本的操作中,大哥毋宁是从主人公“他”的角色内部分裂出去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虽然被作者外化为大哥,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鱼骸》里,少年的“他”对大哥的行动无比好奇,对大哥亦步亦趋,是一个影子式的存在(或者说大哥是一个激进的“他”)。大哥对马共和“中国”的热爱也是“他”的热爱。大哥失踪的前一年,曾教给他方块字并教导他要以“中国人”为傲。对中国的向往,是大哥的乡愁,也是“他”的乡愁。而这一切,都被大哥的生硬的失踪打断了。让我们回到那个创伤性的时刻:那一天,少年的“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尾随大哥,想弄清楚大哥到底在做什么。但大哥最终消失在沼泽和一片烟水茫茫之中。“长兄失踪之后,潜入那片沼泽深处一探究竟是他成长期间挥之不去的欲望。”联系到年少的他认为沼泽中有通向中国的秘密通道的想法,我们可以认定他依然眷恋着“中国”,他一次次地潜入沼泽,抑或代表了他寻找大哥也就是寻找心中大哥所代表的“中国性”。大哥的失踪以及他的寻找,以及由这个“寻找”所象征的“悼亡”,其实是他内心对“中国性”的寻找。
如果我们把大哥作为主人公“他”的镜像,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少年的他在大马华文中学里对政治的冷感?事实上,“他”的主体内部,包含着“中国性”与“本土性”两个向度。大哥之死无疑是对他的震惊体验,也导致了他“本土性”的那一面暴露出来,成为马华政治的局外人。同班那唤作“长白山”的男生说,“也许你注定不是这个大时代的儿女”,下句却说“你大哥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志士”。“他”是时代的迟到者,大哥则是时代的现行者。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主体:“中国性”与“本土性”的纠葛集中于他的主体内部,互相拉扯相互背离。
南洋/中国,以及“本土性”/“中国性”的问题是1990年以来马华文坛纠缠不清的话题③。马华文学是德勒兹与瓜达里所谓的“小文学”,具有去畛域化、政治性、集体价值三个特征④,并且具有本雅明和詹明信所谓的寓言意味,在美学的文本中往往充满了政治和历史的隐喻⑤。而我们的寓言式解读则是要从历史的碎片中寻找整合的意义,在对主体的阐释中发掘其背后的历史背景。由此,我们需要从文本中读出形塑主人公“他”的历史力量,从文本细读中挖掘导致主体分裂与身份焦虑的历史势能。
二、“胡不归”:历史创伤与身份的焦虑
在《鱼骸》的主人公“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影子——总是那般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神情,一个时代多余人的形象。确实,“他”既不属于马来西亚,也不属于台湾。黄锦树正是用这多重的“不属于”象征了主人公边缘化的身份,也托喻了大马流散社群处于“无何有之乡”的生存处境。在多重文化——政治的夹缝中,“他”遭遇了身份的焦虑与认同的危机。
胡不归?此心安处是吾乡。大马的浪游者们试图寻找的正是一个“心安”的地方。在马来西亚与台湾之间,“他”如何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作者黄锦树在此处采用的方法是将身份建构与历史创伤对话。在黄锦树那里,文本内部的细节与马来西亚的历史勾连起来,通过对主人公“他”的生命史脉络的展示,黄锦树让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华人与马共、马来西亚国家之间那复杂而暧昧的关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鱼骸》中的一个吊诡,主人公“他”虽然对中国念兹在兹,却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尽管如此,大哥梦想中的神州,他是一次也没去过,也从来没想过要去。……这一切并非源于政治考虑,而是基于更深层的情绪。中国啊中国,它是致长兄及多少时代儿女于死的诅咒呵!”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片段,解释了“他”没有去中国是因为“中国”是华族子弟命定的诅咒,导致了“他”的大哥的死。回到历史现场:1948年至1953年,英帝国在马来半岛苟延残喘,实施戒严,原因正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风潮波及南洋,在乡愁与爱国的激情之下,华族子弟群起响应,开始了时代的狂飙。主人公的大哥正是马共的成员。主人公的大哥1952年失踪,则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对马共的镇压所致。⑥而长兄之死则导致了“他”对“中国”的愤懑与怨怼,在他看来,大哥参加革命是受到“中国”革命的鼓舞,最后却因这个理想而罹难,这是“中国”对大哥的辜负与背叛。大哥的死亡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也阻断了“他”对“中国”的认同。
毋庸置疑,历史创伤导致认同的挫折,主体受创的经验导致对国家不信任感的发生。与“中国”相同,主人公“他”对马来西亚也并不认同。那生他养他、伴他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却是一个他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去的地方。流散社群的个体在主流社会中常常组成亚社会共同体,以希求互助。但“他”却对马来西亚无动于衷。事实上,那不回去的,不仅是大马的空间所在,更是不愿意回到一个创伤性的原址——无论是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还是1958年建国后的马来政府,都对马共极度厌恶,同时也对在马华人严加管制。⑦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族的压抑构成了“他”的创伤经验,由此也导致“他”成年之后对马来西亚的不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特殊的时代气氛下,“他”懂得了方块字的价值,正是当时政府对华族的压抑使得“中文字在那个时代,像符咒一样充满神秘的魔力。”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其后对汉字与龟甲的迷恋,这毋宁说是一种创伤的伴生物。
“他”对大马的逃离带有幸存者的庆幸,他“带着这两样纪念品和他心底深处的欲望离开家乡,心里一直有一种逃犯的感觉,仿佛他的有效追诉期一直没满。”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可谓是收留他的福地。但台湾也并非他的认同所在。虽然身为台大的教师、在学院中安身立命,但台湾只是他生存的地方、“谋食”的地方。他娶妻生子,循规蹈矩地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审慎生活。在另一重意义上,台湾又是他与历史和解、与自我和解的地方,一个他没有遭受过创伤的地方。但台湾是他的故乡吗?不。“中国”是他的原乡,大马是生养他的故国,而台湾则只是他的栖身之所。他并没有对台湾产生认同,漂流的感受裹挟着他,对这个离散者而言,台湾只是一个暂留地。而这份难言的苦楚只能由自己承担,他逐渐变得自闭,与周边的人际环境格格不入,成为一个孤僻的人。
通过塑造主人公“他”,作者黄锦树经由身份的探索完成了对历史现场的重访。主人公“他”的三个“不属于”是一种个体与空间的错位,也是历史的创伤所导致的个体身份迷失。历史的创伤话语是衍生、回旋、播散的,构成了记忆,也形塑了主体。“中国”、大马、台湾构成了《鱼骸》主人公“他”的生命史的三个空间,也构成了他的三个认同对象。从原乡到他乡,从岛到岛,再到反认他乡作故乡。历史创伤的规避与回应,形塑了马华流散社群特殊的身份认同机制。而作为跨界的马华离散群体的存在,不仅说明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是诸多因素复杂且暧昧的交织,也暴露了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国族身份的种种吊诡与谬误之处。由此看来,对于“胡不归”的问题解答,不仅是他乡与原乡的辩证,更是记忆与身份的辩证。流散在他乡的大马华人,他们回得去吗?
三、龟—鬼—归:骸骨迷恋与“中国性”问题
“我们还记得,现代中文里的‘龟音同‘归。如果‘鬼之为言归也,那么黄锦树的‘归去之鬼可是已化成归去唐山之‘龟?”⑧在黄锦树的笔下,龟甲成为“中国性”的符号。龟甲上所刻的甲骨文,是中华文明始源想象的表征,也是乡愁的对象化客体。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主人公“他”对龟甲的恋物情结,其实是对“中国性”的欲望和想象。
在《鱼骸》中,最耸人听闻的片段无疑是那主人公“他”在夜深人静的台大研究室所做的杀龟取甲的“实验”,“往往在深更人定之时,他就可以如嗜毒者那般独自享用私密的乐趣,食龟,静聆龟语,暗自为熟识者卜,以验证这一门神秘的方术、刻画甲骨文,追上古之体验……”⑨他重演几千年前华族祖先的占卜仪式,是对中国的文化招魂。其神秘幽邃之处,使他自身也显得鬼魅起来。我们俨然听到他那激越的“归”的声音,沉郁顿挫、如鲠在喉。发愤以抒情,那股浓浓的乡愁淤塞于胸,使他化身为巫。而他行为的诡异正是因为“他”严重的身份焦虑所致。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⑩奥德赛的浪游以回到家乡为终点,但主人公“他”的原乡却是回不去的。这是一个颇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生存处境——流散留台的“他”,被抛掷到既非原乡也非出生地的台湾,既去不了中国,也回不去大马(这更多是心理上的隔阂)。去国离乡意味着主体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被连根拔起抛掷到其他的场所,也意味着主体永恒的匮乏与失落。《鱼骸》的主人公“他”就是这样一个匮乏的主体。他乖僻的行为所具有的病理学原因就是:乡愁的渴念吞噬了它的心魂,唯有不断地填塞“中国性”才能治愈。
但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他”念兹在兹的“中国”在文本中却显得无比的吊诡。一方面,“他是一次也没去过,也从来没想过要去”。另一方面,“他对老中国的古董有极大的兴趣,也以老中国符码的研究为毕生的志业”。在他那里,中国不是空间的实有,而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他迷恋的“中国”是古典的、方块字的、龟甲里的中国,一个抽空了时间和空间的“老中国”。这一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中国,既是庞大的能指,也是空洞的、漂浮的能指。这是主人公“他”所臆想的中国。
恰如题目《鱼骸》,以及文中的意象龟甲和骸骨,“中国”对于主人公“他”来说,恰恰是抽空了内容的形式,既是庞大的在场,又是永远的缺席。匮乏的主体对应的是中空的中国符号。主人公“他”是一个老灵魂,一个“骸骨迷恋者”:小说最后写道,少年时的他在沼泽中找到大哥的遗骨,想要把骸骨带回去,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截取与喉结相对的那一节颈椎,考虑的是它位置的特殊性。代价是,它必须身首分离。”他把这块骸骨和旁边的龟甲带到台湾,作为纪念品收藏。在人前,他撒谎说这块大哥的骸骨是热带鱼的脊骨。这身首分离的骸骨似乎对应了前文“龟虽产于南洋,龟版却治于中原。杀龟得版,哪还能还原?”这两个形象说明了南洋华族子弟精神与身体的分裂,认同与生活的分离。他们心中向往的中国是一个脱离现实指涉的空洞的中国,这个老中国既与当代的中国无涉,也与大马的本土无涉,脱离了真实生活成为一个超真实的幻象。这一乡愁的激越恰恰是以抽空“本土性”和“在地性”为前提的。“骸骨迷恋者”种种行径演绎了这个“身首分离”故事的怪诞美学:恐怖、变态、扭曲。但这种种恶托邦的乖僻行径,却是黄锦树有意为之的。
1995年5月,黄锦树受《南洋商报》之邀,正对当时诗歌进行评价,也由此拉开“中国性”论争的序幕。他在《两窗之间》一文中对林幸谦“过度泛滥的乡愁”提出批评{11}。此后,他更是以咄咄逼人的言论在“中国性”议题上暴得大名,成为“本土性”论调的代表,让马华文坛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还记得《鱼骸》的创作正是1995年,由此,黄锦树的创作和论述是同时的,我们可以在创作中重新审视他的论述。黄锦树的论述的核心观点是“断奶论”,摆脱过度的中国乡愁和文化情结。在《鱼骸》中,黄锦树笔下的主人“他”正是这样一个沉湎在老中国世界中的人,他心念所向,是与大马现实毫无指涉的上古世界,更以魂兮归来的态度召唤上古亡灵。对黄锦树这样的“本土性”的作者而言,这样的神州想象自然是对“本土性”的压抑,无益于马华文学的灵根自植。而“这一‘中国符号内蕴两极的召唤:一方面将古老的文明无线上纲为神秘幽远的精粹,一方面又将其简化为充满表演性的仪式材料。”{12}《鱼骸》的写作是一种虚张的写作,黄锦树暴露了“坏孩子”搅局与释梦的天性,玩得不亦乐乎。我们可以看到,《鱼骸》的风格是夸张化、狂欢化、戏剧化的。文本中的“中国性”急速膨胀,中国符号的“表演性”被置于意象与臆想的中心,于是“中国性”铺陈到极致之处,正是文本的内爆与历史的内爆之时。
在这个意义上,《鱼骸》中“他”对神州的渴念恰恰走向了反面,换言之,这激越的乡愁毋宁是一种物伤其类、自虐虐人的表演。然而,我们又要认识到创作与论述的不同,论述是直线的、抽象的,创作是曲线的、具体的。黄锦树试图摆脱“中国性”,去建立马华文学的“本土性”,这就意味着他要摆脱“本土性”,用一套替换性的“华文”和话语体系去建筑自己的族群本位。这在黄锦树对主人公“他”的批判和嘲讽中可以看出。但是,在文本操作的层面,黄锦树却又跌入自设的陷阱之中——我们在《鱼骸》中看到,他对中国符号使用较之他批判的文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中国符号的批判/使用形成了吊诡,这自相矛盾的结果,恰恰是反噬了他本身。而他对南洋地景的描述却并没有达到“本土性”的效果,反而使大陆与台湾读者有了南洋猎奇的陌生化和奇观化的体验。{13}此处主体与他者的辩证,无疑是黄锦树意想不到的。
“他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怪圈:若想建构属性,其起点必在历史溯源;而历史又成为淹没自我的深渊和难以走出的迷宫。”{14}身份建构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黄锦树的《鱼骸》之所以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意味,也与这历史的深渊有关。“历史中的人物和时间在众纭迷离如雾团的叙述中越来越抽象”。{15}《鱼骸》的多重结构与自我解构恰恰说明了马华文化在主体性建构中面对的诸多悖论与迷失。小说是一个族群的心灵史,在宏大的国族论述之下,小说恰恰给我们指出在文化的夹缝、历史的宏大叙述照顾不到的角落中生存的那些人的生存状态与存在处境。《鱼骸》的自反与解构恰恰说明了历史的复杂与暧昧,由此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族群的心灵证词。
结语
《鱼骸》中的主人公“他”有着黄锦树自己的影子。例如,《鱼骸》写作的1995年恰逢黄锦树硕士毕业,其硕论亦与语言文字学相关{16},他本科就读的学校是台大,其文学教养与思想谱系中有日本私小说的渊源{17}。由此,《鱼骸》对黄锦树而言有了更多本纪和自况,有了更多的感慨系之。《鱼骸》主人公“他”对身份的寻找也是黄锦树在书写过程中对自我的寻找。我写故我在,黄锦树有“躁郁偏执的倾向,必得在文字间找出路。”{18}这书写的过程既是慰藉历史的创伤,也是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与位置。而《鱼骸》表述中的种种暧昧与悖论也是黄锦树自己的困惑与危机。
千年之前,屈原踟蹰在南方水泽之畔葱郁莽芜的草木之中,中国的离散诗学由此兴焉。黄锦树负笈台湾后留台任教,在岛屿安身立命,遥望神州与大马,其漂流的身世是否接续了屈原的意绪与遗风?这是南方的写作:意象纷呈、情感浓郁饱满、对家国之梦寄托遥深。身世的托喻,时空的暌违,读者看的是一篇荒诞离乱的往事,对于作者而言,未尝不是一场自噬其身的表演。最华丽的表演要以最暴虐的自伤来创作,那追逐的原乡神话的浪游人将魂归何处?黄锦树每每热衷讲述郁达夫流散南洋的尘埃往事,“失踪与寻找”是他的创作的母题。那失踪者的背影,也深深地定格在《鱼骸》之中。
① 刘小新:《论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小说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1期。
② 黄万华:《黄锦树的小说叙事:青春原欲,文化招魂,政治狂想》,《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③{11} 王列耀、龙扬志:《身份的焦虑:论90年代马华文学论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④ 张锦忠:《关于马华文学》,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09年版,第11页。
⑤ 高嘉谦:《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载《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351页。
⑥⑦{17} 陈昱文:《在如梦的回忆里悼亡——试析黄锦树〈鱼骸〉及其相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3期。
⑧{18} 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论》,《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77页;第374页。
⑨ 黄锦树:《鱼骸》,《死在南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⑩ 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名句,转引自王德威、黄锦树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6页。
{12} 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第367页。同时,参见黄锦树:《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Ⅱ》,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版。
{13} 这些现象被刘小新所批评,参见刘小新《论马华作家黄锦树的小说创作》。
{14}{15} 朱立立:《历史记忆·始源想象·身份建构——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历史书写及属性意识》,《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16} 诸葛靖浩:《迷惑忆往下的丛林重层——浅谈黄锦树〈鱼骸〉中的意象可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Fetish, Mourning and Home-country Fable
---Diaspora Poetics of Huang Jinshus“The Fish Skeleton”
Wang R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Huang Jinshu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new generation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is 1995 short story“The Fish Skeleton”is a milestone in his writing career. With depressed style of writing,“The Fish Skeleton”tells abo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reminiscence of a Malaysian Chinese scholar in Taiwan, and explores thoroughly the hometown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problems of diaspora Chinese. With its bizarre stories and images, the story demonstrates a tropical flavor and a mysterious Chinese atmosphere. It implies cultural politics in aesthetics and rich symbolic meaning under the plot on the surface, and it constitutes a unique diaspora poetics. However, the various ambiguities and paradoxes in the story betray Huang Jinshus own confusions and crisis.
Key words: Huang Jinshu,“The Fish Skeleton”, home-country fable, diaspora po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