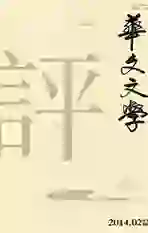客观艺术与浪漫艺术
2014-07-22梁燕丽
梁燕丽
摘 要:对比台湾王鼎钧先生的《那树》和新加坡郭宝昆先生的《傻姑娘和怪老树》,我们发现浪漫艺术与客观艺术的微妙差异,浪漫艺术植基于个人的感受和思想,好像海洋表面的惊涛骇浪或波光潋滟;客观艺术根入亘古不移的海洋之心,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波动,其所揭示的毋宁是“人之宿命”或“宇宙的法则”。
关键词:客观艺术;浪漫艺术;王鼎钧;郭宝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053-05
王鼎钧的散文名篇《那树》写一棵老树,新加坡郭宝昆的话剧《傻姑娘和怪老树》也写一棵老树,并且二者都把重点放在描写老树被砍伐的最后一段生命历程,因此通常都被解读为人类文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老树成为与人类相对立的自然的代表或象征。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除了都市文明与生态环境矛盾的主题之外,两个作品之所以成为名家名作,更在于老树深刻的生命寓意,以及人与自然,以至宇宙一切生灵的一种共存呼应的关系。王鼎钧的散文是少见的客观艺术,即由世界本来的样子写作,人类为了欲望的扩张伐倒了老树,却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丝毫的自省和忏悔,当然不是所有人类都如此,清道妇和老太太作为树的邻居和朋友,本能地带着朴素的感情缅怀树的生前死后,参加树的落幕葬礼;郭宝昆则写一个傻姑娘很喜欢那又老又怪的老树,每天都去看他,和他说心里话,最后用生命保护这棵老树不被伐倒,充满了浪漫奇幻色彩。浪漫艺术依照理想写作,写人与树特别的感情与生命呼应,是另一种无法用科学证明的宇宙真实性。客观艺术渗透了作者现实的洞察力,浪漫艺术充满了作者美好的想象力,殊途同归都是对人与自然矛盾对立的人为性的批判,对人与自然和谐亲善的宇宙性的呼唤。
一、客观艺术:王鼎钧的《那树》①
那是一棵古老的树,见证了人世的沧海桑田。从只有行人的泥泞小路到行驶汽车的柏油路,从只有稀稀落落的老式平房到一排一排新公寓挨过来,那树的形貌总是:“有一点佝偻,露出老态,但是坚固稳定”,“黑霉潮湿的皮层上,有隆起的筋和纵裂的纹,像生铁铸就的模样。几丈以外的泥土下,还看出有树根的伏脉”。②在几乎自然主义的描写中,没有轻浅浮华的美化或主观化,文字形象生动却朴实厚重,是按照老树本来的样子描写的客观艺术。在前现代,人与植物、动物共处一个世界,彼此相得益彰:“在夏天的太阳下挺着颈子急走的人,会像猎犬一样奔到树下,吸一口浓荫,仰脸看千掌千指托住阳光,看指缝间漏下来的碎汞”;鸟儿栖息,情侣止步,孩子们唱歌,“于是那树,那沉默的树,暗中伸展的根,加大它所能荫庇的土地,一厘米一厘米的向外”。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世界万物在争夺空间,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开始因自我膨胀而侵犯其他生物的生存权:“所有原来地面上自然生长的东西都被铲除,被连根拔起”。那树的生命力特别强,虽“被一重一重死鱼般的灰白色包围,连根须都被压路机碾进灰色之下,但树顶仍在雨后滴翠,经过速成的新建筑衬托,绿得很深沉”。在人类的工业化过程中,那树仍然以绿色的浓荫对世界作出贡献,然人类在扩张,自然在萎缩,而自然在人工的衬托下更显珍贵:“毛毛雨比猫步还轻,跌进树叶里汇成敲响路面的点点滴滴,泄露了秘密,很湿,也很诗意”。这是全文描写那树最美的意境,不是出现在泥泞小路和老式平房的前现代,而是出现在新建筑衬托的工业时代,老树成为世界最后一道风景,一片绿洲。
悲剧发生在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无止境的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知、浅薄和短视,那树“被工头和工务局里的科员端详计算过无数次”,“出租车像饥蝗拥来,‘为什么这儿有一棵树呢?”这显然是反讽,贪婪、浅薄使工业化没有如初衷,源源不断地给人类带来幸福,而是使人类逐渐失去了诗意的栖居和自然的情怀。于是那树越来越“无用”了,公共汽车站要搬,水果摊要搬,孩子们的幼儿园也要搬,人类自以为不再需要一片浓绿与清荫,这是树的灾难,更是人类异化的隐忧。人类急功近利至此,必然到处是躁动不安的扩张与征服,逃亡与迁徙,这些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症候,但“树是世袭的土著,是春泥的效死者”。有感于人与土地、与根的分离,作者以树为反衬,“他们的传统是引颈受戮”,“连一片叶子也不逃走”。树的坚定不移,庇护一方水土,得到了上帝的嘉许:“你绿在这里,绿着生,绿着死,死复绿”。在自然所代表的世界律法里,万物在宇宙中各有位置。然而老树终于难逃浩劫,人类找到一个借口就把它伐倒、除根:“一个醉汉超速驾驶而撞树,于是人死,交通专家宣判那树要偿命”,于是人类堂而皇之地对树施暴,“电锯从树的踝骨咬下去,嚼碎,撒了一圈白森森的骨粉……”屠杀在深夜进行,人类的残暴无以复加却又鬼鬼祟祟。作者写道:“夜很静,像树的祖先时代,星临万户,天象庄严,可是树没有说什么,上帝也没有。一切预定,一切先有默契,不再多言”。天地不言,但人类的罪责已昭然若揭,在天道自然之中,我们隐约感到人类的贪婪无度、肆意杀伐终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人类仍不知自省与悔过。以树为邻的老太太说“听见老树的叹息”,这个叹息可以看作是对人类行为的慨叹与警告,但伐树的人什么也没听到,他们沉浸在自己征服自然的胜利之中,只看到自己殖民拓展得到的成就与喜悦:“马路豁然开旷,像拓宽了几尺”,看不到自己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命和生存空间,乃至破坏生态环境,最终将祸及自身。文章娓娓道来不动声色,却饱含了作者深沉的忧思。
在今天,许多地方的绿色正在人类无止境的欲望扩张中消失,面对王鼎钧笔下这棵年轮已被定格的老树,读者会联系起身边许多关于“绿色”的故事。王鼎钧没有主观化地赋予这棵树什么特别意义,只是很真实地写出老树顽强的生命力,和最终被伐倒的命运,寄予了作者深沉的生命体验和悲慨。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必然的选择,王鼎钧说过对于文明发展“决不后悔”的话:“人类以他最杰出的才智,最艰辛的奋斗,最漫长的过程,冲出洪荒,握紧文明,难道现在后悔了吗?不,我们决不后悔,人类的幼苗不再大批大批的死于肺炎和猩红热,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人类可以在一天走完从前一生也走不完的路,立业四海,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人类可以一小时做完从前十年也做不完的工作,从各方面改善生活,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对付文明造成的灾害,是用进一步的文明,不是否定文明!”作者的思维非常缜密,其目的在于对文明发展的深刻反思,对生命意义的深切理解,对都市文明与自然界共同发展的深层思考,希望人类更有远见,更有宇宙意识,与各种生物生灵生命和谐共处于一个地球的空间。作者质疑的是“文明砍伐了丛林,却盖起不见天日的大厦;文明驱走毒蛇猛兽,却制造市虎;文明消灭瘴疠瘟疫,却散布原子尘;文明消灭了人体内的寄生虫,却代之以有害的色素和防腐剂……”作者并不简单地执着于一条思想路线,而是辩证地看待事理,众多的主体、众多的声音、众多的目光代替唯一能思索的“我”。这是客观艺术的基础。老树的遭遇引发了作者深重的感慨和思考,老树是生命的象征,自然的象征,命运的象征,从有用到无用,到成为别人生存和发展的障碍而被根除。这一切作者信笔写来却惊心动魄,尤其是人类为了扩张借机伐倒老树,却是那么理所当然,并没有丝毫的自省和忏悔。这样描写真实而发人深省。楼肇明认为:王鼎钧为了扩大散文以小见大的容量,常将一般的寓意象征,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体的象征,换句话说,他笔下的意象和象征,每每有一种哲学上本体论的味道。这是客观艺术的终极目标。
二、浪漫艺术:郭宝昆的
《傻姑娘和怪老树》③
一棵老树,但不知什么树,或许是千万棵树中的一棵,这就是“那树”传递给我们的哲学本体论味道。《那树》作为散文文体,无论是写实层面,还是象征层面,都包含了作者极为丰富的人生体验和世态观察,因而这棵老树的蕴涵极为深刻饱满,那是一般人写不出来的一棵树。比起《那树》,《傻姑娘和怪老树》作为剧作,富于虚构的戏剧性。标题中“傻”和“怪”的修饰词已传达出特殊的感情色彩和审美意味。傻是天真,是不随波逐流;怪是怪异,是与众不同。剧作开头和结尾都出现布偶,布偶作为一种象征意象,完全是一种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序场之后第2场“怪老树”,由傻姑娘的视角看老树:突出“怪”,一种怪诞的美学特征,“这棵树,很老了。又老又怪”。④“老”是写实,“怪”则带着主观感受和个性色彩,接着的描写更富于浪漫色彩:“他的枝是长长直直的,直直地伸向天空”;“别的树,叶子都长在头顶上;他的,都生在底下,靠近地面的地方”。修长挺直是一种美,天空代表理想,凸显老树的自然美好和独一无二,于是傻姑娘爱上这棵怪老树:“姑娘转身,上前去抚摸大树”。第3场“傻姑娘”,由老树的视角看姑娘,突出她的天真无邪。姑娘天天去看那棵高高的老树,教室、食堂、图书馆、停车场,哪里能看到老树她就往哪里跑。
比较起来,还是停车场最理想。
抬头仰望,老树站在斜坡上,最有气势,最美!
姑娘寻找看树的最佳角度,终于看到老树“最有气势,最美”的形象,暗示姑娘和老树一种特别的感情,充满了浪漫气息。第4场“久远的声音”回到远古,回到永恒的青春。姑娘一首久远的歌《望春风》,使“久已凝固的老树开始复苏”,“犹如僵化了千年的木乃伊重获生机一样,老树的肢体和声音,在姑娘促动下开始复活”,于是老树开口说话,这是一种寓言或童话的笔法。第5场“枯树小岛”通过老树讲述的故事,表现地球上的沧海桑田,以及世界万物共生共存的田园牧歌。在远古时代的一场暴风雨中,“老树曾浮在水面上,游向遥远的大海。大海太远了,他没有游到”。大海和天空都是理想的象征。“突然间,水面下的泥土传来了一股温暖,他感到泥土还是丰美的。在平静的水面上,阳光也依然是那么柔和的,于是,他咬咬牙,把树根死命往下伸,猛向坚实的河床底下钻。头上,他也费尽了力气,吐放新叶,饥渴地吮吸阳光的滋养,以唤起自己体内的生机。”以如此美丽的文字和想象写老树的再生,大自然万物的滋育使他重新焕发了生命力,他也和自然万物结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如此一代代生息相传,前面的又把自己尸骨化为灰泥养料,让后面的衍生不休,终于,那一棵浮游的大树,不久就变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小岛。”在遥远的想象中,一个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故事,正是作者心目中最美丽温馨的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也加入了自然交响曲,过着田园牧歌的生活。那是一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世界,无疑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艺术。接下来老树和姑娘充满哲理的对话似乎回到现实,预示了人类的欲望扩张和躁动不安将使宇宙失去平衡,将使美好自然的生活不再:
老树:我一定在。孩子,树跟人不同。人永远不停,树永远不动。
姑娘:你的祖宗不是游泳到河里去长成小岛的吗?树既然可以动,人是不是也可以停。
老树以静制动,象征永恒的自然,反衬人类的浮躁和贪婪应当适可而止。为进一步表现枯树小岛所暗示的宇宙生生不息的规律,作者又以“树”与“风”的辩证关系作比:
风说:没有风,树就唱不了歌,跳不了舞。
树说:因为枝叶舞动才有风,因为树林唱歌才有风。
第6场“傻姑娘和怪老树的游戏”,接着第5场末尾的哲理性对话,展开更为浪漫的想象翅膀,发出天问,探索宇宙一切生命本体所蕴含的哲学,最终落在人类没有权利剥夺其他生命的存在:
为什么人一定要说话?
为什么石头不会哭?
为什么眼泪不是甜的?
……
为什么星星长在天上?
为什么人要砍树?
第7场“驱魔”,在表现主义艺术中,展示聪明的人们堕落为贪婪成性的魔鬼,只有傻姑娘是个头脑清醒的天使。“铲泥机开过来了,伐树的工人到了,姑娘爬上老树,以生命保护老树不被伐倒。”然而在现实中,姑娘却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带走。第8场“树舞”描写暴风骤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冲向树林,但是树林却以轻盈潇洒的舞姿,把风雨雷电变成甘露和彩虹。雨过天晴,树根扎得更深,树干磨练得更壮,树叶也更加新洁茂盛。“孩子,别怕风雨,爱树的人,在狂风暴雨之中,你才能看到树的真正风采,他的舞……”以如此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达致对树理想境界的表现高潮。
卡尔维诺说:但愿有部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让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例如栖息在屋檐下的鸟儿,春天的树木或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塑料……郭宝昆的《傻姑娘和怪老树》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超越人类自我,让不会说话的老树说话。比起王鼎钧先生《那树》的客观艺术,自是另一种理解世界的不同观念与视角。
三、客观艺术与浪漫艺术的融合
通过与郭宝昆《傻姑娘和怪老树》浪漫艺术的对比,我们确立了王鼎钧《那树》客观艺术的特点。浪漫艺术给人独特的美感和理想的境界,客观艺术给人更多深层的思考和理性的批判。《那树》极为隽永深刻的洞察力使作品成为更朴实真切的生活画像,透露出人类智者更清醒有力的自省意识。作者没有让那树如松树、梅花、竹子或蜜蜂那样成为某种文化的象征符号,或着上主观色彩而成为自我人格的投射和标榜,于是以自我狭隘的眼光观看世界已经不是世界的本来样子,于是在那些松树赞、梅花赞、蜜蜂赞的散文中,我们已经不知道松树、梅花和蜜蜂的本来面目和样子,读到的只是作者自我高标的精神和自我膨胀的视角。《那树》却是极为少见难得的客观艺术。这并非说《那树》没有包含作者的精神和理想,也并非说《那树》缺少浪漫和魔幻的想象力。事实上,最好的作品都是主客体的融合,是写实与浪漫甚至魔幻色彩融为一体,无论是《那树》,还是《傻姑娘和怪老树》,作为名家名作都很自然地做到了这一点。
王鼎钧笔下的那树经久屹立,见证着大地的沧海桑田,给人以邈远的历史感;它在大自然的灾祸面前毫发未损,似是古老而茂盛的生命旗帜;它绿化大地,荫庇人类,世世代代造福于人类,最后却被人类借机伐倒。树是物质的,也是空间的;树是情绪的,也是文化的。作者在描述老树形象、讲述老树故事时融注了浓厚的主体感受,特别是写到老树最终被砍伐,隐含着作者强烈的正义感和自省意识。文中几处引用民间传说,尤为富于奇幻色彩。如为了说明老树的坚固稳定,文章引入台湾地区频发的台风事故:“有一年,台风连吹两天,附近的树全被吹断,房屋也倒坍了不少,只有那棵树屹立不摇”,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连一片树叶都没有掉下来”。老树经受住了台风的严峻考验,在人们的心目中开始有着通灵的神秘感:“当这一带还没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陆上台风紧急警报声中,总有人到树干上漩涡形的洞里插一炷香”。文章最后清道妇讲述“蚂蚁搬家”的故事,最为奇异,亦真亦幻,乃是作者借助艺术的假定性和自由的想象力,由乡村女子之口传达出老树和蚂蚁的密切关系。“老树是通灵的,它预知被伐,将自己的灾祸先告诉体内的寄生虫”,只一句话写出了老树的宽厚仁慈、有容乃大,和自然万物的唇齿相依,令自私冷酷的人类惭愧不已。“于是弱小而坚忍的民族,决定远征,一如当初它们远征而来”,并且“每一个黑斗士离巢后,先在树干上绕行一周,表示依依不舍”,这些描写居于一种思想:作者把老树、蚂蚁等世间万物视作平等的生命,与人一样有生存的权利,都是宇宙的组成部分。人类没有破坏宇宙大化循环和生生不息的权利和能力。但老树终于被毁灭并被遗忘,文章又回到残酷的现实: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日月光华,周道如砥,已无人知道有过这么一棵树,更没人知道几千条断根压在一层石子一层沥青又一层柏油下闷死。
郭宝昆的《傻姑娘和怪老树》虽然充满了浪漫色彩,却是在客观真实和深刻洞察基础上的浪漫想象。因此美丽的想象往往夹杂着写实细腻的笔触,乃至社会批判的锐利。如剧作常常在艺术的假定情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中,突然拉回现实,提到铲泥机的威胁。如第3场,“但是,这里要建房子,铲泥机来了!”突然传来的铲泥机的声音,打断了浪漫的想象与梦想,充满现实的忧患意识;第5场,当姑娘与老树合唱《望春风》,沉浸在青春的遐想,姑娘突然说:“铲泥机会不会开到这里来?会不会……你……”从梦幻中惊醒而回到现实;又如第6场姑娘讲述图书馆里穿鞋子的故事,颇具现实的讽喻意味,以人为的因循僵化反衬老树的自然浪漫,具有批判现实的力度。第9场“老树,老树”写老树虽然还在,但他的枝干全被截断,被修去了叶子,“这样,他才能跟这个地方新设计的景观,融汇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统一体”。这正是作者批判的矛头所向,人类自以为是地规整和规训一切,于是老树被削足适履,自然消失,想象折翅,生命扭曲,浪漫不再,只剩下枯燥而病态的人工斧凿痕迹。“姑娘再也不能自制了,像一个发了狂的野兽,她向着老树砍、砍、砍,要把扭曲的心爱物消灭了。”姑娘为了维护老树的自然本色,而把被修剪后的老树砍了,剧作最终以浪漫的疯狂对扭曲的现实作殊死一搏,创造出浪漫与现实交织的戏剧高潮。
对比王鼎钧的《那树》和郭宝昆的《傻姑娘和怪老树》,我们发现浪漫艺术与客观艺术的微妙差异,浪漫艺术植基于个人的感受和思想,好像海洋表面的惊涛骇浪或波光潋滟;客观艺术根入亘古不移的海洋之心,不依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波动,其所揭示的毋宁是“人之宿命”或“宇宙的法则”。
①② 王鼎钧:《一方阳光》,徐学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200页;第198页。(以下原文引用同出此书,不另注)
③④ 郭宝昆:《郭宝昆全集》(第二卷 华文戏剧1980年代),主编柯思仁、潘正镭,八方文化创作室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35-149页;第135页。(以下原文引用同出此书,不另注)
(责任编辑:庄园)
Objective Art and Romantic Art
---A Comparison between Wang Dingjuns“That Tree”and Guo Baokuns
The Silly Girl and the Odd Old Tree
Liang Yanl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aiwan writer Wang Dingjuns“That Tree”and the Singapore writer Guo Baokuns The Silly Girl and the Odd Old Tree, we can find the subtle difference between romantic art and objective art. The former, like the tempestuous or the sparkling waves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relies on the personal feelings and ideas, while the latter is rooted in the eternal heart of the ocean, unaffected by the subjective will and revealing human destiny or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
Key words: objective art, romantic art, Wang Dingjun, Guo Baok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