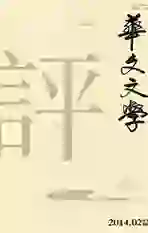寻找诗意:大马新诗史的一个侧面考察
2014-07-22黄锦树
黄锦树
摘 要:本文尝试追索马华文学的诗意,自文学史的开端以迄当代。战前,战后,马来亚建国,马来西亚成立,诗的国籍与诗意的政治,诗的可能性与诗意的自毁,反诗意,诗与歌,与民族的呐喊。这不只涉及马华新诗的处境,也涉及它的可能性。马华新诗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本文尝试沿着历史脉络做一番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马华文学;新诗;诗性,诗意,非诗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091-10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为了生存,他们牺牲了诗意。
——王安忆
我孤冷踯躅在青芜满目的田畴,
几个赤裸裸的农夫正在低头芟草,
口里不住的呻吟着苦命一条,
岂生也不辰陷他于无形监牢?!
我走遍了整年是夏的马来半岛,
随处都显露着人类坎坷。
炎炎烈日只熏蒸着有色的方趾圆颅,
漫漫世界充满了白色恐怖。①
这是南来文人冷笑(朱冷夫)发表于1928年的诗《〈萍影集〉叙诗》九节的其中两节,语言流畅,音色凄楚,生动地传达了一种飘零感。九节中以“我孤冷”开头的就占了四节,分别描述了胶工、黄包车夫、矿工、农夫的苦状,题旨清楚,甚至略显概念化。但清楚地凸显了说话人的立场、态度和心绪,适当的文言让语句显得凝炼,部分迭韵让语音有股不尽的回旋余音。在这断章中,可以看到作者具备一定的语言功力。在战前的殖民地马来半岛华文文坛,文学史开局不过十年,左翼思潮带来的对工农兵的概念化再现伴随着游子去国的孤独之感。在普遍的公共关怀之下、在日军侵华的阴影里,南来诗人接受了祖国的抗战号召,以文字调动各种可能的大众化表现形式——山歌、民谣、鼓词、弹词等,力图让诗歌发挥充分的社会功能。在那样的背景里,诗意是一种吼叫、呐喊,或者悲鸣。以及马华文学的读者都十分熟悉的:
我只是一个无名的歌者
唱着重复过千万遍的歌
(中略)
然而我是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
(中略)
然而我还记得走我的路,还在唱我底歌
我只是个独来独往的歌者
歌着,流放着,衰老着……
……疲倦,而且受伤着②
这是温任平1971年的名篇《流放是一种伤》开头和结尾的几个句子。省略的27行是说明性的。说明那些歌对歌者而言熟悉得“血液似的川行在脉管里”,说明他的曲高和寡,不随时流;说明歌词的古老且中国风,歌者的孤高与受伤。相较于冷夫诗中的“我”明显的异乡人身份,勾勒出的是左翼视域里殖民地马来半岛的世间图象,因而说话人在叙事里勾勒了四个具体的空间(四个典型的工农环境);而后者,在34行里出现了8次的我,其实并没有在叙述空间里移动,“在廉价的客栈里也唱/在热闹的街角也唱”里的空间比较像是比喻,一如个中的唱歌、流浪、受伤,其实都非常抽象,自怜的感觉充斥全诗,从第一个句子到最后一个句子。如果说前者暗袭了闻一多《死水》的格调,那后者是不是宗祧了1960年代台湾准民国遗民现代诗中的流亡诗意?
一、关于诗性
根据一般马华文学史的说法,马华新诗的历史和文学史本身一样长,精神经历也和其他文类并无不同。甚至,在理论和实作上对中国新文学的依赖也十分相似。另一方面,学者在面对马华新诗时,也往往一视同仁——并没有特别关照它的文类特殊性。我这里问的其实是个很简单也很基本的问题:从马华新诗的发展的自然状态来看,马华新诗的“诗意”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被建构的?在历史的发展中是怎么被体现的?
当然,逻辑上我们不可能默认不存在诗意的诗。或,当诗意不存在(诗意真空,或诗意处于悬置的状态)时,问题就变成了,那些——那堆文字组合为什么还可称为诗?如果它们是诗,那是否一切的文字组合都可称为诗。这一来我们又回到文学性的问题上面了。
托多洛夫和伊格顿(其他可以类推)反省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俄国形式主义者可能犯了把文学=诗(借日本人爱用的表达式)这样的错误③,也即是把西方近代(浪漫派)以来对诗的界定推衍为文学性,但那对叙事文学是不适用的。托多洛夫尤其指出,适用于叙事散文和诗歌的“文学”定义是不同的,与前者相关的一组词汇是再现、摹仿、虚构性。而“诗歌通常并不展示外部的真实性,它一般都自给自足。”④以自身为目的,故而往往需充分发挥民族语言的特性,尤其是语言的物质形式——声音。精通十数国语言的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曾指出,各民族语言里自发形成的诗,基本上都是有韵的,于中国这原也切合,但五四文学革命把这一合理性革掉了。因而即使是中国的白话新诗的现代历程,也是一面建构诗歌形式、一面寻找诗意。诚如奚密在《现代汉诗》里指出的,“现代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回答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当现代诗抛弃了格律、文言文和辞藻,它如何被认可为诗?没有古典诗歌那些长久以来经典化的语言和形式特征,现代诗人如何证明自己的作品是诗?”白话诗本身即是现代中国语言危机的产物⑤,因而不得不然的,诗人必须致力于“诗歌重新定义的建构,包括回答‘甚么是诗?、‘诗人对谁说话?和最根本的,‘为什么写诗这样的关键问题。”⑥诗人必然要遭遇尖锐的“文学身份”危机。承白话文运动而来的马华新诗,必然也分享了同样的问题境遇,这三个问题对马华诗人而言也是非常根本的,也涉及了马华文学的根本。
关于“什么是诗”,或许可以借俄国形式主义者像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的路径一探。避开诗本身界定上的多元分歧,而把重心放在诗歌功能(Poetic function),诗性(poeticity)——诗之所以为诗的必要条件:“诗性被呈现,当词被感受为词而非所称客体的简单再现或情感的抒发,当词及其组成、其意义、内在及外在形式拥有其自身的价值,甚于将之漠不关心的委托给现实。”⑦不论是诗性还是诗歌功能,强调的都是经由语言的特殊操作而达致的审美效果(如其在《语言学与诗学》中揭橥的“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⑧,如隐喻的创造)。更重要的是,诗歌功能是雅克布森提出的六种语言功能之一,在具体诗作中,语言的其他功能(表现功能、指涉功能、社交功能、意动功能、后设语言功能)同时存在,换言之,诗性既是诗作品的局部,又是决定性的要素。
那诗意呢?
那当然离不开语言的特殊运作(语言的形象性、感受性),也即需经由诗性的中介。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近代以来被引为圭臬,那和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看法是相当接近的。然而纵使把俄国形式主义者对诗的看法仅仅限定于诗,也不保险。历史相对论者(及形形色色的新主义)会质疑说,每个时代不同的社会集团对诗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往往认为那不过是资产阶级情调,是压迫阶级的品味、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⑨。
关于诗意,《汉语大辞典》提出四种说法,其中的三种说法与本文的论题比较直接相关。一、诗思、诗情。二、诗的内容与意境。三、作诗的方法(用某某诗意)。关于第二点,《辞典》引何其芳《〈工人歌谣选〉序》:“(诗意)是从社会生活和自然界提供出来的、经过创作者的感动而又能够激动人的,一种新鲜、优美的文学艺术的内容要素。”⑩何其芳没说出来的是,“那新鲜、优美的文学艺术的内容要素”必须藉由文学形式与修辞技艺方能被传达。总而言之,诗意包含了诗思、诗的内容及诗的效果(读者接受)三个方面。这样的解说当然并不周全,“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的美感和意境”这样的表述其实预设了对诗的某种认知,因而也涉及了风格化的问题。如果用中国传统的诗学修辞来表述,可以说,诗意涉及了“体”——各种风格类型——大致唐宋诗之分、题材风格(边塞诗、田园诗、宫体诗),小至个人风格(李杜体、李商隐体、东坡体)。依学者分析,以《文心雕龙》为例,传统中国的文体论其实同时规范了理想的风格类型、审美效果、风格要素、形式规范{11}。换言之,“诗意”问题其实和文学体裁问题类似,极少是真正的原创,如俄国形式主义者及托多洛夫所言{12},那总是前有所承,因为写作者毕竟首先是读者,总是得生活在文学传统里,诗意的审美感受力的陶养、形式技巧的习得,都一定程度地来自文学传统。当然,具体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经验和情感上的刺激。总而言之,诗意并不是虚无飘渺的,它其实离不开模仿。差别或许仅仅在于,古今中西,模仿的对象改变了。
即使拥有丰厚古典诗学传承的中国也必须面对革命文学狂暴的挑战。而马华文学,很长一段时间,是新中国革命文学的海外子嗣。甚至可以说,马华文学的历程一直在模仿中国现代文学——这当然源于中国文学的致命影响力——尤其是革命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从方修、杨松年到谢诗坚,都已有明确的论证。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甚至连文学史的结构也(或许是无意识的)模仿现代中国文学。
这么说的理由在于,中国新文学和马华文学同样作为华人的现代性事件,虽有些微的时差,但基本上可说是同时的。除了境外—殖民地(及尔后的他语的民族国家)这地域差异之外,一些根本问题都重复了中国现代文学,如前面提到的那三个问题(什么是文学?对谁说话?为什么写作?),革命文学本身都提供了解答,文艺是启蒙、反殖、抗战的武器,对人民大众说话,为公众而写。延伸出来的问题,诸如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地方形式与口语问题、文学的在地化、民族形式问题等,从《大系》理论卷收录的文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表面上看来这些论题是从中国文学场域搬来的,但其实很多问题是共享的,大至亡国,小至文学自身民族属性的确立(民族形式到了南洋被转化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写作的意义,白话文学于焉是危机时代的表述;它震颤于一种生死存亡的迫切性。那也是马华新诗的诗意的问题情境。至少在马来西亚建国前,因彼时的马华文学尚未有国籍,华人其实多为中华民国籍。而一九五七后的马华现代主义,仍是由晚期“南来文人”所催生者{13}。革命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比或对抗,是不是重演了中国现代诗史中的结构对立呢?
郭志刚、李岫主编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1930~1939》由周同道撰写的第四章《三十年代的诗歌》以“火的呐喊”与“梦的呢喃”这组对比来概括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两种对立的诗歌路径:
以殷夫为代表的左联诗歌、以穆木天、蒲凤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的大众化诗歌及国防诗歌和臧克家、艾青、田间的左翼诗歌构成了现实主义诗歌主潮,劳苦大众和民族悲欢是他们不变的主题。华丽的辞藻、缠绵的软语和卿卿我我不属于这世界,在民族受难之际,他们用诗歌发出火的呐喊;以戴望舒、施蛰存为代表《现代》杂志诗歌和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诗歌构筑中国诗歌发生以来的一个高峰,田园乡愁、都市的风景与疾病和个体命运、个人情怀乃至潜意识的关注统摄了他们的诗歌主题,水旱灾害、异族入侵、军阀争霸都在视线之外,他们精心推敲诗艺,汇整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诗歌宛如梦的呢喃。(117)
因而我们大致可以粗略地概括出两大类型的诗与诗意(既然我们预设了凡诗必有诗意,也知道诗意涉及模仿):革命文学的、现代主义的诗意(前引文把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意也包括进来);细看的话,涉及中文世界(现代中国、台湾、香港)各名家的“体”,从战前到“后现代”。
作为边缘性的小文学体制,犹如脆弱而开放的小经济体,“外来影响”一如季风,总是从特定的方向、周期性地扑来,带来生机,也带来寒意。
二、呐喊与呢喃:殖民地苦难中的诗意
马华新诗的历史如果从1920年算起,已超过九十年;即使从一九五七年起算,也有五十多年。因此这篇论文面对的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遍读那数千百本诗集(也难以遍寻),比较可行(但也可说是比较取巧的)做法,是借重既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涵盖度比较大、较具代表性的选集。如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诗集》(1971)、周粲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诗》(1978)、杨松年主编《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1919~1965)》(2003)、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新诗史读本1957~2007》(2010)。
方修编收的诗是1919~1941的,周粲编选的收诗是1945~1965的,而杨松年主编那本时间上包含了前二者(1919~1965),编选时间也晚得多(差了近三十年),多了时间的沉淀,也可说是对那时段的诗做更为精选的制作。对以上三个选本做了大略的比较后,就本论文的意图来说,杨的选本完全可以取代方、周的选本。理由如下:两部《大系》所选共四百五首左右,但那四十多年间有代表性的马华新诗其实没那么多。一般而言,当时间拉长、标准稍严之后,很多因特定的时代因素而选的作品,会被时代淘汰。杨松年在《前言》里说这部选本“所选取的诗篇,战前部分共118首……战后部分共102首。整部选集选取的诗篇共220首。”(17)大致是方、周选本的半数,虽然从较长的文学史段落来看,值得一选的诗也没那么多。如果以杨选中是否有评析来做切分,有评析的远少于没评析的,相关篇数是战前38:118;战后34:68。有评析的应是更为精选者,总数加起来不过72首,作为那时段的专门选本,可说已是颇为审慎了。“从选集看历史”本身直接界定了那四十多年的诗的特性——诗为时代、向时代而作。这部集合了黄孟文、欧清池、林顺福、郭惠芬、方桂香老中青三代的战前马华文学专家,均为编委,参与选诗评析。虽然文学史分期、文学史主题藉用的是杨松年的架构,选诗的态度较持平,也较少革命文学的偏见,品味也比较好,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读者的文学史视野。
讨论1919~1965马华新诗的诗意,除了前述三个选本,原甸的《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也是重要的参考。
战前马华新诗,以方修的选本为例,大部分诗作当然都是“火的呐喊”,充斥着口号与宣谕,劳苦工人、失业的工人、哀吟的女工、哀叹的人力车夫,概念化、语乏修饰,直白浅露,很难说有什么“诗味”。但那符合编选者偏嗜的口味,方修《导言》里评为“韵味深永”的那些励志性的诗句,在受过当代现代诗洗礼的读者读起来,只怕不免味同嚼蜡。而《导言》中不断强调某某诗人诗作比诸某某诗人诗作“高了一级”、“又更高一级”,着眼的是“思想内容”是否高明,态度是否“积极进取”。字里行间也有提到某些诗作的中国影响(郭沫若、唯美主义),但原甸的表述更清楚。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也如中国1930年代一般同时存在着呐喊与呢喃,“每当社会处在沈闷的时期,这一类创作(按:泛指现代派)的风气便氤氲而起了。这个时期的马华诗坛,便出现了一些如朱自清所说的,‘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的新诗作品,散布在报刊上。”(原甸24)虽然诗作也许不怎样,但可以看出我前面谈到的“文学史的结构性模仿”。郭惠芬《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也有专节处理到受现代派影响的诗风(286~294),甚至格律诗与具实验色彩的图象诗(第九、十章)。更别说吼社的诗歌大众化精神及实践,直接模仿了中国诗歌会,东方丙丁也一如蒲凤,朗诵诗也登场了。这种呐喊的诗意形式一直延续到民族国家成立多年以后(譬如吴岸,譬如“动地吟”)。总而言之,殖民地时代马华诗歌比现代诗运动以来窄化的文学史的图景复杂得多。
在战前留下的最好的诗篇/诗句里——尤其是格律诗与象征诗派意味的,可以看出那些南来文人可能具有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有比较丰富的词汇;经营的诗意也常可以让人唤起古典诗意,毕竟大部分诗歌母题都有着极其长远的历史(彼时人的经验结构还没有因历经现代而有着根本的变化)。而本文一开始引的《〈萍影集〉叙诗》那样较精炼的语言(纵使并非全篇皆佳)并非孤例。那可说比同时期的小说语言好得多了,较具语言的自觉。从《从选集看历史》来看,诸如衣虹(潘受)的《花尸》(1929),詹熹的《南行夜月》;又如署名冰的《破琴》(1931),一首不俗的“咏物诗”:
寂寞衰颓的古木榻上,
静睡着日久被弃的破琴一张;
脆弱的铜弦早已寸寸零断,
劫后的残躯尽委给泥尘裹封。
年岁带走了他青春的颜容,
暗里空自氤氲着金色的古梦;
悲哀的黑影织成了惨淡绞绡,
再没有丽人偎依着他的身旁。
再没有丽人偎依着他的身旁,
再没有玉指在他胸前弹弄,
檐前不见那谛听着梅花雀,
沉沉幽室何处找那妙响琤琮?
何处去找那妙响琤琮?
窗棂外只喟息着阴峭的寒风
在这月明星朗的夜里——
他更披上了雪般苍白的死裳。
寂寞衰颓的古木榻上,
静眠日久被弃破琴一张;
寂寞衰颓的我心之上,
又来了一箭无名沉重的创伤。{14}
这首不见于方选的诗,介于原甸分期“新兴诗歌运动”与“沈郁的低唱”之间,看不到什么“南洋色彩”,或可归入“沈郁的低唱”。但它成功地营造出一个自足的诗的世界,方之于同时中国的格律诗,其实毫不逊色。如果从古琴作为传统文人高洁精神的象征来看,全诗可说是悲吟一种文化精神的坏毁失落,虽然诗作没有给出“社会原因”,但那也不是诗该做的事。整齐的诗句,古典的氛围,一定程度的押韵,围绕古木榻与破琴,不断地增补着色,自伤自怜,劫后弦断、泥尘裹封、年华老去,徒留残梦,文字功力颇佳:“梦”有时间性(“古梦”),有明亮的颜色(“金色”),却如雾气迷茫(“氤氲着”)而以暗为背景(“暗里空自氤氲着金色的古梦”);而“悲哀的黑影”却又具象化为物:缠绕的薄纱(“绞绡”)而它被着于情绪性的形容词(“惨淡”)。第三节出现了不再有的琴声(“妙响琤琮”),复现于第四节,温度下降(“阴峭的寒风”)、星月俱现(“月明星朗”),顺理成章地带出死亡的意象:“披上了雪般苍白的死裳”。一个“弃的故事”。如果拿来和温任平的《无弦琴》相较,还是可以看到明显的高下:“沾满灰尘的陈旧 无弦琴/有一阕无声的哀曲/破碎的回忆,姑娘的圆脸哟/谁不沈湎/听!远处‘归来吧又再唱起/多么深沈的喟息、抑郁/呵,我的歌哀感和愁伤/我的心是那无弦琴”{15}。简单的比喻,简单的抒情。
即使是呐喊,有时不乏语言上的经营。如衣虹的《三等舱客》(1930)在以具体的细节控诉三等舱客的悲惨境遇的同时,也以格律、明喻维系着起码的诗意。又如江风控诉日军侵略的《古城》(1939)语意悲愤激昂,但从首节和末节来看,仍相当程度地以诗语来维护诗意:
一颗落寞的心悬在古城头,
秋空迷蒙依旧飞着肃杀,
蔓草在坟塜上凄惶颤抖,
修长的天道没有雁影,
旧日的回忆是一个梦。
(中略)
匍伏在混沌时日里的人群,
手指着墙上写着复仇的字样,
祈祷着一串带笑的日子,
人群要撕下老妓样的旗帜,
包裹着敌人带血的头!{16}
阶梯形式的文字排列,语言时见泼辣(“膏药旗像老妓样飞上城空”),较好地平衡了时代的需求与诗意。再如星岛吼社骨干之一的刘思的《代募寒衣》(1940)诗旨为北方中国抗战中的战士募寒衣,而诗的最后两节诗意分明:
借一天云/裁无数的棉衣/在不易被发觉的地方绣上最温柔的相思字
寄去/在远方/此时/等着的正是暖意呢{17}
虽然在革命文学的阳刚语境里,“借一天云”这样的句子毋宁是过于文艺腔的,然而“在不易被发觉的地方”却彷佛是一种诗的自觉,一种自我指涉,也合理化了“一个伟大的世纪降临的启示”里这样轻柔的诗意。刘思的《别宫扉》(1940)也是篇商籁体佳作:
你我的命运都像飘蓬
一小时里担心几回风
耐不住这漠漠的黄沙
希望又向别一方开花
但赤道上何处有春天
美梦从来好欺负少年
你看悠悠的新加坡河
可不是一曲离人哀歌
我如野马飞过万重山
剩下只影独对着荒寒
不知前面还有几多程
只觉一程比一程陌生
为了忘却来日的悲哀
你要喝尽这最后一杯{18}
全诗以速度取胜,运用古诗常用以比喻离乡漂泊的用语“飘蓬”(飘飞的蓬草)来喻说话人的无定感,全诗扣紧与飞有关的意象,藉由速度快速运转,漂泊的仿徨一转而为送别的欢快。这些诗,都一定程度地延续了古典诗的情调。但也有法国象征派大家韩波《骰子一掷》式的试验:
以字体的大小、粗黑来强调重点。虽然大致可以看出批判现实的意图,但留下的空白也不少。关于相关的诗意,郭惠芬的解释是,《钞票》一诗“向我们暗示,‘钞票是金钱物质的等价物,但也是万恶的陷阱(即‘暗坑),其中包含着男女老少的血泪。”{19}从“暗坑”和“泪”与标题的“钞票”一样大可以猜想它大概是对金钱的批判,但其中的“瘟”、“脑”、“红”、“白发”及相关的特殊符号,都是难以译解的,它们构成了图象存在的自身目的,体现了强烈的现代感。譬如说整首诗都是孤立的单词,没有一个句子;字与字间以标点符号联结,上下文关系尤其含混不清。另一首《葬歌》有的字如“今天今天”与“力”竟比标题还大,有句子可是上下文关系并不清楚。郭惠芬说它的主题是“死亡是一个亲爱的‘力,它在‘黑暗中埋葬了死者破碎的‘梦,让他在春尚未到人间的时候,可以轻松的安‘睡。”(同前)如果说前面四个句子的主词是死者,他背着破碎的梦,被象征死亡的黑紧紧地追着,他也是在地层里睡、被祈祷安息的主体,根据上下文,那他岂不也是那“亲爱的力”?而那黑和梦何以“今天今天”还没有到来?这一节的“还没有到来”等同于“春尚未到人间”的“未到”,还是是两回事?“一个黑”的“黑”是形容词,用量词“一个”来联结本来就很突兀;而最后的“亲爱的力”的“力”一样非常抽象,是权力、气力、力量还是人名?主题似乎是社会批判,但形式上是绝对现代的。因此如果是郭惠芬讲的老生常谈,就毫无“诗意”可言了。
三、民族—非国家文学的(反)诗意
比较奇怪的是,不论是《从选集看历史》还是周粲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诗》,1945~1965的二十年间,从“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到“本地意识继续腾涨时期”有意思的诗作非常少,语言直白,诗意寡淡。周粲虽然在《导论》里说“以抒情诗为主”,但小诗多平淡,只有威北华的《石狮子》较具诗意。而比较明亮的声音是艾青式的,如杜红《我不能离开你,我的母亲土地》、原甸《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槐华《你死在熟悉的乡土上》、《水塔放歌》、李贩鱼《我永远站立在祖国的土地上》等(多首曾被选进独中华文课本)。这些后来多被归入新加坡文学版图的作者,前引诸颂歌式的放歌,在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也许便是吴岸了。吴岸的代表作诸如《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南中国海》、《独中颂》等,都是直白的颂歌,诗旨显辖,彷佛每个短句后的空白都预设了朗诵的舞台现场。
至于钟怡雯、陈大为编的《读本》,标明选的是1957~2007的诗,显然更自觉地意识到文学史的民族国家身份。它和周、杨选本重迭的时间只有九年(1957~1965),有趣的是,代表那九年,甚至新马共有文学史的诗人只有一位,也就是吴岸(这值得探究)。吴岸之后,就是被温任平誉为马华第一首现代诗《麻河静立》的作者白垚了。如此的安排,强烈地凸显了编选者的现代(及其小老弟“后现代”)立场。就文学史的立场来看,那当然是很不公平的,虽然以1957为起点有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却不符文学史的正义。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1950年代末马华现代主义肇端,诗意历经一番重大变革。兼之两个民族国家先后建立,“马华文学”也被分割。旅台现代主义肇始。较具代表性的诗选也许是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二十七位年轻的作者,最老的杨际光其时四十七岁,最年轻的温瑞安十九岁,所收诗作有相当明显可辨识的现代感。包含了旅台与在地,但排除了分割的新加坡。这可能是马华诗选里最具“诗性”的自我意识的。以新批评为理论后盾,意识到诗歌语言的诗性,藉用温任平在《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中的话:
“一是体制的从自冑到自由伸展。诗节的行数变得不规则,……二是技巧运用之趋于多样化,除了惯用的明喻、暗喻、对比等手法外,更用了象征、并置法、时空交揉、物象转位表象方法”及借鉴电影、绘画、音乐的手法。“三是语言文字方面的推敲经营,……力求曲折深薀有歧义。……企图把经验中相斥的份子冶于一炉。”{20}
而力图让诗达到自身的自足性,一个自足的、语言的小小世界。我想方娥真这首小诗《窗》相当具有概括性,可以作为马华现代诗的一则寓言:
世界上的窗
都在夜里对着灯光发呆
它们同时有着一个古老的记忆
从很久以前起
所有的行人都是陌生客
寒着脸寻找自己的庇护
当你走过长街
当我走过长街
美丽的帘影背后
是甚么{21}
全诗只有十行,几个基本的意象:窗、灯光、行人、长街、帘影。诗分两个部分,开始的六行是专断的预设:窗与灯光是温暖的守候,许诺给陌生人庇护——那无疑是诗意给现代诗人诗的许诺,经过帘影(诗语与相关的诗的手法)的过滤,灯光被转换成一个非疑问的疑问:“是甚么”。是灯火,是守夜人,是美的幸福的许诺,是诗。一个自足的、自我指涉的世界。
现实的艰难,或者被直接转化成一种重新被召唤回来的古典诗意,也即是我称之为中国性—现代主义的天狼星诗社的新古典主义。诚如张景云的提问:“它所代表的中国性写作如何趋近现代性?中国性写作的诗歌语言与诗歌美学精神之间的现代性张力如何化解?”{22}其实古典诗意是马华新诗的“诗意的无意识”之一(藉用互文性理论的“文学的记忆”的讲法),它在汉语的根部,战前诗人曾经调动过,“麻河静立”的白垚也深爱(如写于1960年代的《灵感》的“邀得了一天星斗,一山云梦”;《红尘》全诗及《南斜》的“老来病矣/问还能狂胜那三杯否?/犹记当年醉态/击鼓看剑拍遍栏杆”{23},后者直接化用稼轩词)。在较好的情况下,是像余光中及杨牧那样,转化、延伸古典诗意,或承袭古人的实验精神——如余光中把韩愈李贺李商隐等读成古代的现代诗人——那其实吻合保罗德曼《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的讲法:任何创造性的古人在他的时代都是最具现代感的,是彼时的现代性的代表{24}。当然,现代性的精神之一是与传统决裂。吊诡的是,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传统总是被选择的传统:被选择来决裂与继承的不是同一个传统(譬如:胡适建构新诗的现代性召唤的是古代的白话诗“传统”)。但天狼星的召魂毕竟还是遁入一种古典中国的拜物教,从唐诗宋词到江湖、武侠,自恋自伤;终至在香烟缭绕的仿古的神龛里把自己神格化为一尊“精致的鼎”,现代感也就“云深不知处”了。但那样的诗情不乏继承者(如林幸谦,加上情色的向度),在它的更新版里,诗语努力挖掘想象的心灵伤口,以创造诗意。
然而在那样的诗意里,确实看不到新生的民族国家马来西亚在不久前{25}方动了大手术,割除了新加坡那颗毒瘤;看不到这民族国家急遽的马来化、华文教育水深火热——更别说几年前的种族冲突——那“此时此地的现实”,因现代诗不屑应时,应时总嫌伤诗质。那是现实主义者们的主题了,虽然彼辈的诗总是诗味寡淡得难以确认是否为诗。
在诗意的精神史里,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当现代主义已快速地老化为一匹“疲乏的马”,当诗意被困于过剩的自我意识;同样衰疲的老现实主义因现实的急迫在文学新人手上获得自我更新,马哈迪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们(方昂,游川,小曼,傅承得,陈强华等)登场了。有留台背景的或者承继彼时台湾诗坛主流的音色(杨泽、夏宇、罗智成),或者藉用本学科的传统抒情腔调;在地的从大白话出发,而诗的自我指涉成了反讽,如方昂的《歌手与诗人》(1988):
有许多歌歌手不能唱
唱了成噤声不出的禁歌
有许多诗诗人不能写
写了成噤声不出的禁诗
歌手与诗人是浅池里青蛙
吞吐着单调的咯咯咯与呱呱呱{26}
依诗中的论证,现实存在的急迫迫使诗如果要存在必须自我牺牲,犹如《鸟权——和游川》所言:“听不听非关你的义务/唱不唱却是鸟的权利/被锁了起来还是要唱/唱你爱或不爱听的歌”{27},用的是被现代派唾弃的豆腐干体,且题旨显露,语无藏锋,如果根据前引《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里对诗的规范要求(“力求曲折深薀有歧义”)来看,这简直是“非诗”{28}。他所和的游川的诗《养鸟记》(1989)四句更其白话,“养了一只鸟都不唱歌/真是叫人扫兴的事/放了牠嘛又怕牠/海阔天空唱了起来 这只鸟,真鸟!”很难说有甚么诗意,甚至单从诗本身也看不出题旨是甚么,诗的附记却有详细的叙述:“柯嘉逊博士在甘文丁拘留营不肯唱营歌。出来之后却抱着吉他到处大唱特唱其民权歌,真鸟!”{29}相较之下,《养鸟记》那几行字反而像是不过在发挥“交际功能”,而游川的诗大类如此{30}。存在是沉重的,而诗是粗鄙的。陈强华和方昂的诗《读〈鸟权〉直喊他妈的——致鸟诗人方昂》(1990)一样直白无余味{31},但正是这喧哗的鸟叫与蛙鸣,“单调的咯咯咯与呱呱呱”诗意的自我坎陷,为了呐喊——比战前殖民地马华文坛更为严重地牺牲了诗意。在那诗意悲凉的马哈迪时代,存在的危机被以诗为名的一种赤裸裸写作,转化为诗自身的危机,于是转而为歌(一如抗战的年代),藉由表演——舞台、空间、现场、声音、公众的激情来拯救诗意——把它转而为现场的、声音的诗意{32}。而文字本身,却往往惨白如诗的骸骨。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战”了。对民族国家而言,毋宁是非常反讽的。
反诗意的诗意
然而,正是这时候,后现代诗风潮从美国经台湾转口,直接影响了更年轻世代的诗人。这方面相当有代表性的诗集也许是《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但也许本文不必再征引诗句了。学养很好的老诗人张景云先生为它写了篇相当有意思、水平很高的序,在马华文坛简直是空谷足音。但竟也没征引任何诗行。
他谈到集子里有些复调式的写作,有些他自己偏爱的“非/反诗意写作”,尤其关于后者,解说颇为耐人寻味:
前者作为一种技法可用于任何诗歌美学意图,而后者本身就是一种诗歌美学意图。非/反诗意写作是永远在边缘地带的(不是安于,而是主动)追求自我边缘化的诗美学态度,它不局限于任何流派或时代,因此即使是在革命再革命的现代主义及其颠覆者后现代主义里,也有它们本身的诗意写作主流,通过规范化写作形成一种习套,对非/反诗意写作倾轨挤迫。{33}
这是很精彩的提醒。涉及的已不只是诗意,而毋宁是诗性(poeticity)——诗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本身。它为本文一开始引述的雅克布森的界定补充了政治—历史条件:单是语言的自足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诗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
我的理解是:作为边缘的小文学系统,马华新诗太容易受到其他中文系统(或其他系统)的影响,很容易变成附庸。而诗的诗意本身,就是那风格化的陷阱。以反叛起家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到后来都不免如此,因为它们都对诗意有所预设{34}。因此,马华新诗的现代性或许不在于诗意的自觉,而是反诗意(或反—反诗意)的自觉,对特定模子的反叛。马华新诗的边缘性,也即是它自身成立的条件,它的诗意,必须是(反)反诗意,或非诗意。但那并非对诗意的否定,让语言赤身裸体、私处暴露,而毋宁是发挥诗意自身的否定性——否定性的诗性,经由对诗自身的哲思、对现实的介入、反思历史{35},以找到马华新诗自身的边缘位置。
在这前提下,我们可以把李有成的《槟城》(1971)读为诗性与诗意的微妙互动:
是谁?用错愕的眼睛瞪我
是谁?咬着唇忍着泪
在我的记忆中狠狠的拧上一把
昨天我走过的
今天我又来了
昨天和今天
是谁?为了我,跟他们争辩
昨天的我,今天的我
每一条街,都要伸出头来
每一支灯,都要睁大了眼睛
每一块熟悉,都要拔去新长的陌生
我于是默默地向前走
当你美丽但痛苦地爱我
我除了往后望
再也不能回头走
只因你对我,竟是一条
单行道,就在那儿
流泪地叫我:故人!故人!{36}
诗意深爱着诗性,但后者不能不和它保持距离,因为它毕竟是条单行道,即使那诸多“美丽的帘影”很诱人;纵然用情很深,告别很令人感伤。
① 方修,第39-40页;杨松年,第44-45页。
② 《马华新诗史读本》,第94-95页。
③ 伊格顿(Terry Eagleton),“像形式主义者一样看待文学实际上是把一切文学都看做是诗。”《当代文学理论》,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④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文学的概念》,《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⑤ 我过去尝试从系统的角度做了些讨论,详见《文之余·论现代文学系统中之现代散文,其历史类型及与外围文类之互动,及相应的诗语言问题》,刊于《中外文学》32卷7期2003年12月,第48-64页。
⑥ 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页;第25页。
⑦⑧ Roman Jakobson,“What Is Poetry?”Language In Literatur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378,p.71.
⑨ 对当代中国新诗有深远影响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是一例。
⑩ 《汉语大辞典》卷十一,第531页。
{11} 颜昆阳:《论〈文心雕龙〉辩证的文体观念》。
{12} 前者见托马舍夫斯基,《主题》收于方珊编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1986);后者见《体裁的由来》,收于《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
{13} 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第52-57页。
{14}{16} 《从选集看历史》,第113页;第151页。
{15} 《无弦琴》,第33页。
{17} 《从选集看历史》,第169页;方修,第186页。
{18} 《大系》,第185页。
{19} 《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第406页。
{20} 《愤怒的回顾》,第68-69页。一个较简略的解说的版本,详见谢川成《如何欣赏现代诗》,《蕉风》第339期,1981/6,第75-86页。
{21} 《大马诗选》,第35页。
{22} 《语言的逃亡》,《有本诗集》,第2页。
{23} 《缕云起于绿草》,第234-236页。
{24}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第165-189页。
{25} 诗集所收的多为1971年前几年内的作品,新加坡1965年独立,1969年发生“513事件”。
{26}{27} 方昂的“时事诗册”,《鸟权》,第83页;第82页。
{28} 1970年代马华文坛确曾发生过一场水平非常低的“是诗·非诗”的论证。因水平太低,恕不讨论。文献见陈雪风编《是诗?非诗》。
{29} 游川:《血是一切真相》,第42页。
{30} 早在1978年,时任《蕉风》编辑的张瑞星(张锦忠)就质疑过游川(时笔名子凡)那样的诗歌写作的诗意问题。《蕉风》没看出质疑的信,倒是刊出了子凡的答复。他自我辩护是在走一条“有人间性、有人情味,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诗”,强调“写平朴的诗是要有勇气的,你要舍得放弃那些华丽的语言、缤纷的意象、迂回的隐喻……而驱使生涩、散漫但朴素亲切的口语,使它们发生关联和火花,以表现平凡事物的高贵情操。这下子,就像高空飞索,只要一个不留神,就会跌入‘非诗的深渊。”(5)讲得很好,“舍得放弃”四字尤其有意味。可见他并非没有自觉。但那种拿捏本身就是困难的,更何况有时在冲动之下或许就会忘了拿捏。
{31} 陈强华:《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第119-120页。这本集中这样的诗不少,但也有比较“富诗味”的。这是平衡的问题了。
{32} 关于“动地吟”,详参田思,《“动地吟”与马华诗歌朗唱运动》,www.hornbill.cdc.net.my/data/henaiz01.htm
{33} 《语言的逃亡》,第4页。
{34} 本文初稿完成后,读到香港评论家叶辉的《城市:诗意和反诗意》,文中是这么界定诗意与反诗意的:“‘诗意指传统意义上的意境元素,‘反诗意是指有别于传统诗意、构成诗的新感性、新美学据点的另一种可能的因素”,《书写浮城》,第162页。不知道张景云的论述和它有没有观念上的血缘关系,不过叶的论述是比较简单的二元模式。
{35} 序文亦重申老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给诗人的老告诫,“诗人必须平衡存在意识与历史内容”,并对抗语言被政治谎言挪用,关心政治、捍卫语言的纯粹性。
{36} 《蕉风》第217期,第64-65页。
参考文献:
Roman Jakobson,“What Is Poetry?”Language In Literatur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368-378.
Roman Jakobson,“Linguistic and Poetics,”Language In Literature, pp.62-94.
子凡:《“非诗”的深渊》,《蕉风》302,1978/4:5。
方昂:《鸟权》,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0年版。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诗集》,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71年版。
白垚:《缕云起于绿草》,PJ:大梦书房2007年版。
伊格顿(Terry Eagleton):《当代文学理论》,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版。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文学的概念》,《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李有成:《槟城》,《蕉风》217,1971/1:64-65。
周粲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诗》,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89页。
原甸:《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香港:三联书店/新加波:文学书屋1987年版。
奚密:《现代汉诗十四行探微》,《现当代诗文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孙玉石编选:《象征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张景云:《语言的逃亡》,《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吉隆波:有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张德厚主编:《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年版。
众人:《有本诗集:22诗人自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3年版。
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郭志刚、李岫主编:《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1930~193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郭惠芬:《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陈强华:《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加影:彩虹出版社1998年版。
陈雪风编:《是诗?非诗》,吉隆坡:野草出版社1976年版。
游川:《血是一切真相》,吉隆坡:千秋事业社1993年版。
杨松年主编:《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1919~1965)》,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年版。
温任平:《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温任平主编《愤怒的回顾》,天狼星诗社1980年版,第63-86页。
温任平:《无弦琴》,霹雳:骆驼出版社1970年版。
温任平主编:《大马诗选》,天狼星诗社1974年版。
叶辉:《书写浮城》,香港:青文书屋2001年版。
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2009年版。
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新诗史读本1957~2007》,台北:万卷楼2010年版。
颜昆阳:《论〈文心雕龙〉辩证的文体观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编《文心雕龙综论》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73-124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In Search of Poeticality: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 New Poetry
[Taiwan]Huang Jinshu
(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Taiwa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ndeavors to trace the poeticality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oday, including the nationality of poetry, the politics of poeticality, the possibility of poetry, the self-destruction of poeticality, anti-poeticality, poetry, song, and peoples cry.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osi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new poetry, and what is more, it investi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new poetry through tracing its historical contexts.
Key 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poetry, poetic quality, poeticality, non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