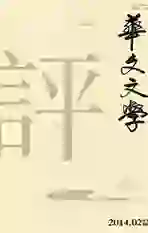历史困境里的现实突围
2014-07-22周之涵
周之涵
摘 要:“钓运”不仅是民间自发的社会运动,也是历史给予文学的一次契机,促使文学反映并反思现实。以刘大任的文学叙事为例,他参照“钓运”描绘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红色经验,反思“钓运”与文革中扭曲变相的历史,并重估了“钓运”的历史价值。通过文学的描绘、反思与重估,刘大任探索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困境里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轨迹。
关键词:“钓运”;刘大任;文学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085-06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日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私相授受,这一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引起了港澳台及全球华人社会的强烈不满。台湾当局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依赖美日,采取消极容忍,息事宁人的态度。然而,相对于官方的无所作为,由一群海外旅美华人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保卫钓鱼台”民间运动(简称“钓运”)却得以迅速展开,形成激荡之势,影响深远。
然而,与历史上其他所有社会运动一样,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经由酝酿发动,达到高潮顶峰,然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颓息落。拨开历史迷雾,以今人眼光来检视那段春雷声声的岁月,这种社会人事嬗变的自然定律,并不能成为我们抹灭其历史价值,阻隔探寻其时代意义的理由借口。因为就其当时意义而言,它击碎了日本吞并钓鱼岛,使其成为囊中之物的美梦。另外,它还促使人们从政治上附美,经济上依日的“台湾式”民主繁荣的神话中苏醒过来。时过境迁,“钓运”距今已近半世纪之久,社会历史结构已发生巨大改变。世易时移,当结构改变,“钓运”所压抑的历史解释空间不断扩大,这就有了“第二个五四运动”的历史命名,①也形成了“海外华人文化思想运动”的思想史定位②。而这些阐释除了由运动本身的社会学释义引起以外,当然还包括那些终其一生受“钓运”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投入,刘大任的文学叙事即是其中之一。
一、书写知识分子的左翼台湾经验
“钓运”影响下的刘大任文学叙事,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对左翼台湾经验的记忆和捕捉。光复初期,作为台湾文学史上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左翼文学曾在台湾社会扮演着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的角色,出现了杨逵、吕赫若等左翼作家及《送报夫》、《冬夜》等反映社会问题和时代症结的作品。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威权体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台湾左翼并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得到充分发展。但压制威胁的结果不必然是屈服,左翼运动和思潮始终作为一股潜流,影响着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刘大任个人经历就是很好的明证。早在中学时代,他就阅读了屠格涅夫反映俄国知识分子革命前夕心理状态的小说《前夜》,并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期间广泛接触马列经典理论著作,阅读鲁迅、矛盾、巴金等左翼文学作品。1964到1966年,他又与陈映真同时参加了邱刚健创办主持的《剧场》杂志。与陈映真一样,他毫无保留地批判《剧场》脱离台湾现实的倾向。另外,他还受邀参加陈映真、李作成、邱延亮、陈述孔、吴耀忠组织的地下读书会“扩大”会议。可以发现开始崭露头角的刘大任,在这个时期基本保持与陈映真一致的步调。此后他自陈:“与陈映真转折期的文学思想不谋而合。在《剧场》不定期而颇为频繁的聚会中,两人因意见相近,仿佛结了盟。”③
这些左翼经历成为日后他创作长篇小说《浮游群落》的生活素材。《浮游群落》创作于1970年代中后期,小说围绕两份同人刊物《布谷》和《新潮》杂志的数次论争,以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为主线,串联起台湾196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表达在台湾社会异常严酷的思想氛围中,风起云涌的文化思潮对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内心所造成的冲击。小说虽然是对1960年代台湾社会的观察,但从小说人物刻画、情节设计、主旨意蕴来看,明显有一个“钓运”的视角作参照。因为时间上,这篇小说创作于1976至1978年,是刘大任从“钓运”抽身后,前往非洲任职期间的产物。此时,大规模的“钓运”已经基本结束,他“从一个政治的血性参与者,变为一个冷眼的观察者。”④联系他在青年时代的左翼经验以及留美参加“钓运”,“冷眼”所观很大程度上是左翼社会实践的成败得失。对此,小说有详细交代。
《浮游群落》要探索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史困境里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轨迹。小说概括了三类知识分子:第一类是受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以《新潮》杂志柯因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横的移植”,认为永远存在一个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什么内容的问题,强调现代主义理论是诠释台湾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只有放眼世界,向外汲取思想资源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途径;第二类是将知识视为商业盈利工具的知识分子,这是台湾1960年代新兴社会势力,他们具有商业头脑,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罗云星是其代表人物;第三类是坚持“阶级”、“反抗”、“人道主义”立场的左翼知识分子,主要以林盛隆及《布谷》杂志负责人胡浩、吕聪明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左翼现实主义思想观察台湾社会,思考文艺的立足点与台湾现实之间的关系。小说在谋篇布局上,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状态,无疑是作者言说和关注的重点,表现有三:
第一是两份同人杂志《布谷》与《新潮》的三次思想交锋。第一次交锋是由林盛隆发表在《布谷》的一篇论文引发,以现代主义为旨归的《新潮》主将柯因批判林盛隆“用三十年代的solution来解决六十年代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时代错误,不可原谅。”⑤认为现实主义文学观刻意强调“现实”和“道德”,与反共八股、军中文艺同流合污,这对于突破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钳制来说,无异于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面对指责,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杂志——《布谷》的代言人胡浩则指出,现代主义在台湾难以形成气候的根源在于它沉迷于形式、技巧,而不去探讨文艺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不思考民族绵延的历史,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第二次思想交锋聚焦于“为什么而创作”的问题。《新潮》主将柯因担心一旦回到“为什么而创作”的思路上,便有可能被官方文艺政策中“为民族立场而写作”、“用现实的形式”等口号收编。林盛隆则认为,现代主义的反理性源于西方文明的衰微,如果台湾文学盲目照搬西方,就等同于犯别人的精神分裂症。第三次思想交锋由讨论罗云星的纪录电影而引起。林盛隆坚持认为题材是衡量文艺作品优劣得失的关键,艺术工作者应该思考在具体的年代地域为具体的人写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去关注形式上的“怎样写”、“如何写”。小说中以《新潮》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因为主张“横的移植”,摒弃传统历史文化,缺乏现实生命力,最终为代表市场商业逻辑的企业文化所吞并。而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布谷》杂志因为扎根现实、联系历史,走人民群众路线,作者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同情和关怀,这与“钓运”的历史关怀、立足现实、强调社会参与意识具有一致性,因为“钓运”“形成回归民族与关怀现实相结合的文艺观念,……启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参与意识。”⑥
第二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地下活动。这一左翼经验的起点是对廖新土的人道主义救援。廖新土因为“台独”势力无辜受牵连,《布谷》杂志负责人胡浩因此事看清了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真面目,促使他从自由主义转向左翼人道主义立场,明白“应该为这块地方做一点事,不能让那些不讲理的恶势力横行无忌,不能让老廖这样的人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苍白、发狂。”⑤通过林盛隆的推荐,胡浩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左翼人士,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地下小组会议,汇报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革命工作重心及部署当前任务,从《布谷》杂志办刊的思想路线到团结左翼人士,都提出了明确的计划。随着形势发展,左翼知识分子的地下活动也从地下走到街头。按照林盛隆的意见,他们先是积极拉拢徘徊在虚无主义边缘的陶柱国,致使他发现理想对于精神的拯救功能。《布谷》杂志也重新调整办刊思路,刊发了林盛隆对罗云星纪录电影《坟》具有左翼色彩诠释的文章,并在革新号宣言中强调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另外,日资工厂将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台湾,造成工人中毒事件,引发工人阶级的罢工潮,林盛隆与地下小组成员也积极投入到这次工潮的组织当中去。
第三是林盛隆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台独”观念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在权力分配上外省人与本省人所占比例相差悬殊,应当反抗这一外来政权。因此,他们主张脱离中国,建立独立的政治实体,培育独立的“台湾意识”。但是林盛隆认为他们并没有看清台湾社会的真相,主张不应把焦点集中在政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上,造成台湾人与人的内斗和无休止的纠缠,而更应该关注公正、公平属于哪个群体,体现哪些人的利益。“台独”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失败,是因为它改变不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弱势地位,它只是一个阶层取代另一个阶层,循环统治的问题。
小说中这三个左翼经验所呈现出的意志和力量,固然可歌可颂,但其失败的教训却更值得记取。小说结尾反映出刘大任对这一左翼群体命运的担忧:由于余广立告密,林盛隆和胡浩被当局逮捕,左翼小组烟消云散。刘大任在近年专栏写作中回顾“钓运”,提到各种社会势力渗透“钓运”,包括“台独”势力、国民党革新保台派。“台独”势力抱着分离意识见机行事,革新保台派威胁、恐吓、造谣,试图打击“钓运”的爱国主义传统。由于这些影响,运动最终走向分化、衰颓、息落,这不正是余广立式的人物,人前光明磊落,背后却阴私偏狭,渗透左翼组织而造成运动受挫的写照吗?
二、反思“钓运”与文革扭曲变相的历史
1970年代中后期,“钓运”由于内部势力逐渐分化,外部势力威胁利诱,由高潮转向了低谷,文革也因为极端左倾化路线,表现出荒诞的性质,投身于“钓运”的多数人不得不质疑这些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运动左统派代表人物郭松棻便在“钓运”后不久宣称“对政府垄断的宣传永远要采取质疑的态度”。⑦张系国、李雅明等保钓右派“甚至不无带有怀疑与嘲讽的观点,去强调‘保钓的乱象。”⑧可以看到,“钓运”由当初蕴含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运动,到这一时期却变得问题重重,成为一个亟需反省和批判的对象。刘大任也不例外,反思质疑“钓运”与文革成为他在1970~1980年代文学叙事的一个重点。
首先,他将视角聚焦在文革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以此为题材的文学反思主要集中在小说《风景旧曾谙》、《杜鹃啼血》、《故国神游》、《清秀可喜》中。《风景旧曾谙》写“我”记忆中的四舅,是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知识分子,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但历经文革风暴后却与之前判若两人,变得自闭、胆小、忧郁,人格被木质化。文革结束后,“我”将他接到美国,让他忘记文革那段悲苦的记忆,他却说:“老在这里这么过下去,将来要挨人家批斗的。我看还是趁天冷下雪以前,让我回去吧。”⑨可见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之深。《杜鹃啼血》是“我”回大陆探望“细姨”的一段经历。小说讲述“细姨”在早年游击队生涯中,因爱人移情别恋生吃其心肝,因这一段历史,“细姨”在文革中被批斗而精神失常的故事。《故国神游》写归国华侨曲汉生在北京丢失了护照和身份证,而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被拘留的故事,反映了文革风暴中知识分子对个体身份的恐惧和担忧。《清秀可喜》借小田这个人物,描写了红卫兵对知识分子思想和身体的双重摧残,以及这种情势下被极度扭曲的师生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刘大任的文学叙事,整个基调“显得意外的凄厉与激切”。⑩
其次,走出政治迷思后阐发自由主义观念,也是刘大任反思“钓运”与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有关“钓运”的奇闻轶事他写过不少,不仅有对运动走向息落的无可奈何,还有带着自嘲意味的戏谑。如《密会》里提到为避免国民党特务和联邦调查局窃听,在寒风刺骨、空旷寂寥的公园里召开秘密小组会议,讨论如何将革命的热潮带回台湾。刘大任回忆起当时的场面“像贝克特的荒诞剧”,唯一作用“大概只是彻底透露人性中深藏着的对神秘事物无法抗拒的倾向罢了”。{11}甚至他还提到在“钓运”中以团结、集体、组织等革命名义,大义灭亲将自己的亲生骨肉赠送与人的事情。由于看到“钓运”存在的种种流弊,并亲历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民主自由,这直接影响到他的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生。表现在他的文学叙事领域,就有了人事回忆、谈园艺、说山水的散文杂文创作,以及对运动文学的身体力行。《园林内外》和两本运动文集《强悍而美丽》、《果岭上下》就是这种心境的产物。《园林内外》一书收录五十篇刘大任二十年间各篇以花草园林为题材的作品,从一株非洲堇写到一片家人共同栽植的纽约州园林,从寄情花木的文人墨客心境到以自然为师的哲学境界。《强悍而美丽》与《果岭上下》则是刘大任运动天赋在文学领域的延伸,从NBA、乒乓球、棒球、网球到高尔夫,这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刘大任企图摆脱政治运动的龃龉,寻求精神栖息的尝试。唐诺甚至认为刘大任的园林写作和运动文学,是“钓运”热情过去,新观念尚未确立之前的“一心一意,聚义养气”。{12}
第三,在“无梦时代”思考知识分子的精神“散形”,无不具有反思“钓运”与文革的意蕴。刘大任将人们对集团、党派、国族政治、极权主义的崇拜称为“神话”,宣称每个人的生长过程中,都应该有一个神话时代。但是走出“神话”国度,进入理想熄灭主义荡然不存的“无梦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散形”状态也一并潜滋暗长。在这种知识分子精神“散形”阴影的笼罩下,刘大任的文学叙事可以用“灰色”来形容。小说《下沉与升起》描写一位青年时期靠着坚强意志打拼出事业,建立家庭的知识分子,因为美国的安逸环境而逐渐失去往日“不服输”的性格,只能终日徘徊在肉欲、家庭琐事以及“太平洋盆区研究计划”之间。小说曲折隐晦地表达了因理想沦丧后,知识分子精神的虚肿状态。《散形》则以在美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讲师秦川为主角,叙述了他的三个重要生命片段:一个是现实生活的困局感,在这个困局里充斥着他的性冷淡与乏味的社交生活;另一个是他的家庭生活的半枯干状态,虽然小说安排了一个第三者的“她”作为救赎,但最终仍挽不回他的精神大溃散;第三个是“钓运”激情过后,他试图以园艺山水建构其精神王国的虚妄。通过这三个片段,小说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生命枯竭状态中的精神挣扎。《长廊三号》接过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描写了康雄姊姊的画家情人俊彦离开台湾,流浪到巴黎,最后因理想幻灭,精神溃散,失去生存意义在异国他乡疯狂自杀的故事。《草原狼》写当年参加过“钓运”,热情拥抱理想的一群左翼知识分子,而今都各奔东西,或纠缠于俗世,或钻营于生意,或将全部精力放在了“猛钻学问”上,他们年轻时的理想、冲动、激情在时间的冲击下节节败退,显得物是人非。
三、重估“钓运”价值及中国视角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官定意识形态逐渐退潮,市民社会全面复活,民主法治进程步入正轨,这一全然改观的社会文化氛围为海外知识分子重估“钓运”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揭露反思“钓运”和文革阴暗面不同的是,随着“钓运”可供阐释的空间不断拉大,客观的理性认知和情感上的颂扬成为重估“钓运”的主流。近年来,刘大任的文学叙事就是这一语境下的产物。
2009年创作的《远方有风雷》可以看成是刘大任重估“钓运”历史价值的集大成之作。小说写一个美国西岸大学的保钓青年雷霆,他在南京时期就已参加带有左翼色彩的读书会。国民政府迁台后,随其姑父抵台,并在台读了大学,大学期间因为在大陆的左翼经历,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坐了黑牢。出狱后赴美留学,此时正值“钓运”风起云涌,他也成了激进的左翼成员。他在美娶妻生子,后因为革命需要,将亲生女儿送给另一对不孕的革命同志,其妻一气之下遂偕同长子返台,家庭名存实亡。多年后,其子雷立工成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对父亲的“失败”人生展开了寻根的旅程,要探索出父亲那一代人生的真相,为他“失败”的人生还一个公道。小说主要以“我的故事”、“母亲的故事”、“父亲的故事”三个章节展开,通过我、母亲、父亲三个彼此不同的观点试图对“钓运”进行真实还原。小说中“父亲”、“母亲”一生,象征着在“钓运”中奉献青春,投身理想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们的生命历程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缩影,而“我”则代表对“钓运”进行历史解剖和真相还原的后辈,即现时代的我们和社会。
由于“钓运”杂糅了各派社会势力,当今活跃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从“钓运”崭露头角,思想主张也在这个运动中出现或成形,因此对“钓运”的历史功过和看法不同,其立场也就迥异。例如以“钓运”为题材的,张系国1978年创作的《昨日之怒》和李雅明1986年所写的《惑》具有代表性。张系国和李雅明都参与了“钓运”,但在思想谱系上属于“保钓右派”,在他们的作品里,都以多少带有犬儒色彩的笔法去叙述“钓运”的进程,主要以纪实的方式来叙述运动的内斗特性,因此他们无法从“钓运”里抽离出正面的讯息,只能以表面现象叙述“钓运”的过程,甚至不无怀疑与嘲讽的观点。但作为“保钓左派”的刘大任,在《远方有风雷》中的叙事笔法、情感取向以及题旨意涵,所传达的信息却是积极、正面气象。在小说第四个章节“我的总结”里,我以一名社会学者的身份,通过父亲雷霆的一生总结出三个法则。在“属于我个人的法则”里,我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对于“钓运”的积极看法:“……他们不是俘虏。而且终其一生,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也包括母亲在内。老兵不死,他们只是在越来越远、越来越弱的风雷声中,渐渐消失。请问,我能不为他们感到自豪吗?”{13}
这种还原“钓运”历史真相,追讨公道的文学叙事,还可以从刘大任不同时期两篇专栏文章看出其观念的嬗变。1980年代的《又是保钓》与2008年左右的《保钓长期抗战》都以“钓运”为题材,但《又是保钓》虽然肯定保钓的成绩不可抹杀,但作者的行文落笔明显集中在批判运动的内斗、分裂和自毁僵局上。而《保钓长期抗战》不仅提出留学生需要在运动中具备“国家统一的历史勇气”,还强调运动的“这股气不能断了,后来者必须接过香火,传递下去!”{14}
这种价值重估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当然还要以调整观测中国的视角为前提。粗略地看,刘大任的中国视角经历了从形成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过程。
1960年代是刘大任中国视角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他在台湾、夏威夷、香港的生活经历,使他得以阅读到大陆三十年代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左翼作品,并接触到中共革命建国的全套理论,从刘少奇、毛泽东一路读到斯大林、列宁以及马恩,在香港还观看了《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四十年代左翼老电影,回到台湾又与陈映真等人创办《剧场》杂志,参加读书会,组织批判现代主义,等等。这些经历直接刺激了青年刘大任左翼观念的形成,从情感上影响到他对左翼中国的态度,这也为他日后以左翼立场投身“钓运”埋下了伏笔。当运动发生后,他组织过游行示威,也串连美国各州保钓小组,统一行动,还创办《战报》,积极参加各种读书讨论会,并最终将“钓运”推向了统运。可以说1960、1970年代初的刘大任,对新中国是理想主义的,这成为他观测中国的主要视角。
对中国社会的否定发生在1974年,刘大任怀着“朝圣”心态首次访问大陆,然而这次访问却使他亲眼目睹了“文革”、“林彪事件”、“四人帮”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戕害,触目所及让他“坐立难安”,心理上产生了强烈震撼,返美后公开宣称:“那里的人,活得不像人!”{15}这些因素导致其理想主义破灭,并在1970年代中后期、1980年代陆续对集体、组织、主义、极权展开了批判。这一时期,他处在一个神话破灭,走出神话国度后,进入无梦时代的状态。
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肯定是在近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两岸的敌对情绪逐渐消散,以及经贸文化互动往来频繁,刘大任曾数次游访大陆,其视角和观念又有了新变化。他坦承“每次旅行后,便发现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形象,产生了或大或小的调整”。1992年刘大任在三峡之旅后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中共革命以来统治基础的官定意识形态全面退潮;中共建国以来全力压制务求消灭的市民文化全面复活”。{16}进入新世纪以来,刘大任多次游访上海、杭州、中西部等地,“直觉”到上海正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世纪大翻腾,西部大开发的开展,使得中国下一代的精神面貌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务实精神盛行,市民文化全面繁荣。在四谈“中国崛起”的专栏文章里,刘大任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文化思潮、民族心理状态等多个方面,论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后今非昔比的局面,认为在今天,如果全世界无视中国崛起这一事实,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阶段,这就无异于坐井观天。
从参照“钓运”描绘台湾知识分子的红色经验,到反思“钓运”与文革中扭曲变相的历史,再到重估“钓运”的历史价值,以及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和修正自身的观念,我们看到一个在历史困境中不断寻求现实突围的刘大任,其文学叙事布置的空间可以是他长于斯的台湾,也可以是他想象中的彼岸大陆,还可以是他海外寓居之地,在时间上也贯穿了自国共内战以来的所有年代。通过文学的描绘、反思与重估,他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困境里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轨迹,发人深省!
① 郭松棻:《“五四”运动的意义》,林国炯、胡班比等合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② 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钓运与我,我与钓运(1971-1975)》,龚忠武、王晓波等合编《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页。
③ 刘大任:《雪耻》,《冬之物语》,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9页。
④ 刘大任:《赤道归来》,《赤道归来》,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5页。
⑤ 刘大任:《浮游群落》,台北:三三书坊1980年版,第48页。
⑥ 刘小新、朱立立:《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6页。
⑦ 李怡:《昨日之路:七位留美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林国炯、胡班比等合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755页。
⑧ 南方朔:《“保钓”的新解释——历史没有被浪费掉的热情》,刘大任《远方有风雷》,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30页。
⑨ 刘大任:《风景旧曾谙》,《浮沉》,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版,第125页。
⑩ 吕正惠:《论四位外省籍小说家:白先勇、刘大任、张大春与朱天心》,《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9页。
{11} 刘大任:《密会》,《冬之物语》,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0页。
{12} 唐诺:《溯河回游的桑提阿哥》,刘大任《强悍而美丽》,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5页。
{13} 刘大任:《远方有风雷》,《远方有风雷》,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61页。
{14} 刘大任:《保钓长期抗战》,《忧乐》,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77页。
{15}{16} 刘大任:《直观中国》,《晚晴》,台北:INK印刻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18-222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Realistic Breakthrough in Historical Dilemmas
---On Liu Darens Literary Narrati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efend Diaoyu Islands Movement
Zhou Zhiha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Defend Diaoyu Islands Movement is not only an ungovernmental social movement, but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literature to reflect and rethink reality, as exemplified by Liu Darens literary narrative. Liu describes the red experience of Taiwan intellectuals, reflects on the distorted history of the Defend Diaoyu Islands Movemen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assess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movement. Through literary description, reflection and reassession, Liu investigates the mental state and ideological track of intellectuals in historical dilemmas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The Defend Diaoyu Islands Movement, Liu Daren, literary nar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