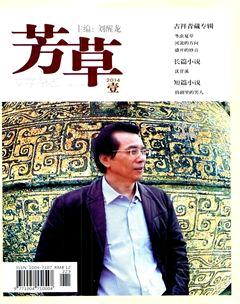消失的阿旺(短篇小说)
2014-07-16扎西才让
扎西才让
一
如果在南山的半山腰看仁贝村,就会发现,这村子像一只不规则的葫芦。葫芦的底朝着西北方向,而葫芦嘴儿却朝着东方。
仁贝河从西山根下流出来,经过葫芦底,绕着葫芦边缘,弯弯曲曲地朝东山脚下去了。
昨天夜里,发了一场洪水。
我家在葫芦底端,仁贝河恰好经过。前半夜里,暴雨如注,水声渐渐大起来。后半夜里,水声依旧浩浩,仿佛就喧嚣在我的血管里。
我去找阿旺的时候,他的房屋已经从洪水中隐现出了墙基,洪水流过的暗黄印迹,清晰地印在青石砌成的墙面上,占了整个墙面的五分之一。
阿旺家就在葫芦嘴儿上,多少年来,仁贝河一旦暴涨,就擦着了他家的房身。但昨夜那么大的洪水,没有伤到阿旺的房子,看样子用巨大的青石砌成的房子还是比较坚固的。
我用门环轻叩了门页一会儿,左边厚重笨拙的木门就被人从里打开了。
阿旺从门缝里露出那张满是坑坑洼洼的脸,斜着眼问我:“哦,是村支书呀,有啥事吗?”
我说:“阿旺阿克(阿旺大叔),我来给你办低保的事。你有空吗?”
他“哦”的一声,表示明白了,打开了门。
我侧身进去,站在院子里。他养的那条四眼藏獒已经老了,但还是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对我发出沉闷的吠叫。阿旺喝了一声,那藏獒就重新卧倒了。
阿旺家穷,只有上房三间屋子,除房身外围为青石砌墙,其他只是土木结构。那院墙,则是黄土夯成的。就这,也是乡政府在三十年前专门给仁贝村的几个五保户盖的,后来归到了阿旺的名下。
上房中间的房间,设成了佛堂。本来供着释迦牟尼佛的地方,却供着药王佛。供桌上停着一口硕大的铜制香炉,炉内插着密密麻麻的藏香,白色的烟带袅然升腾。
左边那间的门被打开,一个喇嘛走了出来,长得白白净净,又瘦又高,一副圆框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
我扭头问阿旺:“阿旺阿克,这位尊敬的喇嘛是谁?”
阿旺用他失去手指的右手擦了擦腮帮子说:“远方来的连手,你就叫喇嘛吧。”
我赶忙伸出右手,想跟他握手。喇嘛双手合十,微微点头,算是跟我打了招呼,转身引我进屋。
我跟随喇嘛走进去,上午的阳光从玻璃窗外射进来,照得屋内一片光明。半腰高的土炕上,铺着几张羊皮,一张柏木炕桌占据了炕面的一小半。桌面上,摊开着一本窄长的经书,已经被翻到了某一页,土黄色的纸页上,整齐地排列着蝌蚪一样的黑色经文。
我不敢多看,斜倚在炕沿边,随口问阿旺:“在念经啊?”
阿旺点点头,脸上浮出羞赧。
这时,喇嘛已在我的对面盘腿坐下来,定睛看着我。
我的心里有些乱,忙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小本子,递给阿旺。
阿旺问:“这是啥?”
我说:“你申请低保的事,乡上批准了。这是“农村牧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你收着。有了这个本本,你就能每月领取低保了。”
阿旺转身把证撂在身后的八脚柜上,拉过咯吱作响的椅子,坐下来。
我本来以为阿旺会仔细地收藏好低保证,却没想到他竟是这种态度,心里升起一丝不快,但还是抑制住了情绪。
喇嘛看了看阿旺,又看了看我,没说一句话,低下头,开始小心地翻他的经书。
我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阿旺低着头,不看我。往日里,他早就端来茶杯,拿出茶盒,叫我自己泡茶了。但今天,似乎有一种不满,或者有一种异样的精神在支撑着他,我清楚地感觉到一股来自他身上的抵制的力量。
我坐不住了,起身告别。喇嘛点了点头,但没从炕上下来。阿旺起身送我出门。我刚出大门,他就从里边把门用力地關上了。
伴着门扇的撞击声,那只藏獒也发出一声狂吠,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二
我只好踏着穿越过村庄中心地带的大路回家,心里的那种不舒服一直没有散去。
妻子已经做好了四五道菜,都摆在桌子上,冒着热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不说住房的宽敞和穿着的时兴,只说这每日两餐,早就告别了那中午牛奶加糌粑,晚上糌粑加牛奶的日子了。
妻子看我眉头不展,关心地问:“遇上难事了?”
我点点头:“给阿旺去送低保证,不知道啥原因,他不高兴。”
“就是那个癞子阿旺?”妻子说,“他有啥不高兴的?该得的便宜都得了!”
正在写作业的女儿突然插进话来:“阿爸,啥叫癞子?”
我呵斥女儿:“好好写你的作业。小娃娃家,净管大人的事!”
妻子不高兴了:“别吓孩子,你告诉她癞子到底是啥,她也算长了学问呢!”
我只好告诉女儿:“癞子是一种病,你们的老师把这种病叫麻风病。”
“哦,我知道了,”女儿说,“这种病很厉害,会烂眼睛烂鼻子烂嘴的。”
我说:“你认识的阿旺阿爷,小时候就是得了这种病,后来治好了,但右手的手指头再也没有长全,脸上那些坑坑洼洼也没有长好。”
女儿说:“就是,红兮兮的,看起来怕怕的。”
我说:“再别写作业了,来吃饭,阿爸慢慢给你说。”
妻子端了两碗羊肉面片出来,恰好听到我的话,恼了:“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说阿旺的病了,还叫人吃不吃饭?!”
我说:“我就给娃娃说个古今,再给她长点学问。”
一听讲古今,女儿高兴了,赶紧跑到饭桌旁,装模作样地拿起筷子,眼睛却盯着我,等着我开口。
于是我说:“你的阿旺阿爷其实很可怜的。”
女儿打断我的话:“他才不是我阿爷呢!”
我生气了:“他虽然不是你的亲阿爷,但你还得叫他阿爷,这是辈分的事。”
女儿不吱声了。妻子说:“你赶紧给她长学问,就别说别的了。”
我把一块鸡肉夹到孩子面前的小碟里,接着说:“阿旺的阿爸阿妈都得了这种病,没治好,脸、手、脚,还有屁股,都烂坏了,烂得认不出来他们都是谁谁了。”
女儿赶紧把嘴里的鸡肉吐出来:“阿爸,你叫不叫我吃了?”
我赶忙说:“哦,不说病,不说病,就说人,这是解放前的事了。解放前知道吧?”
女人说:“解放前就是新中国建立前,老师都说了千百遍了。”
我说:“知道就好。你阿旺阿爷一家在我们这个村里无法待了,被赶到癞子沟去了。”
女人奇怪地问:“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沟啊!在哪呢?”
我说:“癞子沟是以前的名字,现在叫央宗沟,三十年前就改名了。”
女儿说:“哦,知道了,我和伙伴们常去那里呢!”
妻子一听,跳了起来,呵斥女儿:“去那里干啥?那是人去的地方吗?”
我劝妻子:“别骂孩子了!央宗沟有啥去不成的?都六七十年了,麻风病早就被控制住了,沟里也没癞子了,你激动啥呀?”
妻子坐下来,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反正那沟不能去,万一传染上怎么办?”
女儿紧张起来:“阿爸,那阿旺阿爷家也不能去,对吧?”
我说:“有啥不能去的?不是给你说了吗,阿旺的病早就治好啦,再也不传染啦!”
女儿说:“就是说到阿旺阿爷家喝水,不会烂鼻子烂嘴了?”
我说:“你放心去吧,我常去阿旺家,常喝他家的水呢!”
妻子把自己的碗筷哗哗啦啦地收拾了,说:“叫别说这个病,还说着呢!”
我只好对女儿说:“快吃饭,看都凉了!”
三
午饭后,我躺在炕上,想眯一会儿,却总是睡不着。一闭上眼,阿旺阿克那郁郁寡欢的表情就出现在脑海里。我只好爬起来,准备再去一趟阿旺家。
妻子正在给女儿缝补袜子,见我在穿鞋,就问:“去哪啊?”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要去阿旺家的事。我说:“去村委会,下午有事情呢!”
妻子撇了撇嘴:“当了个破村支书,整天都是事,人家村长也没你这么忙!”
出了门,踏上大路,才走了几步,路就分叉了,突然心里一动:上午是从中间大路穿过村落直直去的,似乎不太顺利。这次不如从左侧小路走,远是远了几步路,却是右旋,会大吉大利的。
这样想着,脚就随了想法,慢慢地走。
走到中途,就是一个小广场,大概方圆三百平米吧。广场是去年仁贝村搞新农村建设时建的,场边是不锈钢围栏,场中间是格萨尔王骑马奔腾的塑像。用水泥打的场地宽阔平整,看起来很舒服。这里已经成为仁贝村男女老少休闲娱乐的乐园了。
广场北边山根处,一尊白塔傲然挺立,在夏日的阳光下闪耀着银光,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塔基下,几个老人摇着玛尼筒,走着碎碎的快步,似乎被什么给驱赶着。我朝他们挥挥手,没人看到我。我摇头笑了,算是对自己的嘲笑。
大概半炷香的功夫,到了阿旺家门口。
我又用门环轻叩门页,院内的藏獒闻声狂吠起来。
叩了好长时间,就是没人来开门。我急了,大力推门,门却没有从里上锁,咯吱一声就开了。
佛堂的香炉里,藏香早就熄灭了。但站在院子里,藏香奇异的香味还是能闻得到的。
左侧那间的房门半开着,我推门走进去。室内的光线已没有中午那么明亮了,但亮度并没有减少更多。那个念经的喇嘛,已经离开了,只阿旺一人趴在炕上,头朝着炕沿,双手捂住脸庞,双肩微微抽动,似乎在抽泣。
我小心地问他:“阿旺阿克,你怎么啦?”
阿旺安靜了片刻,突然间放声大哭,算是对我的回答。
我把他翻过来,他的双手始终不愿离开他的脸庞。
我说:“阿旺阿克,你再想法捂住脸,也不会改变你的样子。”
听了这话,他终于把手放下来,搁在大腿上,低着头不看我。
我脱掉鞋,偏腿上了炕。我说:“阿旺阿克,你到底怎么啦?”
阿旺终于抬头看着我。也许因为曾经痛哭过,他的眼睛红得吓人,嘴、鼻、眉心处的疤痕,也红得厉害,仿佛醉酒过敏者的皮肤。
他抽抽噎噎地回答道:“村支书啊,我活得真没意思。”
我吃了一惊:“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他说,“我苦了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我过得比死还难受!”
我说:“以前你不是好好的吗?有时候你还有说有笑的。”
他说:“你不知道,那都是装出来的,装出来的。”
我沮丧地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依然抽噎着:“我上街买东西,他们用夹子来接我的钱。我去转郭拉,他们不会靠近我。我在村口只站了一会儿,就吓跑了几个来旅游的年轻人。我回到家里,没人陪我。早知这样,我就该跟着父母到那边去。早知这样,我就该一直待在癞子沟里,不管谁叫我也不出来,不出来……”
这些话,阿旺几乎是一口气说完的,说到最后,似乎连气都接不上来了。
我说:“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知道,佛祖在看着你,会保佑你的。”
阿旺一听,又带着哭声说:“啥呀,我天天去寺院,从早到晚转郭拉,到佛祖那里祈祷。这么多年了,佛祖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真的没有。”
我说:“你可不能这么想,喇嘛都给你念过经了。”
一听我说到喇嘛,阿旺阿克的眼睛顿时亮起来。
他说:“对,喇嘛来念经了,他说我受的苦太多了,只有纯净了自个的灵魂,才能有好的来世。”
我心中有了隐隐的不安:“这话是啥意思?”
他说:“没啥意思,就是叫我怎么做才能够变得好起来。”
我问:“喇嘛是啥时候走的?”
他说:“他给我念了经,就走了。”
我说:“阿旺阿克,其实村里人对你都挺好的。现在,你也开始享受低保了,这可是好事情,你可要想开啊!”
他说:“我早就想好了,只是觉得心里难过。你劝了我半天,我这心里舒坦多了。”
我说:“那就好,那就好,一定要想开啊!”
他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又到我这来,有事吗?”
我说:“就是放心不下你,过来看看。”
“我没啥,”他的嘴角浮出一丝笑意,“你有事你就走吧,我真的舒坦多了。”
我也觉得他好多了,就下了炕,准备回去。低头穿鞋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八脚柜下,躺着一个大饮料瓶,里边盛满着黄黄的液体。
我问他:“柜底下那是啥东西?”
阿旺紧张起来,坐直了身子,脸上那些退去红色的疤痕,瞬间又变得红兮兮的。
他说:“那……那是尿。”
我禁不住呵呵呵地笑起来。
阿旺也跟着我笑起来,声音有些刺耳。
四
我对我在阿旺家里发出笑声的事后悔不已!
从阿旺家回来的那天晚上,做了好一阵噩梦,梦见自己跟着阿旺走向一处幽暗昏惑的地带,身边冷风飕飕。走着走着,阿旺就不见了,留下我一人,忽然就踏入狂雪纷飞的世界。我冻得瑟瑟发抖,似乎连骨头都被冻坏了。我努力寻找温暖的地方,又一脚踏入一片火海,周身炙热难耐。我无法呼吸,也无法呼喊,只痛苦地挣扎。有人一把把我拉起来,在我耳边呼喊:“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我惊醒过来,浑身是汗。我的妻子紧张地抓着我的双肩,眼睛里蓄满惊慌。
我发了一会儿楞,才完全清醒过来。
我说:“没啥,做了一个噩梦。睡吧,睡吧!”复又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一大早,我家的门扇就被人拍得山响,妻子赶紧去开门。来人是村长,看样子是跑着来的,满脸大汗,上气不接下气。
他说:“你,你,你还有空睡觉啊?出事了,出大事了!”
我吓得从被窝里跳起来,一边穿衣一边问:“到底出了啥事?”
村长说:“阿旺,阿旺他,自个把自个,给烧了!”
我被吓傻了,很难相信这消息的真实性:“谁说的?在哪?”
“谁说的?我说的!”村长说,“刚才我亲眼见的,就在小广场上。”
我着急了:“走,快走!”套了鞋就走。
还没走出大门,感觉脚很不适服,仔细一瞧,竟然穿反了,忙脱下来换了。
到了小广场上,早有一群人,在接近白塔的地方围成了一圈。一看,都是仁贝村的村民。人们一见我们,就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我走进去,心里乱糟糟的。
圈内的平地上,躺着一具尸体,虽被一条毛毯给盖住了,但仍在冒着看得见的烟气。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焦肉味和毛发味,令人觉得不安。
我轻轻地解开毛毯,尸体仰面躺着,面容已无法辨认了。四肢焦黑,蜷曲着,显然有过过度的抽搐。烧焦的尸体比正常人的要小得多,仿佛一个从煤矿里挖出的小孩的样子。
我盖上被子,不知说什么好。踌躇间,泪水溢出了眼眶。
见我哭了,周围的村民也哭起来,先是几个人,后来都在号啕。有人甚至扑在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
我突然惊醒过来,忙制止大家:“哭什么,哭什么,赶紧把尸体抬到村委会。”
村长说:“对,对,大家来搭把手。”
不知谁眨眼的工夫就把自家的门板给卸下来了。于是大家把尸体搁在门板上,抬了就走。
尸体停过的地方,一摊灰黑的污迹,似乎已渗入水泥地,任凭岁月如何冲刷,这生命消逝过程中的印记,是不会被轻易抹去的。
大家腾空了村委会里常年闲置的一间房子,摆了一张长条桌,把阿旺的尸体搁在上面,依然用毛毯盖着。
我问村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村长说:“谁知道呢?我也是被拉栋吵醒的。是吧拉栋?”他扭头问身后的一个年轻人。
叫拉栋的年轻人说:“嗷唻,嗷唻。”
我对拉栋说:“你说说经过吧。”
拉栋说:“我起得早,想到广场上转悠。去广场的路上,遇到当智,我俩就一搭里去了。对吧当智?”
个头矮小的当智在墙旮旯里点点头。
拉栋接着说:“刚到广场上,就看到一团火焰在晃动。仔细一看,是个人呢,把自个儿给烧着了!我赶紧喊叫,扑过去把那人压倒,脱下衣服扑火。当智也用衣服扑火。那火半天扑不灭。对吧当智?”
当智又在墙旮旯里点点头,仍然不说话,似乎被吓傻了。
我问拉栋:“当时你们就没认出是阿旺?”
拉栋说:“那人浑身都是火,谁能看出是他呢?”
村長对我说:“找你前,我就派拉栋去了阿旺家。刚才拉栋还给我说,阿旺不在家,家里的灯泡亮着,炕上乱糟糟的,像一夜没睡的样子。”
拉栋说:“嗷唻,嗷唻,死的肯定是阿旺。我和当智把火扑灭后,那人就死了。我们看了死人的右手,手上没有手指头。那这死人不是阿旺是谁呀?”
大家哦了一声,似乎都清楚了。
我问拉栋:“知道他是怎么烧自个儿的吗?”
村长接了口:“好像是用汽油烧的。当时旁边就扔着一个装过汽油的塑料瓶。”
我突然想起在阿旺的八脚柜下见到的那个横躺着的瓶子,顿时明白了:这个阿旺,当时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那瓶子里装的肯定是汽油,不是他的尿!
我问:“那个瓶子带来了吗?”
村长说:“带来了,那可是证据,不能丢的。”
五
大家接着商量该怎么办。
村长说:“当年阿旺一家被赶到癞子沟后,就和村里断绝了来往。解放后,听说他的父母都死了,只他一人被曼巴(医生)从沟里救了出来。这些年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亲人的。我看不如这样吧,我们自己把他火葬了算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再把他烧一次?这不行!我看还是报告给乡政府吧,叫公家来处理还是好一些。”
众人不说话,但都在慌乱地点头。于是我给乡政府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一听情况,就赶紧报告了乡长。乡长看样子也很紧张,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只一支烟的功夫,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就坐着车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先看了尸体,又去事发现场查看、拍照。
一个小时后,大家重回村委会。乡党委书记把其他围观者都轰走了,只留下乡长、村长、我和拉栋等几人。我们把阿旺自焚的前前后后都一一汇报了。
我顺嘴把在阿旺家碰见念经的喇嘛的事也给说了。
乡党委书记说:“知道是哪里的喇嘛吗?”
我说:“不知道,阿旺没给我说。”
乡党委书记的脸上露出很纳闷的样子。
我赶紧说:“也就是一个念经的。现在想想,阿旺叫人念经,是希望有个好的来世吧!”
乡党委书记还是觉得阿旺自焚的事比较严重,又报告了分管的副县长。
中午时分,副县长一行四人也赶到了。副县长面色凝重地从车上下来,随后露面的公安局局长和宗教局局长脸上都是悲哀的表情。最后一人是个短发青年,很有精神,架着一台摄像机。
落座后,乡党组书记向副县长汇报了情况。听完后,副县长和公安局长低语了几句,公安局长连连点头,叫来宗教局局长,似乎在交代什么事。宗教局局长走出村委会,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拨打。
下午的时间,副县长先向在座的人了解阿旺自焚前后的情况,然后带领众人前往阿旺家里,也查看,也拍照。随后回到村委会,召集大家,继续了解有关阿旺生前的事情,了解阿旺自焚的详情。那个短发青年,从不说话,始终用摄像机记录着这个过程。
快吃晚饭的时候,突然来了几辆车。来人据说是县委书记、县长和司法部门的领导。打头的那个,确实是在电视上常见的县委书记仁青,肤色黝黑,又高又壮。我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吓得连话也说不利索了。村长更是一个劲地用袖子抹汗,一双手不知道往哪放才好。
我让村长赶紧安排晚饭。村长派人前往五里外的小镇上,买来了饭菜。仁青书记也不推辞,匆忙吃完饭后,依然是座谈,听取汇报,前往广场实地查看,进入阿旺家里了解情况。
仁贝村的月亮浮上西山的时候,仁青书记终于把各级干部和村民召集在一起,对阿旺自焚的事,开了个通报会。那个短发青年刚想拍摄,却被公安局局长给阻止了。
仁青书记沉默了一会,似乎在理思路。大家都凝视着他,等待着他。
仁青书记终于说道:“同志們,乡亲们,仁贝村村民阿旺自焚事件,不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策划的,而是偶然发生的。他的去世,是因为他本人对生存有了厌倦之心,所以才采取了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阿旺的去世,我们很伤心,很遗憾,也很同情。他的离去,他自己有责任,仁贝村有责任,我们更有责任。我们能理解他的处境,但我们要反对这种极端可怕的行为,抵制这种人神共泣的行为!”
说到这里,仁青书记停住了,接着就是一段长长的静默。我看了看四周,有人点头,有人沉思,有人擦拭眼泪,有人面无表情。
仁青书记打破了静默:“同志们,大家都知道,自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党和政府对藏区给政策、谋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得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已经初具规模。在这种大好前景下,我们要认清形势,分清善恶,把力量集中到小康社会的建设上来,集中到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上来,集中到我们仁贝村的发展上来。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干扰,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把建设搞好,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香巴拉,共同走向美好富强的康庄大道!”
我有些激动,觉得仁青书记说得真好,但又不知该如何表示。这时,有人鼓起掌来,众人跟着鼓掌,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鼓掌。掌声持续了好长一阵时间,我感觉手都拍麻了。
会议结束后,仁青书记带着一干人连夜走了。公安局局长、宗教局局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却留了下来,说是要指导村委会处理阿旺的后事。
六
两天后的早晨,阿旺的尸体还是按照仁贝村的习俗,火化了。
火葬是在距离村子三里外的央宗沟里举行的,仁青书记、公安局局长、宗教局局长、派出所所长、乡党委书记、乡长和仁贝村的男人们,都参加了葬礼。
仁贝寺院里的总管也来了,穿着黄色的袈裟,戴着高高的帽子。一群喇嘛抬着用于祭祀的乐器,神色黯然地跟在后头。
劈断的松木堆成一座平台,上面躺着阿旺焦黑瘦小的躯体。柏枝被点燃,桑烟升入高空,转眼就消散了。有几只鹰在天蓝的空中飞旋,鸣叫,显得躁动不安。
祭乐响起来,喇嘛开始念经,他们的语速很快,但仍能听得清那些祈祷和祝愿的话。我听着听着,两行泪水滑下脸颊,流到嘴角,湿湿的,涩涩的。
火葬结束后,我回到家里。
一进门,就发现家里的气氛很异常。我的妻子看着我,眼神躲躲闪闪的。
女儿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阿爸,阿哥从城里回来了!”
话音刚落,我的读高中的儿子就出现在我的面前,面色白白净净的,表情却怪怪的。
我问他:“啥时回来的?”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却神秘地问:“阿爸,阿旺阿爷把自个儿给烧死了?”
我反问:“谁给你说的?”
他说:“还用说吗?网上都有新闻了!”
“啊?谁弄的?”我大吃一惊。
儿子说:“我不知道。”
我着急了:“哪个网上有?你亲眼见的吗?”
他说:“就是啊,我见的,就在昨天上午。”
我紧张起来:“网上是怎么说的?”
他说:“就是什么不满现实、自焚抗议、以死明志这样的说道,我也没仔细看。”
我惊叹起来:“佛祖啊,这是谁搞的啊!怎么能这么胡说呢?”
儿子很奇怪:“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说:“你傻啊?是阿旺不想再过落单凄惶的日子,就走了。”
儿子说:“我知道,他确实活得很不开心。”
“就是,他觉得活着没意思。”我说,“他把佛祖都不信了。”
儿子吃了一惊:“啊?怎能那样呢!”
我说:“走,你陪我到村委会去一趟。”
儿子问:“干啥去?”
我说:“村委会里有网,我要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烂新闻。”
儿子随我去了。上了网,儿子打开了好几个网站,都没有他说的那个新闻。又输入“阿旺”、“自焚”、“仁贝村”等词语,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
儿子以奇怪的语调自言自语地说:“明明我见过的,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心中悬起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我说:“没有就好,没有就好。这样的新闻,应该出来一条,消灭一条!”
儿子说:“阿爸,这新闻真的是假的吗?”
我說:“我都见了,经历了,是真是假我当然知道。你说的这个网络,我看不是个好东西!”
儿子说:“也有好处呢,查找资料,收发邮件,跟朋友聊天,很方便的。”
我生气了。“那乱整说道就好吗?乱整的东西,要好好查查!”
儿子赶忙劝慰我:“就是,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说:“就是嘛,凡事都不能乱说,乱说前先要摸摸自个儿的良心。”
三天后,乡党委书记来了,撤掉了我和村长的职务。在听到这个决定后,我顿时傻了眼,心里凉透了,两年前刚担任村支书时的雄心壮志,仿佛突然间就被人抽掉了。
第二天,又听说仁青书记去了乡上,免去了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职务。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想通了:阿旺自焚的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因为我的疏忽,让悲剧给发生了。我明白自己的确犯了不该犯的错误,职务被撤,是对的。
这样一想,我的懊恼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抹去了,一缕轻松的感觉在心头慢慢浮起。
在送儿子回学校的路上,我告诉他:“你的阿旺阿爷一定不会知道,他的离开,改变了好多人,也改变了好多事。”
儿子回答我:“谁知道呢,也许就是一股风吧,就像那条新闻一样,转眼就消失了。”
我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责任编辑:张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