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咆哮
2013-04-17牧然短篇小说
文/牧然 [短篇小说]
大雾淹没偌大的烟城,灯光格外透明。阿旺又出摊了,阿旺现在是个卖小笼包的。他卖的包子馅多,皮厚,拿在手里能拍人。曾经的阿旺是卖煎饼的,也卖过卷饼。曾经的曾经卖油条、肉夹馍。阿旺这人卖东西有个缺点,同样价钱分量总给的比别人多,给少了自个也不乐意。这也分对象,男的没这待遇,女的有。姿色欠佳的没有,姿色中等偏上的有。姿色绝佳的,阿旺会把持不住流口水。年轻时候碰上姿色中等偏上的也流过,现在大了,眼界宽了,流口水的标准也提高了。
阿旺有个弟弟,身居银行要职,官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阿旺眼里则是很大,其他人觉得小,其实就是个银行看大门的。
阿旺还有个哥哥,身居政府要职,官职也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阿旺眼里却很小,其他人觉得大。其实是一位城管头头儿。
阿旺的工作流动性较大,其流动性主要表现在:占摊不缴锐,城管跑,阿旺也跑。城管停,阿旺也停。日子久了,收入没提升多少,体力倒提升了。有一次被十八名城管堵在巷口,本来罚一百,阿旺一提城管头头儿是他哥,被追加五十。
虽然阿旺看起来有点傻,其实也没那么傻。后来城管队员隔三岔五来追,别的摊主都跑,阿旺不跑,嘴里叼根烟吸两口拿出来朝地上吐唾沫。城管一到,阿旺点头哈腰递过去十八个肉夹馍。城管一看,拍拍阿旺肩膀,自觉,真自觉。
好景不长,城管轮番换。阿旺原先勾搭的城管早不知调往何方,阿旺只有一轮接一轮地递肉夹馍,还直接导致阿旺从卖肉夹馍的改卖油条,从油条到卷饼,从卷饼到煎饼。完全依照城管们的口味变化而变化。就在最近一次过渡时想改卖馒头,谁知遭遇了一轮从东部调来的城管。阿旺就成了现在卖小笼包的阿旺。
前些日子,阿旺的小笼包做成了大笼包。东部城管吃得不爽,吃完抹抹嘴把阿旺的包子铺给掀了,扬长而去。
面对生意被砸,阿旺无计可施,阿旺也想去找他那当城管头头儿的哥哥帮忙。不是不想找,哥是亲哥,弟也是亲弟。问题是,两人虽是同爹妈生但不是一个爹妈养的。
三十年前,阿旺他哥那时十岁。
阿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哥吃西瓜时总把大块的留给阿旺。以前阿旺不知,现在想起来暖心窝。后来爹妈把阿旺他哥卖给了城里人,一个姓左的人家。阿旺年少时曾随他妈去看过一次,阿旺他哥那时已经被养成一名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改名换姓叫左轮。
阿旺那时成天幻想要是自己被卖了该多好!
伴着大雾,阿旺推着车,不自觉竟掉下了泪。阿旺擤了一大团鼻涕,骂道,妈的,别惹我,狗急也能跳墙。扔下车,便跑了。
阿旺来到他弟看大门的银行,已是正午。透过玻璃门,看到他弟揣着警棍在那儿调戏妇女。二十五年前,又有一次被卖的机会摆在阿旺和阿旺他弟的面前。阿旺想起了左轮,一马当先扇了他弟一巴掌。他弟当时就被扇晕过去,等醒来时,阿旺被人领走了。十几年后,领走阿旺的那家人全蹬腿了,仅留给阿旺一台做肉夹馍的三轮车,临终遗言是:阿旺,凭本事吃饭,有胃口。等阿旺认祖归宗时,阿旺他弟继承家里一亩八分地,也继承了阿旺他亲爹看大门的衣钵。阿旺只得流浪,到如今三十好几了,媳妇也没娶上。
阿旺现在每每回想起往事,总是蹦出一个字:冤!
阿旺每次来找他弟,他弟总要请他喝酒,每次都是喝两杯就倒,没一次付过酒钱。阿旺琢磨,定是二十五年前那一巴掌扇重了。他弟不认这个哥,阿旺得认这个弟。每次阿旺烦心都来找他弟。
但现在看到他弟揣着警棍调戏妇女,阿旺心里就不是滋味,要是二十五年前卖的是他弟,现在站在里面揣着警棍调戏妇女的人就是自己了。
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冤。
阿旺和他弟去了常去的东风街一号老马大饭馆,通常号称大饭馆的饭馆都不是大饭馆。阿旺不图老马大饭馆别的,就图便宜。以前老马大饭馆没现世,这里坐落着老侯大饭馆。阿旺曾经在老侯大饭馆门口卖过油条,老侯大饭馆的老侯没给过他好脸,怨阿旺抢了他的生意,两人因此还干了一架。结果,阿旺被打成近视眼。后来花五块钱在北街二手市场买了一副眼镜,整天戴着。要不是阿旺整天推一辆煎饼车,人家真以为他是个斯文青年。
烟城是座重工业的大城,东风街从建成至今老被划上破落户。似乎这东风从来没吹起过,新上台的烟城头头儿早想把它改造成专属别墅。老侯从内部得知要拆迁,立马转手卖给老马大饭馆的老马。老马高兴,准备大干一场,四处募集资金。阿旺开始羡慕老马,阿旺的梦想就是在东风街开一家大饭馆。结果老马赔了,阿旺的梦想仍是在东风街开一家大饭馆。
傍晚时分,阿旺和他弟坐在老马大饭馆。阿旺正想发泄自己的苦闷,阿旺他弟噌一声,醉了,倒头睡了。叫来老马,老马平常不喝酒,老马说今日有事,破例一回。阿旺酒倒一半听到有事,抬头看老马,哟,啥好事!
老马端起酒,一口闷下去,饭馆怕是开不下去了,明天就回老家。
阿旺一看事态挺严重,刚想开口多问几句,老马噌一声,也醉了,大脸趴在筷子上。

回的路上阿旺想起了他早上抛弃的三轮车,被扔在观音巷公共厕所旁。待到一看,除了车上插的三角旗还乱七八糟地躺地上,其他物什全被掠夺。阿旺吃饭的家当没了,自然恼怒,气上心头,跑旁边公共厕所足足撒了两分钟的尿。
第二天阿旺赶了个早,在火大哥胡辣汤馆喝一碗胡辣汤,又转到小丽理发厅理发,小丽技术很好,三下五除二令阿旺油光满面。再到观音巷早市老杨水果摊称两斤苹果,又到观音巷拐角的独眼老头那儿擦皮鞋,独眼老头除了会擦皮鞋还兼算命、看风水、办证、刻章。
阿旺也是听说过这独眼老头的能耐,特地跑来擦皮鞋,顺便算命。或者说特地跑来算命,顺便擦皮鞋。阿旺脱掉鞋,倒把独眼老头熏个够呛。
独眼老头低头擦了半天鞋,阿旺说,老头,听别人说你神算,你看我是做什么的!
独眼老头先抬头,后摇头,再点头,鞋好了,两块。
阿旺跳起来,什么,两块,这么贵!
刚花两块钱擦一双二十块钱买的鞋,阿旺内心有点不爽。不爽归不爽,可事还得办。坐了两小时的人力三轮车,到左轮家。又在路上称二斤香蕉。
阿旺五年前来过一次他哥左轮家,五年后又来,五年前是纯认亲,五年后是有求于人。有求于人是因为五年前的亲没认成,也没见到他哥。见的是左轮的太太,年轻、漂亮、白,搞得阿旺差点把她认成左轮的女儿。
阿旺五年后又来,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不同的是地方更大更气派,保安越来越多,周围越来越空旷。阿旺有些忐忑,本来想好的计划,自个把自个搞乱了。待到大门前,保安上来询问,阿旺开始说以前他和左轮的关系以及现在和左轮的关系,由于乱,阿旺说得也比较乱。先说现在的关系,从现在扯到以前,又从以前回归到现在。急得阿旺一头汗,见两个保安萌生要揍自己的冲动,阿旺果断地往后撤。在撤的过程中,保安队长挺着肚子走到阿旺跟前。阿旺见此人眼熟,此人眯着两眼叫,阿,阿旺。
原来此人是阿旺五年前来左轮家结交的一名俊俏的小保安,当时阿旺以为他是大保安,送了一条烟。送烟没问题,关键是送了没办成事。阿旺颇为后悔,现在此人成了保安队长,阿旺一下倒不乱了。拉着此人的手叫道:甄健。
我,我现在改名了,叫,叫我甄不健。
两人仿若是那久别重逢的故人,搞得场面是那样的温情。
阿旺心中不免感叹,变了!人还是一个人,以前甄不健说话结巴,自从跟人学习不结巴,结果更结巴。但只是说第一个字结巴,后面挺顺溜。阿旺心急,甄不健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搞得阿旺好生郁闷。
在甄不健的帮助下,阿旺没见到左轮,见到的还是左轮的太太,她依然是年轻、漂亮、白。阿旺有个毛病,见着漂亮女性就哆嗦、流口水。索性把正事忘了,左轮太太看都没看阿旺转身走掉了。阿旺把头伸长,弓着身子,看甄不健,甄不健松松裤带,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字:走!
甄不健公务在身,无法远送阿旺。只说改日请阿旺喝酒,阿旺待出了左家大宅,就找一处僻静地,做好死等左轮的准备。找来找去没处僻静地方,便随便找一处蹲下。待到第二天一早,阿旺方知身后是家金银首饰店。蹲一宿,阿旺又饿又冷。掏出昨天自备的干馍,因为阿旺想到这恐怕是一场持久战,所以又自备了点咸菜。待充饥后,阿旺便站起来踱步。头伸着,背弓着,双眼丝毫不懈地盯着金店、街上姑娘、左家大宅,典型一副贼样。来回踱了半个钟头,十辆警车堵住主要交通路口,随后下来几十名警察。阿旺爱凑热闹,跑上去和警察搭讪。那警察看到阿旺脸色铁青,问,哎,你怎么过来了!
我过来看热闹。
警察笑了,左家大宅开门了,一辆车驶出来,阿旺判定左轮就坐在里面,便中止搭讪去追那辆车。警察立马停止笑容,几个警察在阿旺迈出一步半后按住阿旺,戴上手铐押到局里,关了两个月。原因是金店老板把在金店门口头伸着、背弓着、来回踱步的阿旺当成个贼,报警了。
阿旺他弟死活不去替阿旺做证。阿旺也料想他弟不会来,哪知他弟不但不会来而且也没承认阿旺是他哥。为这事,阿旺绝食一顿饭。
全哥是阿旺在里面认识的,认识的原因在于两人都喜欢嗑瓜子。阿旺一开始不喜欢嗑瓜子,但嗑着嗑着就喜欢上了。以前炸油条之余,就是边炸油条边嗑瓜子。累了就蹲在地上嗑会儿瓜子,嗑累了去炸一会油条继续嗑。时间久了,阿旺就专挑一家瓜子店的瓜子吃。城北夫子街阿毛瓜子铺是阿旺常去的一家店。

全哥的工作很清闲,主要是拿把椅子坐在门前看守犯人。也不是真正的犯人,没犯事,也不知怎的稀里糊涂就被抓来了,就像阿旺这种。
全哥的活儿,说起来也是技术工种,首先样子要长得威猛,不说意志有多坚定,起码面子上要唬得住人。阿旺注意全哥已有些日子,阿旺佩服的是全哥一坐就是一整天,但最让阿旺佩服的是全哥一整天嗑下来竟不喝水。阿旺不行,嗑两小时就得进一次水。可见全哥嗑瓜子的道行比自己深,阿旺便虚心向全哥讨教。说着说着两人就一块儿扯到城北夫子街阿毛瓜子铺上。也因为阿毛瓜子铺,阿旺和全哥成了嗑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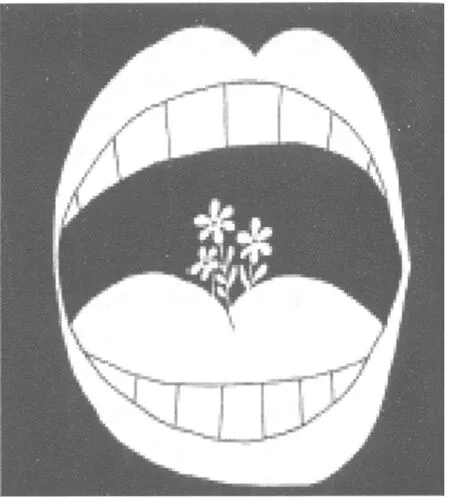
待警察实在没能力白养活阿旺,阿旺也没亲人来赎阿旺时,阿旺出来了。虽出来了,但也欠了六百块钱的伙食费。如果还不上,还得进去,但那时进去就不是进看守所了。
阿旺的当务之急是还清六百块的债,既然是债就要还。如要还,就要收自己的债。东风街老马大饭馆的老马就欠着阿旺六百块,当时阿旺还在老马门前出摊,老马准备大干一场时曾借阿旺六百块至今未还。上次阿旺和老马一起喝酒正好是阿旺借钱给老马六百块一周年,老马说要回乡,本来阿旺想起来,但因他醉了,这六百块也随着老马一块儿回乡了。

阿旺去了趟东风街一号老马大饭馆,现已成一片废墟。阿旺站在废墟久久伫立,当务之急要找到老马,找到老马才能有钱,有钱才能还钱。但阿旺对老马的家乡一无所知,该去哪儿寻,天晓得。阿旺第一次感觉不得劲,之前摊子被砸也没这么不得劲,被人误抓也没这么不得劲,在里面待两个月也没这么不得劲。老提不起劲,阿旺想嗑瓜子,由嗑瓜子想到了阿毛瓜子铺,由阿毛瓜子铺想到了全哥。
两人约在阿毛瓜子铺见面,都不说话,全哥习惯坐着嗑,阿旺习惯蹲着。阿旺本来想找全哥谈个心,见全哥的嘴不停地嗑。阿旺也不好意思打扰,陪他嗑。在嗑的过程中,阿旺觉得全哥故意不让自个说话。谈心主要不是说话,是在于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有的人通过打麻将交心,有的人通过喝酒交心,阿旺觉得全哥想和自己通过嗑瓜子交心,从嗑瓜子当中领悟一些人间真理。
左轮遇上事了,这件事埋在左轮心头不少日子了。左轮的牛秘书一眼看透左轮遇上什么事,说来说去还是家里头那点事。早上牛秘书去接左轮,立马嗅到气氛不对,左轮一副皮鞋脸出来。车里,牛秘书开始说起自家那事。左轮听半天,不耐烦了,老牛,有什么说什么,别拐弯抹角的。
左大人是不是昨晚和左夫人没睡好?
是有点,昨天晚上在床上她说累了。奇怪,我都一个礼拜没碰她了,谁累着她了?我当时就骂她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为这句话,她闹了一夜。你说我怎么办!唉!
牛秘书也跟着长叹一声,安慰说,古人也说了,连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何况您这个……
左轮瞪了一眼牛秘书,牛秘书后脑勺直冒汗,忙接上说,何况您这个大清官呢。
左轮的车在闹市中来个急刹,直接导致左轮和牛秘书头往前栽,待镇定下来,左轮出门前精心梳的油头乱了,油头乱了没事,主要是眼镜也破了。左轮没火,牛秘书倒先火了。伸出头,朝乱哄哄的人群咆哮,谁他妈在前面挡道!
这句“谁他妈在前面挡道”很快淹没在喧嚣闹市之中。
牛秘书给左轮点上一根雪茄,左轮猛抽一口,老牛啊,你知道我最像谁吗?不是我爹,不是我娘,是曹操。曹操说大奸似忠,太伪似真。千百年来人们都看错曹操,现在人们依然看错。但曹操依然是曹操,我依然是我。我从小的愿望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从开始走上这条路,我就是如履薄冰。今天我走到这一步,完全靠我的双手努力创造的。如果烟城没有我,不知道会有多少小摊小贩影响社会治安,有多少人随地吐痰影响市容市貌。知道我为什么前后换了七个夫人吗?就因为这七个没一个值得我信任的。我信任的是我的初恋,可惜她走得早,而现任的这个夫人长得比较像我的初恋。我知她不真心对我,可我也不能就这么放开她。宁我负人,休人负我。
说到动情处,左轮潸然泪下,透过没有镜片的眼镜在那儿擦泪。
左轮如果跟下属说话喜欢拿曹操做比喻,引用曹操的名言,最爱用的两个词是“依然”和“我左轮”。用曹操的话来引出下面的事,有时只说曹操的话,不说正事。左轮如果跟上级说话会自比诸葛孔明。
待到左轮抹干眼泪,牛秘书说,我有一计。
左轮开了一上午的会,牛秘书趴到左轮耳边悄悄地说,你儿子来了。
左轮皱皱眉头,我哪儿来的儿子?把那人带进来,我倒想看看我儿子长什么样!
阿旺被牛秘书带到左轮办公室,左轮正坐着老板椅面对着墙抽雪茄,烟雾缭绕。
左轮,来了!
阿旺,来了。
左轮转过身,摘下眼镜,笑了,你是我儿子!
阿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事先准备的高仿雪茄递给左轮,是是是,我是你儿子。
你怎么是我儿子!
你是我哥,都说长兄为父嘛!
左轮走到阿旺面前,拍阿旺的肩,阿旺,你别以为我做了官,就不认你这个弟弟。你以前是我弟弟,现在依然是我弟弟。说吧,什么事!
听左轮一番肺腑之言,阿旺感动得想哭,便把自己之前遭遇的事从头到尾慢慢道给左轮听……
阿旺从左轮办公室出来,又去找全哥。把今天见左轮的事儿告诉给全哥,全哥帮他分析,姓左的让你帮他捉奸夫,捉到他就干掉他。然后,姓左的保你没事。赔你三轮车,给你十万,再撤掉砸你摊的城管。
全哥,你说这生意该不该做?
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做。
全哥,你说这生意能不能做?
能是能做,这人不好杀。
阿旺陷入深深的深思。全哥问,这事儿你应了没有?
应了。
既然应了就是信义问题,只能这样了!
万一出事被抓进来呢?
进来也好,我也有个伴。
阿旺没杀过人,以前想过杀人,杀那些白吃自己东西不给钱的城管。但只是构思,现在真要杀人了,阿旺又有些怵。杀谁,怎么杀,杀完自己有没有事都是问题。阿旺给自己灌了一瓶白酒,酒壮胆,阿旺不怵了,说杀就杀。
左轮让阿旺去办这事,也有点担心,虽是亲弟,毕竟不“亲”。万一出事,杀得不干不净,名声上也不好听。牛秘书告诉他,不杀,名声上更不好听。左轮懂了遂以出城办事为借口暂离烟城,待接到阿旺的捷报即回。牛秘书也不傻,这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据,便瞒着左轮自己也出了城。
事情过去半个月,左轮迟迟没有接到阿旺的捷报,有些急。便让牛秘书把阿旺找来,牛秘书派人在烟城地毯式搜索也没找出来,阿旺就这样消失了。
十年之后,阿旺在城北夫子街阿毛瓜子铺——现已改成“老毛瓜子铺”——碰见了全哥,阿旺十年不见全哥,全哥哑了,跟人聊天只能点头或摇头。
还是十年前那样,全哥坐着嗑瓜子,阿旺蹲着一边嗑一边回忆十年前的那件事。
十年前,阿旺说杀就杀。在左家蹲守了三天,终于蹲到左轮夫人独自开车出门。阿旺慌忙中拦一辆三轮,对蹬三轮的人说,跟上前面那辆老爷车。
蹬三轮的有些迟疑,大哥,俺这可是人力车。
说话间,老爷车开出老远。阿旺急得跺脚,知道你是破车,不走拉倒。
蹬三轮的急了,客人说自己体力不行可以,但说自己这车破可不答应。蹬三轮的也是有职业操守的,破车也是车。他吆喝阿旺坐稳,就为赌一口气,“嗖”一声蹿出老远。不一会儿便追赶上老爷车,幸亏那辆老爷车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开得不算快,不然蹬三轮的为挣阿旺五块钱的车费怕是要活活累死。
老爷车先在一家商场停下来,后又在一家美容店停两小时,之后便原路返回左家大宅。
阿旺有些纳闷,又去找全哥。全哥又给他分析,既然这女的出去,还自己开车出去,定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定不是好事。但这女的出去没去开房,而是去了商场和美容院,难道在美容院?……
那这事就奇了怪了!
全哥埋头嗑会儿瓜子又悟了会儿,不奇怪,你明天再去跟踪那女的,如果还是去商场和美容院,那十有八九是和野男人搞一起了。
阿旺一听,感觉是这意思,左家男丁那么多,随便就能搭一个,何况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阿旺突然觉得这女的不那么好对付。
第二天,阿旺继续跟踪,结果跟第一天一样。
阿旺跨过全哥没找他分析案情,直接去找甄不健。主要是想通过甄不健挨个了解左家大宅里的男丁。
阿旺找到甄不健,甄不健欲请他喝酒。阿旺说有正事要办,甄不健说我的事也是正事。阿旺没详问,既然断定奸夫就在左家大宅内,陪友人喝酒权当减压。
甄不健把阿旺拉到一家四星级客栈,酒过三巡,阿旺才想起来甄不健有事,便问,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甄不健一饮杯中酒,从包里取出一沓钱和一瓶药放在阿旺面前,这是二十万。
阿旺眼睛眯眯地看着那一沓钱,什么意思!
甄不健结结巴巴得让人着急,意思……你,你应该知道,打明儿起你不用跟着左夫人了。知,知你是左轮派来的,也知你是左轮他弟,拿,拿上这二十万,回,回去把这瓶药倒在左轮酒里。你知道什么意思,完,完事后,我甄不健保你没事。
说得甄不健一头汗。
阿旺隐约觉得事情变得比想象中复杂,自己施个螳螂捕蝉,谁料想黄雀在后。也没承想甄不健这个结巴小白脸,内心竟这般狠毒。明明自己睡了别人老婆,反过来却还要杀了老公,实乃当代西门庆!
左轮、左轮夫人、甄不健都要杀人,都不是什么好人。这三个人令阿旺夹在中间酸不酸甜不甜的,不是滋味。
阿旺说与全哥听,全哥当时说,都是红颜祸水呀!这话阿旺现在说与全哥听,全哥扯着嗓子就是说不出话来。
阿旺把甄不健要贿赂自己的话传递给左轮,但没说是甄不健说的。左轮以为他耍心眼,趁机抬高价码。
左轮怒了,你不就是想要钱嘛,我给你三十万,告诉我奸夫是谁!
为这句话,阿旺感觉到此时的左轮已不再是三十年前把大块西瓜留给阿旺的阿旺他哥了。
阿旺虽爱财爱色,但更爱面子。谁的钱也没收,走了,一走就是十年。
老毛瓜子店依然忙碌着给客人称瓜子,太阳照常下山。阿旺把事儿说完了,全哥没什么表情,起身欲回,留下一声沙哑及沉重的叹息,咳!
十年没有回烟城,阿旺去了小丽理发厅、观音巷早市老杨水果摊,店铺仍在,人却不是那人了。唯一曾经在观音巷拐角身兼多职的独眼老头不变,只是独眼老头连一只眼都没了。阿旺颇为心酸,坐在瞎眼老头旁边。瞎眼老头欲用拐棍捣阿旺,可惜手艺不精,捣三遍没捣着,嘴里不停念叨着,俺的、俺的、俺的……

瞎眼老头颤抖着身体,捣着拐棍,俺的、俺的、俺的……

安娜是阿旺五年前花一千块钱娶的老婆,便宜是便宜点,但这安娜绝对称得上货真价实,姿色没得说。和阿旺结婚不到一个礼拜,安娜便怀上了孩子。阿旺冲动之下,就说两个字:谁的!为这两个字,安娜和阿旺离婚了。
安娜离婚后,没离开烟城,也没马上给自己找郎君。和阿旺结婚完全是个意外,既然是意外,凭安娜的姿色,不愁嫁不出去。但如今怀一孩子,事就变了。和阿旺离婚三天后,安娜有些后悔。连相几次亲无一合适,十月之后,孩子出世,取名阿宝。
阿宝出生后,被安娜遗留在医院。后来听说被医院一名女护士收养,从此杳无音讯。
烟城十里坡有家小饭馆,老板是老马。也就是十年前在东风街一号老马大饭馆的老马,去年得了脑血栓,没事总爱用手比画“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