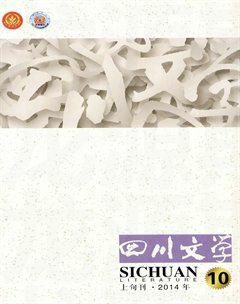我爱着,我悲伤
2014-07-13杨献平
◇杨献平
我和妻子凌晨赶回家里。从西北到北京,再到邢台,一路火车。凌晨两点,一直蜷缩在面包车上等我们的姐夫眼睛惺忪,在昏黄灯光下与我们相互找见,一句话也没说。司机抄近路,面包车在春天的冀南平原凌晨拼命穿越。呼呼风声外,村庄和山岗接连不断。四点多到家里,我迈进门槛,灯光昏黄,氛围肃穆,父亲躺在旧时炕上,身上衣衫整洁,脚蹬一双清代官靴,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脸上蒙着马头纸。亲戚们坐在炕上,形成一个半圆圈。袖着手的妗子说:不要哭了啊献平,等天亮了再哭!我走到父亲头边,想掀开看看父亲。却又不敢。母亲替我掀开,说恁爹右眼一直没合上。小姨妈说:俺姐夫是在等你们两口子!前天晚上,马上就不行了,叫献平。俺为了哄他,叫聚平假装从门口进来,说是你赶回来了。谁知道,恁爹看了看说不是献平,是聚平。
我鼻子酸了一下,想哭。也明知道,小姨妈说这话,也含有催泪成分。可我就是哭不出来。憋了一会儿,哭声都到嗓子眼儿了,也还是没哭出声。我叹息一声,坐在凳子上。
这是2009年3月10日凌晨,父亲已经故去27个小时了。冷空气还在南太行乡村逗留,不一会儿,腿脚就冻麻木了。第二天一大早,按照老家风俗,要赶在阳光落地前,把左边的门板(男左女右传统)拆下来,再用凳子和砖头架在屋子中央,然后把父亲肉身从炕上抬过来。我和弟弟,还有几位帮忙的叔伯和堂兄弟,分别抱了父亲的头脚和身子,一起用力,把父亲安放在屋子中央的门板上。
父亲的一位远房堂兄,是个阴阳风水先生。做这件事之前,他神色严肃地对我说:恁爹肉身过屋梁时,你和聚平一定要大声告诉他。我懵懂,母亲过来说,就是让你喊爹,告诉他说:过屋梁了。要不然,他不知道。魂儿还在炕上呢!这显然是一个相信死而有灵的传统风俗,在他们看来,人死了,灵魂一定还在。后来,我去打问上年纪的人,他们说:人死后七天,灵魂还没有意识,仍旧附着于肉身。
停放好后,父亲仍旧躺在那里,脸上是马头纸。一位堂兄抱来了一堆谷子秸秆,放在灵台屋地上,我和妻子,弟弟及其媳妇,还有干姐姐等人跪在上面。因为正对着门,风不断把父亲脸上的白纸掀开,露出已经刮干净胡子的脸,还有早已经脱落了的下巴,尤其是那只一直不肯闭上的眼睛,好像还在看着我。
我感到惊悚,又觉得悲伤。有的时候,我想父亲会忽然坐起来,或者伸出手掌,像往常那样,冲我要烟抽。在我意识里,我从没有想到父亲会这么快死去。春节时,我和妻子儿子在老家,虽然他一直躺着,吃东西很少,几乎以药液维持生命,但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不糊涂,也不怨艾。我们说话,他有时候也突然冒出来一句。想吃花生了,我们就剥一些,用铁勺给他炒好,再用擀面杖擀成粉末,喂给他。隔几天,我和妻子为他洗洗头,刮掉胡子,再洗脚,擦身子。
可我们离开还不到半个月,他就故去了。我和妻子急忙往回赶,要是那天有航班,我们就可以见他最后一面了,他不会至死眼睛都不闭上。想到这里,我才觉得,父亲其实在人生最后一刻想见到的人竟然是我和我妻子。这其中,我长子的身份可能占一定比例,但母亲和弟弟,还有弟媳妇、干姐姐,以及他的三个孙女,都是一样的亲人。可他为什么至死也不糊涂呢,小姨妈故意让弟弟冒充我从门外走进来,要是他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就不会那么清醒甚或固执了。
想到这里,我愈发觉得悲伤,更多的是惭愧。
渐渐上午了,阳光稀薄,人声鼎沸。我一直跪在父亲灵前,低着头瞎想。这种仪式,是我平生第一次。临近中午,我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我不会连哭带说,只是一声一声喊爹,要把嗓子撕开一样。我明显觉得,自己的咽喉好像也裂成了几块,长条状的,粗粝如碎铁。我就那样喊叫着——爹!
那一时间,我觉得世界上就是我一个人了,父亲的尸身和灵魂也不存在一样。我也确信,从那一刻开始,父亲的灵魂已经离开了具体的生活乃至尘世,进入到了我的肉身和精神。
日光稍热一些时,表哥他们开着拖拉机,从村里老房子拉来了父亲的棺材。
那棺材早就做好了,为了防止被父亲看到,做的时候在隔着一道山岭和一道河谷的村子老房子里,存放也在那里。母亲让我去看看。弟弟带着我,进门,看到那么一口白灿灿的东西,我忽然吓住了。站在门口,脑子刹那空白,像是头颅一下子被割断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我叹息一声,走进门,抚摸了一下棺材盖,咬着嘴唇。沿着它转了一圈,临出门时,我狠狠地用拳头砸了一下,头也没回。
现在,白色的棺材已经被油漆了,绛红色的,四边有花色图案。下午,我在父亲口中放了铜钱,好像是很多年前的。又帮着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帽子,靴子,下面铺了一床新的被褥。然后和一些人一起,把父亲的尸身抬起来,缓慢放进棺材。我还在哭,那位做阴阳先生的堂伯嗔怪说,这时候不能哭啊孩子!我戛然而止。收殓完毕,他们给了一根缠满白纸,头上做了吊穗的木杖,还有父亲的遗像。我走在最前面,弟弟随在身后,再是我妻子、弟媳妇和干姐姐。
按照风俗,我们要把父亲带到麦场上。麦场与我们家也隔着一道河谷,要过去,得绕着马路,再上小路,再回到村子里,才能到达。这之间,要路过一座村庄,数户人家,还有几个拐弯和几个石拱桥。那位堂伯告诉我,遇到桥、拐弯,都要告诉恁爹,要不然,他过不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不是棺材过不去,也不是人,而是父亲的灵魂。在乡间传统看来,灵魂很容易被世间的桥梁、自然的山势和道路所迷惑,从而把自己丢掉或者就永远在那里徘徊。
到麦场上,一切安置妥当,我和妻子,弟弟,儿媳,干姐姐坐在棺材一边。外面是前来帮忙或看热闹的乡邻。妗子交代我说,到麦场上,你们要使劲哭,让别人看看,孩子们多孝顺。我没有吭声。心里觉得,这口棺材里装的是我的父亲,生了我,并且纯粹用汗水和肉身的苦难将我养大,他死了,作为他此生不倦劳作,且毫无怨言的动力源泉之一,我如何不悲伤。而要我大声哭,悲痛地哭,是叫别人看,证实自己的孝顺。我觉得这比不给父亲送葬还要可耻。
可是,我还是很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地方的风俗,是一个地域的人心要求,或者检验各家儿女们是否真孝顺的杠杆之一。可是,到麦场上后,我真的没再大声哭。晚上又下起了雨,开始小,继而连绵。按照风俗,请了一台胡乱扭唱的歌舞团,以作为逝者哀荣之一种,向他人证实和炫耀。远近村人吃了饭,就带着孩子来看。我很反感,以为这是对父亲的一种惊扰和不恭。雨下起来了,正好把那些人驱赶回家。
深夜,就近的堂哥、表弟拿了被子,还有白酒,要和我和弟弟喝酒,陪我们一起为父亲守灵。后来是雾,我喝多了。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冷。灵棚的灯光在雨中沉默,四周苍黑如铁。我回到父亲棺材旁边,在他灵前续燃了一根香,换了一根蜡烛。然后在一边的干草上坐下来。忽然觉得,这沉穆的气氛中有着一股穿透人心的悲凉。
外语隐喻能力自主发展与学习型词典介入:路径与方法 ………………………………………… 杨 娜(5.23)
第二天有人前来悼唁,主要是亲戚,还有我当年的老师和同学。然后起灵,父亲的棺材盖被三寸长的铁钉钉住了。这时,我是要哭的,可是我没有怎么哭。按照风俗,我跪在地上,摔碎瓦盆,然后又举着招魂幡,沿着小路向下。我放声大哭,鼻涕眼泪糊得满脸都是。几次回身跪下,送葬队伍停了。那位懂阴阳的堂伯说,让吹鼓手多吹一会儿,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松就拿了咱的钱。另外,距离掐算的下葬时间还不到,这样既拖延了时间,又使得吹鼓手吹的时间长。
我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到大马路上,我再次转身向着父亲的灵柩跪下,放声大哭。这一次的哭,是自发的,无法抑制的,悲伤在我全身搜刮。我大声喊爹,像第一次放声哭那样,要把喉咙撕破,要把心脏吐出来,要把我从他病后至死淤积在胸中的不甘、惭愧、不解、疼痛等全部倾泄出来。
巨大的坟穴像是一口水井,张着嘴巴,一副心安理得,甚至落井下石的样子。他们把父亲和他的棺材放进去,叫我拿了铁锨,站在棺材上,左右铲了三锨土,盖在上面。然后又让我出来。那位堂伯说,你要给乡亲们磕头,交待他们把恁爹埋好。我依言而行,向着帮忙的乡亲们下跪,请他们帮我把父亲埋好。
他们动手了,铁锨铲起新土,往父亲身上扔。我哭,妻子也哭。那位堂伯弯着腰跑过来说,这会不能哭了。我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闭住了嘴。可是我妻子是西北人,可能那里没这个讲究,仍旧在喊爸,悲恸不已。
回到家里,家什堆得哪里都是,帮忙的人、亲戚们还没走,但我却觉得了一种不明所以的空洞。回到屋子里后,往炕上看,空了,打量屋子,也空了,再到院子里,人虽然多,但我好像听不到任何声音。我知道,这个家因为没有了父亲,很多地方都空了,空得让人心慌,如同掉进地洞找不到出口。
为了答谢帮忙的人,请客,喝酒,弟弟在喝,叫我。我把他训了一顿。他生气,和我争吵了几句。我站在院子里那棵父亲生前种的椿树下,看着袭上来的黑夜,却感到自己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这么大的家,房子那么多,自己却哪间房子都不想待。这些都是父亲亲手垒起来的,那些石头,包括地面,甚至墙皮,都是他用手一点点做起来的。而现在,他不在了,作为他的儿子,我觉得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家里一切,哪怕是堆在墙角的柴禾,也都是父亲捡回来的,那些不动声色的家什与房屋包括树木,都有父亲的气息。
去小姨妈家答谢,姨夫说了附近村里很多亡者的安葬方式。有的买了水晶棺椁,还有大理石的,还有的把墓穴用水泥浇筑了,甚至灌了水银。有人请了戏班子,歌舞团,还有六支吹鼓手等等。我才知道,我为父亲做得太少了,棺材用的是奶奶院子里一棵老梧桐树拆解的板子,也没有打防腐针,灌水银,更没有水晶和大理石棺材。我确实不懂,要是早些知道了现在南太行乡村的丧葬风俗,我一定为父亲买一口水晶或者大理石的棺材。
我对母亲和妻子说了这个想法。妻子说:生前待老人不好,死了,用金子做棺材也是白搭。母亲则旁敲侧击说:听说柏木棺材最好。我没有接她的话。回到西北后,直到现在我都无法释怀,总觉得欠了父亲很多,愧疚深重,胃部一直鼓胀。看到好吃的,还有香烟之类的,就想起父亲,心想,要是他在多好,我要好好孝顺他,能吃上的、抽上的和用上的,都给他享用。有时候看到和父亲长得相像的老人,就要快走几步,到人家前面看看是不是真的像我父亲。
每天夜里,躺在床上,我都会想起老家。父亲在时,老家总是很清晰,还有一种很恬淡和温暖的光泽。父亲死了,老家在我脑子当中忽然变得稀薄、不真切,恍恍惚惚,似乎是落在地上的一枚巨大树叶,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卷走。
2011年7月,正值草木葳蕤、日光浩荡之际,我和妻儿再一次回到南太行,在家里二十多天,数次路过父亲坟茔下面的马路。抬头看,庄稼和树木遮蔽了他,齐腰深的茅草也覆盖了他。我几次都想去看看,可最终没有。甚至说话都不愿意提及父亲,即使别人说起来,我也赶紧岔开话题。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放下,几年来积攒的惭愧和不甘,缺憾与疼痛仍旧根深蒂固。有几次,我站在家后的山岭上,看着父亲埋身的地方,独自叹息。我知道,那个人虽然不在了,但我仍旧爱着他,因为我爱着,才会时常觉得一种绕身钻心的悲伤。
可时常又觉得,这种悲伤是虚妄的。一个人的消失,似乎是永远的。有朝一日,当我也故去之后,我儿子的儿子肯定记不得他的曾祖父是何模样了。人在时间中,真的如同一把烟尘,缭绕一圈后,就会无影无踪,埋在地下,也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就是从土地与离地五尺的地方如草木般萌发、生长、衰亡,并终会乌有。唯一可资证实的是日日行走的大地——人的出处。有时候,我觉得《圣经》中的“尘归尘,土归土”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看起来像是谶语,其实也是极为科学的,符合人及万物之本质规律。
前一段时间,干姐夫把父亲丧葬时的录像寄给我,我拷进硬盘,没有加密,也没设置隐藏,很多次看到那个文件夹,总是想打开看,可还是没有勇气。我想,我还是在惧怕什么吧。想起父亲病重期间的淡然态度,愈发羞愧,同时也想:死亡对于父亲这样一个劳苦一辈子,始终卑微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件幸福的事。尽管他在最终,留着一只眼睛,想要再看到我和我的妻子。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个念想。也或许,他之所以最终都不肯闭上眼睛,就只是想把他所在的这个家和与他亲近的人留在瞳孔,进入到灵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