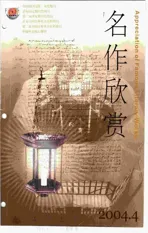风止步(节选)
2014-07-12胡学文
/ 胡学文
1
那个人是从后面抱住王美花的。往常这个时候,王美花肯定在地里。那天她去了趟营盘镇,回来快晌午了。天气晴好,王美花想把闲置的被褥晒晒。被褥是儿子儿媳的,每年只有春节前后用那么几天,大部分时光躺在西屋昏睡。但每个夏季,王美花都要晾晒两三次。晾出一床被子一条褥子,抱起第二床被子时,意外地瞥见燕燕的花布棉袄。王美花顿时僵住。西屋用来堆放杂物和粮食,窗户用黄泥封着,仅留半尺宽的缝儿,光线不怎么好,但王美花一眼就认出来了。棉袄被压皱了,那一朵朵紫色的小花没开放便枯萎似的,蔫头耷脑。晕眩漫过,王美花扶住旁边的架子。
被抱住时,王美花结结实实吓了一跳。但啊到一半便及时而迅速地收住,像坚硬的东西撑胀了喉咙,头跟着颠了几颠。她闻到呛鼻的老烟味,整个村子,只有他一个人抽老烟。王美花奋力一甩,没甩开,便低声喝斥,放开!他不但没放开,反用嘴嘬住她的后颈。王美花再一甩,同时掐住他的手背。他的胳膊稍一松脱,她迅速跳开,回头怒视着他。
马秃子一半被光罩着,一半隐在阴影中,这使他的脸看上去有几分变形。左眼下方那一团鸡爪似的褐痕格外明显。他笑得脏兮兮的,咋?吓着了?
王美花往后挪了挪,竭力抑制着恼怒,你疯了?怎么白天就过来?
马秃子欲往前靠。王美花喝叫,马秃子定住,不痛快?你明白我为啥白天过来。你明白的。这半个月你黑天半夜进门,天不亮就走,你让我啥时过来?
王美花艰难地吞咽一口。嗓子里什么也没有。我干活去了,谁干活不这样?我没躲你,真是干活去了。你快走,大白天不行!
马秃子目光从王美花脸上移开,往四下里戳,寻找什么的样子。王美花闪过去,竖在马秃子和被垛中间。不能让他看见那件小棉袄,绝不能。马秃子歪过头,叼着古怪的笑,不行?
王美花声音硬硬的,不行!
马秃子又问,不行?
王美花喘了一下,说,不行,大白天,你别这样。已经带出乞求。
马秃子的笑抖下去,我就要干,干定了。你不痛快,我还不痛快呢。嫌我大白天过来,你再躲,我去地里找你。要不你试试?来吧,你自己脱,还是我替你脱?今儿我帮你一回吧。
王美花叫,别过来!
马秃子已经抱住她。你大声喊嘛,声音这么低,谁听得见?
我自己来,出去别在这儿。王美花像摔到石头上的瓦罐,哗啦成一堆碎片。
马秃子说,这就对了嘛,又不是我一个人痛快。
王美花带上西屋门,出去关院门。院子大,多半一块被矮墙隔成菜园,从屋门到院门那段路便显得狭长。走到一半,王美花心慌气喘,但她没敢停步。阳光像剥了皮的树,白花花的。两侧的门垛各有一个铁环,王美花把丢在一侧的椽子穿进铁环,院门就算闩住了。其实是个摆设,从外面也能轻易抽开。刚才就是插上的,马秃子还是闯进来。门前是一条小街,经过的人很少,王美花仍吃力地却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往两边扫了扫。返回的时候,她逡巡着左右。其实两边都没人住。左边的房盖起不久,院墙还未来得及垒,那对结婚不久的夫妻便打工去了。再左边是马秃子的院。右边倒是老户,三年前老汉就死了,住在县城的儿子封了房门,再没露过面。再右边是菜地。王美花住在村庄的孤岛上。但她仍怕得要命,毕竟青天白日。一只鸡赶上来,在她脚面啄了一下。王美花蹲下去,那只鸡却跑开了。起身,王美花借机回回头。一棵又一棵的日光竖到门口,密密匝匝的。王美花掸掸袖上的灰尘,把慌张死死摁在心底。
马秃子已扒个精光,除了脑顶不长东西,他身上哪个地方都毛乎乎的,两腮的胡子多半白了,胸前腿上的毛却一根比一根黑。王美花发呕地扭过头。马秃子催促王美花快点,他憋不行了。王美花扣子解到一半,又迅速系上,然后把裤子褪到膝盖处。马秃子拧眉,就这么干?王美花骂他老杂种,想干就痛快点。马秃子说我不是驴。王美花说你就是驴,比驴还驴。马秃子欲拽王美花的裤子,王美花挡着不让。你滚吧,你他妈快点滚吧,你个死东西。马秃子缩回手,看来,你非要等天黑啊,我有的是工夫。王美花被他捏到疼处,边骂边把裤子蹬掉。
王美花火辣辣的疼。她好几年前就绝经了,身体与村东的河床一样早就干涸了。她强忍着,一声不吭。马秃子喜欢他干的时候骂他,她偏不。老东西六十多岁了,一下比一下猛。王美花觉得什么东西滴到脸上,她抹了抹,同时睁开眼。马秃子嘴大张着,一线口水还在嘴角挂着。马秃子的牙黑黄黑黄的,唯独上门牙左边那颗通体透白。镶牙的钱是她出的。王美花没再闭眼,死死盯着她的钱。钱已长在他嘴巴里。她想象那是一棵树,那棵树疯长着,疯长着,终于戳裂他的脑袋。马秃子啊了一声,脸上却是心满意足的痛快。
王美花迅速穿了裤子,抓起马秃子的衣服摔他身上。马秃子磨磨蹭蹭,终于穿上,却赖着不走。王美花恶狠狠地,你要死啊,滚!马秃子说偏不滚。王美花的手突然攥紧,顿了顿,又慢慢松开。声音出奇的平和,说吧,还要怎样?马秃子说这阵子手头紧,借我几个钱。王美花胸内有东西杵出来,瞪视数秒,很干脆地说,没有,我哪来的钱。马秃子挠挠脸,我知道你去镇上了,去邮局,干什么,你清楚。王美花说,你休想!马秃子说你也是一个人,要钱干什么?好吧,没有就算了。
王美花看着马秃子的背,他迈过门槛那一霎,叫住他。王美花背转身,摸出一百块钱。钱带着她的体温,热乎乎的。马秃子捏了,说,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就够了,我会还你。王美花的目光在他胡子拉碴的脸上咬了几下,掏出来,同时低喝,滚!
马秃子闪出去,却又退回来,你记住暗号,我白天就不来了。
王美花咬住嘴唇,嘎嘎吧吧地响,像干裂的柴。她瘫下去,歇了好大一会儿。随后换了衣服,洗了手洗了脸,把留在身体上的老烟味抹得干干净净。燕燕的棉袄仍在那儿团着。揣在怀里发了会儿呆,放进柜里。那节红柜专门放燕燕的东西,鞋,衣服,布娃娃,彩笔,手推车,干脆面的卡片。燕燕吃干脆面似乎就是为了搜集这些卡片。然后,王美花把余下的被褥全晒出去。
那只褐鸡又啄她脚面了。王美花晓得它馋了,撒了两把麦粒。王美花养了七只鸡,别的鸡懂得去他处觅食,褐鸡却是又馋又懒。王美花并不讨厌它,它一只脚残了,跑起来一跛一跛的。王美花坐在门口,看着褐鸡啄麦粒。啄一下,看看王美花,再啄一下,看看王美花。
阳光仍然白花花的。没那么粗,也没那么硬了,柔软得像麦秸。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王美花很安静地倚着。褐鸡吃饱,大摇大摆地离开。王美花终于想起一件事。她从被垛底摸出手机,还有那张硬纸片。纸片上记了两个号码,一个儿子的,一个女儿的。女儿在东莞,儿子儿媳在北京。女儿在什么厂子,两年没回家了。儿子儿媳都在收购站,过去每年都回来,今年不会回来了。王美花知道的。拨了两通才拨对。女儿很恼火也很紧张,说过白天别打电话,怎么记不住?王美花慌慌地说钱收到了,我有的花,别寄了。女儿说知道了。王美花发了会儿愣,犹豫好半天,还是拨了儿子的电话。儿子没那么恼火也没那么紧张,好像刚睡醒,声音松松垮垮的。王美花说是我,儿子说知道。王美花说鸡蛋攒一筐了,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儿子说吃不了就卖,没人收,卖给小卖部。王美花说舍不得卖,如果捎不到北京,她打算腌了。儿子说你看着弄吧,腌也罢卖也罢,就这事?王美花顿了一下,声音不自觉地压低,燕燕还好吧?儿子没答,王美花以为儿子要挂,她的手有些抖。儿子没挂,她能听见他拉风箱一样的喘息。王美花快要撑不住了,鼻子又酸又涩,我就是问问。儿子终于挤出一个音儿:好!
2
男人穿了件夹克衫,可能是风大的缘故,往前冲的时候,夹克衫蝶翅一样张开。嫌疑人不像电视中演的那样戴着头套,他的脸裸着,脖子细而长。男人动作猛,但仅砸了一拳便被警察扯住,倒是他暴怒的声音一浪又一浪,余音久久不去。
那天,他们就是看完这段视频后争吵的。有那么几分钟,左小青微垂着头,表情混杂,双手不停地绞着。吴丁觉得他的话起了作用,但她还在挣扎和犹豫。毕竟,这是个艰难的选择。这需要一个过程。只要迈出第一步,不,哪怕半步,吴丁就会推着她往前走。吴丁语气适度,这没什么可耻,隐忍那才可耻。看起来一切过去了,与你没关系了,其实是欺骗式的遗忘。一个人是很难骗自己的。被垃圾蹭到,再脏也要捂着鼻子丢进垃圾箱,今儿绕过去,说不定明儿还会被蹭上。
左小青突然抬起头。她眼睛大,睫毛长,如波光粼粼的深潭。即便她生气,吴丁也喜欢凝视,甚至有跳进去的冲动。此刻,深潭结冰了,透着阴森森的寒气。
你就是为这个才跟我在一起的,是不是?
吴丁叫,你想哪儿去了?我怎么会?这怎么可能?
左小青叫,你就是!你就是!!她的脸青得可怕。
吴丁试图抓住她,左小青狠狠甩开,你别碰我,我是个脏人,脏货,垃圾。吴丁没想到她如此暴怒,退后一步道,你别乱想,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该明白我的。
左小青挥舞着双手,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吴丁劝,你冷静些。
左小青哽咽,你撕我的伤口,还劝我冷静,你个冷血动物。难怪你第一个女友会疯。她是被你逼疯的,她跳楼也是你逼的,你个凶手!
血呼地涌上头顶,吴丁脑袋涨涨的,你别提她!
左小青叫,就要提!你怕碰自己伤口,凭什么给别人伤口撒盐?
吴丁大叫,这不是一回事!
左小青毫不示弱,这他妈就是一回事。你还想把我逼疯吗?还想逼我跳楼吗?你还想当凶手吗?你上瘾了是不是?
吴丁动手了。后来,吴丁一遍遍回想当时的场景,懊悔得直想把自己剁了。他劝左小青冷静,自己却昏了头。他的巴掌并没落到左小青脸上。挥过去的同时,触到左小青冰冷的眼神,迅速回撤,还是慢了些,指尖掠过她的鼻翼。吴丁不是暴躁的男人,也没长出打人的样子,整个学生时代,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那样的举止他自己都吃惊。没挨到左小青的脸,也是打了。事实上,他当场就认错了,抓着左小青的胳膊让她打他耳光。左小青甩开,他抓住她一条胳膊。吴丁一遍遍地咒骂自己,并以实际行动惩罚自己。左小青仍要走,怎么劝也不行。那时,十点多了。吴丁让左小青留下,他离开。他被逐出门外,这总可以吧?左小青一言不发,执意离开。吴丁揪心地说,黑天半夜的,你去哪儿?左小青终于将寒冷的目光甩过来,她一直低着头的。不劳你操心,地方有的是。吴丁央求她明天走,至少要等到白天。左小青讥讽,你担心什么?我被强暴?你煞费苦心,不就想让我当证人么?我成全你!你会拿到证据的。从未有过的痛肢解着吴丁,左小青拽门的一霎,吴丁及时从身后抱住她。不让她走,有些耍横的意思。左小青仰起脸,对着门,一字一顿,你还想把我逼疯么?吴丁松开,左小青闪出去。
吴丁木然地站着,许久,突地给自己一个嘴巴,追下去。哪里还有左小青的影子?她的手机关着。吴丁仍然拦了出租。转了数条街,直到午夜,没有收获。皮城不是很大,八九十万人口吧,转遍每条街也是不可能的。左小青不会失去理智,故意在深夜的大街上游荡,那么说不过是气他。但整个夜晚,吴丁没有合眼。他候在电脑前,一遍又一遍给左小青留言。她的QQ头像是灰的,但她总会上线的。他觉得已经挖出自己的心,那么,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让她瞧个清楚。
黎明时分,吴丁进入了正义联盟QQ群。这个QQ群是他建立的,三年了。在这里,他是令狐大侠,是盟主,他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交到这儿。他在这个世界能嗅到现实世界嗅不到的东西。这个世界是吴丁进入现实世界的通道。永远有人夜半不寐,吴丁进去不到一分钟,便有人和他打招呼。
3
燕燕离开那日,天阴沉沉的。从医院出来,径直去了车站。王美花小声提醒,昨儿个燕燕说想去公园。儿子没反应,王美花便闭了嘴。儿子走得快,后面的王美花只能看到儿子那一头乱发。车站广场两侧挤满店铺,王美花给燕燕买了一瓶饮料,一包饼干,两包干脆面,交款时,瞥见架上的雨衣。儿子已经买了票,正四下寻找她。王美花紧赶两步凑上去,把东西往燕燕手里塞。儿子皱着眉问,这是什么?王美花说雨衣,没准要下雨。儿子狠狠巴咂着嘴,在车里坐着,哪会淋到雨?王美花说到了北京,回家不还得两三个钟头么。儿子看着她,谁说北京要下雨?儿子眼睛赤红赤红的。王美花说,万一……儿子说,用不着,你拿着吧。王美花知道儿子窝着火。王美花和儿子耗了一个通宵,凌晨时分,儿子终于同意了她的决定。她吃的咸盐多,知道怎么做更合适。不,那不叫合适,是没办法的办法,是没选择的选择,是钝刀子割肉。往远想想,也只能这么割。不是她说服了儿子,是那个理由压住了儿子。儿子要把燕燕带到北京,没有任何征询的意思。王美花没说什么。能说什么呢?
从县城到北京的车要经过营盘镇,走了一段,王美花和儿子商量能不能回家一趟,燕燕的书包还在家里。儿子在王美花前排,没有回头,但王美花看到了他的神情。票都买了,回什么回?王美花说燕燕冬夏的衣服……儿子打断她,北京什么都有,你别操心了。王美花闭嘴。她不怪儿子,过去儿子没有过这种口气。
在镇上下了车,王美花有些惊恐地看着客车远去。那么快,霎时就没了影儿。王美花站了好一会儿,嘈杂的声音终于爬进耳朵。从镇上到村里十几里,平时也就一个多小时,根本不停歇的。但那天,她走了一段,腿就成了软面团。她打算稍歇歇,坐下去,身体彻底成了摊饼。疙疙瘩瘩的云悬在头顶,要砸下来的样子。王美花大睁着眼,等待着。云层翻卷变幻,却不肯触碰她。她一声又一声地哀叹着。
看见村庄,已经是下午。王美花立住。她仔细拍打着衣服,把衣服上的沙尘一粒一粒摘干净,然后蘸着唾沫,将头发捋顺。后又反复揉搓脸,觉得不那么死僵僵了,才往回走。她没去地里,从县城回来的,得有从县城回来的样儿。燕燕闹了点儿小毛病,在医院住了三天,没事了。儿子把她带到了北京,什么事也没有。没发生过别的事。对于一个村庄,一个女娃随父母进城不是什么重要新闻,但总会有人问的。
王美花怎么也没想到撞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马秃子。其实也不奇怪。王美花和马秃子都住后街,是邻居。马秃子常常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晒太阳。王美花要么从东边进院,从西边进院必经马秃子家。从镇上回村恰是走西边。王美花看见他的刹那,血液几乎凝固。本打算从房后绕到东面,马秃子却已经看见她。王美花低头疾走。她不是怕他,是不想看那张老脸。没发生什么事。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吞咽着唾液,吞咽着血,吞咽着刀叉棍棒。她没看见石头,没看见石头上那个出气的东西。
经过马秃子身边,王美花突然定住。不知道自己咋就定住了。并不想停下的。她吞咽得鲜血淋淋,那一刻却怎么也吞不下去了。那一块东西飞出来,射到马秃子胡子拉碴的脸上。
畜生!
马秃子抹着脸,什么也没说。
王美花终于拔起脚。后背始终有东西扎着。王美花已经懊悔了。她把那层膜捅破了。刀子都吞进肚里,咋就咽不下一口气呢?王美花走了三天,鸡都饿坏了,特别是那只褐鸡委屈地往她腿上靠。王美花飞起一脚,褐鸡甩到墙角,哀怨地咕一声。王美花愣了愣,扑过去将褐鸡抱在怀里。
马秃子就是那个晚上叫门的。天才黑了不久。王美花胡乱塞了一口,独自发呆。先是敲玻璃声,王美花打个激灵,问谁呀。听出是马秃子,王美花的胸顿时炸了。马秃子让她开门,他有话说。王美花让他滚,滚远远的。马秃子没滚,反敲得一声比一声响。话一句比一句高。王美花慌了,老东西不怕,她怕。
王美花几乎是把马秃子拽进来的。插上门,挥手就打。已经捅破,还装什么装?马秃子并不躲,伸长脸挨着。她要打青打紫打碎打裂。打了几掌,脑里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她骂着畜生,蹲下去,爆出凄厉的哀号。就那么一声,戛然而止。她洗过脸,逼视住马秃子。说真想杀了他。
马秃子胡子重,那张脸看不出什么变化。他说,我也想杀了自个儿呢。你动手吧,我不躲。
菜刀在案板上,两人都看得见。
王美花骂,你是个畜生。
马秃子说,我早就是畜生了。
王美花压制着恼怒,问他还想干什么。
马秃子说,人交给你了,蒸也好煮也好,你咋解恨咋来。
王美花吐了一口,吐到地上。我嫌恶心呢。别在这儿戳着,赶紧滚!
马秃子问,撒完了?
王美花大叫,滚!
马秃子摸摸头,往前移移,竭力看清王美花似的。呛鼻的老烟味扑王美花脸上,王美花没躲。你下不去手是吧?那就去告发我,让政府惩罚我。
王美花猛地哆嗦一下。她扭过头,不让他看她的脸。
马秃子不说话,似在等王美花回应。好一会儿,他说,我去自首。
马秃子转过身,王美花一阵狂抖。马秃子推开门,王美花怒喝,你他妈站住!马秃子回头,王美花恶恶地叫,你不能去!马秃子盯住王美花,眼四周的肌肉往中间缩去。他看穿了她,在她捅破那层膜的时候就看穿了她。自首不过是虚张声势,不过是试探她。可是她怕呢。她撑不住。王美花不是没有主心骨,可万一呢?马秃子已经坐过三次牢,再坐一次又能咋着?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东西,牢里牢外都是政府的累赘。他豁得出去,她不行。
不是王美花剐他,是他在割王美花。王美花已经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他仍嫌不够,问为什么不能自首?她不就盼他千刀万剐么?王美花叫,我说不能就不能,没有为什么。马秃子说,我正想找个养老的地方,你成全我吧。王美花戳着他的眼窝,你个畜生,看你敢去!马秃子反问,我一定要去呢?王美花拍打着炕席,喘息一会儿,声音软下去,别去了。马秃子说,是你求我的对不对?王美花说,是我求你的,咋?马秃子再次靠近王美花,我是畜生,还没坏到脚底流脓的地步,我听你的。不过,你也得帮我个忙。我会对你好的。我会牢牢管住嘴巴。王美花看出他打什么主意,一点点退到屋角。顺手抓了一把铲子。只要他再靠近,就让他脸上见血。她的家什挡住了他,却不能挡隔他锯齿般的声音,你不想让我管住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