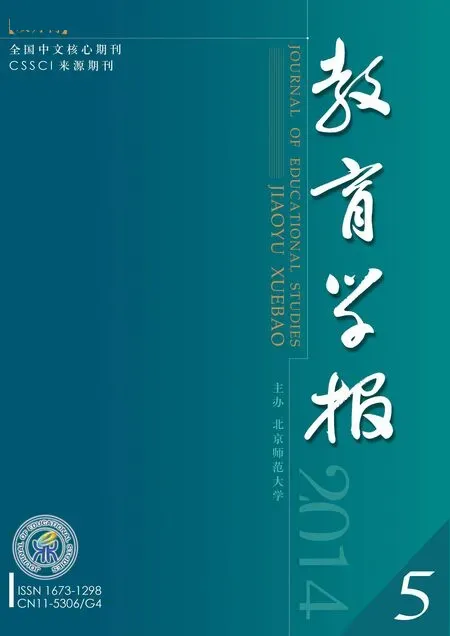“学—教”之道以感应(通)为根本机制
——儒家教育观的义理阐释
2014-06-21于述胜
于述胜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青海师范大学“昆仑学者” ,西宁 810008)
从字源上考察,汉字的教是由学发展而成的,中国人的教的概念是由学的概念发展而来的,使得教、学二字可以通用,但只是学字可以毫无障碍地通用为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学字实际上承担了表达教的概念的功能,即“以学论教”……这种以学为核心的教育话语体系直到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和制度传入中国后才发生转变。[2]
“教”、“学”之反义共字及“以学论教”,确为中国传统、特别是先秦教育观之重要特点。儒家思想尤为其突出代表。熟悉中国教育思想传统且不抱任何偏见者,大概都会同意上述见解。上述现象何以出现?高华平教授以楚人之辩证思维解之。然而,“辩证思维”固可对“反义共字”有所说明(即:学之与教相反亦相成也),却无以明“以学论教”之故,恐非的解,当更深求其故。“‘学—教’以感应(通)为机制”,或可成一解。
一、“‘学—教’以感应(通)为机制”的中国文字诠释学根据

《说文》曰:“爻者,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本此,以“爻”为“交”,乃取占卜时蓍草交互之象,而寓人与天地精神交感互通之意。“爻”示“学—教”,乃“交神”的转化和引申,以喻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交感互通。在古代中国,“學(教)”不管有多少种不同写法,皆不离“爻”一要素,实即以“感应”、“交通”为其根本寓意所在。*今人将“學”字简化为“学”,确实“简易”了不少,却失其“交易”之根,终难成“不易”之教,笔者遂以“学不神交脑灌水”讥之。
熟谂《说文》者或疑吾说而难之:《说文》明以“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学,觉悟也”以及“,觉悟也”*《说文》把“学”看作是古“”字之省,而孔安国的《尚书大传》释《古文尚书》“学半”时说:“,教也。”后释近之。为释,那么“爻”与“效(觉)”是什么关系?此自有其说。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把“爻·象·放·视·教·学”系于同一义类,认为它们皆通于“效”:
爻者,《系辞传》云:“爻也者,效此者也。”又云:“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又:“效法之谓坤。”古本皆作“爻”,是“爻”、“效”同声同义。
以“爻”为“交”,乃取蓍草等交互之形,而寓以人之作为感天应地之意。以“爻”为“效”,要义有二:其一,系指圣人作《易》,以六爻来模拟天、地、人三才变化之道(其结构与过程);其二,系指圣人承天而起、顺天而行、效天而动。一言以蔽之,以“爻”为“效”,重在强调在天与人的一体感应中,人(圣人亦人也)对于天地之道的顺成性。推而广之,则人类之一切作为,不过是顺应天地之道而成就之。正是在此意义上,“爻”、“教”、“学”皆通于“效”。《太平御览》引《春秋元命包》云:“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之为言,效也,言上为而下效也。”所谓“上为而下效”,即处上位者如何作为,处下位者即感而应之、仿而效之。《说文》解“教”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今人或以为“教”乃“”篆化之讹。其实未必如此。“教”和“”可能皆为先秦时“学—教”字的不同写法。《说文》解“孝”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承”者,继也、奉也;故“孝”亦有后继前、下效上之意。古文中尚有一从爻从子之“”字,《说文》径以“放也”、即“放效”解之。王力先生也认为,“教·学··效”为同源字[4],即它们最初本为一词、完全同音,其后才分化为两个以上读音,并产生细微差别。
综上所述,“学—教”字以“爻”(即交感)为根,以“效”为要义。所谓“效”,主要表达下之于上、后之于先、小之于大之间的承应、法效关系,其与《易传》所呈现的先秦思想世界密不可分。《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对于中华圣哲而言,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易传》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系辞上》)日移于北,则地上万物应之以生、长、成;日移于南,则地上万物应之以收、敛、藏。如此,则坤之于乾、地之于天,亦呈一法效关系,且成为一切教化关系之原型、典范。故《孔子家语·问玉》引孔子之言曰: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吐纳雷霆,流形庶物,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有物将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与圣人相参。
《礼记·孔子闲居》有一节文字与其相似而略显错乱,郑注孔疏皆释“无非教也”为圣人奉天地之行以为政教。《孔子家语》明以“天地之教”相示,如此,则天地亦有其“教”、其“学”也。这个“教”不是别的,就是天、地交感而万物应之以生生,恰如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亦如《易·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上文中的“兆”,就是感应之“几”——盖自然之感应,其初甚微而幽,其后渐显而著。天地之变,无思无为,而万物欣然以生、森然以备,生生不穷。天地以自然之变成其化育万物之功,其功至伟、其用至神。自其无思无为言,谓之变化;自其生成、长养万物言,谓之化育。故《中庸》有“天地之化育”之说。“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之教”。这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教化的典范。其中的思维逻辑并不难解。按照下法上、后承先、小法大的原则,其自下而上之层层效法路线是:常人法圣人、圣人法地、地法天(或:己法父、父法祖、人类法天地)。“在天成象”即天之“教”,“在地成形”即地之“学”,如斯而已。
清儒章学诚深明此理,故其《文史通义·原学》必将“學”原之于“效法之谓坤”: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
按照《易》理,乾与坤不仅是六十四卦中独立的两卦,也是表征阴阳相对、交合、迭运之道的根本体相,故《易传》分别以“乾元”、“坤元”称之,而后来的学《易》者称其为“《易》之蕴”、“《易》之门”及“天地之根”等。其中,乾代表着阳动、创生、主导的力量,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其属性为“健”;坤代表着阴静、顺应、辅成的力量,故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其属性为“顺”。从根本上讲,“效法之谓坤”之“效法”实即“乃顺承天”之“顺承”,是坤元在对于乾元的顺应、承续中成就变化之道、生生之德。以“学”为“效法”,突出的是“学”如坤元一样所具有的顺成而非创生特性。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之“学”,无论人们把它理解为“学问”、“学说”还是“修身”、“学做人”,它在本质上都具有顺成性:如果是“学问”,那它不过是圣人将自己所感通了的世界呈现出来而已;如果是“修身”,那它不过把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实现出来而已。圣人所以伟大,端在其生命(“气志”)与天地之化同其神妙(“如神”),在事至物交之际,能一如其准、恰如其分地与世界相感通,所谓“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
当然,常人非皆能如圣人般恰如其分地与世界相感通,因而有“教”—“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必要。故《文史通义·原学》接着说: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故士希贤,贤希圣,希其效法于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于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
“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下》)以及古字书的诸多训释来看,“学”也好、“教”也好,似乎均可训作“效”,亦均可训为“觉”。只是“教”用在使动的意义上,即“使之效”、“使之觉”;而“学”则表示主动地“效”与“觉”。“觉”与“晓”可以互训:“觉”本义为从梦中觉醒,引申为“晓”即知晓;“晓”字本义为日出天明,引申为知晓、觉知。二者的互训本身即表明:“觉”的原始意象即有感应(通)在,即人应天之明而醒来;人本能眠亦能觉,但正常的眠、觉是与日夜交替的节奏相一致的。“教”和“学”并不是相互外在的对象化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的感应关系:“教”者之指示“学”者,其行为具有施动性,但其施动并非强使“学”者成为单一的、对象化的“教”者,而是“学”者应教者之所感而起,进入其自身的生命、生活节奏,此所谓“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而“善其效法者也”,亦所谓“士希贤,贤希圣”之道也。在《文史通义·原道》篇中,章学诚又说:“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如此,则非唯众人学于圣人,圣人亦学于众人。学于众人即是学于天、效之于天。所谓“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既意味着“道”即在“阴—阳”的交感迭运之中,也意味着“学—教”之间即是“阴—阳”交感迭运的感应关系。
总之,中国传统的“学—教”概念无论在文字构形还是意义赋予上,都与《易传》所呈现的思想世界密切相关。此世界乃一“天人一体”、“物我感应”、“生生不已”之生命世界。纵向观之,即“天地—万物—父祖—己身—子孙”,世界乃以己身为中枢、承前启后之连续体。横向观之,即为“己身—家—国—天下”,世界乃以己身为原点、层层外推的同心圆。近世通儒刘咸炘曰:“万物相感,即成万事。人为本身,纵之感者父母,历史为遗传;横之感者物质,社会为环境。”[5]14-15物(人)感我而我应之,即是学;我感物而物应之,即是教。在物我感应之中,“学—教”乃一体两面之事,正如“见”之一字兼指“看见”与“显现”一样。“学—教”之反义共字,即基于此“阴—阳”交感迭运的感应原理,岂是所谓“辩证思维”所能尽之?《尚书》“学半”一语,表达的就是“学”之与“教”乃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之事也;《学记》引之,欲证其“教学相长”之意,而以“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为言,已非“学半”本旨。
石中英教授曾言:“‘教育’概念只有在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才能得到恰当而充分的理解。离开了民族文化的语言背景,我们也许只能在逻辑或技术层面上理解另一种‘教育’概念,绝不会把握它的精髓、它的质。”[6]诚哉斯言!
二、修身为意义传达之根:兼释“以学论教”之故
与《易》学世界观的直接而密切关联亦表明:以儒家为杰出代表,中华圣哲的“学—教”观念首先指向人(类)意义世界的形成、传达与建构。《易传》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系辞上》)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
《易》之道与学,说到底,即是“知死生之说”、“顺(顺者,通也)性命之理”而“穷理(‘穷’亦‘尽也’,‘穷理’即尽物之理或成物)尽性”、立人于仁义之途的道与学。此学名之为“学做人”、“明人伦”、“修身”可,名之为“圣贤之学”、“君子之学”、“义理之学”、“学道”亦可。一言以蔽之,儒者之学即是让人成为人、“成己—成物”的意义之学、价值之学,而非求知识、成技艺、谋财货的工具、技术或功利之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今人或基于现代的教育民主、平等及普及观念释之,其实二者了不相干。孔子之意盖谓:做人之学与教乃人之通学、通教,无分于种族、阶层、性别,无间于长幼、贵贱。在此,笔者以“修身”概指儒者之学。
“修身”必展开于日用常行之中。《论语》开篇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学”即修身、学做人之事,为一名词而非动词;其“习”即习行、践履人道之事,亦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之事也,其义已详于笔者之文[7];“时”者,“以时”且“时时”也,言修身之事行之于生活之各种场域、人生之各个阶段,无一时或息。至于“学文”—诗书礼乐、前言往行—亦为儒者所当为,但必本于习行,且验之于习行而可传,故《易传》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易·大蓄·象传》)相示,而曾子以“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自省。
“修身”之“身”即是“己”。在儒者心目,“己”从来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单子式孤立个体,而是处于人伦物事中的共生性存在。故齐景公问礼,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顔渊》)一个人,相对于父、祖而言是子、孙,相对于子孙而言又是父、祖;对于君而言是臣,对于臣而言又是君;对于兄而言是弟,对于弟而言又是兄……这些对生性关联是人生本身所固有的,并不存在撇离上述关联的抽象个人。最原本的“学—教”关系,即发生于上述一体、对生、互动的人伦关系之中。
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人通常译作“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8]如此翻译,虽不算错误,却丢失了孔子言说中“君—臣”、“父—子”互动、感通的深刻意味。如同“生生”一样,“君君”作为一动(动词)一静(名词)的重叠词,用法十分灵动,既可以是主谓结构(自动),也可以是动宾结构(使动),意即“君者成其为君”或“使君者成其为君”。“臣臣”之义亦复如是。如此一来,则“君君,臣臣”非仅表达了君要成其为君、臣要成其为臣,亦且表达了君只有成其为君、臣才能成其为臣,它甚至还表达了君若成其为君了、臣自能成其为臣(反之亦然)——因为君也好、臣也罢,都不是在“君—臣”关系之外而是在其中成其为君或臣的;二者一体联动,恰如一跷跷板之两端。如果说“君者成其为君”乃君之“学”,那么,它所联动起来的“臣者成其为臣”便是君对于臣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到底,就是让人成其为人,它与“生生”之道遥相呼应。此即儒者的“成己—成人”之学:在成己的基础上成人,又通过成人来成己。
笔者此举,是否有过度解释、牵强附会之嫌?我们不妨从如下三方面更予论证。首先,孔子确实十分看重并有效实践着教、学间的一体联动。上文提及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已不必赘述,《论语·述而》记曰:“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与”即大篆“”,从舁,四手,上下向各二手,取“共举”之意,故包咸《论语章句》释之为“我所为无不与二三子共之”[9]。对于孔子来说,教与学并不是外在于孔门学团日常生活的多余举措,而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体联动。在此联动中,孔子之言行就其自身人格的成就来说是“学”,就其表现此人格并作用于学者来说就是“教”;反过来,学者的人格、言谈和举动,对于孔子来说,也具有“学”与“教”的双重意蕴。以此反观《论语》,我们将会发现,体现孔子“学—教”一体联动精神的举措府首可拾,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从“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到对弟子“问仁”会因人、因时、因地进行灵活回应,无不体现了随感而应的教育精神。而颜渊以“欲罢不能”回应孔子的“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则体现了这种教、学感通的理想境地。难怪孟子会以“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赞颂孔子。所谓“时”,在教、学关系上,就是师生一体感通的时机化、艺术化、自由化。这正是儒家“教学相长”理念的实践原型,其方法论基础则是颇具中华文化特色的阴阳感应(通)学说。
其次,孔子是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信且自任的。这在孔门,向来被视为“成己—成物”一如的仁、智合一之学。《论语·述而》曰: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
从《孟子·公孙丑》提供的线索来看,这段话可能是孔子因应子贡之问而发: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很显然,子贡是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视为仁、智合一之学的。而在 《中庸》里,此仁、智合一之学亦便是成己、成物一体之学。《中庸》曰: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盖子贡尚智,故以智为体,以仁为用;《中庸》尚“诚”亦即尚“仁”,故以仁为体,以智为用。但无论如何,在孔门那里,学属成己之事,教属成人之事;学是体、是本,教是用、是末,故成己方能成人。但己身不是孤立的个人,总是在与人的对待、互动中实现己之所以为人的,故成己的同时便能成人、便是在成人,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内外之道也”。成己、成人一体联动之学即是儒家的“为己之学”。对于“为己之学”,今人会自觉不自觉地释之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或“自我超越”。其实,这种诠释是现代性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对)、个人主义思想先入为主的产物。它在诠释之前,已将己与人、个人与社会先行割裂,似乎更适合杨朱的“为我”主义,却无法切合儒家的“成己—成人”一体联动之学。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修己安人”思想。《论语·宪问》曰: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此处的“君子”,指在位之人;“修己”即《大学》所谓“修身”,即儒者之“学”;“修己以敬”,敬其身、正其身也。孔子以为,君子之事不过“修己以敬”。子路大概觉得君子若仅如此未免一自了汉,遂以“如斯而已”不断追问之。孔子进一步开导说:修己始能安人、自能安人。故朱子《论语集注》释之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积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无他道也。人对己而言,百姓则尽乎人矣。尧舜犹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诸近也。” “自然及物”, 十分准确地表达了修己与安人、学与教之间的自然感通关系。
此一体感通之道,于《中庸》则为“取人以身”及“以人治人”之道。《中庸》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为政之要,在得人心、取贤才;得人、取人之要,在于为政者之己身,而非外在的教令、规条。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己为何种人,则其所取、所聚亦如其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者,导也。所谓“道之以德”,即导之以已修之己身。对于人生意义之传达而言,政即教,教即学;为政与为教同根,皆生发于修身之学之根。关于“以人治人”,《中庸》引孔子之言曰: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朱子乃旷世大儒,而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释“以人治人”,且以“其人能改,即止不治”释“改而止”(《中庸章句》),殊失孔子本旨。孔子始以手执斧柄以伐取斧柄为喻,其所取与所执为同一尺度,故曰“其则不远”。然而,此种尺度仍需在所执与所取间打量、比照,还相当外在,故曰“犹以为远”。至于君子,则已让己身成为活的生命尺度,其所用以裁度他人者即其一己之身、一己之行。梁漱溟先生用“以人(指己身)治人(对待人)”释之,[10]深得其旨。其实,“以人治人”之道即“忠恕”之道。它意味着:用己之性行带动、感通他人即是教,且为具有最高生成能力之教。至于“改而止”,正与前面的“道不远人”相呼应,即改而止其为道远于人、远于身之病。
此一体感通之道,于《大学》即是以身为譬之道、“絜矩之道”。归结到最后,还是一个恕道。关于以身为譬之道,《大学》以“人之其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明之。郑玄注云:
之,适也;辟,犹喻也。言适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亲爱此人,非以其有德美与?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与?反以喻己,则身修与否,可自知矣。
郑氏此注打通了《论语》《孟子》《中庸》与《大学》思想,彰显了《大学》以身为譬、为喻之旨,可谓得其神韵!“喻”者,晓也(《玉篇》)。从教、学关系上讲,“喻”乃教者用口与言来告、诫、导学之者,使之明通事理。“譬”者,谕(喻)也,匹而喻之也。(《康熙字典》)“譬”是教者在相同、相类事物的匹对、比方中晓喻学之者。由此而进之于“恕”,则教、学互动已超越了表面化、外在化的言与口,而深入到身与身、心与心、情与情的共振联动之中。“恕者,如心也”(《说文长笺》);“恕,忖也,忖度其义于人也”(《礼记正义·中庸》疏)。“恕”即是在己之心、身与人之心、身的平等比观、互动中,生成切近的生活准则,既以自喻自修,亦以喻人导人。此即以身为譬之道。关于“絜矩之道”,《大学》曰: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不过是恕道的另一表述。“絜”者结也、挈也(《礼记正义·大学》注),度也(《大学章句》);“矩”者,规矩、法度也。是则“絜矩之道”即执持规矩以裁量事物之道也。此处所言之规矩不是别的,就是以情挈情、与民共其情而同其欲之己身。与外在、单一而僵硬的规律、原则、规范不同,此以情挈情之矩、之身即是鲜活而动态的生命尺度,它在物我互度、互通中裁己量物,以自己的美善之身、之心、之行,去兴发他人,以与他人共同进入亲亲而仁民的意义世界。贯穿于《大学》“修·齐·治·平”之中的,即一“恕”字。如果说“格·致·诚·正”乃尽己之心、之性、之情、之德,那么,“齐·治·平”即是尽人之心、之性、之情、之德。合而言之,即是忠恕之道。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而“修身”则处于合内外、通人我的枢纽地位,同时关联着成己与成物:内有以应人之感而竭其诚,外有以感人之心而动其身,故《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综上所述,儒者之学乃意义之学,可以“修身”括之。“修身”必展开于日用常行之中,展开于己与人的一体联动之中。所谓“以修身为本”,实即以“修身”(即“学”)为意义传达(即“教”)之根。它意味着:身修即是教,君子之嘉言懿行本身即是无形的教育力量,能发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易传·系辞上》)的神奇功效;身修始能教,那些发自教者的教言、教令,只有植根于教者的身体力行,始能发挥其劝善禁恶之教化效能,此所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古人之以学论教,其要义盖本于此。
三、呈现“感应(通)”机制之学术史与思想史意义
近世以降,以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为标志,现代中国的文、史、教育之学义无反顾地步入用“科学方法”整理传统思想之路。所谓“科学方法”,说到底就是生成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学术理论。这些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学人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之双重作用。它固然让我们获得了新的问题意识,却也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问题意识,甚至丧失了理解和进入自己的思想传统、意义世界之能力。本该在“接着说”和“借来说”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中国学术生长之路,变成了比较单一的“借来说”。百余年来,以“中国教育思想史”为名之著述,大致不出这一樊篱。
就笔者目力所及,在众多教育史著述中,能对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有深入把握者,首推黄绍箕与柳诒徵合著、据说是国人自撰的第一本《中国教育史》。处在新、旧交替,作为本土与外来思想相错杂的产物,书中亦不乏“中话西说”之处,但对古圣贤“教育大义”之把握却堪称精道。其书开篇即以“中国古圣人教育大义”立题,其中说:
凡治一科之学,必先明其学说之统系;统系不明,则散殊之事理,无由考见其指归。中国古无教育专书,而圣哲相传微言大义之散见经籍者,固自有科条纲目之可寻。学者先明其义,则古代教育之制度、方法,罔不可溯其原理,而知吾国文化卓越之所由,此固治史者所宜揭橥也。古圣人教育大义有三,一曰贵人,二曰尽性,三曰无类。虽帝王迭兴,文质相代,周衰礼废,庠序不修,而此三义未之或湮也。[11]
在黄、柳二先生看来,治中国教育史须先明其思想“统系”。这个“统系”,用古人之言表达即是“义理”:“义”者,意义也;“理”者条理也。况之今日,“统系”即思想范式,“意义”即一种学说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而“条理”即证成此价值的根本思维方式。在对统系的把握上,作者突出的是古圣人“教育大义”。况之今日,“教育大义”即所谓“教育理念”或“教育精神”,是作者之情思与历史文本共振共鸣的产物——它兼摄已然与当然,乃古人之所本有与今人之所当为的统一体。其所标“贵人”、“尽性”、“无类”三大义,非对传统思想有深入体贴与贯通者所能为。所谓“贵人”,即贵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及人之所以异于物者,引而申之即是贵生、贵生生之仁;所谓“尽性”即尽其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即“成己—成物”之“学”、之“教”;所谓“无类”,由孔子的“有教无类”发其嚆矢,乃以尽性之学为人之通学,即孔子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比较而言,黄、柳二先生之作,于“意义”之把握比较充分,于“条理”的呈现则有所未备。
笔者不揣浅陋,亦以“明其学说之统系”自任。以“感应(通)”呈现古人之“学—教”关系原理,即属此种努力之一。刘咸炘先生在《一事论》中说:“世界者,人与万物相感应而成者也。万物感应人,而学之的乃在人之感应万物。然不明乎万物之感应人,则不能明人之感应万物。”为明此理,他进一步解释道:
感应即心理学家所谓刺激反应,言影响嫌太不用力,言支配、对付则太用力,故言感应。《易传》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万物相感,即成万事。[5]16-17
刘咸炘先生特别过人之处,在于明统知类,能呈现传统思想的内在理路。他指出“感应”异于“影响”,亦不同于“支配”,很有见地。当然,说“感应”不同于“影响”,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庄子·在囿》:“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庄生本意,乃在将“大人之教”与百姓之学比作形与影、声与响相互亲和的一体联动关系。这正是“感应(通)”之道的要义所在。当然,任何譬喻都有其蹩脚的一面。刘咸炘嫌其“太不用力”,盖因在形与影、声与响的比附中,“学”过于影子化而失其能动性。不过,庄生继申之以对话或应答关系,似对“太不用力”之偏有所补足。至于刘咸炘把“感应”等同于“刺激—反应”,虽前缀以“心理学”之限定,仍不足以充分表达感应(通)之道的独特之处。因为所谓“刺激—反应”,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是有机的,传统的感应(通)之道则是有机论的。
这一有机论的“感应(通)”原理,要义有二:其一,它以“天人一体”为人的生存论前提。所谓“天人一体”,系指天、地、万物(含人类)乃一有机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从而相遇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关系,首先不是相互外在的对象性关系,而是有机生命体之同体异位关系。唯其一体,故相感应。即此而言,所谓“感应(通)”,亦可谓之“一体联动”。充分而顺畅之“感应”即是“感通”,或简言之曰“通”:“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易传·系辞上》)其二,“感应(通)”乃教者(感之者)与学者(应之者)间的生命整体互动,遵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理则,且依教者之不同生命境界,而生出不同的感应层次:“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粗矣。其智弥粗者,其所同弥粗;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同”亦“通”也。“同名”、“同居”、“同力”、“同义”、“同气”,标志着“感通”由浅而深,由表及里的不同层次。处于最高层次的“同气”,实即“气志”相通,即帝者之于其民,是身(气质)、心(神志)高度凝聚、和谐的生命整体间的互通;而处于最末端的亡国之君之于其民,只具有名分上的关联,其感应亦仅发生在单一而外在的“耳”的层面上。
近世以降,尽性成德之教为成材之教所涵盖,生命意义之学为知识技术之学所笼罩,“意义—感通”之道隐而不彰,公民道德教育日趋“公理”化而迷失了修身之本。则以学论教之“劝学”为以教论学的“教授法”、“教学法”所取代,良有以也。中国现代教育家论“学—教”之道最近古人精义者,莫过于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之说。陶先生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12]若易其“做”字为“修身”,正合儒家思想本义。只是陶先生所说,毕竟偏于经验主义之知识论,而与尽性成德之教相去甚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主体—客体”论“学—教”关系之风渐盛,继之以“主体性教育”及“教育的主体性”,又进之以“主体间性”。此类话语于救正其时教育流弊或不无小补,于深化人们之教育识见却难睹其功,遂同归于昙花一现。以一体联动的感应之眼观之,学者之于教者,究竟谁为主体、谁为客体?此似为一无解且虚假之教育理论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即对此类提问方式深予质疑:“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庄子·齐物论》)而所谓“主体间性”,说白了不就是“人—人”间性么?我们与其借来无根之说热闹一番,不如接着古人的“感通”之道往下说。倘如此,虽未有独知新见,亦不失“继人之志”、“述人之事”之令名。
参考文献:
[1] 高华平.由楚简中“教”族字的使用看楚人的辩证“教学”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70.
[2] 杜成宪.以“学”为核心的教育话语体系——从语言文字的视角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重“学”现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75.
[3] 王贵民.从殷墟甲骨文论古代学校教育[J].人文杂志,1982(5):21.
[4] 王力.同源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0.
[5] 刘咸炘.推十书(甲辑)[M].上海: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出版社,2009.
[6] 石中英.“教育”概念演化的跨文化分析[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4):22,17.
[7] 于述胜,包丹丹.儒者之学:修身与学艺——以《四书》为中心的义理阐释[J].教育学报,2013(3):112-117.
[8]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8.
[9]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85.
[10]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06-107.
[11] 黄绍箕,柳诒徵.中国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1.
[12] 陶行知.陶行知选集(第1卷)[M]. 顾明远,边守正,主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347.
参考书目:
1. 郑玄,注.礼记正义[M]. 孔颖达,等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王弼,韩康伯.周易正义[M]. 孔颖达,等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 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卓,点校.北京:中华收书局,1987.
5. 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M].济南:山东出版社集团齐鲁书社,2013.
6. 吕不韦.吕氏春秋通诠[M]. 王晓明,注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7. 王叔岷.庄子校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刘笑敢.老子古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