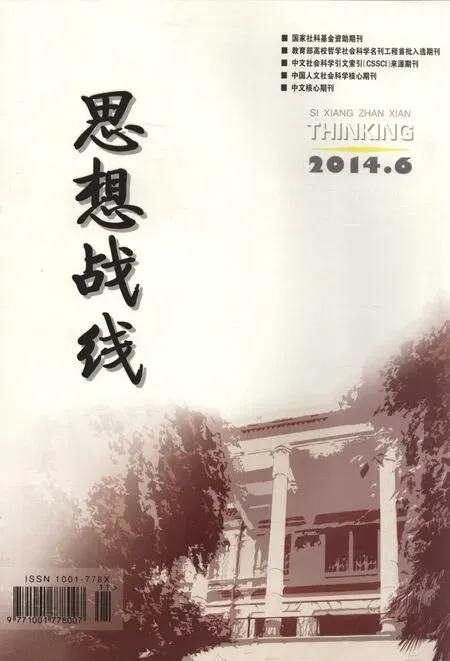遗产,从古代到现代:祖产、垃圾与奖励
2014-06-09NelsonGraburn著郑向春译
[美]Nelson Graburn著,郑向春译
遗产,从古代到现代:祖产、垃圾与奖励
[美]Nelson Graburn著,郑向春译①
从过去与现在、文化与人类学的关系维度中看待与研究遗产,遗产将呈现出动态性、易变性与转换性特质,透过祖产、奖励与垃圾理论的实践,遗产的这一动态转换与变迁过程得以进一步体现,但同样在这些过程中所显现出的遗产社会化、固态化与网络化现象与问题则值得反思与探讨。
遗产;祖产;垃圾;奖励
引 言
本文将研究遗产中所涉及的文化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的事例与维度中呈现出现在与过去、遗产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由此,文章将涉及以下要点与层面:其一,文化与遗产之间的关系;其二,祖产——家庭遗产与国家遗产;其三,遗产奖励的历史背景与 “二战”后日本遗产奖励制度;其四,旅游与遗产景点的选择过程;其五,遗产博物馆与它的观众;最后,垃圾理论 (Rubbish Theory)——从考古学到收藏品。
文化与遗产的关系:定义与人类学
其实,人类学自身从来都不曾离开过我们今天所谓的遗产。作为英国人类学奠基者、人类学最早创始人之一的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早在1871年其所著的 《原始文化》中便对文化做出如下定义:“文化是……作为人类社会成员所习得的所有事物,包括知识、信念、艺术等等。”①Tylor,E.B,Primitive Culture,London:J.Murray,1871,p.15.所以,文化本就是人类所创造、展演,并且传递给后代的一切事物,它虽然排除了自然现象,但是并没有排除凭附于自然之上的权利、信念与故事。在其书中,泰勒进一步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具体的事物与精神文化 (Mental Culture)——观念、想法、语言、方法、故事、艺术等等。在今天的人类学中,我们依然谈及物质文化,它通常与博物馆、技术与手工联系在一起,而我们已很少使用精神文化,因为人类大部分的文化都是非物质的,所以我们直接用文化来指代它。
虽然在西方文明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概念的运用已长达一个世纪,并且在此后也提出了标示遗产的概念,如遗产的有形现象和地方——世界遗产地 (World Heritage Sites)与无形文化遗产。但其实,所有的遗产都是文化的,无论其是物质的或精神的;有形的 (建筑或自然)或无形的。而反过来,我们却不能说所有文化都是遗产。因为在任何将文化标示为 “遗产”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有意识的争论与或许无意识的断言。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遗产概念已经突破了其原本作为祖产 (Patrimony)的历史意涵。祖产是其所有者所共同分享与认同的文化,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如权利、传统、主张、传家宝等。而与此同时,存在另一类财产——它也许也归属个人,只是并不在继嗣的法律认可之内,因此可以根据所有者的意愿进行转让。这便是西方遗嘱概念的起源——发表申明将部分财产转让他人,这并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祖产继嗣范围。而今天,遗产或是祖产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均已发生转换,从其原初与家庭继承的不可分割性 (如祖辈农场、手工艺者的工具等)转化成了现今族群、地域或国家文化事项的符号,成为一种群体性 “继承”。
遗产是较为笼统的文化概念中的一部分,它是有意识的选择、明确的价值,以及被公众分享的部分。而这恰与布尔迪厄 (Bourdieu)所提出的惯习 (Habitus)概念意涵相反,惯习是文化中无意识的习得、默默的分享,以及个体表达的部分。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人们早期生活中所习得的事物,而人们常常又会忘记曾经学习过又或是如何接触它们的,比如学习语言的能力便是其中一例,其中所包含的诸如品味、特定喜好与倾向性特质,使人们通常感觉它似乎是自然而然 (nature)的。惯习在人们今后的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选择事物的态度,而这些事物甚至可被宣称为遗产,而惯习延伸出的另一重要概念便是 “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遗产由文化中的物质性、自然性与无形性等层面构成,进而往往使人们觉得它是永恒的与可被传递的 (Lowenthal 1985,1996),从这一层面而言,遗产概念类似于另一术语 “传统”。 “遗产”需要被挑选出具体特质以便被支持与展示,并维持其在多元社会中民族—国家群体中的竞争,以及在分层社会中不同阶层间的抗衡。
文化奖励与遗产选择
(一)奖章、奖励与提名:文化奖励的背景与日本案例
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历了一段较长且有益的尝试性阶段。1993年在汉城举办的第1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下简称UNESCO)大会上,韩国政府便提出建立 “活态文化遗产”(人间珍宝)奖励制度。其实,奖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悠久习俗,古典时期的地中海文明,便为优秀运动员或是诗人颁发月桂花冠,这标识了当时社会的优秀标准,对持有传统的人授予奖励,有效维系了这些传统的保护与传承。
在现代社会中,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于1804年首次颁发的法国 “军团荣誉”勋章 (Legion d’Honneur)是最早的国家级文化奖励之一。这一开创性奖励结合了两个传统:其一,欧洲表彰为军民做出贡献的骑士与军士的 “荣誉与祖国” (Honneur et Patrie)制度;其二,在学术或专业团体领域中,各级政府表彰让国人引以为豪的公共服务与创新表演的层选制度。此后,这一制度迅速传遍全球,由此肯定了“国家”作为一个自主性评选单位的重要地位。现代表彰制度和国际声誉进而推动与形塑了一系列国际性事件,如现代奥林匹克盛会,而各个国际性组织则最终形成了今天以UNESCO为代表的,几乎收纳全世界所有国家为缔约成员的国际组织。
日本是最早实施一整套文化奖励的国家之一,1919年成立了日本艺术院 (The Japan Art Academy),其120名会员轮流为非会员颁发年度帝国奖与学院奖,内容涵盖美术、文学、音乐、戏剧与舞蹈;1950年,日本国家教育厅在10个被称之为现代艺术的领域创立 “艺术鼓励奖”与 “新艺术家鼓励奖”,同年,一位叫松田権六的漆器工艺制作大师,在麦克阿瑟 (Doug⁃las McArthur)将军的援助下,创设了 “人间珍宝”(Living National Treasures)荣誉称号,以寻求对传统技艺的保护;1973年,日本又新设文化勋章 (the order of culture)对上述领域和艺术表演剧场进行奖励。
1950年,日本 《文化财保护法》出台,该法案是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ICH)的直接源头,其创设了 “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制度 (更广为人知的说法是 “人间珍宝”),即传承人制度,以 “评选在各艺术、手工艺或艺术表演领域的杰出代表”,并为其详细制定各项标准:该手工艺者必须展现出曾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产品或表演,并保证是用天然材料手工制作,而且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该技能至少追溯至伊多时代,即日本被西方势力打开国门的1858年以前。那些在纺织、绘画、陶艺、金属、木材和竹子工艺方面,以及在艺术表演中出类拔萃的大师们均可被指定。
考虑到 “人间珍宝”奖励制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典范,由此应该特别注意以下3种对于传统的选取过程:其一,选取过程最简单却也存在最大问题。挑选出的代表是惟一且几乎是最后能够进行某项古老传统操作的大师,虽然这些人很容易被识别,比如日本萨摩琵琶大师鹤田锦史 (已故)、今年荣膺 “人间珍宝”的纺织大师、已90岁高龄的冲绳老人佐田,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现今他们年事已高,已无法担任起老师的角色培养后继者了;其二,拥有独特表演技艺的在演团体。如大阪文乐剧团的木偶戏表演者,由于 “人间珍宝”的认定,政府给予财政支持,防止了木偶戏剧团数量的下降,同时,通过名望与巡演,木偶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观众。虽然,木偶戏表演繁杂,且无法吸引年轻人,但是它所携带的荣誉与声望,以及团队精神与家庭式的表演,依然能让木偶戏保持目前的繁荣状态,不至于青黄不接;其三,为依然繁荣的某项古老传统选择传承人。这些传统本就没有濒临灭绝的危险,而且目前依然能够组织起保证该技艺得以传承发展的培训班。如制陶,目前有14名 “人间珍宝”依然健在,最年轻的出生于1941年。从1955年开始,共30名传承人先后被任命,目前,制陶技术是日本最为活跃的古老传统,经常举办各类展出与比赛,而且获得资金雄厚的个人、公司与机构势力的支持。而与此相比,规模略小的是日本的制刀技艺,目前有5名传承人,每年日本制刀保护团体都会组织国家级比赛,据此对新晋者进行排名,并对连续超过两年获胜的选手,给予 “人间珍宝”候选人荣誉。
从1996年开始,日本又启动了名为 “艺术计划21”(Arts Plan 21)项目,以嘉奖传统艺术范围之外的新艺术创造力。如今,日本每年投人约6亿日元 (合6 000万美元)支持具有创造性的传统、节庆、旅游与表演,这一支持力度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每年的申请者数以千计,审查委员会与专业委员从中的选取率为25%~50%。如致力于 “精准传承和保护阿依努文化”的阿依努人文化促进组织,由于该组织在保护与举办文化节方面的贡献,1994年被日本命名为 “重要民俗文化财保护组织”,成功保护了濒临灭绝的阿依努原住民文化,而且还与志同道合的冲绳琉球人文化组织通力合作。
(二)遗产选择
遗产选择过程致使了遗产的体系化与制度化,这一选择过程类似于马康纳 (Dean MacCan⁃nell,1976)所论述的对于旅游景点认同与选择中的符号公式,即地点+标示物+旅游者=旅游景点。这里的关键在于标示物 (Marker),它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某一特定标签。景点标示,即其名字与重要性通过广告、宣传牌、导游书、电视节目、地图与地图册向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进行宣扬与传播。马康纳指出,任何事物如果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公式都能够成为旅游景物或遗产物。如美国中西部用一幅写着 “邦尼与克莱德死于此”的巨大广告牌来标示自己 (邦尼与克莱德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一对富有传奇色彩的亡命夫妇)。
马康纳进一步指明了旅游点或遗产地的符号选取过程:
1.命名 (Nam ing)。命名本身是选择的重要一步。从社会众多默默无闻的事物之中命名出特别的物、地点、地方甚至是一个人。如为了选取英国科茨沃尔德村庄 (Cotswold village)作为典型的英国村庄,而通过将其 “放在地图上”(put it on the map)的概念来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以及社会与财政支持。
2.装裱 (Framing)。用显著的界限、门廊或是大门区隔出一个区别于世俗、普通的仪式与神圣空间区域。
3.提升 (Elevation)。从拥挤的人群中提高吸引物的辨识度或是拉开距离。值得注意的是,我所提到的强调某地或某人的宗教性与神圣性,神通常被认为居住得高高在上,如天堂,与神的相遇需要到山顶上或是祭台上进行祭祀仪式。
4.物理再生产 (Mechanical Reproduction)。这是一种提高声望、重要性、吸引力与神圣性的方法。通过模型、雕刻或是绘画的形式使普通事物变为古物遗迹。伴随着19世纪 “物理再生产时代”的到来,照相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一再生产环节的效率,进而挑战了事物在最原初时候所具有的神圣性光环,而到了此后的20世纪,这一挑战由于新技术的发明而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其中包括网络。再生产的扩增甚至导致了根本不存在原初的无穷无尽的影像,博德里亚 (Bau⁃drillard)将其称为幻影 (Simulacrum),尽管博德里亚的初衷只是将幻影用于指代美国虚假与再生产的文化产品,比如迪斯尼乐园,而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圣诞老人或是复活节兔子。
5.社会性再生产 (Social Reproduction)。通过效仿而对地方或人群进行重构,比如新塞勒姆纽约,可通过游戏、电影等方式对宗教与仪式的再造,对基督教或佛教生活的重构,或者是对某位世俗领导者的重塑。重要的遗址或是人类展演同样屈从与此相同的过程,而且表演者与展演的持续性重塑是遗产保护与维系的重要部分。
从过去到遗产的转换是一个选择性并且系统化的过程,其类似于诺拉 (Pierre Nora)在所著《记忆之地》 (Lieux de Memoire,1989)中对历史战胜记忆的论述。历史是被社会所认可的“过去”版本,是从众多基于人类记忆的物质遗存与文献中挑选与记录下来的;而记忆,是群体共同分享的关于他们过去的回忆,这里的过去是“活态的”,它持续性地添加不同的要素而舍去缺乏生命力的部分,它总是根据当下的想法与价值来重塑自身态度。由此,诺拉指出,记忆是易变的、活态的,是不依赖于文献记录与遗迹而与当下群体对应的部分。而历史是从基于已被社会成员所认可的关于过去的文献记载中所挑选出的,记述它们的或许是历史学家,或许是遵循于国家意志与民族意识的学者。历史由此 “杀死了记忆”,在这一意识结构的背后,再没有活生生的记录。对此,诺拉对法国的过去做了大量调查并指出,如今法国普遍的记忆之地均化为了官方性的遗物与遗迹,以此提醒公众曾经有重要历史事件发生于此,这一过程非常像马康纳所论述的旅游吸引物的挑选过程。
历史对待记忆的方式如同古迪 (Jacky Good⁃y)在其著作 《野蛮思维的驯化》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中所指出的书写对待口述与记忆的方法:书写的持久性最终磨灭了诗性的口述历史与记忆,并最终杀死了记忆的技巧。记录与文档取代了诗歌与故事。不论是诺拉或是古迪所论述的有意的选择版本,都非常类似于过去150年中遗产及其登记名录的出现。对于文化历史的检视均指向过去的去民主化过程。尽管一些学者不断地提出 “过去属于每一个人”,确实,过去依然持续性地存在,但是它已经落人了被训练、被专制与被专业化的过程中,就如同法国旅游社会学家莫里斯与索特 (Jean Maurice&Gaetane Thurot,1983)所指出的那样,它已成为一种书写性与官方性的历史。选择者,亦即官方遗产的创造者,如今已成为享有特权的一群,他们代表着官方意志、商业利益等等,成为了阿什沃斯 (Ashworth,1996)意义上的符号性书写。
然而,民主的力量依然在发挥作用,虽然书写控制了过去,但是学界与学校的公众性与民主性依然在扩散传播,更多人以此能够进人到对过去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此外,近些年来非官方的围绕历史与过去的观点也正通过网络的普及而越来越得以传播。
遗产博物馆与观众:隐喻与转喻
(一)博物馆:遗产的与继嗣的
现在来讨论遗产博物馆与其观众之间的关系,为了便于理解,我将运用早先关于遗产博物馆与它的拥有者、观众之间关系的分析思路讨论该问题。其实,博物馆是遗产的隐喻,类似于一种体系化的阐释性分析;而转喻则是遗产重要的象征性部分。
博物馆包括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区域、地方与国家博物馆,以及一些科学性博物馆,如伦敦南肯辛顿英国科学博物馆。尽管大多数博物馆都聚焦于一个 “物”类 (object),但是人们越来越致力于创建一种多元性的 “活态”(living)博物馆,如今从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到华盛顿,都可以听到一种呼声—— “把博物馆从墙上取下来” (bring museums out of their walls),而其中一个成功的尝试便是史密斯尼博物馆在华盛顿购物商场中的年度民俗节庆,商场中的 “国家草坪”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展演艺术家集中到了一起。这其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缩影。但是节庆的组织也面临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开始就遭遇到的选择与表述问题。
从下表中我们看到,横排顶部是 “主人”,这里的 “主人”不一定是法定继承人,也可以是拥有挑选、安排与展示遗产条目权利的人,而且同时也选取与控制着观众,显示出一种递增性的民主趋势,或至少正在增加着的观众数量。而这种趋势伴随着19世纪大众教育的普及越发明显,与此同时,博物馆成为了一种杰出的教育机构,而且其年度的财政拨款的使用也越来越倾向于对不同观众的教育目的。

表1:博物馆与观众
沿着表往下,我们会看见欧洲 (也是美国)的历史序列,它表明了这一历史期间观众及其兴趣的变化。重点在于,虽然今天大部分国家已经不再有皇室与贵族,但是他们遗存下来的器物与遗址在今天依然与我们相伴。由此,遗产博物馆,包括遗址与展演依然拥有大批的观众怀揣着不同的期望、需要来接近这些贵重的器物。这被概括为是一种对权力与博物馆权威表述的需要,以及对遗产中世袭传统与控制的需要。我的分析框架基于西方博物馆,而我也经常叩问亚洲博物馆:如果博物馆是一个储存重要的神圣与世俗器物的储藏室,那么像京都早在公元742年便开始储藏天皇遗物的正仓院 (Shosoin)便可视为最早的博物馆之一。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观众,就好比基督徒集中于中欧,佛教徒集中于印度,而博物馆中则只是被区分为国家的、宗教的或是世界的遗产。
(二)观众:个人的与政治的
从表格与其他的学者的研究中,可以概括出3类参观博物馆与遗产遗址的旅游者,这一定程度重叠于厄里 (John Urry)所论述的游客凝视(gaze)的两个版本:一种是浪漫凝视 (the Ro⁃mantic Gaze),在此凝视中,观光者想要在神圣的遗迹、遗产或艺术品中寻觅一种亲昵关系;另一种是集体性凝视 (the Collective Gaze),观光者首要认可的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身份,然后在某一时机或舞台上提高他们的社会声誉。前者,类似于马康纳所论述的现代人的疏离感,他们需要通过在历史、自然、宗教与药物中寻得一种日常生活之外的真实。但是,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马康纳模式只能概括当下旅游者情况的一部分。
若简要回顾今天博物馆或遗产地与遗物的观众,其中有所谓的 “当下贵族” (contemporary nobility),如经管董事与捐赠者,有以受教育为目的的旅游者等,他们均是集体凝视的代表。博物馆之所以矗立于此,是因为人们想要它们在那里,它们是可以去参观、去对话的便捷之地,人们经常去那里并非因为它们真实,而是因为那是一个可以展示出他们关系的便捷舞台。许多博物馆都在试图使自己能更加吸引这些社会群体,它们目前正在模仿迪斯尼世界:以一种不真实的缩影来构筑真实与权威的堡垒。
也许大量的博物馆观众与文化遗产旅游者都想要从它们的观光经验中学习些什么。但是在沉默与敬畏中也并不尽然,就像马康纳意义上的旅游者相信真实也会撒谎,而且还屈从于这种谎言,这些 “严肃的旅游者”或是会进行平等的集体性学习或是相互学习,他们还可能形成一个层级式的集体,拥有一个领导者,他或许会是教师、讲解员或是导游,他的追随者们想要学习他们正在观光着的文化与遗产,以及隐匿于幕后的过程,包括后台的选择、重塑、研究,以及文本制作。
而在旅游与博物馆参观中,阶级与教育是关键因素。厄里基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相关行为而概括出的两种凝视类型的研究,在此又进一步推进。在浪漫凝视中具有更多教育意味,人们愿意更多地沉浸于自然、异国之中;而集体性凝视,人们在假期中形成一个具有阶层的工作团队,并在其中度过美好时光,他们并不介意真实与否,当然也不惧怕孤独。

图2:垃圾理论
垃圾理论:从物品到垃圾到遗产收藏品
汤普森 (Thompson)搭建了遗产中社会阶层同价值取舍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极富启示意义的图表中,显示出了社会产品的生产,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所消费的两类物品:一类具有持久特性而趋向于在时间流逝中价值的递增;而另一类则是由于易耗或被丢弃而计划被报废。虽然这些物品会被简单地划分为昂贵的与廉价的,但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通常是社会阶层,比起财富与收人,等级阶层更多是根据教养与教育来作为物品价值的衡量标准。持久性物品的主人都很富有,就像他们所持有的物品价格会更高一样,其间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身上附着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这些主人知道什么是值得拥有的,他们甚至相信这正是在于物本身的 “先天品味”(innate taste),一种来自于特权环境中的先天禀赋。
易耗品很难具有持久性,当它们被消耗后便被轻易丢弃,如轿车、衣服、廉价首饰或是DVD。只是关键在于,倘若通过 “变换主人”(change of ownership),那么这些被丢弃的或是被用过的物品便会重获新生,如通过跳蚤市场、廉价买卖、二手商店、教堂市集,或是从柜子里、阁楼上与谷仓里被找到。物的新主人,怀揣着增值、个人品位或是时尚的眼光来审视它们,甚至开始收集与重塑这些物,也许会将它们展示在橱窗前,或许会放置进当地的博物馆。这一切增加了这些物品的可见度,然后志趣相投的人们开始了有趣的旧物交换会,进行博物馆捐赠或是开始文章与图册的撰写。因此,一个新的收藏品就这样在怀旧气质与当下的反现代品味的氛围中成为遗产。一个简单的例子便是玩偶,玩偶被留下来、收起来、遗忘又随后被发现,人们寻找到它们并且收集它们,用于装饰房间或交易;而更大尺寸物品是轿车:每年都有大量的轿车丧失它们的价值,就像前图中的下降曲线,但它们却很少达到零界线,原因在于虽然它们中的大部分被废弃,但有一些则被存贮于车库里或仓库中,之后又被发现,它们中有的被穷人留下来,而更多的是被怀有怀旧情怀的人保留下来,于是在经过了20年、30年甚至40年之后,它们重焕魅力,甚至博物馆都竞相想收藏它们,杂志开始赞美它们,拍卖会里到处都有它们。而另一种情况是,少量轿车则从未曾丧失过它们的价值,待它们变“老”之后会更具价值,当它们被收藏进博物馆后,便会成为 “无价之宝” (beyond price)。我就曾经拥有它们其中的一辆——谢尔比眼镜蛇福特289轿车,我1964年买下它,而令我万分诧异的不仅仅是其火箭般的速度,更是人们所投射于其上的关注与赞美,事实上,到了2012年,国家运动汽车博物馆想要在整个夏季都展示它。对某些人而言,一部眼镜蛇轿车便是英国/美国独创性、简约性与完美性的杰作。
其实,除了商业领域,在不同的领域中我们均能看见这种类似的复制过程。比如在遗产研究中的考古学,它培养了大批专家去挖掘、收集、解释、展演与公布已被不同文明所丢弃的记录;而且我们也有地理学家,他们同样挖掘、收集、解释、展演与公布不同物种的残存物。我曾经在英国新坎特伯雷的煤矿中收集到石炭纪化石,并且写了一篇围绕它们的获奖论文,如今它们被展示在大英博物馆中。而且今天获得UNESCO命名的地质旅游地或地质公园,展示出了当下人类文明所认可的另外一种遗产的探索与发现。
结论与讨论
文章中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作为一名旅游者如何去理解与欣赏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过去的变化?我们在如今这样一个即时性、多重关系与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如何把文化推向旅游者与社会?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简单,尤其是最后一个。我们已看到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遗产与消费,其间伴随着遗产道德与学习,同时在所谓的专业化过程中充斥着个人或地方对遗产的潜在侵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记与标准化,实际上扼杀了其与真正创造它们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但是众多民俗与展演均面临这样的挑战:为了旅游者而使用 “真实”作为参考标准;为了当地人的自豪感;以及人们所认为的展演与所编辑的DVD版本之间的差异,而且这一登记过程在网络的流传中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遗产的类型变幻多端,在这里,我们应该理解与掌握的是遗产的研究方法与内涵:首先,在文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文化研究中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且这种早期的彻底的研究体现于对惯习的洞察。惯习是一种我们很难觉察到的文化知识,除非它被挖掘或被质疑,否则很难改变;其次,我们被众多研究者不断告知仪式展演是下一个围绕庄重、愉悦与精神研究的十分透彻的事项,它们大大提升了体验的强烈程度;再次,这些研究都超越了通常的学校知识,甚至透射出电影、影像与博物馆痕迹;最后,在过去的10年中,网络已经渗透进各个领域,它为我们打开了更多的世界,而其中的一些世界是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孩子们能够阅读到更多西方与亚洲的世界,并从中了解自己,但是这种接触、多元与去地方性(placeless)的网络关系,导致了一种平面且变幻无常的世界影像,比如它所谓的教育,很少得到监管且很难与父母及老师分享。
在此,电脑网络预示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蔓延趋势:对权威与地方的挑战与替换。过去,当地的人与地方通常是保障真实与权威的最后防线,但是如今通过此精妙的网络连接,任何地方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传播。这也是遗产最终转变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终极力量,所以,如今通过UNESCO,任何人都可以宣称拥有世界遗产;而且专业人士与管理者聚集在一起,共同登记这些地方与事件可见与可知的部分。如今储存于电脑中的信息成为了事物真实性与持续性的保障者,避免当地人在为我们保持他们遗产活态性方面有所闪失。
但是,这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挑战,很多“战士”都在抗拒这种使用电脑来储存知识与文化的方式。而当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通过网络建立相互的联系时,也许也更容易达成对文化、实践与真实性本质的共识,只是这已经是一种文化、实践与真实性的新形式了,而这种真实性也已成为了一种曾经对于上帝敬畏的内心之旅了(inner journeys)。
Baudrillard J.,La sociétéde consommation,Paris:Gallimard Press,1979.
Becker,H.,Art Worl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Bourdieu,P.,Outline of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Goody,J.,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7.
Graburn,N.H.H., “Whose Authenticity:A Flexible Concept in Search of Authority”,Cultura Desarrollo[Havana: UNESCO], vol.4,2005, pp.17~26.
Graburn,N.H.H.,Anthropology in the Age of Tourism,Guilin:Gu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vol.34,no.5,2012,pp.1~16.
Hafstein,V.,“Intangible Heritage as a List:from Masterpieces to Representation”,Laurajane Smith,and N.Akagawa,eds.,Intangible Herit⁃age,New York:Routledge,pp.93~111,2009.
Lowenthal,D.,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Lowenthal,D.,Possessed by the Past: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
MacCannell,D.,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Schocken,1976.
Nora,Pierre,“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 de memoires”,Epresentations,vol.26,1989,pp.7~25.
Thurot,Jean-Maurice and Gaetane, “The Ideology of Class and Tourism:Confronting the Dis⁃course of Advertising”,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0,no.1,1983,pp.173~189.
Thompson,M.,Rubbish Theory:The Crea⁃tion and Descruction of Valu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Tunbridge,J.E.and Ashworth,G.J.,Disso⁃nant Heritage: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J.W iley,1996
Tylor, E.B., Prim itive Culture, London:J.Murray,1871.
Urry,J.,The Tourist Gaze,London: Sage Publication,2002.
(责任编辑 段丽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阶段性成果 (11&ZD123)
尼尔森·格拉本 (Nelson Graburn),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UC Berkeley)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国际旅游研究院创始人(America Berkeley CA,94710);郑向春,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云南昆明,6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