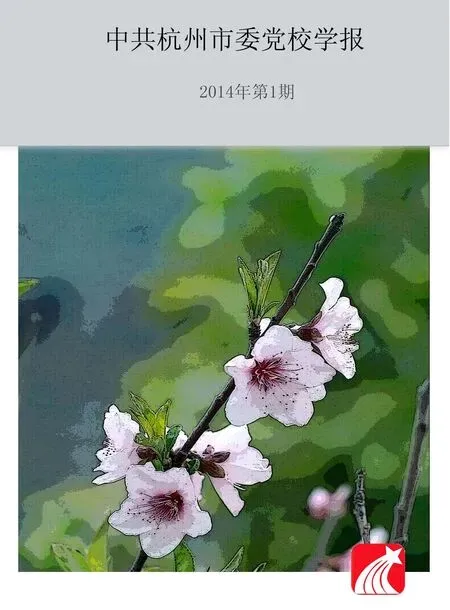陈炯明互助进化论思想探析
——《闽星》时期的考察
2014-06-07付金柱
□付金柱
陈炯明互助进化论思想探析
——《闽星》时期的考察
□付金柱
闽南护法时期是陈炯明政治思想转化及确定的关键时期,其政治思想由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转变为互助进化思想。陈炯明的政治思想以“全人类社会”主义的互助进化观为基础,以“不为罪恶的奴隶”的人格观及生活与生趣兼备的人格养成路径为辅翼,以“金刚性”的暴力革命观为手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互助进化思想体系。
陈炯明 互助进化论 政治思想 《闽星》
陈炯明(1878—1933)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任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并因在政治上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发生冲突而决裂。陈炯明幼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成年后入海丰师范学堂和广东法政学堂始接受西方法政思想及其观念,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同时,在时任法政学堂教员朱执信的影响下,陈炯明接受了革命思想。陈炯明思想再度发生转变则是辛亥“3·29”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之后,他参与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组建的“支那暗杀团”,通过与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时相往还,使其与闻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为其所吸引,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一些核心价值和观念成为他终生持守的信条。
陈炯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时代背景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是中国20世纪初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一种社会思潮,一度占据了革命思想的中心地位,被认为代表当时世界上最激进的革命思想,[1](P12)以致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许多要人都不同程度地信膺过无政府主义。在参与支那暗杀团活动期间,没有直接资料表证陈炯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程度,根据现有资料,他广泛而深入地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则是在闽南护法时期。在这一时期,陈炯明以《闽星》为阵地,发表系列诗文,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互助进化论思想体系,进而演变为陈炯明独具个性的政治人格特质。
一、《闽星》:闽南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源
陈炯明自1918年8月30日进驻漳州建立援闽粤军司令部,至1920年7月12日率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是为闽南护法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陈炯明偏居闽南一隅之地,致力于政治、社会革新的地方建设,使其辖下的漳州地区被称为“闽南的俄罗斯”,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一致称誉。同时,他敏锐地捕捉时代潮流的涌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发表电文支持学生运动,办报纸,写诗文,使闽南呈现出新文化革命的风潮,他的政治价值观也第一次通过系列诗文为世人所知悉。
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陈炯明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他发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痛斥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吾人处此,不独为自卫计,当抵死力争,即为世界永久和平计,亦宜表示各联盟加入国,俾速觉悟”。[2]由于陈炯明的支持,漳州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新文化运动展开之后,陈炯明经常邀请朱执信等党人赴闽,[3](PP302-303)在粤军总司令部与许崇智、邓铿等高级将领“讨论学术,注意新思潮之发展”,热心赞助革命党在上海的新文化宣传刊物《建设》杂志的出版。[4](P24)为了使新文化运动在闽南生根发芽,陈炯明听从朱执信的建议,邀请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陈秋霖、刘石心等来到漳州,成为在漳州宣扬新思想的中坚,最主要的则是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日刊。
以“在福建为圆心的起点运动,做新文化运动”[5]的《闽星》半周刊,创刊于1919年12月1日,发行3个月刊出了16期之后(2卷8期),因为准备粤军回粤的军事行动,正式停止出版。另外,有感于闽星半周刊在“智识锢蔽的漳州”产生的回响不大,1920年1月1日,又创办了《闽星》日刊,每日出一大张,目的在“为地方人士增广见闻”。[6]陈炯明除了热心支持、倡导漳州的新文化运动外,还亲自一试身手,系统阐发自己的思想。在《闽星》半周刊两卷16期中,发表了4篇专文、5首白话诗和1通信函。从陈炯明此一时期的著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互助进化论思想的形成。

《闽星》半周刊刊发陈炯明诗文篇目表
无政府主义思想旨在构建一种具有最大限度个人自由的理想社会,物质财富得到公平的分配,公共职责通过自愿达成的协议而得到履行。但是,在怎样实现这些理想目标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存在着重大分歧,主要可以区分为四大思想流派:个人主义、互助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7](P23)这些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播转到中国,而灌输于当时中国人脑海中的主要有:(一)蒲鲁东的社会革命论和私产制度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及补充达尔文进化论的互助论;(二)反对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备黩武;(三)反对剥蚀人权的买卖婚姻而主张自由恋爱;(四)强调个人自由、大众平等、社会有组织没有阶级;(五)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壁垒,促进世界大同;(六)反对麻醉性的宗教,集中人类智慧充实物理世界。[8](P6)陈炯明在参与支那暗杀团时就与无政府主义者相接纳,广东光复后同刘思复等交往愈趋密切,成为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从事政治活动的庇护人,在漳州又邀请了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等帮助他实施闽南的新文化运动。因此,陈炯明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互助进化政治思想。下面即以他在《闽星》半周刊上发表的4篇专文,来讨论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
二、互助进化的“全人类社会”主义观
陈炯明的政治思想,总体上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进化论的影响。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同达尔文主义一样,他从研究生物演化入手进而研究人类。但是,他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及人类演化规律,不同意把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他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以及人类进化的真正因素。克鲁泡特金断言,“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并且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可以消除竞争。因此,互助是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克鲁泡特金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没有权威、没有强制的社会才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完美社会。[9]陈炯明虽然在法政学堂学习期间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但是,后来随着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接触及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吸纳,他的进化论思想开始发生转化,即由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进化论转变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他的互助进化论思想在《闽星》发刊词中得到系统的阐发。
同所有的进化论者一样,陈炯明把人类发展的历史描述为一个永无止境、永远向上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炯明强调思想的重要作用,“世界的进化和人类的思想很有密接的关系”。他认为,世界进化是由人类在里面努力创造的,“经历许多年代逐渐表现出来”,而人类的创造主要是由思想所促生的。思想的变迁达到什么程度,人类的进化就自然体现出来;如果人类的思想永久不变,那么人类的进化乃至于世界的进化就自然停止了。因此,为了不断地创造一个新世界、完成健全的进化,就一定“先要改造全人类的思想,为齐一的努力”。这种“齐一努力”的人类思想,不是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竞争法则,而应是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共同适应、毋相侵碍”的互助思想。只有这样,世界才能不断地永远向上永无止境地进化,才能达到进化的极致,即“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10](PP402-406)由此可见,陈炯明论述人类进化的观点,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想痕迹清晰可见。
陈炯明对于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还没有达到“共同适应、毋相侵碍”的思想境界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无国界的博爱互助思想境界还无法达到,因此国家主义仍然是必要的,“当然不能抛弃的”。当时国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秉持这种观点,他们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提倡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先求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以恢复国家主权与列强平等。基于无政府主义人类互助的原则,陈炯明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认为“国家主义就是政治野心家借来做一种‘欺世诬民的手段’”。为什么这样说呢?陈炯明认为,强者利用国家主义来侵略,固然不必说了。即便革命党人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因为受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为了“抵抗他的危险,唤起民族自觉,促进民族努力”,拿国家主义来维持生存,这固然可以得到一时的效验。但是,“效验到了表著的时候”,这个民族便会养成一种“排他性、自大性、睥睨世界的野性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国家主义便会被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迷信政治的万能,恣意侵略,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来扰乱世界、残杀人类。陈炯明呼唤,“试看近世各大强国,那一个不是从弱国爬出来的呢”!因此,他视国家主义是动荡的根源,“世界各国,有了国家的形式,一日不能打破,人类社会就一日不得安宁”,而要有“打破国界的武器”,就要依靠“全人类的思想,因为思想的努力,应该用来创造进化,不应该用来制造罪恶。全人类的思想能够变迁,一齐努力,就会造成一个打破国界的武器出来”。在这里,陈炯明认为要求人类破除国界,互相帮助,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因为“世界人类,本来各有博爱本能,既然晓得爱国,何不教他充其本能,去爱全人类社会?”于是他提出以“全人类社会”主义的主张,来替代国家主义。[10](PP402-406)陈炯明的“全人类社会”主义主张虽然迹于迂阔,不近实际,但是他对国家主义所产生的政治结果的分析,堪称洞幽烛微。
三、“不为罪恶的奴隶”的独立人格观
在全人类整体进化的政治理想基础上,具体落实到单个的个体人格发展,陈炯明由徐谦的一句话——“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引发出“我就是上帝,不为罪恶的奴隶”的呼吁。陈炯明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做主人,即每个人的“形骸只做了精神的寄寓”,每个人的“官能感觉只听了精神所指挥”,独往独来,并与社会、宇宙的精神融为一体,在理性中经营社会、宇宙的进化。这样,经过理性证悟的个体精神,与社会、宇宙达到同一,“就是社会总体的精神,也是宇宙总体的精神”。相反,如果要靠上帝赐我恩惠,赦我罪恶,来安排我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就是没有自主的生活,就是奴隶的生活。
陈炯明说:“罪恶是人人不承认去做的。奴隶没有人格,更是人人不甘心去干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没有人承认作恶,也没有人甘愿当奴隶。但是,社会现实吊诡并可怕的是,虽然我们不愿去做罪恶,却干了罪恶勾当;不甘心去做奴隶,却从事了奴隶的职业。恰恰是这最吊诡最可怕的事情,实际上却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因为今日的社会,“到处都是魔鬼,到处都是罪恶”,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因此,陈炯明呼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都要尽自己的力量,打破罪恶的藩篱,摆脱做奴隶的命运,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去创造真正的人生”。
那么,什么是罪恶呢?一言以蔽之,“凡是剥夺或束缚自由平等的事情,就是罪恶”。自由平等是人的自然本性,却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被剥夺或束缚了,而每个人又不能去打破它,成了罪恶的奴隶。因此,“恶制度不解放,恶习惯不打破,恶心理不改造,这个社会就要天长地久做了一个罪恶圈,牢禁我们一生不能自拔”。可是,要解放恶制度、打破恶习惯、改造恶心理,单靠几个少数的“先知先觉”者是不行的。因为,一方面,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力量有限,无法冲破这个庞大的罪恶圈;另一方面,即便少数先知先觉者革了国家的命,但是,“第一层奴隶解放了,第二层奴隶依旧承袭起来”,就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人的奴役,挂上了共和的招牌,“说是人人都有参政权”,可是一些自称优秀的先知者,“抢了个头等奴隶来做”,依旧制造起罪恶来,自称霸主,叫其他人做他的二等、三等……奴隶,历史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罪恶循环。所以,要想摆脱做奴隶的命运,就要“人人都晓得社会里面所有恶制度,就是奴隶制度,所有恶习惯,就是奴隶习惯,所有恶心理,就是奴隶心理。能够这样猛醒,大家耻以为奴隶,就要努力去推翻去创造,这是不怕不能革命的”,[10](PP408-418)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有独立人格的个人。
四、“生活与生趣”的人格养成路径
陈炯明对个人人格发展的阐述,是从“破”上下功夫,即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打破剥夺或束缚自由平等的恶制度、恶习惯、恶心理,成为真正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在《生活与生趣》一文中,陈炯明则从“立”上着手,探讨个人人格的养成。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二是生趣。前者是物质的,是人的第一生命;后者是精神的,是人的第二生命。两者对人生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缺失任何一方面,人生都有破产的危险。但是世人只知求生活,而不知求生趣,“只知生活要求满足和优越,却不知生趣更比生活为要紧,愈要求满足和优越”。因此,由于只追求生活的满足和优越,就生出独占的问题,由独占就要生出阶级的问题,由阶级的问题,就要生出斗争的问题。问题愈演愈烈,一部人类史就成了斗争史。究其原因,一是只知有生活,不知有生趣;二是只知有共同的生活,而不知有平等的生活。
为了消解人类间永无休止的竞争和争斗,首先就应该明了人类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生活。陈炯明认为平等的生活,就是“各尽所能以生产,各取所需以分配,一律平等”。如此,则就没有了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满足,就用不着去谋独占和优越,也就弄不出阶级和斗争来,只要凭着互助的精神就能达到平等生活的目的。从陈炯明平等生活的生产、分配方案来看,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可是,同时他又不赞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根本不会生出阶级和斗争来,因此,这时起作用的只有无政府主义的互助精神。这样,人生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有余闲去寻求生趣了。
什么叫生趣?陈炯明认为,“万物生活之中,各有各的生趣”,“万物的灵活,各有各的不同”,因此,“万物的生趣,各有各的存在”。万物生活之中,都有周围的对象,能吸收对象的精神,来发达生趣的本能,这个生趣就比生活更有意味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在生趣方面就更有力量。陈炯明认为,人类的生趣又可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精神作用的生趣(科学的),第二,是精神生活的生趣(哲学的)。”对于中国人有无生趣,陈炯明很悲观。他说,中国人一直“浑浑沌沌过了日子”,说到生趣,“直是无产可破”。因此,他认为要救济中国生趣破产的现状,首先应该使中国人知道,不仅人生不可没有生活,更不可以没有生趣。其次,要努力救济中国人的生活问题。救济生活问题,不能拿西方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去做工夫,而“应该拿人类主义平等主义的一个群性去做工夫”,互援互助,没有独占的利益,人人平等生活,这样生活问题就解决了,然后才可谈到生趣的救济。陈炯明认为,生趣问题的解决不能从国家主义入手,这样决不能成功,反而弄坏,而“应该拿一个个性去做工夫”,个性发达后,“就觉得宇宙的材料,社会的精神,取之无穷,用之不竭”,[10](PP423-427)这样,生趣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陈炯明关于生活与生趣救济的观点很有特色,即生活问题必须施以群体平等的工夫,不要谈个性,不要谈自由;而生趣则相反,必须从自由的个性上着手。
五、“金刚性”的暴力革命观
在此一时期,陈炯明对革命问题亦发生系统的阐述。陈炯明对革命问题发生讨论的直接诱因,是康白情、戴季陶刊发在《建设》杂志上的两通书函。实际上,陈炯明作为一名有着一定资历的革命者,对革命问题早就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康、戴讨论革命问题的书函,正好引发了他的思考,以此为由头作专论系统表明自己对革命的意见。在这篇《评康戴两君论革命的书》中,陈炯明表述了他对革命的一些具体看法。
其一,革命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这是一个发生在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期的老话题,当时陈炯明在私人信函中就已表明了这个观点,[10](PP260-261)借此机会又详加申论。在康白情的书函中,有这样一句话:“革命的事业也就不是可以让给哪一部分的人专利的”。对于这句话,陈炯明发问:“专利的话,是从哪里来呢?”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之所以如此说,是有意为孙中山遮护。接着,他就直接回答,“革命两个字并非孙中山的别号,革命党三个字也不是孙中山一党立了案的老招牌。我们只管去做革命党人,中山先生决没有把专利的成案,来和我们打官府。”表明自己对革命的看法,并为孙中山“辩诬”。由于革命的事业是要个人牺牲的,不是为个人谋利益的,实际参加革命的人,就是拿牺牲个人的生命作为底本,才能出入危险,从事革命的事业。由于革命的这种性质,无丝毫利润可图,因此,根本不可能成为某些人的专利,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参加革命,并且也不要求思想和手段有多么的高超丰富、高人一等,革命只需身体力行,“用手不用口就得了”。
其二,革命党是革命的团体,是一个统称的名词,不是各个的分子,也没有新旧之分。陈炯明认为,既然革命是践行的,就不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是一个什么分子,只要在革命进行当中,投身于革命事业,那么就可以称作革命党人。反之,如果以前你是革命党人,但是在革命时脱离了革命事业,或是从事革命以外,还分心去干一些与革命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么就不是纯粹的革命党人。陈炯明认为,革命党是一个统称的名词,无论政治革命还是经济革命,其革命的侧重虽然不同,但“均称得为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因时代的要求,革命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会出现昔时的革命党人和后起的革命党人,但是无论革命内容、思想如何变化,什么时候加入革命党,都无新旧之分。在这个关于革命的认识上,陈炯明是很激进的,他进一步推论,只要是革命的,就是新的,不革命无从谈新。不要革命则已,只要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去实行,就要“革命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革命也”。
其三,“革命是一种事,人的美德是一种事”,两者不必要产生关联,即革命与道德是两码事。陈炯明认为,革命是一个实行问题,当奔走于革命的时候,就尽可能去干革命的勾当,不必解剖他的性质如何?节操如何?而一个节操、德行上佳的人,如果不投身于革命,那么也是与革命事业无补的。其实,陈炯明在这里所进行的革命与道德的划分,主要是指不要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人身依附关系带到革命事业中来,并不是说革命是不讲道德的。如前述,他认为革命是讲牺牲、不计利益的,对于康白情引孟子“富贵不能淫”来品评革命党,陈炯明直接指出:“要做一个革命党,还有什么富贵呢?”并建议:“我们中国的字典,应该删了这两个字才好些。”由此可见,陈炯明对革命党的道德性是有所要求的。
其四,革命需要必要的暴力形式和手段。对于戴季陶在书函中提到一个革命运动的新形式,即“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和手段”,陈炯明表示反对。他认为,革命的事业,往往与平和的主张相反,应该以“金刚性的态度”,采用暴烈的手段。陈炯明提出,当今世界革命有两种潮流,“一是俄之李宁(作者按:即列宁)主义,固把政治暴力去达他理想社会的组织,一是美之工会主义,也用罢工怠工的暴力去收拾资本家的生命”,都不是平和的手段。因此,平和与暴烈,只是手段不同,“和人类的进化没有什么重大关系”,没有高低优劣之别,而现在的国内政府,“都恃海陆军为暴烈的高压”,[10](PP431-440)要打破这高压,实在用不得平和的形式,必须采用暴力的手段。
综上所述,陈炯明以《闽星》为阵地,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表明闽南护法时期是其政治思想形成最为关键的时期。他的互助进化政治思想主要体现的是以平等互助、独立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念,更多的是要求摆脱束缚、压制自由平等的制度与习惯,呼唤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要求生活与生趣的养成和“金刚性”的暴力革命突破。陈炯明这一互助进化的政治思想,主要源自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亦含有中国本土儒家传统的因素。他曾计划写一本《孟子社会主义》的书,阐述孟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思想,以其与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相融合。[11](P956)同时,儒家的大同思想也是他思想来源之一,特别是他的超国界、超种界的大同社会理想,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乡贤康有为基于中国传统“三世观”而形成的大同思想的影响。
[1][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申报[N],1919-5-17.
[3]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4]陈演生,黄居素.陈竞存先生年谱(增订本)[M].香港:龙门书店,1980.
[5]闽星广告[J].建设,1919(5).
[6]闽星报社启事[J].闽星,1919(7).
[7][英]米勒、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海隅孤客.解放别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9][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0]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11]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黄俊尧)
D693
A
1243(2014)01-0047-05
作者:付金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邮编:163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