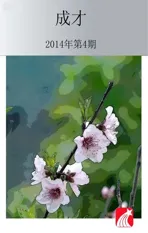如何走出文学作品僵化解读的误区
2014-06-06黄礼贵
■ 黄礼贵
如何走出
文学作品僵化解读的误区
■ 黄礼贵

有一种批判语文高考试题的强力证明是作家不会做根据作家本人的文章设计的阅读题。散文《寂静钱钟书》入选2009年福建高考试题,作者周劼人说他只能得1分;散文《岳桦》入选吉林高考试题,作者任林举说他的回答与标准答案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固然暴露出某些语文试题的设问方式可能有死板僵化的缺陷,但这一质疑可以简单地引用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一段情绪颇为激烈的话来回答:“古典主义的批评从未过问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看来,文学中没有别人,而只有写作的那个人。现在,我们已开始不再受这种颠倒的欺骗了,善心的社会正是借助于种种颠倒来巧妙地非难它所明确地排斥、无视、扼杀或破坏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罗兰·巴特随笔选》)可以说,如果认定一篇文学作品的作者就是解读作品的终极裁决者,那么这类看似前卫的语文高考批判者自己就选择了一个因循保守的逻辑。
文学作品解读的社会——历史分析法就是传统的知人论世法。以高中语文必修4宋词单元为例,讲柳词必然要讲“奉旨填词”“白衣卿相”,讲苏词必然要讲“乌台诗案”“黄州惠州儋州”,讲辛词必然要讲“缚贼南归”“美芹悲黍”,讲易安词必然要讲“美满优裕、悲慨感伤”的人生分期。古典诗文如此,现代文学作品亦然。讲鲁迅《药》结论无非辛亥之失,讲曹禺《雷雨》落脚在资本家周朴园之伪善,讲徐志摩《再别康桥》必定补充其与林徽因之间的恋情故事,讲朱自清《荷塘月色》之“不宁静”总是归因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种固化的文本解读方法本无可厚非,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比如古典文学中数量巨大的用于社交唱和酬答的诗文,创作背景对于解读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课堂设计的最大弊端尚不在于造成具体哪一篇文学作品解读的偏颇,而是造成学生获取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的模式固化。日复一日的文本解读都是社会历史、知人论世,学生自然而然形成这种程序性、策略性知识:了解作者和时代背景是解读文学作品的前提,反之,文学作品后面如若不曾附上“作者简介”则束手无策。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红楼梦》解读的“索隐派”,这种程序性知识一旦固化极易成瘾,不是有红学家得出贾宝玉就是纳兰性德吗?不是有教师讲《醉花阴》把李清照之“愁永昼”归因于她与赵明诚虽情好如初然膝下无子之惨痛吗?
为什么这种社会——历史或者说知人论世的分析方法如此传承千年广有市场呢?这和我们民族文化中讲出处、讲出身、讲传承、讲道统的传统有关。历朝历代的政治终究是路线之争、派系之争、山头之争;《水浒传》中众多好汉争相与宋江结拜兄弟,即使这样,一百单八将排座次时还得看出身、渊源,而不只是论武艺、军功;如今小街穷巷贩夫走卒都喜欢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于政坛八卦,大概也是这种文化基因决定的。
罗兰·巴特用“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手指自己的假面具”这个比喻来概括“全部文学”,恰恰表明文学语言所叙述的材料具有多种可能的解释。在文学教育中,宽容的态度胜过对时代背景的精细考证。即使《汉书·苏武传》这样经典的史学名篇,如果学生认为苏武可以投降匈奴,也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在厘清“忠诚与背叛”的基本价值取向之后,也完全应该给思想来一次松绑。毕竟在“朝廷”“君臣”“社稷”这些历史名词之上还有“人”“人生”“人类”这些更为本原的概念。
要扭转这种思维僵化单一的文本解读模式,看上去难其实也简单。那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讲《雷雨》时,周朴园是否伪善不是争论不休吗?教者不必大包大揽,只管叫学生从文本中找依据。如果学生从周朴园在不熟识的人(此时只知是“四凤的妈”)面前“汗涔涔”“苦痛”而认为老周对侍萍始终情深意切时,教者也不必为是否“政治正确”而恐慌。再举西文文本解读为例。如果文学作品全是像高尔基《丹柯》那样的“讲道理的小说”,我们的课堂就省事了。然而小说生态的多样性实在让人目不暇接。节选自雨果长篇小说《九三年》的课文《炮兽》中,保王党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固然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面人物,但在课文节选部分,他是那样沉着果决,那样英勇刚毅,全无反派人物常见的阴险狡诈、猥琐颟顸,这对习惯于泛意识形态分析的授课者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没想到在“革命”“阶级”“国家”这些宏大名词之上还有普世的人道主义精神。地主、贵族、富足、奢华、矜持,这些词藻长期被我们的话语系统所痛斥、所唾弃,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的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却一反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传统,竟然对这种看上去“腐朽”“堕落”的生活无比留恋,完全站在了革命文学的对立面,那么站在讲台上的我们是不是做好了文学教育回归文学本真的准备?
布鲁纳有言: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以一种简化的、理智上是诚实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段的儿童。“简化”“理智的诚实”,简言之就是多考虑儿童的立场。纵然教师采用的是以教为主的教学系统设计,那么只要教师注重了“前端分析”,对学习者、学习需要及解决问题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自然可以实现奥苏贝尔所谓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的效果。比如武汉教科院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袁汉杰送课下乡执教《荷塘月色》,他既不回避“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难以索解的文眼句,也不生硬地把学生拉向教师预定的答案轨道。袁老师充分倾听学生的见解之后,提供无力抗争现实、思乡、家庭矛盾等三个情感解读途径。不仅如此,袁老师进一步总结说没有唯一解读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这就好比《林黛玉进贾府》中分析“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一句,教者一般要乘机大掉书袋,什么“木石前盟”“神瑛侍者”“绛珠仙草”很要费一番口舌。其实这应该不是最重要的,贾宝玉这样说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心心相映,是由他的审美情趣决定的。退一步说,我们甚至可以承认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这种“一见钟情”的神秘意识发生机制尚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抒发了改造世界、主宰国家民族前途的革命豪情。这是教参上的定论,教者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指点江山”那几句词总结给学生。可是学生是否对“改造世界、主宰国家”的革命豪情有发自心底的敬意和兴趣呢?墙上“做一题会一题,一题决定命运;拼一分高一分,一分成就终生”的励志标语提示我们:或许这个时代的学生有另一种的人生境界。教者哪怕抓住“恰同学少年”一句,提出几个问题:年方弱冠的毛泽东有些什么样的同学?这些“书生”课内课外怎样安排学习和活动?效果怎么样?今天在座的诸位“同学”能从前辈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扪心自问,我们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语文课堂上再一次加高毛泽东的伟人形象对学生情感熏陶、价值观建设又能有多大意义?匍匐在分数下的高中生,游走于游戏之中的大学生,通过这类文学作品的阅读,倘若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为琐屑而严酷的现实所“矮化”,进而重拾历史传统,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家国天下意识,那才真是功德无量。
学习不是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这样看来,上述问题设计可以看作是“抛锚”,再进一步,也可采用支架式教学模式。按孔子“登高必赋”的说法,在曹操《观沧海》、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望岳》或《登高》等古诗中挑一首或几首,让学生合作探究古往今来个体生命的情怀思绪倾注于自然山水的一般范式,让神性回归到人性,让充满热情积极投身社会建设的青年学生,成为复兴中华的志士。而正是这样的青年、这样的志士,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串起了不能断裂的链条。
人们经常引用叶圣陶“教材无非是例子”的著名断语,也就是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按照维果斯基的说法,任何教学设计都不能只停留在学习者的“现有发展水平”,而是要着眼于学习者的“明天”,达到和通过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具体到文学作品解读,就是要教师放弃真理持有者的身份,敲碎附着在文学作品上的非文学的坛坛罐罐,引导学习者进行适应其终身发展的自主探究,才有可能深入文学作品阅读的洞天福地。
(作者单位: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中)
责任编辑 王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