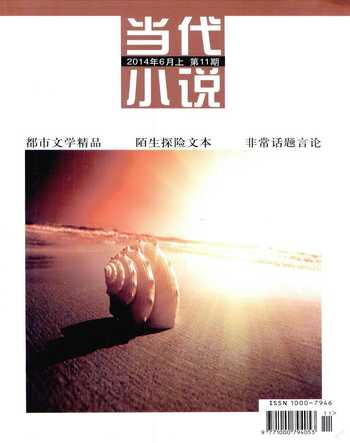郝庄那人
2014-05-30程相崧
程相崧
1
程富渊没有个儿子,这新近让他愁得不行。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要愁,早就该愁。可大闺女小玲都已经嫁了人,二闺女小惠也长到十八九了。这些年里,他从来没有为这事儿这样愁过。这些天,他却忽然日怪地愁起来了。他的理由是,从前自个儿活蹦乱跳的,用不着为这事儿操心,也没闲心为这事儿操心。现在突然地病下来了,一病下,就有工夫好好想想这件事儿了。
他不知道得的病叫啥名儿,却能感觉到这病劲儿大得很,牛性得很。冲过来一下子就把他撂倒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个正站在石板路上看光景的人,冷不防一下让他摔在地上,“当啷”一声,脑袋就啃了地,浑身也散了架子。他眼冒金花,站都站不起来了。那病却还不肯放过他,撂倒之后还坐在他身上,拿腚暾他,暾得他喘都喘不过气儿来。程富渊得病是在农历的四月间,正是将要收获大蒜(这里年年、家家都要种蒜)的季节。程富渊心想,没料想的,眼看着就要收大蒜了,俺却病下了。俺的个娘亲,这可咋整哩?立夏就要拔蒜薹,小满就要挖蒜头儿,就这样死猪一样躺在床上,咋能行哟?
不行又有啥办法?他一开始是想好好看的。他盘算着,看好了,还有好多事儿等着人做哩。可是。金乡县人民医院的专家却跟他说,你这就是个慢病,只要静心养着,没啥事,吃好喝好,一时半会儿就算想死还死不了。死不了是死不了,可想跟从前一样拾起来身子。再到地里去做活儿,那是想也别想了。你得的这是个富贵病。以后一辈子都不用再干活了。他听医生说完这些话,心想,住不住院也没大意思,便让女人抓了些药,用地板车把他拉回家里来了。回来之后,一天到晚被女人跟二闺女小惠伺候着。程富渊有时候就想,若不是半个身子木木的没有感觉。若不是一张嘴歪歪扭扭地说不清个囫囵话,这日子恣意得也赛过神仙了。在床上躺了几天,女人就又给他买了把躺椅,竹子的,能折叠和放开的那种。吃完饭女人就把那躺椅放在院子里或者院门口,把他架上去。他觉得躺在躺椅上比躺在床上强多了,至少不知道的人远远地看过来,看不出他是个病人,还以为他是躺在那儿恣儿哩。可恣儿哪有这样恣儿的?一躺下就没个头儿啦。他觉得。再好的事儿一天到晚弄也就没意思了。别的不说,就说跟女人做的那个事儿吧,一天到晚弄也是个够,更别提一天到晚总在椅子上坐着。
从前地里的活计,都是他操心出力来弄,现在躺在椅子上,自然还是想着地里的事儿。他女人黑女虽然这些年地里的啥活儿也跟着干,可每一件都是他事先计划好安排好的。啥时候犁地,啥时候浇水,啥时候种蒜,啥时候打药,啥时候拔蒜薹,啥时候挖蒜头,她不需要动脑筋,也从来没有操过心,跟着他干就行了。他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有一天做不动了。会有一天连句话也说不清白。现在他不行了,让女人一个人谋划,他还真是担心她会想不周全。二闺女小惠哩?就更不用提了。这女娃儿一年前才从中学下学回来,农田里的活儿她还任啥不会哩。
太突然了。这病来得太突然了。
这时候,似乎才显出一个男娃娃儿在家里的重要来了。想想,他家里女娃儿倒有两个,大的小玲嫁出去了,婆家在五里外的郝庄;二的小惠呢,连媒还没有说就。家里缺的就是个男娃儿嘛。如果家里有个男娃——假如小玲是个男娃吧。一个已经娶了媳妇成家立业的男人——自然能顶起来一个家。退一步讲,就算小玲是个女的,换成小惠是个男娃儿,十八九的半大孩子,也一准能把自己肩上的这条担子接过去了。可惜的是,俩人都不是男娃。
女人黑女不想给他心里添愁烦。哭也到地里没人的旮旯去哭。从地里回来,脸上还带着隐隐的笑影儿。她说,地里的活计不用你来担心,虽然不会计划,不会安排。好在跟人家一样种的都是大蒜,人家啥时候干啥,咱也跟着干啥。话虽这么说,他知道女人只不过宽他的心罢了。有些活计虽然可以计划到,却未必能干得来。就拿给地浇水来说吧,百十斤的水泵,就不是女人能弄动的。拿着老虎钳子接电,胆小的女人也有些做不来。幸好,这年该浇地的时候,小惠去郝庄把那人叫来了。那人来家帮着忙活了两天,才把拔蒜薹前的那一遍水浇了。
说实在的,一开始程富渊简直把郝庄那人给忘了。为啥会这样哩?他想,莫非自个儿是打心里把他当成了外人?要说,那个人也不算外人——可不算外人。又该算啥人哩?他有些说不清。郝庄那人是他的大女婿,是农田里的一把好手,干啥有个啥样子。这年,蒜薹没有老在地里,蒜头也并没有烂在地里,说起来全是郝庄那人的功劳哩。其实,他大女婿有名有姓,他不知道这些年家里人为啥从不叫他的名字。而用“郝庄那人”来代替。仿佛给农药取名666,给麦种取名4531,都是个代号。过去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想,许是那人来相亲那天。二闺女从街上跑回来报信儿,一边跑一边喊着:“郝庄那人来了,郝庄那人来了”,便让他有了这么个奇怪的外号儿。说实在的,头一次见面,他对这个未来的女婿却并不怎么中意。二十来岁的半大孩子,却蓄了一脸的胡子。瞅上去比他还要老成一些。他第一眼就没看中。媒人领着孩子走了之后,他没有明确说不行,但态度总有些消极。没想到的是,小玲却非常满意。明里暗里地交往了几回,一来二去,非要嫁给他不可。女大不中留,嫁就嫁了吧。结婚之后,这络腮胡子在干活儿上倒没让他失望,并不是他原来想象中的懒汉二流子。
今年的蒜季,多亏了郝庄那人的帮忙。一提这个事儿,黑女就一个劲儿地赞叹,说这个女婿真是比儿子还强。不但女人这样说,村里人也这样说。平素里,村里人吃了饭都要在程富渊家院门口的那棵大榕花树下凉快。村里人在那儿乘凉,程富渊也躺在那里听他们说话。大家都赞叹说:黑女(富渊瘫痪之后,村人提到这个家时,一家之长也不知不觉变成了黑女),你命真好,摊上了个勤快又能干的好女婿。
程富渊坐在那里不说话,心里却是美的。
如果村里人都说这样的话。这事儿也就没了。程富渊心里也就没啥烦恼了。可巧是那天,村里一脸皱巴皮儿又总是在丧礼上问些事儿的那个老人f他是村里的大老知,即主持安排丧葬婚礼等事儿的人)却说了一句话,说得程富渊心里怪不痛快。那老人说啥哩?那老人说:
“女婿再好,有时候总不顶儿子的用。”
程富渊心里一动,没有说话。
“咋说?”村里有人似乎没有听清白,又似乎听清白了,却并不赞同那话,所以打问道。
皱巴脸皮仿佛觉着这问题不屑回答,咳出一口痰吐在地上,才不紧不慢地说:“譬如说吧,老人走了,启坑打穴的时候。第一锨的血土,又有谁能替儿子挖的?出殡的时候,要摔老盆子了。又有谁能替儿子摔的?”
人们缄默了。
“这事儿在别的村,也都不成个问题。懂规矩的人少,没这些讲究。可咱们程庄咋能跟他们一样哩?咱是宋朝大儒程颢、程颐的后人,跟别的村儿一样,那多让人笑话?村里建着供奉两位夫子的祠堂,那本自北宋一直延续下来的家谱。就在村里的二程祠里摆放着,足足几十卷,每一卷比方砖还要厚。过年的时候,你们不也,都去看过哩?如果在那部家谱里你后继无人,你咋有脸入土见自己的祖宗哩?”
人们听了皱巴脸皮这一番似乎乘胜追击的话,都低着头到一边儿思索去了。
从那天开始,程富渊就觉得。有些从前认为眼下根本不用想的事儿,现在该好好地想一下了。
是的。地里的活儿郝庄那人是能帮着做不少,可女婿毕竟只是女婿,有些地方就是代替不了儿子。
村里的那个大老知那天说得对,人死了之后,选好了坟地,都是要让儿子来踏踏血地。挖上一锨头血土的。在程庄,如果没个儿子,那抔血土谁来给你挖哩?
2
这件事儿也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按照程庄老辈人的说法,如果没有子嗣,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还不止一条。其中之一就是过继一个儿子。这个方法很简单,在同宗里找一个侄子,兄弟家的可以。叔辈兄弟家的也可以。约集齐对方的父母跟族里有威望的老人,说好在你百年之后他给你挖血土,给你摔老盆。你撇下的家产遗物呢,也都归他所有。当然,除此之外。在老人健在的时候,双方还有如同亲生父子般的抚养及赡养义务。双方签字画押,见证人也按上手印,这事儿便算谈妥。谈妥之后,一千人便到家祠给二程先祖磕头。举行仪式,打开家谱,在你名下写上过继的这孩子的名字,就算是你儿子了。这个情况虽然普遍,但更适合那些没儿没女的老光棍儿。如果没有儿子,却有女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招养老女婿,也即入赘。
这个事体,程富渊打心里早就盘算过,这两个办法,只要拿到一处一比较,就能轻易分出好坏。过继一个,不是自己的孩娃儿,却要在死后把财产分给他,总没有招一个划算。那样的话,家产等于说是给了闺女家,并没有跑到外面去。他从前是没怎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若不然,当初把郝庄那人入赘过来,又会过日子,又能干活儿,倒是一件挺美的事儿。当然,现在说这都晚了,眼下可以考虑的就剩下小惠。
从那天开始,程富渊跟黑女就开始张罗着请媒人来给女儿小惠提亲。这里的惯俗,在儿女的婚事儿上,总是女方家里矜持些,男方家里积极些。都是男方请了媒人到女方提亲。富渊两口子为了给小惠及早找个合适的人儿,就表现得有些积极,把这习惯反了过来。他们找了好几个媒人,媒人也的确尽心尽力地给张罗了几个半大孩子。有些孩子一听说要入赘,就散鸟尿了,见也不见。有些孩子虽然一开始愿意见见,可一听说未来的老丈人是个瘫子,是个花钱如流水的药罐子。就觉着以后一准没啥好日子过,也就借故推脱了。再后来,终于介绍成了一个。男娃儿十九岁,人很老实。在见面儿之前,媒人跟他说结了婚要到女方家里来过活。他也同意。这样交往了一二十天,富渊跟黑女两口子觉得差不多了,就拾掇了些饭菜,把那孩子叫到家里来。族里几个上岁数的也都请到场,一起吃了顿饭。吃完了饭,黑女跟小惠收拾干净碗筷,端上茶来,几个人陪新女婿喝着茶,说着话儿。
“你跟小惠成了亲,你就是我们老程家的儿子。”村里一脸皱巴皮儿的那个老人先开口说。
“那是,那是。”那半大孩子说。
“富渊呢,是没有男娃儿,等他百年之后,血土就让你挖,老盆子,也让你摔。”
那半大孩子又是点了点头。
“有一条,你姓儿要跟我们的姓儿,姓程。”
这回,那半大孩子没有点头,而是不解意地盯着众人。
这也难怪,入赘归入赘,别的地方的入赘可都没有改姓这一条儿。不但女婿不改姓,将来生出娃儿,也是跟爹娘谁的姓儿都可以。可程庄人觉得。宋朝理学大儒二程的后人,怎能跟别的村儿一样?改是一定要改,不但要改,能让他姓程,能让他用这个“程”字,也已经是对他的恩典了。
“招到村里来,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跟咱的程姓嘛!”皱巴皮老人瞪着小黄眼睛说,“你没听清白?咱程家老祖宗是宋朝的二程,让你姓程,多荣光哩。”
“是哩,是哩,咱的姓多好,”另一个村人说,“咱是一个程哩!成成成成成,不用说。这事儿一说也准‘成…。
那孩子愣了愣,仿佛并不知晓大家说的这个似乎颇为重要的“二程”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二程”跟他能扯上啥干系。一群人看那孩子不说话,都觉得这事儿约摸有门。越发七嘴八舌起劲儿地说起来。让谁也没想到的是,说着说着,那屁孩子竟然抽抽搭搭地哭开了。他边哭还边把两手夹在裤裆里,紧紧地夹着。像是别个要拿刀割他的命根子一样。
人们忽然不说话了,盯着孩子,半天才有一个人说:
“不愿意就不愿意,哭个尿哩。”
这样的结果,是任谁也没有想到的。让他姓“程”,按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哩,却并没有办成。这《百家姓》里,难不成还有比程更好的姓吗?那孩娃儿回去第二天,就让媒人捎来信儿,说要退婚,散茄子了。对于这件事儿,村里许多人都想不清白。几个老人经历事儿多,琢磨了半天。才开解说,这半大孩子虽然性子绵软,心里头却是个倔驴子。嫁了这憨熊,日后准也没个好过。姓程多好,咱程家祖上是宋朝的二程,大儒的后人,脸上多荣光哩。
不久之后,家里就又给小惠介绍了一个。这孩子五大三粗,虽然没上回那个文静,也没上回那个好看,却的确有把子力气。那回小惠喊他来帮着拉粪车,粪车装得都冒了尖儿,他还嚷嚷着让装哩。他拉着这大约也只有牲口能拉得动的几百斤的粪车,还轻松地吹起口哨哩。这半大孩子来家里帮着干了几天的活儿。家里人对他都很满意。
这事儿都毁在几个娘们儿身上。
那天,那半大孩子来帮小惠锄地,跟小惠一前一后,扛着锄头走到半路。村里几个女人就跟他闹着玩儿。闹着闹着,一个女人就说,嫁到村里来,你就能姓程哩。这女人说这话的意思本是给他透露一个好消息。没想到的是,这女人刚一提改姓的事儿。那孩子就恼了。
“站不改名。坐不改姓!”那半大孩子说。
“改个姓儿算啥?”女人拿眼瞅瞅小惠,“能有个女人晚上给暖被窝儿,让我改啥姓我改啥姓。”
“啥女人不女人的?没女人照样弄得成!”那半大孩子说,“不日人日狗,省下钱喝酒。”
女人们听这半大孩子的话,似乎有些二杆子的味道。
女人们还没来得及弄太清白,没想到那半大孩子说完这话,竟然就从肩膀上撂下锄头。撇下一群瞠目结舌的女人,转过身一闯一闯地滚蛋去了。
这是啥人哟,这是他妈的啥人哟!
小惠回到家,捂着被子就哭了三天。
村里人都不解,说改个姓儿就能要他的命吗?更何况改了后不是让他姓别的啥。是让他姓程哩!天底下人麻麻地跟蚂蚁一般多,能有多少人有幸姓上这个程哩?大家满肚子疑惑地把这荒诞事儿学给皱巴脸老人,老人听了之后,抿了口茶水说:
“当个程家人,那是八辈子荣光的事儿哩。若不是老辈里积了阴德。这辈子咋能摊上这样的好事体哩?这操蛋的毛孩子,真是不懂个尿!”
这几日玉米地里的草长得膝盖高,小惠儿原说好了让那半大孩子帮着来割草。人家这一走,草就割不成了。
小惠就又去叫她的姐夫——郝庄那人。
3
程庄人弄不清白的是。虽然程姓甚好,虽然改成程姓也甚好,可那些半大孩子就是不依。一次不成两次不成,小惠的婚事儿也就这样搁下了。
农田里的活计是不等人的,挖完蒜之后,棉花、玉米一天天地往上蹿个子。给玉米上肥料的时候,郝庄那人来过几次,忙了几天,给棉花打农药的时候,郝庄那人又来过几次。郝庄那人从前来家的时候,是有些拘谨的。让他坐他就说不累,让他喝水他就说不渴不渴。仿佛总是把自己当成了个客人。后来,郝庄那人来家勤了,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在地里干完活儿,回家来之后。接过小惠递过来的洗脸盆子跟毛巾,扒光了膀子就蹲在那里洗。洗完了头脸,还要洗胸毛,洗胳肢窝儿。这些都洗完之后,就旁若无人地坐在桌子前吃饭。也不推说不饿。也不客气地说你们先吃,你们先吃。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一样。有时候,程富渊看着看着,就感觉气得不行。气归气,气完之后,连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仿佛为这事儿不该生气似的。也是,有时候他就会想,如果这人是他的儿子。不就该是这个样子吗?可这毕竟不是儿子,他就觉得稍微有些别扭。
程富渊只是觉得别扭,而村里人呢,就渐渐觉出点儿什么其他的意思来了。天旱的时候,乡灌电站里给农田电网送了电,各家就争着占井浇地。有一家人清晨拉着水泵去地里早,回来之后就抵着头儿跟邻居小声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这事儿说来也平常,那就是她看见小惠跟她姐夫在地头浇水,小惠在畦埂子上蹲着。身上披着她姐夫的褂子。
这事儿仔细想想,其实也平常得很。郝庄那人自己也有地,也要在这几天浇水,所以,白天就没有工夫,晚上才有时间过来帮老丈人家浇。浇地的活儿一个人干不了,尤其是晚上,更需要个帮手,所以小惠就跟着帮帮忙儿,照照手电啥的。浇了一晚上地,累得不行,一早晨的时候,两人就蹲在地头休息。因为露水重,天气冷,郝庄那人便说,我脱了褂子给你披吧。小惠推让了几次,看姐夫诚恳,便接过来披在了身上。如果说有啥不对的地方,也许他们为了防备别人的闲话,应该避避人。在有人可能看见的时候,把褂子脱下来还回去。当然,也许他们原本是避着人的,可是早晨雾气重,远处的小径在雾中若隐若现,所以在看见人来的时候,就没来得及。
可是呢,这事儿经那女人的讲述,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女人说。晚上冷成那个样儿。光披个褂子哪行?白天就披个褂子,晚上还不得搂抱到一处?女人还说,她往前走着走着。就看见小惠踩在畦埂子上的白脚丫了。蓝色凉鞋里露着粉嘟嘟的脚趾头。那脚丫儿那个嫩样儿,让人恨不得放嘴里吮。郝庄那人能把持住?就算能,女人说她走过去的时候,还悄悄回头瞅了一眼,瞅见小惠蹲在那里的两个大腚盘儿,圆溜溜地像布口袋里装着的两个篮球哩!郝庄那人看不见?他眼瞎哩?
人们就说,俩人不能没点儿啥事儿。
这话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程富渊的耳朵里。程富渊躺在那里不能动,就有些英雄气短的意思。他把个脸涨巴得通红,眼珠子血呲呼啦地盯着他和她,嘴里唔哩哇啦地乱叫。他想,日你母,日你们的母!你咋能披着你姐夫的褂子哩?你咋能脱了褂子让你小姨子披哩?富渊伸出那个稍微能活动的胳膊朝前狠狠地一抓,抓住了一股空气。他恨恨地想,如果能够着,我一准一把把那褂子给扯将下来,然后再往那不要脸的女子脸上劈脸扇两个耳光。
那件事儿之后,人们都说,那狗熊是尝到了腥头儿哩。要不然,在拾棉花的时候,明明活儿不重,也没见小惠去叫。郝庄那人竟然自己就来了哩。来了之后,就跟小惠一块儿去地里拾棉花哩。郝庄那人用自行车驮着小惠下地,俩人有说有笑。不知道的人看上去还以为是小两口哩。村里人仔细盯着,心想,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早晚让我逮住。果不其然,有一次,就有人发现,他给小惠挤棉花包的时候,搂住她的腰,搂了好大会儿,才松开哩。日娘的,挤个棉花包用花那么长时间?
“狗日的,打我们老程家女人的主意哩!”村里许多人愤愤地说着。牙缝里溅出些酸水水。
人们就观察得越发仔细了。
不久之后。果然,他们就又让人给碰见了一回。那是掰玉米的时候,郝庄那人跟小惠从玉米地里一前一后地出来,当着小姨子的面儿,郝庄那人扛着满登登一大袋子玉米棒儿。上半身却布丝儿不挂,就赤着光光的脊梁哩。村里人看到这个场景,既生气,又觉得不解气。心想,若是他们真做了啥,这会儿也已经做完了,没有能够亲见。日娘的,真是后悔没有早来一步,没有及早冲进玉米地里逮个正着。
村里人想要逮个正着,没想到刚过几天,就果真逮了个“现行”。那一日,几个人在富渊家门口说话,郝庄那人也在。小惠是刚去马庙集买了苹果回来。一塑料袋的苹果,红红的,馋得人淌口水。一圈儿的人,谁不想咬一口哩?可是,小惠她拿出来一个在压水井前洗了洗,口里说吃哇吃哇,手上却头一个就递给她姐夫哩。她难道不晓得避人?她是忘了情哩!日娘的,弄了一圈儿人一个个大长脸。
“可怜啊,富渊兄弟!”村人说。
“狗日的倒会趁火打劫哩。”村人又说。
“不怪人家!”另一个人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哩。”
“咱祖宗老早就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又有人说,“咱程家门就没出过这样闺女。”
“程家历代读书识礼,出了这样的。早该吊起来打死了。”
“切!”有人就这样叫了一声,不知是恨,还是在骂。
这样说着说着,村里人仿佛觉得越来越过瘾了。
村里的那个皱巴脸老人一开始是沉静而安详地捋着山羊胡子,捋着捋着,却忽然大喊了一声:
“杀!”
村人都让皱巴脸吓得不轻,半天没有再说话。
4
程富渊听了女儿跟女婿的这些风言风语,时时就想,这病既然好不了,还不如死了干净哩。他这样想着想着,没过两个月,果真就死了。也许,连他自己到死也没弄清白,是因为他这样想才死了呢。还是因为他要死了,才会生出这样的想法。
相比之下。倒是村里人弄得更明了些。想得更清白些。村人都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富渊是让小惠跟郝庄那人给气死的哩!
程富渊的死让村里人感觉有些突然。有些措手不及。那意思仿佛是,光顾着看郝庄那人跟小惠的热闹,没想到富渊就嫌人冷落他了。就死尿了。
在程富渊死屎了之后,由皱巴脸牵头儿,村里人张罗着给他踏坟打穴,料理后事的时候,才发现麻烦来了,到现今给富渊挖血土的人还没有找下哩。村里几个上岁数的老人,吃掉几支烟之后,说这事儿也好办。咱村里的辈分是“怀、玉、秀、渊、元、相、传、大、千、年”,富渊是渊字辈儿,从村里元字辈里找下几个年轻娃儿,给他叔挖血土摔盆子。
一会儿,几个元字辈儿的娃儿都找来了,问了一阵,竟然一个都不肯。有的说,穷家烂舍的,谁给他挖血土摔盆子哩?图个啥?有的说,就他家,除了个小惠,还有啥值钱的东西?——就这个小惠,也还是只能干看着过过眼瘾。
“我给叔挖!”郝庄那人说。
村里几个老人瞅了瞅他,在心里都画了个问号。心想,眼下也只有让他挖了。话说回来,郝庄那人是女婿,该不着这个。莫非,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接老丈人家的财产?
日娘的,野心不小!几个老人一商量。说这如意算盘不能让他打成。所以,他们很快合计出了拒绝他的理由一、二、三、四。然后推举出一个能说会道的代表,去跟他谈了。
“挖是可以,可你能不能继承他家的财产,还得另说。”
“行!”郝庄那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日尿的,没想到竟这么容易。负责跟郝庄那人谈话的老人愣了半天,才清白过来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一边回身一边愤愤地嘟哝了一句:日娘的!一肚子的话都没让人说,一身的本事都没用上。日娘的!那意思仿佛颇为委屈。
程富渊的葬礼,村人都仔细看着那女婿有啥表现,小玲有啥表现,还有小惠儿有啥表现。仿佛是,任谁有啥差池让人看出来,等着好好收拾舅子的!没想到的是,一连三天下来,他们始终也没啥把柄落到人的手里。幸好的是,在第三天傍晚出殡下葬的时候,人们就在悄悄传说着一个大秘密了。
这个秘密就是,刚才,据在礼账屋里帮忙的人说,郝庄那人给丈人上礼竟然上了两千哩!
两千块,一提到这个数儿,人们都有些惊异。按照程庄的规矩,别人家女婿给丈人上礼都是一千。他却上了两千,足足是别个的二倍哩。这样琢磨着,许多人从心里都感觉有些惭愧了。心说,没想到呀没想到,没想到这杂种竞这样有良心?没想到这么久的时间,大家竟然错怪了他!同时呢,村里别个有女婿的人家,也似乎都有些因为嫉妒而愤愤然了。
“两千算啥,不还有小惠哩?”不一会儿。有人恍然大悟地道。
冷不丁的,像是炸响了一个大雷。唢呐不响了,日头也看不见了。人们都感觉身上的血一起往头上涌。日娘的,刚才还以为他是个憨厚老实的人,原来狗日的猫腻藏在这里头哩。这花花肠子绕绕得那个难受劲儿。村里许多男人清白过来之后都觉得有些愤愤不平了。心想,乱了纲常了!乱了纲常了!暗里弄也就算了。俺程家爷们也就忍了。你还这么光明正大地欺负起人来了。
这么晚才弄清白这小子的花样,村里人觉得实在是让他侮辱了智商,实在是羞臊得要死。
清白得很,这事儿清白得很哩!他竟然一个人交了两个闺女的礼钱。真是太欺负人了!当程家门没人了吗?当程家门都死光了吗?真是太气人了!人们都觉得憋屈得要命,心说奶奶的,真是让他辱没了咱程家的老先人哩。
郝庄那人在那里跪着,忽然就有一个村人实在忍不过,冲过去一下子把他按倒了。
“打他!”
郝庄那人就被打倒在地了。
“干啥打他哩?”小玲跟小惠跪在那里,似乎还有些没弄清白。
“在富渊叔的面前。狠狠收拾收拾这舅子!”村里人不理会她姐俩,只顾揪着那男的痛骂道。
小玲没有弄清白为啥要打,但是她也不敢阻拦。因为老程家在丧事儿上有啥规矩,谁能说得准哩?难不成岳父的葬礼上就有女婿要挨打的风俗?那也说不定!在这几天里,跟别个村里不同的风俗礼仪,他们是也领教了不少了。比如给老人穿寿衣前,至亲都要先吃一口灰土;比如在起棺出殡前,晚辈无论男女都要解开怀趴在地上给爹娘“暖路”……小玲心里想,打就打吧,只要不打太狠。
郝庄那人是在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的时候被一砖头拍倒在地上的,接着就是铁锨、棍棒……他一开始还叫唤,后来不叫了。
人们都累得气喘吁吁,汗如雨下。
郝庄那人抱着脑袋,竟然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
“打是打,不要打头!”小玲大喊一声,用牙咬住了下嘴唇儿。
也许是因为听到了小玲这话,有个人一棍子就狠狠照头砸了下去,把郝庄那人一下子砸倒了。村里人都觉得,不怪别的,单单看那头型像个扫帚头儿。头发也油光光的,就实在是该打!不打不解气哩!郝庄那人跌在他老丈人的坟前,村人手里的铁锨就往那人身上一阵乱拍。一边拍一边喘着粗气叫道:
“日娘的,叫你拿两千,叫你拿两千!”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