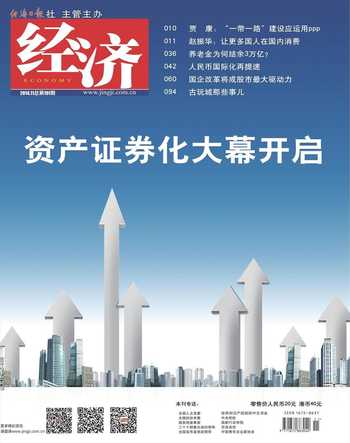姚洋:根植本土的经济学家
2014-04-29乔宠如
乔宠如

“年轻的时候想要改天换地,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还是做研究。顶多时不时地伸出头来,在社会上呐喊几句。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说这话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清癯的面庞上浮现出了几分腼腆。
姚洋身上贴了不少标签,除了有“经济学界的梁朝伟”之称外,他还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开山弟子、“北大经济中心的乔丹”、农村发展问题专家、“中性政府”的提出者。
与北大结缘
祖籍江西,但由于父亲被调往西安“支边”,1964年,姚洋出生在西安。“那时候西安还算‘边疆,生活真的蛮紧张的,再加上我妹妹又快出生了,可能家庭负担比较重。”刚满10个月的他,被送回到江西老家,由二伯父一家抚养。
“二伯父、二伯母他们没有孩子,加上我总共3口人。”在姚洋的记忆中,尽管童年生活谈不上富足,但是也从没有饿过肚子。“自留地还是蛮大的,差不多有七八分。”甚至还有余粮可以喂猪。“从吃这个角度讲,比城里还要好。”但也是因为这个,姚洋的二伯父后来还挨了批斗。
“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别人和我说,你们家锅被端走了。我回家一看,伯母就在那儿流眼泪。再跑到村里的小广场一看,我伯父就顶着一口锅跪在地上。”这画面竟成为姚洋最深刻的童年记忆。
8岁的时候,姚洋被父母接回“武斗非常厉害”的西安。“很长时间,厂子里都是有碉堡的,家属楼门洞里面都安着机枪。阵式很吓人。”
尽管政治运动不久便结束了,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大家都被‘斗怕了。稍微有点文化、有点思想、不是理工科的,都是挨批斗的对象。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父母对我的第一要求就是报工科。”
但姚洋还是想读文科。他左挑右选,看中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地理专业,“感觉好像偏文科。”
“知道我要报这个专业,我父母特意从工厂请假跑来学校,一定要我改成西安交大。”姚洋感慨道,“多亏了我的高中政治老师,他给我父母说,‘让他上北大,甭管什么专业都行。”姚洋这才有机会到北大读书,并从此缘结半生。
“年轻时有很多阴差阳错”
“虽然以高分考入地理系,但我还是喜欢文学。”姚洋告诉记者,这个专业应用数理化的东西比较少,学起来相对轻松。于是在整个大学阶段,姚洋在学校图书馆的文科阅览室,读了很多“闲书”。很想加入五四文学社,当时,“五四文学社还非常正式地派了一个社员来找我谈话,最后也没要我。”姚洋笑着说,很遗憾没能成为五四文学社的一员。
在“闲书”中,《走向未来丛书》让他印象深刻,这本译介了大量西方最新思想学术成果的书,为姚洋打开了哲学与思辨的大门,使他受益终生。
本科毕业前夕,本打算追随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先生做研究的姚洋得知,侯先生当年不招硕士生。他在好友的建议下,报考了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即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丁石孙任中心主任,厉以宁任副主任。
“说实在话,我们那时候讲的这些东西,只有理论没有应用,所以我也不知道管理科学到底是什么。还学了一大堆很高深的数学,有点稀里糊涂的。”等到要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姚洋遇到了深刻影响他此后学习和工作的林毅夫。
“有一天,管理科学中心的孙来祥老师和我们说,有一个台湾人,想招学生,你们去见一见吧。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有台湾人来呢?就跑去了。就这样认识了林老师。”
姚洋始终记得,他与林毅夫初见是在1988年1月2日。这一年,他24岁,林毅夫36岁。
作为第一位留美学成回国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娴熟应用和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都令姚洋大开眼界。“就这样从管理转向了经济。”
申请出国留学时,姚洋还是向林毅夫借钱交的报名费,“至今也没有还过。”
可惜的是,当年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没有给奖学金,姚洋只得请求学校保留入学名额。1989年夏天,“学校也不管分配,大家都‘鸟兽散了。”姚洋万般无奈地回到了父辈供职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度过了人生中最低谷的两年。
“当时在变压器厂‘企管办工作,其实就是给厂长打杂。而且厂长也有秘书,不需要这么多人。根本就是人浮于事,没啥事做。”
这份清闲的工作显然不适合胸怀大志的姚洋。加之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人心思变,姚洋也动了“不如去深圳下海”的念头。
就在此时,他却突然接到了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全奖录取的通知。“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真的有很多阴差阳错。”
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CCER)。同年秋天,林毅夫到威斯康星大学举办讲座,师生二人在美国重逢。“我当时就和他说,希望能回北大工作。”
就这样,取得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姚洋即刻动身,终于在1997年元旦之夜回到了令他魂牵梦萦的母校。2012年,姚洋接棒周其仁,担任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繁忙的行政工作,却没有改变他“每个周末和MBA的学生打一次篮球”的习惯。“我这么大年纪,跟着他们一起跑全场都没问题。”
不过,哪怕私人交情再好,姚洋也不会丝毫降低对于学生的要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BiMBA是一个小而精的项目,一年就招250人。论文写不好的一律不通过,考试没通过也要补考。我们有一个班的班长论文没通过,尽管他之前捐了200多万,也没有给他开‘后门,只能重修。不能因为你是班长,你捐了款,我们就放你一马。”
关注中国最现实问题
回国后,姚洋长期关注农村发展问题,这与他小时候在江西农村8年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2004年,姚洋返乡探亲。然而,童年记忆中的参天樟树和袅袅炊烟都已然不复存在。令他更为失落的是,原本干净整洁的小村变得污水横流,而村里人却对此熟视无睹。他思考认为,乡村公共精神的丧失,很可能正是村庄无组织化的后果。这激发了他研究村民自治、推行乡村直选的热情。在一次对8省48个村庄的研究中,姚洋发现:村民选举使村级行政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使公共支出增加了25个百分点。“假以时日,村民自治也许可以催生中国农村基层新的政治文化和公共治理模式。”
这位成长于变革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从未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于农村发展领域。他的思考,从政府与市场,逐渐衍生到公平与效率、民主与威权,就像他的学术偶像、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一样。
这位被称作“经济学良心肩负者”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出身于印度贵族。但是他对于底层百姓的切肤关怀和知行合一的学术品格,令姚洋十分钦佩。“我们很多做发展经济学的人,包括很多印度出去的经济学家,都不是真正地关注穷人。森虽然长期在国外教书,但是他每年都回印度去影响现实。”
读了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后,姚洋开始关注自由和平等问题,并将其融入到他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中,写作了《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一书,首次提出了“中性政府”这一概念。
姚洋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的数次革命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使得政府不与社会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结盟,以免增加其失掉政权的风险。而政府变得中性,也正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与众多习惯于“借他人之镜以鉴中国之现实”的知识分子不同,姚洋希望能够从中国经验中挖掘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有的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