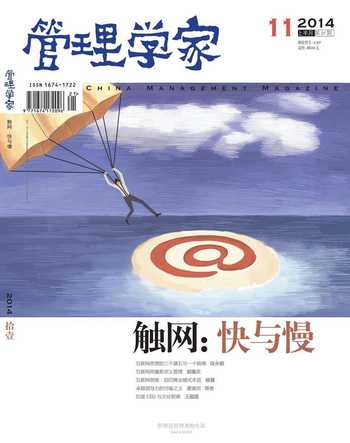进退皆忧的精英
2014-04-29
终结与死亡:人是人的祭品
普希金说:菲伯(太阳神)退休了,缪斯成了老太婆。英国政论家托马斯 · 卡莱尔说:经济学忧郁了(dismal science)。约翰 · 霍根说:科学终结了。卡斯比特说:艺术终结了。美国历史学家福山说:历史终结了。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恋情终结了。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意识形态终结了。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说:农民终结了。美国学者比尔麦克基说:自然终结了。英国物理学家巴布雅说:时间终结了。劳伦斯 · 弗斯说:现代医学终结了。
尼采说:上帝死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霍金说:哲学死了。法国社会学家福柯说:人死了。马原说:小说死了。符号学大家米勒说:“作者”和“读者”都死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是的,死了。亚里士多德跳进厄里帕海,屈原投身汨罗江,王国维自沉湖底,海明威用猎枪把脑袋打飞,川端康成含着煤气管睡了。自杀精英的名单打印出来,一条长长的哈达。
生不如死的精英更是不胜枚举。博弈论的鼻祖纳什一生与精神分裂症痛苦的反复博弈,新教伦理的大师韦伯被精神病折磨得不伦不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自画像,八大山人皆疯癫,海涅在疯人院里油干灯枯,莫泊桑发病时说他奸污了全世界的女人。
滨田正秀《文艺学概论》:调查了782位著名人物,精神极端反常者占83%,健康者仅占6.5%。
精英们这是怎么啦?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称赞精英:你们是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是原动力的原动力,是世上的盐中之盐啊。
分析精英的抑郁问题,不是消极。哲学家贺麟《乐观与悲观》:心理学家研究悲观,正如社会学家对愁苦事实的统计分析,是“观悲”而不是“悲观”。
而且,精英们的所谓“死了”,“终结”,有更深层次的涵义。不在弥赛亚情结的画布上,看不懂“死了”和“终结”之深意。
阿葛叶《随想》:文明史祭祀的长长的开场白,是在寻找奉献牺牲的永恒的动机。因为人是比人伟大的思想和理念的创造者,为此人奉献牺牲,所以,人是人的祭品。
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人用历史的强盛和伟大这样的幻想的目的折磨自己和他人。无数人的牺牲,为了王国的建立和毁灭。进步有个习惯,为了将来的完善牺牲活着的一代人。
天职与拯救:麦田里的守望者
杜甫《赴奉先咏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韩少功《夜行者梦语》:对于有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责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苏格拉底:我是一只刺激的牛虻。
克尔凯郭尔:我的整个生命是让人人知晓的预言性质的警句。
别尔嘉耶夫:任何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
席勒《警句集》:你能够,因为你应该。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真正的学者是那些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接受时代教养训练有素的、为真理与道义负责的人。
德国浪漫主义先驱诺瓦利斯:我们承担了使命,我们的任务是构造世界。
马克斯 ·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阐述:做好本职的工作,就是完成上帝授予的天职。
托尔斯泰:牺牲与痛苦,便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的目的是大众的福利。
《阿摩司书》:把社会机构的腐朽和摇摇欲坠的情况告诉百姓,这是我的使命。唤醒破烂不堪、多灾多难、腐朽透顶的社会。
马志尼《论人的责任》:人们愿意承担责任比接受权利重要。讲权利的人和讲责任的人之间的区别,就前者来说,一旦获得了个人的权利,便失去了动力,再也不想继续努力了;而后者的工作只有到生命结束时才会停止。
德富芦花《我为何做起小说来》:用你的眼泪去慰藉人,用你的愤怒去唤醒人,用你的笑声去羞耻人。你的笑虽小而你的权力和责任至大。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萨特与阿隆》:萨特是出现在所有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种社会责任的光辉,穿越了时空,照耀的不仅仅是麦田。
高度与境界:独上高楼,高处不胜寒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孑然独立,无人同我说话,孤寂的严冬令我发抖。谁若振聋发聩,必定长久缄默;谁若点燃闪电,必定如云般漂泊。
雨果《悲惨世界》:这世界上确有一些人,能在梦想的视野的深处,清清楚楚地望见绝对真理的高度和无极山峰的惊心怵目的景象。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
弘一大师《<二十自述诗>序》:欣戚无端,抑郁谁语?言为心声,乃多哀怨。
歌德: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是的,这是精英的烦恼。
先知与预测:俄狄浦斯效应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王子,其父忒拜王得到神谕,说他要杀父娶母,把他丢到荒山野岭,成为别人的养子。长大后知道自己将杀父娶母的神谕,为了逃避这杀人逆伦的命运,他离开了自己的养父母四处流浪,与一个老人争执而误杀了他,那位老人就是微服出访的忒拜王,他的生父拉伊俄斯。他以自己的出众才智铲除了危害忒拜的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被忒拜人民拥为国王,并娶了前王的王后,他的生母。
英国社会学家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将这种“预测可以影响被预测的事件”的现象命名为“俄狄浦斯效应”。
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尼采《快乐的智慧》: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不久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
美国社会学元老W·J托马斯提出定理: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当成为真实的。
舍普《预测科学》和鲍尔的《预知社会》:公布民意预测估计,无意中会影响投票结果。
科学预测揭示出事物演化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促使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并避免“坏”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至少将其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病蚌与珍珠:天才是人类的病态
亚里士多德:天才和忧郁、疯狂形影相随。
巴尔扎克:天才就是人类的病态,如同珍珠是贝的病态。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感性的人为世俗物事而绝望,理性的人也就为拒绝自我或选择视绝望为最终真理而绝望,将自己置于永恒的绝望中。
美国作家肖姆:所有表现出色的人,都是忧郁的。忧郁的背后是一个高贵的灵魂,高贵的灵魂背后,是颗孤独的心。
拜仑《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记》: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却总喜欢作非分的幻想和憧憬。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们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尼采称赞荷尔德林发疯时作的诗是诗歌中的真正精品,有深刻的官能与突然降临的疯狂之夜的角斗,表达了至深的忧郁和对安息的渴望。
浮士德就是一个灵魂永远不知满足的典型。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无论是在人间或是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
托尔斯泰:我有六千俄亩的土地,我有三百匹马,我的名声将超过果戈理等世上的一切作家。那与我何干?有何裨益?脚下的大地消失了,我没有立锥之地,没有生命的依托。
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
茨威格《富贵梦》:只有内心不安的人才会使自己全部感官处于最大限度的紧张状态, 意识到随时可能有的危险——这种本能使他变得异常聪明,超过了自然赋予他的智力。
叶夫图申科《随笔短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心理晦暗的隐私和最底层的洞穿一切的透视只能用他癫痫病的猝发来解释,这病的猝发如同暴风雨中的闪电,使他瞬间洞悉了意识和潜意识的那些神秘角落。
患有抑郁或分裂症的名人很多,哥白尼、安培、爱因斯坦、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康德、黑格尔、奥威尔、安徒生、巴尔扎克、小仲马、席勒、托尔斯泰、拜伦、雪莱、普希金、歌德、罗伯特、帕斯卡尔、意大利的小提琴家帕格尼、波兰钢琴家肖邦……
天才是在激情里游荡的精灵。智慧从觉醒之时起就包含着绝望。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真正的深度在哪里开始,他的深度就归于灭亡。
悲悯与悲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地址的信》:为人们工作,而人们并不理解工作的人,这对于工作的人很不舒服,而且对于工作的成效也很不利。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土耳其人中间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谓“英雄的人民”不过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空洞概念,现实革命中的人民越来越响亮的抱怨声终于变成伟大俄罗斯革命中农民及全民暴动的绝望哀号和怒吼,是流氓阶层、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
鲁迅《以眼还眼》: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
萧红《呼兰河传》:中国农民的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徐晋如《如何为知识分子去魅》:我对底层却从不抱幻想。绝大多数情况,底层所产生的只能是对优秀人群抱有深深怨恨者。
陈诚《陈诚回忆录》: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郝伯特 · 斯宾塞《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同情和爱戴的对象如果被理想化,困苦的真相就会被扭曲。流浪汉、醉鬼、罪犯,靠父母过活的年轻人,靠妻子过活的男人,靠妓女过活的小伙子,值得同情吗?
卡拉姆津倡导的自由主义改革,宫廷和茅舍一块骂他。悲凉地发出“高贵的失望的呐喊。”“到民间去”的青年,不仅得不到农民的理解,往往还被农民告发被捕。
精英们的慷慨激昂会不会变成一厢情愿――甚至被说成伪善?
困顿与漂泊:世代的苦酒 永远的乡愁
杜甫: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万里悲秋常做客。
李白《菩萨蛮》: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萧红《饿》: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能吃吗?椅子能吃吗?草褥子能吃吗?
钱理群: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
《顾准日记》: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来。
卡夫卡:他已经不理解家乡的情形了,他无论如何都会留在异国他乡。唯一能逃避的,只是这逃避本身。
在路上,既是一种实际生活状态,也是生命漂泊的象征。若兹-库贝洛《流浪的历史》描写的是躯体的流浪,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刻画的是精神的流浪:昆德拉慢慢转动移民官递过来的地球仪,“还能去哪里呢?”轻轻地问道:“您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困顿与漂泊,肉身与精神,此岸与彼岸,之间巨大的张力,是精英们世代的苦酒,永远的乡愁。
幽暗与启明:黑夜给了精英黑色的眼睛
李清照《小重山》: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
大仲马《蒙梭罗夫人》:心情忧伤的人往往喜欢黑暗,因为黑暗可以使他们在想像中充满幻觉。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开头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夜里——那一夜有云,黑沉沉的。
海涅《考狄利娅》:李尔王的神志中有一抹烟云,它随后会凝缩成最黝黑的精神黑夜。
司汤达《德·圣依斯米埃骑士》:黑暗对我有利,它使我能完全保持冷静。
叔本华:宗教如萤火虫,为了发亮,非要有黑暗不可。
茨威格《夜色朦胧》:人们在晚上讲的故事,终归都要陷入淡淡的哀愁的情绪。
埃利希-诺伊曼《关于阴影的看法》:正是阴影带来了关于藏在深处宝藏的好消息,带来了生长在黑暗中、其神秘力量能使吓人伤口止血的治伤草药的好消息。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白昼的光,如何能够了解夜晚黑暗的深度呢?尼采《浪人与影子》:凝望更多的,是影子,而非光明。黑暗和包围着生命的天光将阴影投射到人类灵魂理性的天性里。
帕斯卡《思想录》:如果根本就没有幽晦,人类也就根本不会感到自己的腐化;如果根本就没有光明,人类也就根本不会期望补救之道。
卡夫卡: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厨川白村《缺陷之美》:正因为有暗的影,明的光这才更加显著的。
培根《论逆境》:最美的刺绣,是以明丽的花朵映衬于暗淡的背景,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映衬于明丽的背景。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檀香,通过烈火焚烧会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正如恶劣的品质将在幸福中呈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逆境中被显示的。
海涅《考狄利娅》:在感情黑夜的最幽暗的阴影旁画出谐瘧的最亮丽的光辉来,在醉狂暴的行动旁画出最安谧的静物来。
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哲学问题的答案可与神话故事的智慧比较:它在魔幻般的城堡里显得妩媚动人;但在白昼,它在户外看上去仅是一块普通的铁。
《浮士德》魔鬼先生靡菲斯特的话:“光明本来生于黑暗”。
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世界的历史像一个幻灯。它在现代黑暗背景上,放映出明朗的片子,说明那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在怎样走着荆棘路。
科塞《理念人》中转鲁特尔《精英们能胜任其肩负的责任吗?》:现在危机已经达到我们的核心区域,精英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能够胜任其肩负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