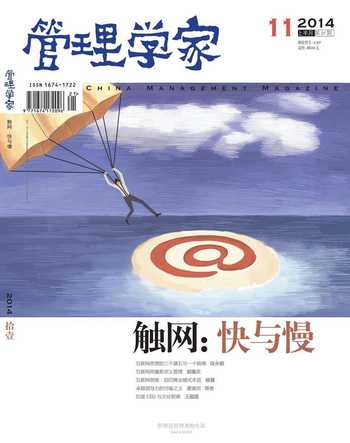互联网思想 的三个基石与一个困境
2014-04-29
1984年春夏之际,我心潮澎湃地看完了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编导的专题片《信息时代》。片中有一句话:“穷国和富国,从此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同一起跑线”,就是指“信息时代”。时至今日,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们想知道,它还会在哪些方面颠覆和改造我们所熟知的一切?我们更想知道,这些令人气喘吁吁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说:“思想成就人的伟大”,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其实,人们对思想的理解,除了“史诗般的激情”之外,还有一个强烈的动因,就是试图获得横扫一切的能量。在我所亲历和见证的互联网历史中,总有一个疑惑如鲠在喉,那就是:对于信息时代,我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们何以真切地确信,所言不差?我们可以从文本中接受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从眼花缭乱的数码产品中领略强劲的科技旋风,但我们却总是“聆听者”、“接受者”、“赞叹者”的身份。
在细究互联网发展史,考察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重新审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我认为,可以把复杂性思想、社会网络和公共空间看作互联网思想的三个支柱;而隐私与知识产权则是互联网思想的一个困境。
复杂性思想
凯文 · 凯利在《失控》一书中强调:失控并不可怕,反倒是秩序涌现、生命诞生的活的源泉。复杂性思想启示我们两点,第一是要拥抱不确定性,要同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确定性、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做斗争,学会超越确定性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第二,互联网是“活”的,充满了有机体、生命的特征,是多样性的、自组织的、共生演化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存在的背景,“交互”、“涌现”都是很重要的关键词。
已经有很多比较成体系的知识描述复杂性,主要集中在突变论、分形几何、非平衡热力学、非线性动力学、凝聚态物理学、流体力学、协同论等领域。但是,复杂性拒绝将“复杂”一语收编在任何既有的知识体系中,它本身就是结论:这原本就是一个悖谬丛生的世界。复杂性是介乎秩序和混乱之间的边缘状态,是意蕴丰富的状态,活力四射,充满各种可能性。目前,微博、微信、淘宝都积累了大量数据,大家觉得这些数据都是金矿,希望深入挖掘,但是怎么挖呢?目前的思路还停留在探索现象的阶段,还是还原论的方法。还原论往往对应着同质化,排斥异质性,所以应该用复杂性思想去研究微博、微信中涌现出的行为。
复杂性有五个特点。
第一是“高度结构化”。结构,是20世纪下半叶流行开来的语言、文本、组织、生态、宗教和社会形态常用的分析用语。比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对能指和所指的划分,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对文化结构的划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对人的自我结构的划分等等。高度结构化,强调观察和思考的视角必然是整体论的,无论这种结构我们是否能够辩别、释读出来。
第二是“非高斯分布”。高斯分布,即正态分布,假设所有个体独立存在,并且是均质的。《爆发》一书的作者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发现,在互联网中,这种独立、随机的分布场是不真实的。互联网世界,越来越呈现出真实世界中的差异性、异质性、多样性,是符合“幂律分布”的。无论是安德森的“长尾模式”,还是“二八定律”,或者“占领华尔街”的口号“99%:1%”,都是巴拉巴西所言幂律分布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是耗散结构下的非线性。耗散结构表明开放系统不可避免,表明任何试图描述某个对象的符号体系,都注定是“降维”后的结果,即降低难度系数之后简化的结果。非线性,意味着不可重复。传统科学总是假设光滑的、可微的数学物理方程,但是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简单,如此漂亮”!
第四是临界相变和自组织、涌现。物质的“相”,是格局的转变,也就是结构的转变。相变,就是这种存在样貌、架构的转换。液相到固相、气相的转变,就是相变,不是种性层面的改变,只是样貌不同了。《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里的相,就是指外在的样貌、表征。临界相变,要特别关注内外条件作用下,相的转化和迁移。这时候所激发出来的状态是丰富的,也是最好的洞察事物本来面目的机缘。
第五叫“结构变异”,时空不对称。古希腊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将万物归结为水、火、风、土四大元素;东方圣哲们则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太一。太一之下,万物都是“象”。结构变异,其实说的是“结构的可变异性”,即可以相互转化。这种看上去玄虚的哲学思想的背后,是生生不息的、万物有灵的思想情感。这个思想情感需要完全不同的时空观。时空不对称,正是让万物之联通、扭结、聚合、生化,有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所在。
研究复杂性无非是回到事情本来的面貌,这种原貌是没有经过简化处理的,保持了“毛发丛生”的状态。你不能用奥卡姆的剃刀把它剃光,在这种情况才能能够真正“解决”复杂性的问题。不,复杂性的问题不是需要“解决”的,是要“超越”。那么,复杂性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第一,复杂性提示我们还原论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但是,如何理解还原论和整体论的关系?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创立的系统论,其实是一种“巨型”的还原论。它还是希望用清晰的、光滑的方式,来刻画所谓“终极真理”,并且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思维来驾驭它。这些信心满满的理性主义还原论,骨子里有强烈的“收编欲望”,相信所有新的发现,新的原理,终将归并入同一个宏大的科学体系。这种科学的理性精神或者说信仰,已经深入骨髓。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性冲动,是现代性的来源。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分析的那样,它会让垄断企业、权势集团,让政治上的极权主义、集权社会,让老大哥式的宏大叙事生产出来。所以,传统科学在给我们诸多成果之余,也使得我们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以至于很难与另外的语境对话。
第二,复杂性告诉我们“确定性”和人的关系,以及“可知的限度”是什么。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甚至“杀死”了上帝。从此,人失去了宗教意义上的确定性。确定性以及附着在确定性上的意义,都被生动的、现实的世界一一粉碎。但是传统的科学精神却许诺我们一个确定性的世界,好像宗教教义许诺我们的那样。再想一下,互联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秩序井然的吗?我们希望它如此吗?这个问题可以从复杂性角度来思考。我不认为这种思考是反智的,因为理性最可贵的品质不在于它能计算很多问题并且分毫不差,而在于它可以用来怀疑自己。理性的思考是建立在悖论的基础上的,而不是驱逐和回避悖论。
第三,我们可以用复杂性思想理解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文艺复兴之后 ,人文与科学的分野日趋严重。互联网能否迎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汇合?我相信,这种汇合不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而是深层次的、痛苦的融合。为何痛苦?传统的科学往往致力于驱逐悖谬,致力于寻找干净的、纯粹的、自洽的科学图景,这种科学观也许需要改变。这个问题在当今的科学界尚未取得广泛的共识,但互联网有机会促成这种转变。互联网可以容忍差异性,丢弃理性基础上的共识,更多的交流发生在“会意”层面而不是“同意”。
复杂性,是理解互联网精神的重要支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认识互联网的信号灯、标志线将会是模糊的、混乱的,你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两分法、确定性、还原论的惯性轨道。这时候你会很惬意,很舒服,也很习惯,但这会离“互联网状态”越来越远。我们要对今天世界的种种变化迹象保持敏感,要知晓这种变化绝不是数量的变化、质量的提升,而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只不过,它暗藏在毫厘之间。保持敏感,你才能看到更细微的频谱。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会在不同语境中跳转,逻辑未必会连贯,语义也未必清晰,但是,你会越来越习惯在双重、多重语境下思考问题。还原论的逻辑思维并未完全失效,但是我们要学会超越它。
社会网络分析
互联网的第二个重要的基石是:社会网络。
自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创立社会学以来,这门学科一直遮蔽在经济学的光辉之下,其基础首先是经济学。经济学给出了人性假设,传统社会学只不过是研究“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上层建筑”而已。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 · 巴顿(Allen Barton)曾经这样评价社会调查方法:“在过去的30年里,经验性的社会研究被抽样调查所主导。从一般的情况而言,通过对个人的随机抽样,调查变成了一个社会学的绞肉机——将个人从他的社会背景中撕裂出来,并确保研究中没有任何人之间会产生互动。”“社会学的绞肉机”,形象说明了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所言社会学研究中的“低度社会化”问题。这种“把个体从他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的方法,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下受到挑战。
从“低度社会化”到“过度社会化”,社会学的传承经历了一番波折,主要表现在对人际关系的发现。从1924年到1936年,科学管理深入企业管理实践,美国西屋公司在霍桑工厂进行了一场断断续续的著名实验。实验的初衷是想证明电力、灯光等工作环境因素,对人的工作效率是有正面激励作用的,然而实验结果却并非如此。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跟车间的灯光亮度并非显著相关。为什么如此?1927年冬,哈佛心理学家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等人受邀参加了中途遇到困难的霍桑实验。在实验的基础上,梅奥分别于1933年和1945年出版了《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两部名著。霍桑实验指出,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不是孤立的、只知挣钱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成员,个人的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作积极性上只具有次要的意义,群体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是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后来,研究霍桑实验的卢因(Kurt Lewin,1890-1947)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继续进行情境研究、群体动力学研究。
格兰诺维特于1980年代指出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问题,“低度社会化”指大量数理分析、大量模型的运用,离社会学真的很远。“过度社会化”,则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强调大一统的理论架构。社会网络分析还谈不上有一致的理论体系,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的《社会网络分析讲义》将其总结为七种理论:机会链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弱连带理论、镶嵌理论、结构洞理论、强连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资本不像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有明确的所有权,而是必须在使用中存在,也必须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存在。社会资本是越用越有价值,越分享越好。这跟互联网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把群体和个体纳入相互连接着的网络环境下研究,但限于客观条件,之前的研究范围往往局限在小样本、局部环境的个案空间内。互联网提供了大范围、大尺度、复杂网络分析的可能。无论微博互粉结成的好友网络,还是微信呈现的熟人圈子,获取关系数据、展现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困难。同时,将不同的网络结构叠加起来,组成有耦合的复合网络(超网络)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网络分析的热点。以下七种问题,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最基本的。
第一叫关系研究。传统网络分析中的所谓关系,是对连接节点之间连接属性的描述。这里所说的关系研究,一方面包括这种关系属性,另一方面要看关系场,即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说的“场域”(field)对关系的影响。场域是结构层面的概念,首先需要度量一个完整的网络连接,如何形成了具备一定“场力”的辐射能力,比如家族血统的强弱、人脉势力的强弱。关系研究还有浓厚的文化背景,比如中国本土社会的结构,费孝通(1910-2005)提出了著名的“差序结构”——以血缘为纽带、长幼尊卑为圆圈,向外逐级递减。
第二类问题是关系怎样影响行为。我们把网络区分为两种:个体中心网络和企业组织网络。当个体纳入某个网络结构之后,他的行为受网络的制约、规定和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网络分析通常采集一个人的社交圈和他的行为数据,来分析个体行为的影响因子,“易感”指数等等。企业组织网络也是如此,个体在网络中行为,并非只是受与之直接相连的节点的牵制、影响;事实上,还有整个“气场”的影响,而且有时候这个“场力”还更重要一些。
第三类问题是场力如何决定个体的位置。当个体处于一张大网中的时代,势必会受到各种影响,有些影响会改变个体行为,有些则会改变个体所处的位置。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一个是静态的位置,就是你目前所在的位置;另一个是潜在的位置,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下一步落在哪里。关系如何促使一位置生成?机会链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告诉我们,位置并非是“空”在那里,而是等待你去识别、发现。影响一个公司重要战略决策的可能是小圈子里的某个人,不见得是总经理本人,甚至可能是局外人把握着话语权。位置的变化,既是对个体的影响,又是对结构的再造。
第四类研究是个体在结构中的位置如何影响行为。这个问题是对前两类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举个例子来说。微博比较火的时候,有投资者说:考察一个创业者的能力,有个很好的指标,就是看他过去半年的微博。为什么呢?第一,发微博不是那么刻意,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创业者的状态;第二,微博上的关注与被关注,可以刻画出创业者的社交网络;第三,关注微博的时间点,会反映其工作与生活习惯;第四,根据对其微博的文本分析,可以了解其知识和兴趣图谱。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行为之间的连锁关系。
第五类问题是个体行为如何影响网络结构。如果个体行为是大幅度、大范围,或者是关键性的,就可能改变整个网络的结构。比如一个关键节点,如桥(Bridge)节点、中枢(Hub)节点的变化,比如微博上大V的行为,就可能引发网络结构的动荡。
第六类问题是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群体行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网络结构的变化可能引发网络节点的多米诺效应,引发大面积崩溃的重大事故。电网、交通网络、流行病网络,都存在这种可能。多米诺效应可能暗示了某种逻辑链条,事实上,在复杂网络上,更多的情形是,你可以发现某个区域、某个网络结构崩塌的临界点,但你未必能抓住所谓因果的链条。面对复杂的社会网络、生物网络,我们可以锁定网络的稳定性、脆弱性,给出某种可能性的描述,但很难写出确定性的议程来表达这种复杂现象。
第七类研究,是群体行为如何凝聚为场力。在群体行为背后,是怎样的网络场力?意见领袖、引爆点、多级传播可能只是表象,背后的网络能量是什么?如何进一步预测这种场力对其他个体的影响?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舆论传播理论、流行病传播理论都关注这个领域。
社会网络分析,一方面是结构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行为对结构的影响。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将这个七个问题循环来看,才是演化的思想,是真正动力学的思想。研究社会网络已经有很多成果。电子科技大学周涛教授有一篇综述文章《人类行为的时空特性的统计力学》,对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规律,给出了详尽介绍,在呼叫网络、社会推荐、交通问题、城市规划、流行病学等领域,都有鲜活事例。我个人比较看好中科院王飞跃教授大力鼓与呼的人工社会和ACP方法(A指人工系统Artificial system; C指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P指虚实系统的平行执行Parallel execution)。人工社会的基本思路是在计算机上建立某种仿真模型、仿真环境,同步捕捉过程信息,对特定对象的复杂网络过程进行模拟,并与真实的结果相比照,进而用于预测、机理分析、解释等领域。ACP方法可以计算出不同的情景,并且实时监测平行系统的输出状态,给出预测、优化的对照结果,是一种探索结构复杂性的好方法。
公共领域的重建
互联网思想的第三块基石是:公共领域,或者叫公共空间。如果说未来会发生什么重大的社会变局的话,“公共领域的构建”一定是相当重要的、重量级的一个历史进程。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说了两件事:一是十八、十九世纪公共领域的兴趣,二是公共领域的衰落。我们今天所感受的,依然是“衰弱了的”公共领域。那么,互联网是否是公共领域重建的契机?怎么理解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
十八世纪中叶,伴随工业化兴起的,是欧洲现代城市的膨胀。大量乡村农牧场主的后代、手工业者的后代涌入城市。当他们与陌生的城市接触的时候,他们需要模仿城里人的言谈举止,需要将所有泄露自己身份的痕迹掩盖起来,需要尽快成为某个社交圈子的一员。这时,剧场、咖啡馆、公园、公共广场等公共场所大量崛起,人们热衷于无拘无束地交换趣闻,散布消息,打听别人的隐私。然而,这样的公共场所毕竟不同于雅典的广场辩论和广场政治。这里没有公共利益,只有小道消息;没有对他者的关怀,只有对陌生人的恐惧和提防。所以,当这样的公共场所“介质化”之后,就势必使某种公共空间走向衰落。所谓介质化,就是公共场所成为某些固定圈子、确定的腔调、某些流派聚焦的场合。这种圈子使得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和陌生人的相处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圈子实际上对陌生感是恐惧的。
公共领域的衰落,导致了“逃逸”的出现,不光是理论的逃逸,还包括实践的逃逸。理论方面,在后现代之后、现象学之后 ,理论不能正视和面对本质问题。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尽管主张“悬置”“终极拷问”,回归到现象层面,但并不意味着理论可以从此不发声。后现代的学者拒绝承认任何“主义”的标签,但也存在着“建设性缺失”的问题。一旦你要建设性,你就必得构建某种基石、体系、假说、原则,就落入他自己唾弃、批判的窠臼。实践的逃避又是如何体现的呢?那些与主流保持距离拒绝标签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如拉康(Jaques Lacan, 1901-1981)、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人,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一切“格式化语言”撇清关系,沉醉于批判的快感之中。他们批判“宏大叙事”,消解中心,消解权力,消解意义,使得任何试图重构中心、重构叙事、重构意义的图谋,都变成“自反”的悖谬。
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逃逸,就是我们探讨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的一个初始条件。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思维特征是“自我中心”、“由内向外”的话,信息时代的思维特征则是“关系中心”、“由外向内”。关系中心,即关注他者的存在;由外向内,即从关心外物到关注内心。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构建公共空间可以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第一,我们知识工业时代的大众媒介把公众变成了大众(mass),变成了大批量生产,那么,信息时代的新媒介怎么让它重归公众?
第二,媒体人的把门人规则可能被颠覆。传统社会里,记者被称作“无冕之王”,被视为天道良心的载体。对于媒体这个“中介”来说,互联网首先会有一个含义叫“去中介化”。媒体首先是信息的中介。“去中介化”即意味着媒介的传统信息中介角色,将被颠覆。互联网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在去中介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目击者、报道者,真相有赖于社会网络的长期质疑,而不是哪一个媒介观察者的断语。
第三,商业化浪潮带来什么?媒介与商业机构联盟,在现代媒介诞生之后就存在了。媒介的“二次营销”理论,就是基于与商业环境的共生关系。一次营销把内容卖给受众,二次营销把有购买力和消费欲望的受众,卖给广告主。新媒体环境下,有人希望这个二次营销模式依然奏效,即媒体人操弄着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式的媒介武器,一边更快地售卖内容,另一边更精准地售卖广告。这是媒介的未来吗?商业该处于何种角色?
今天我们熟悉的商业环境,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商业化。在这个大框架下,你可以看到GDP主义、增长导向、创富故事、金融大亨,你也可以继续看到对确定性的迷恋,对预测、控制的不可遏制的偏好。今天的商业化已经变成了癌症。很多拯救地球、绿色能源、救助欠发达地区儿童的事情,最后都不得不变成一个个项目,纳入到工业化的滚滚巨轮中,苟且存在。在工业化话语依然强大的时候,探讨未来新的商业生态、商业文明,我觉得注定是贫乏的。我们真的能从GDP导向转变为“快乐经济”吗?互联网时代最本质的经济特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在“产消合一”的框架上,快乐最重要。也许互联网会重塑人类,这种重生、新生、再造,并非全然褒义,也许还有贬义呢。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对公共领域的阐释对我们依旧有启发意义。凯文·凯利说:“在女性扮演更重要角色之前,Internet不可能更文明。”有学者评述阿伦特,说她颠覆了几千年来男性学者沉思的装模作样。我高度认同。在公共领域里,阿伦特的观点是行动。这种行动并非单一的指称某种具体的行为,而是与言说共同交织在一起的意义的存在。意义并不先于人而存在,意义也并不先于行动而存在。她认为所有与意义相关的东西,都蕴含在真正的行动中。并且,你不是一个人在行动,是人们在行动,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她的公共空间。她说:“行动,是唯一无需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它对应于人的复数性条件,即对应这样一个事实,是人们,而不是单个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并居于世界之中。尽管人的境况的一切方面都以某种方式与政治相关,但这一得数性尤其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
隐私与知识产权
“没有秘密的社会”,这个说法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商业社会永远在呼唤“诚信”,也永远在与背信弃义做斗争;亲情、友情永远渴望“亲密无间”,但却屡屡受到“鲁莽闯入者”的威胁;乌托邦的政治蓝图中,试图用消灭秘密来达成最广泛的谅解与合作,但同时为无所不能的老大哥留下地盘。“没有秘密的生活”,即伊甸园的生活,是纯粹生活的标志。然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每每与此相背而行。孔子悲叹“礼崩乐坏”,《圣经》称之为“原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以及爱恨离别、勾心斗角,使得人类代复一代地饱尝“私欲”之苦。人类在“私”的问题上,事实上落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意欲去之,心向往之。
人们在高声反对老大哥的同时,其实无不幻想自己可以坐拥山头、呼风唤雨。这其实是隐私的真相。强调保护隐私者,对窥探他者的隐私其实兴致勃勃。任何商业的竞争、政治的计谋,都离不了对他者隐私的窥探。声称隐私的放任主义者,无论多么大胆,都会为自己留下一爿隐秘的保留地。窥视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感——对不确定的焦虑感。假若窥视者所窥视的世界给他一个意料之内的回声,他将因此获得存在感;假若在意料之外,他会惊惶失措。所以,思考隐私、隐私权,我们需要新的视角,需要理解复杂性,需要超越在保护和放任之间二选一的困境。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隐私的含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施者与受者“同体”,是互联网下身体、思想受到约束、规训的总体特征。当施与受无法分离的时候,隐私将不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的紧张、斗争,而是全部集中在个体身上的斗争。一方面,人们希望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隐私(潜台词其实是对隐私泄露带来的危害的警惕、恐惧);另一方面,充分连接的、无边界的、彼此日益交互的互联世界,客观上已经在打破各种隐私的边界。大数据、物联网、社交网络,以至于脑神经网络的发展,已经日益将每个人的所谓“隐私”转化为能见度很高的比特信息,透过你不经意的注册、上传、购物、浏览、转发、点评等行为,“泄露”在公共平台上。换个角度说,隐私这件事将越来越难以确定,正是因为“个性化运动”的崛起。私密信息本身并不会给人带来伤害,能带来伤害的,是对私密信息的恶意滥用。所以,我认为未来互联网的隐私边界,将从定义什么是隐私,转向寻求对隐私的使用权、解释权的界定。
在所谓公民记者时代、自媒体时代,媒体传播已经泛化,任何一个架设网站、开设微博、微信账号的个体或组织,其实都是在做传播。广义上讲,人人都是传播者。在微博等公共空间,你的转发、评论,不能简单地“快意文字”,而应该有所思考。一是要看清楚现状,即,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在现行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解读、诠释的框架之下,调整自己的行为。二是不满足于表面的信息采集、故事还原、线索追踪,借助具体事例思考新闻事件的社会背景、理论价值,要善于从假设前提入手,推演它可能的变化。隐私权的立法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小尺度上如此,大尺度上更是如此。
另外,在传统媒体里,事实的核查是由媒介机构自行完成的。新媒体时代,事实的核查除了由自己完成,还可以借助广大网友的力量来“纠错”、“纠偏”。当然,这种纠结机制、净化机制存在一个问题:滞后性。它需要有一定的扩散量,需要扩散一段时间,才可能得到纠正。而且,是“可能”,不是“必然”。那么,如何看待网络的这种纠偏功能?有些未经验证的信息在网上散布,事后证明是谣言、中伤,那就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损害,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害。但是,如果僵硬地理解“事实核查”,甚至以此进行舆论干预,就大大偏离了我们讨论问题的范畴。互联网具是自我净化能力,因为它注定是构建未来公共空间的基础结构,这一结构更多是自组织的,而不是他组织的。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传播的门槛是零。互联网注定是越来越多的连接,越来越深的连接。裸露态,是互联网无法避免的一种局面。
隐私的主体是人,机构、企业、法人不构成隐私的主体,没有隐私可言。但是,机构有秘密,比如商业机密,比如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大致分两种:版权和工业产权。版权和著作权最重要的体现是文学作品;到了电子时代,版权的外延有了拓展,除了传统的小说、戏剧、音乐、绘画以外,还包括游戏、软件。工业产权典型的就是商标权和专利权。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以软件为代表的新型著作权。
作为新型著作权,软件有目标代码和源代码之分。传统著作权中,可以认为只有一种“代码”,你无法想象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有1.0、2.0版。把软件放到著作权法的框架里保护,有两个问题:第一,软件的版本是不停更新的;第二,软件属于“不完全交易”,你买到的是目标代码,不是源代码。传统的版权体系拿来做软件保护,根子上是有问题的。
1984年,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1953-)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他认为,软件是人类共同的智力财富,不应该由商业公司据为私有。自由软件的作者除了拥有署名权之外,放开一切权力,比如改编、编译、重新装置、分发、多次安装等。自由软件主张彻底的共享主义。这一做法除了与商业软件势同水火之外,也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激励志愿者工程师?如何持续发展?1990年前后,自由软件群体出现了分化,雷蒙德(Eric S. Raymond,1957-)提出了开源软件(opensource software)的概念,承认软件应当开放源代码,但也不排斥软件可以卖钱。时至今日,开源软件公司的境况并不舒服。商业公司对开源社区的侵蚀、并购,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开源都无法解决问题,说明自由软件的确是一个乌托邦情怀的梦想。
在工业知识产权方面,莱斯格(Lawrence Lessig,1961-)提出了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CC)协议,主张人们更灵活地进行知识共享。这方面的冲突似乎越来越小,而在隐私的问题则越来越扩大化。传统的隐私观,集中在对泄露隐私带来的伤害的恐惧——无论是丧失钱财还是担忧陷入窘境。互联网环境下,新的恐惧感恐怕在于我们已经很难定义隐私。因为瞬息万变的网络存在、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川流不息的网络数据,都使得任何一种试图“遮蔽起来”的愿望,变得不可能实现。门已经打开,不可能关闭了。
今天的互联网,还只是互联网的史前史阶段。它脱胎于工业文明,继承了工业文明的物质,比如对速度的热衷。互联网也有它独特的、反叛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比如拒绝确定性、拥抱复杂性,因为复杂性才是孕育生命的土壤。复杂性要求用“活”的眼光看世界,社会网络希望网络世界是有温度、有生命的,公共领域希望真正进入人的内心,这些都是围绕互联网的灵性复归。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还在初级阶段,互联网也还稚嫩。思想可以是我们的拐杖,也可以成为借口。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在《数字化生存》里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造出来。” 我们需要言说,也需要行动。我们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所以,我们既要承受痛苦,又要迎接曙光。(本文根据商务印书馆《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