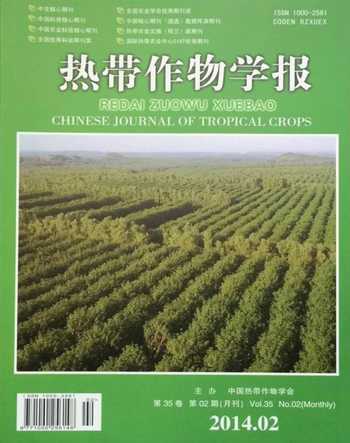福建中部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基于NTSYS和STRUCTURE软件的ISSR分析
2014-04-29赖恭梯赖钟雄刘炜婳叶炜林玉玲刘生财陈裕坤张梓浩吴高杰
赖恭梯 赖钟雄 刘炜婳 叶炜 林玉玲 刘生财 陈裕坤 张梓浩 吴高杰
摘 要 为进一步完善福建野生蕉遗传背景研究,对采自福建省三明市和福州市的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共100份叶片样本进行ISSR分析,并结合NTSYS、STRUCTURE和POPGENE等软件,进行居群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13条引物共扩增获得175个稳定、清晰的条带,平均扩增条带数为13.5个,扩增产物主要介于200~2 000 bp,其中总的多态性条带为158个,居群总多态性条带百分率为90.3%;通过NTSYS和STRUCTUR软件聚类分析发现,岩前、莘口和赤壁野生蕉共100份样本严格按照地理来源划分为3个大组,3个大组可进一步分别划分为3、3和4个亚组;采用POPGENE进行遗传多样性参数分析发现,野生蕉居群总的变异中,群体内变异大于群体间变异,野生蕉居群内存在丰富的基因交流,3个野生蕉居群总体多样性水平较高,从高到低依次为岩前、莘口和赤壁。说明福建野生蕉居群遗传结构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水和人为因素在野生蕉群体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野生蕉;ISSR;聚类分析;遗传结构;遗传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S668.1 文献标识码 A
香蕉是芭蕉科(Musaceae)芭蕉属(Musa)大型单子叶草本植物,栽培香蕉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全世界重要的水果,也是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的食物来源[1]。品种退化且单一[1]、病虫害侵扰[2-3]、育种进程缓慢[4]、自然灾害频发[5]是香蕉栽培的世界性问题,加快香蕉育种进程、选育新品种是防止品种退化,提高抗病虫、抗寒、抗旱等香蕉抗性的重要途径。由于栽培香蕉有性繁殖能力的衰退,传统有性繁育的方法在香蕉上并不适用,因此遗传改良成为香蕉育种研究的新方法,而且新近不断被发现的野生蕉被认为具有多种抗性特点[6-7],是抗性基因发掘的宝贵资源,野生蕉可为香蕉遗传改良提供新的研究思路。目前,中国野生蕉的分布主要在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福建和台湾等,福建野生蕉的研究早期见于吕柳新[8]的报道,赖钟雄等[7,9-10]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福建省野生蕉资源丰富,在全省各个地市均有分布。福建省是中国栽培香蕉的北缘,也是具有大面积野生蕉分布的北缘地区,福建省栽培香蕉受到冬季寒害的严重威胁,而野生蕉一般能够正常越冬,福建野生蕉体现出较强的抗寒特点[7],能为香蕉抗寒研究奠定遗传基础。由于福建野生蕉的遗传背景研究尚浅,并且该地区野生蕉自然居群受到严重的人为破坏,完善福建野生蕉遗传背景研究和采取适当措施对野生蕉原生境加以保护,是野生蕉优质种源保护和利用的必要工作。在本实验室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调查新发现的福建野生蕉3个自然居群共100份样本为材料,开展ISSR分子标记研究,以NTSYS和STRUCTURE等相关软件进行聚类分析,探讨了野生蕉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特点,以及野生蕉群落的形成和相互关系,可为野生蕉群落的自然演变提供新的观点,并提出野生蕉的保护对策。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野生蕉的分布调查 3个野生蕉居群分别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莘口镇和福州市永泰县赤壁风景区,3个自然居群分别记为Pop1、Pop2和Pop3。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经实地调查、拍照取证和记录分析,初步掌握其分布特点。
1.1.2 野生蕉样品采集 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共100份样本分别采于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30份)、莘口镇(37份)和福州市永泰县赤壁风景区(33份),100份样本编号为p1~p100。样本要求健康无病虫害的鲜嫩叶片,采样点相距约10 m,采集的叶片于液氮中速冻后置于-80 ℃保存。
1.2 方法
1.2.1 DNA提取与质量检测 DNA提取采用改良CTAB小量法进行。吸取稀释10倍的DNA样本4 μL于1%琼脂糖凝胶中电泳,溴化乙锭(EB)染色后,用凝胶成像仪进行拍照,检查DNA的完整性,并用微型核酸测定仪测定DNA浓度和检测质量。
1.2.2 ISSR-PCR扩增 以本实验室建立的香蕉ISSR-PCR体系为基础,从陈红俊等[14]筛选的16条引物中,选择其中扩增效果较好的13条进行PCR反应,引物依次为UBC807、UBC810、UBC811、UBC815、UBC823、UBC825、UBC843、UBC844、UBC845、UBC855、UBC856、UBC857、UBC891。PCR反应体系和反应程序见陈红俊等[14]的研究方法。PCR扩增产物于2.0%琼脂糖凝胶中电泳,EB染色,蒸馏水漂洗后于凝胶成像仪中拍照。
1.3 数据处理
根据电泳迁移水平,以“1”和“0”记录同一引物相同水平位置谱带的有和无,采用NTSYS软件计算其遗传相似系数(GS),以非加权组配对算术平均法(UPGMA)对其进行聚类分析;采用STRUCTURE 2.3软件,设置运行参数K(2-12),8次重复,以似然值为基础,参照Evanno等[11]的方法计算△K,获得群体数K;并用POPGENE软件分析3个居群野生蕉样本的遗传多样性参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福建三明市三元区岩前、莘口和福州市永泰县赤壁野生蕉分布的调查
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分别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莘口镇和福州市永泰县赤壁风景区,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的生长环境有共同特点,都位于湿度较大或水源丰富的地域,居群内部植被组成相对简单,但是3个居群的分布亦各有特点。岩前镇和莘口镇位于三明市西南部的三元区,东连梅列区,西邻永安市,南靠大田县,北接明溪县,位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的汇水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岩前和莘口2个野生蕉居群均分布于公路附近的凹地,夏季野生蕉林长势旺盛、叶片浓绿,居群较显眼。岩前野生蕉居群(Pop1)前方受到公路设施的压迫,而后方则遭到山间林木的排挤,群落趋于萎缩(图1-A)。莘口野生蕉居群(Pop2)的生长除受公路和农田的威胁,同样受到高大竹林的竞争抑制,在光线的争夺中,野生蕉明显处于弱势(图1-B)。永泰赤壁风景区位于福州市西面的永泰县境内,闽江南港大樟溪畔,水源充足,动植物种类繁多,赤壁野生蕉(Pop3)位于溪流沿岸(图1-C),野生蕉粗壮的根状茎可穿过石缝延伸长至数米,形成吸芽发育成完整植株,能够在土层浅土壤贫瘠的环境中形成茂密的蕉林(图1-D)。野生蕉除依靠吸芽进行无性繁殖,亦可通过种子进行有性繁殖。综上调查,野生蕉群体脆弱,亟需妥善的保护措施;个体坚强,可在恶劣的环境下繁衍发展,有利于抗性和抗逆基因的挖掘及利用。
2.2 DNA提取与PCR扩增
所提取的DNA完整性好,无拖带,无污染,OD260与OD280的比值介于1.8~2.1之间,所提取DNA可用于后续试验。
13条引物共扩增获得175个条带,扩增产物主要介于200~2 000 bp,平均为13.5个,100份野生蕉样本的ISSR-PCR扩增的部分结果见图2,其中多态性条带为158个,居群总多态性条带百分率为90.3%。岩前、莘口和赤壁野生蕉居群内PCR扩增条带分别为155、148、130条,平均分别为11.9、11.4、10.2条,其中多态性条带分别是107、94、80条,居群内多态性条带百分率分别为88.6%、84.6%、75.4%,各引物扩增结果见表1。
2.3 100份野生蕉样本基于距离聚类的结果
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共100份样本ISSR-PCR电泳结果的数据,采用NTSYS软件运算输出聚类结果(图3),当遗传相似系数(GS)为0.69时,地理距离相近的岩前(Pop1)和莘口(Pop2)野生蕉没有聚到同一类,属于三明市的岩前野生蕉与属于福州市的赤壁野生蕉(Pop3)聚为一类,莘口野生蕉为单独一类。当遗传相似系数为0.70时,可将100份样本划分成3个大组,3个组(I、II和III)分别对应于岩前、莘口和赤壁野生蕉居群,100份样本的划分严格符合按照地理分布的群体系统。当GS为0.82时可将第I大组,即岩前(Pop1)野生蕉居群划分为3个亚组(I-I、I-II和I-III),样本10和12被单独划分开来。当GS为0.84时,第II大组亦可进一步划分成3个亚组(II-I、II-II和II-III),即莘口野生蕉居群(Pop2)的所有样本可完全地被划分到3个亚组中。当GS为0.91时,第III大组可被划分成4个亚组(III-I、III-II、III-III和III-IV),即赤壁野生蕉居群(Pop3)可被划分成样本数比较均等的4个群体,而样本95、96和99从4个亚组中单独开来。因此,100份样本符合地理来源划分成3个大组,3个大组分别进一步划分成3、3和4个亚组,其中个别样本被单独划开。
2.4 100份野生蕉样本基于模型聚类的结果
基于模型的STRUCTURE软件运算结果,K与△K的关系由图4-A可见,当K为3时,△K出现峰值,因此,100份野生蕉样本可划分为3个群体,群体聚类结果见图4-E,3个群体分别对应于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100份样本的划分与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完全一致,体现了STRUCTRURE软件群体聚类的正确性。进一步对居群内部进行STRUCTURE聚类分析,在岩前(Pop1)野生蕉居群中,当K为3时,△K出现峰值,表明能将Pop1划分成为3个群体(图4-B),群体划分结果见图4-F;当K为3时,可将Pop2划分成为3个群体(图4-C),群体划分结果见图4-G;当K为4时,可将Pop3划分成为4个群体(图4-D),群体划分结果见图4-H。综上所述,100份样本可划分成3个大群体,结果严格符合群体的地理分布,进一步分析发现,Pop1、Pop2和Pop3可分别再划分为3、3和4个次级群体。
2.5 基于距离和基于模型聚类结果的比较分析
比较距离聚类和模型聚类的结果可见,总共100份样本均划分为3个大组,3个大组的样本归属符合采样的地理来源,聚类准确可靠。再进一步对3个大组内部进行群体聚类时,2种聚类结果亦将3个大组划分成3、3和4三个亚组,2种方法的不同主要是亚组内个别样本的划分有所差异。NTSYS距离聚类和基于模型的STRUCTURE聚类在Pop1的划分中略有差异,首先表现在NTSYS聚类的I-I亚组的p23和p26两份样本在STRUCTURE聚类中分别被划分到了不同的2个亚组中;其次是Pop1中归属不明确的样本p10和p12在STRUCTURE聚类中被划分到了相应的亚组中。在Pop2的划分中,37个样本中只有1个样本的划分出现了差异,即样本p49在2种聚类方法中出现差异。而在Pop3的划分中,NTSYS聚类归属不明确的p95、p96和p99,在STRUCTURE聚类中被划分到同一亚组中。因此100份样本的2种聚类中,有2种差异,首先是样本划分差异,这些样本分别是p23、p26和p49,其次是NTSYS聚类中归属不明确的样本在STRUCTURE聚类中能够被划分到相应的群体中,这些样本包括p10、p12、p95、p96和p99,以上样本在NTSYS聚类中显示出独立的特征,可能是这些样本的遗传信息具有特殊结构。以上分析结果显示,2种聚类方法总体保持一致,将2种方法结合分析可以相互补充。
2.6 3个居群野生蕉遗传多样性分析
野生蕉群体间及群体内的遗传多样性可以通过相关遗传多样性参数进行衡量,3个居群野生蕉的ISSR-PCR结果经POPGENE进行遗传多样性参数计算(表2),观察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Nei'基因多样性、Shannon's信息指数、多态位点数目、多态位点百分率共6个统计量中,Pop1的6个统计量值均为最高,Pop2其次,最低的为Pop3。以上结果表明,3个野生蕉居群的遗传多样性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Pop1(岩前)、Pop2(莘口)和Pop3(赤壁)。
进一步分析显示,居群基因多样性(Ht)为0.280 2,群体内基因多样性(Hs)为0.171 9,基因分化系数(Gst)为0.386 3,基因流(Nm)为0.794 2。以上结果表明,野生蕉总的遗传变异中,38.63%来源于各个野生蕉居群之间,而61.37%的遗传变异来源于野生蕉居群内部,因此3个野生蕉中居群内部的遗传变异大于居群间的变异。
3 讨论与结论
3.1 距离聚类结合模型聚类的分析方法提高野生蕉样本聚类的准确性
NTSYS软件和STRUCTURE软件的运算方法,体现距离聚类和模型聚类的2种截然不同的模式,2种聚类方法都在各个研究领域中起重要作用。距离聚类可以根据不同的遗传距离或遗传相似系数查看样本间的关系,但是不同的遗传距离或不同遗传相似系数对应不同的群体划分,因此聚类群体的判别受人为影响。模型聚类可将距离聚类中归属不明确的样本划分到相应的群体中,而且可以通过查看Q值获得样本被划分到相应群体的概率,但是群体K值却比较难以确定,Evanno等[11]发展了K与△K在模型聚类中的关系,可根据△K确定K值,但是需要多次重复运算获得。
2种聚类方法各有特点,但是在同一研究中同时采取2种方法进行试验分析的报道较少,本试验结果表明,2种方法的聚类结果总体上保持一致,但是也有不同,首先是100份样本中,p23、p26和p49共3个样本在2种聚类结果中存在矛盾,其次是距离聚类中p10、p12、p95、p96和p99共5个归属不明确的样本在模型聚类中被划分到相应的群体中。秦君等[12]和吴承来等[13]在大豆和玉米的研究中,认为距离聚类中划分不明确的样本在STRUCTURE模型聚类中有正确的归属。2种聚类出现差异的结果可能由于这些样本的遗传基础相对特殊,说明本试验聚类分析的100份样本中的8份差异样本可能具有遗传特异性。因此距离聚类和模型聚类相结合,可掌握群体间或样本间的亲缘关系,解决样本归属不明确的问题,而且可发现群体中遗传基础特殊样本。
3.2 福建野生蕉自然居群间遗传背景相对独立
根据调查发现福建野生蕉不同自然居群呈不连续的片状分布,本试验结合前人研究结果发现,目前福建野生蕉15个分布在不同地域的自然居群已经通过分子标记研究。陈源等[14]对三明荆西岭(AB)和福州北峰无名山谷(AA)的2个野生蕉自然居群进行RAPD聚类分析,结果表明,野生蕉个体按各自居群聚在一起。张锐[15]也采用RAPD的方法对福州闽侯十八重溪景区、福州闽侯三叠井景区和三明尤溪3个野生蕉自然居群进行分子标记分析,3个居群的聚类关系与其地理分布呈正相关,聚类结果体现了3个居群各自的独特性。陈红俊等[10]采用ISSR技术研究了福建东南部共7个野生蕉自然居群的群体结构,结果发现只有分布在宦溪3个不同海拔高度的野生蕉居群间的亲缘关系与地理分布呈一定相关性,其他居群间的聚类结果与地理距离并无特定关系,但是289份样本严格划分到7个居群内部。本试验发现三明三元区岩前的野生蕉未与邻近的莘口野生蕉聚为同一大类,而是与相隔较远的福州永泰赤壁野生蕉聚为同一大类,莘口野生蕉独立开来,但是所有样本依然严格归属于3个地理来源的群体系统,因此,福建野生蕉自然居群间遗传背景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综上可知,(1)一定距离范围内的野生蕉自然居群的遗传背景与地理距离密切相关,超过一定范围遗传背景与地理距离的相关性不大。有研究结果表明,鸟类和蝙蝠不仅是野生蕉有效的授粉者[16],也是种子散布的重要传播者,前人发现犬蝠对小果野蕉种子的散布范围约为200 m[17],再经过鼠类、蚁类等地面动物的二次散布[18],范围可在200 m以上,但二次散布后种子的分布范围仍然有限,因此一定范围内的不同野生蕉居群可能源于同一原始群落的迁移或重建,而较远距离的野生蕉居群可能经过较长期独立的群落演变形成。(2)野生蕉自然居群具有遗传独立性,主要体现在野生蕉个体聚类结果严格服从相应群体系统,无论地理距离近或远的群体内个体与群体外个体的亲缘关系相对独立。原因可为2个方面,首先野生蕉保持较高的无性繁殖能力,并且可能占主导作用[7],其次是野生蕉呈不连续分布,有性繁殖中授粉方式可能以居群内授粉为主,群体间遗传交流受地理隔离,本试验结果表明,野生蕉总变异中61.37%的遗传变异来源于野生蕉居群内部,与上述推测相符。
3.3 水是野生蕉自然群落迁移和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
成熟野生蕉种子呈饱满、不规则,质地坚硬,淀粉含量高[16],进行野生蕉种子的田间播种发现,其萌发时间主要集中在初夏,而萌发时间与播种时间的关系未有特殊规律,可见野生蕉种子的萌发与种子特殊结构对水分的需求有密切关系,春季到夏季降水量大,正好满足了野生蕉种子萌发的条件,此不排除温度等自然因素对种子萌发的影响。Chin[19]研究发现,低含水量可以促使野生蕉种子进入休眠,而有利于种子保存,高含水量则是导致种子萌发的关键因素,可见水分对野生蕉种子的萌发具有重要作用,野生蕉在新环境重建的基础正是依靠种子的萌发[20-23]。曾惜冰等[24]研究显示,野生蕉个体水分含量可达97%[22],野生蕉分布于湿度大含水丰富的区域利于自身的生长发育,香蕉是水敏感性植物,因而水是野生蕉自然居群得以维系的关键要素。
水不仅是香蕉种子萌发和个体生长发育的重要影响因子,也是野生蕉群体迁移和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经调查研究发现,福建野生蕉主要分布于溪流附近或峡谷等湿度较大的地域,这与广东、海南、云南等地的野生蕉分布范围类似[21,24-25],而且发现相邻野生蕉居群鲜有水平分布的现象,主要呈垂直分布,而这种垂直分布主要沿水流进行,而且该区域流水带常伴有土表崩塌的现象,可带动该地带野生蕉的转移。唐占辉等[16]研究发现,犬蝠不直接在植株上进食,而是另选地方,能将大量种子传播到受干扰的生境,其发现这些地方往往靠近溪流,这些种子可依靠流水进行地理转移。本试验中的野生蕉可能通过水流进行迁移和发展,尤其是赤壁野生蕉正位于流水量较大的的溪流沿岸。由次可见,流水对野生蕉的迁移表现为2个方面,第一,水流对母株掉落的果实或种子具有由上往下的迁移作用,种子在原始群落的下游流水附近可重新萌发形成新的野生蕉群落;第二,香蕉根系浅,暴雨或长时间雨水冲击,土层松动,可导致野生蕉植株从原始群落转移到流水下游相应位置而进行群落的重建。因此,水影响野生蕉种子的萌发、个体生长发育、种子和植株的地理转移,是野生蕉自然群落迁移和形成的关键因素。
3.4 人为因素破坏野生蕉自然居群也促进野生蕉自然居群的重建
在调查中发现,福建野生蕉自然居群受到人为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忽视野生蕉具有的经济价值,而且有些罕见的野生蕉新种的分布地独一无二[26]。目前,多地野生蕉未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利用,野生蕉遭到林地开垦的盲目砍划,亦受到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破坏。福建福州、泉州、三明等地野生蕉自然居群不仅分布于人亦罕至的山间沟谷地带,也分布在人类活动频繁的林地或公路附近,群落本身及原生境受到严重损坏,如本研究中的岩前和莘口野生蕉,因此中国南方成片的野生蕉群落正在不断萎缩甚至濒临灭绝[27]。
野生蕉作为先锋植物,能在砍划迹地和森林林窗依靠种子迅速侵入发展[24-26],西双版纳野生蕉在入侵阶段,该区域植物群落由17个科组成,定居和扩散阶段达到50和55个科[24],植物群落的多样性水平不断提高,物种间总体竞争加强。研究显示,野生蕉对土壤养分含量吸收不大,生境水分充足,不与其他植物进行养分和水分的激烈争夺[26],随着群落演变,高大乔木逐渐占据上层空间[26],威胁野生蕉群落的发展。本研究调查发现高大树木和竹林对野生蕉产生竞争抑制,野生蕉在空间和光照的争夺中处于弱势,野生蕉居群可能最终消亡,因此野生蕉将依靠种子开始新一轮的入侵,这一现象属于野生蕉种子散布的逃避假说[21]。然而,在水分条件满足下,砍划迹地和森林林窗可为野生蕉的生长提供必要的光照和生长空间,而这种满足野生蕉群落重建的条件除自然形成,更主要是源于人类活动的遗留,人类的活动解除或缓和该区域植物群落的生存竞争,野生蕉通过种子的传播进行新环境的侵入和定居,而通过无性繁殖实现占据和扩散[21]。综上所述,人类活动导致野生蕉自然居群遭受破坏,人类活动也促进野生蕉自然居群的重建。因此,首先应通过对野生蕉原生境高大林木的适当清除,恢复适宜野生蕉生长的空间和光照条件对野生蕉进行保护;其次,人工创造野生蕉原生境模拟保护地,转移原生境受破坏严重濒临消亡的野生蕉加以保护;另外,采用组织培养的方式,建立野生蕉种质试管苗库,进行野生蕉的离体保存和繁殖。
参考文献
[1] Lescot T.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banana in figures[J]. Frui Trop, 2008, 189(155): 29-33.
[2] De Lapeyre de Bellaire L, Foure E, Abadie C, et al. Black leaf streak disease is challenging the banana industry[J]. Fruits, 2010, 65: 327-342.
[3] Dita M, Waalwijk C, Buddenhagen I, et al. A molecular diagnostic for tropical race 4 of the banana fusarium wilt pathogen[J]. Plant Pathology, 2010, 59(2): 348-357.
[4] 刘伟良, 王静毅, 魏燕雄. 现代生物技术在香蕉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应用[J]. 热带农业科技, 2009, 32(1): 49-52.
[5] 张妙霞. 野生香蕉(Musa spp., AB group)抗寒相关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D]. 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 2010.
[6] 郭堂勋, 莫贱友, 何禧严, 等. 广西栽培蕉和野生蕉抗枯萎病调查与鉴定[J]. 中国热带农业, 2008, 3: 49-50.
[7] 赖钟雄, 陈 源, 林玉玲, 等. 三明野生蕉基本生物学特性调查[J]. 亚热带农业研究, 2006, 2(4): 241-244.
[8] 吕柳新, 陈景渌, 陈晓静, 等. 福建若干品种类型香蕉的细胞学观察[J]. 园艺学报, 1986, 12(8): 169-174.
[9] 赖钟雄, 陈 源, 林玉玲, 等. 福州野生蕉(Musa spp., AA Group)的发现及其分类学地位的初步确定[J]. 亚热带农业研究, 2007. 3(1): 1-5.
[10] 陈红俊, 赖钟雄, 刘炜姬, 等. 福建东南部野生蕉7个自然居群289份样本的ISSR分析[J]. 热带作物学报, 2012, 33(12): 2 115-2 124.
[11] Evanno G, Regnaut S, Goudet J. Detecting the number of clusters of individuals using the software STRUCTURE: a simulation study[J]. Molecular ecology, 2005, 14(8): 2 611-2 620.
[12] 秦 君, 李英慧, 刘章雄, 等. 黑龙江省大豆种质遗传结构及遗传多样性分析[J]. 作物学报, 2009, 35(2): 228-238.
[13] 吴承来, 张倩倩, 董炳雪, 等. 我国部分玉米自交系遗传关系和遗传结构解析[J]. 作物学报, 2010, 36(11): 1 820-1 831.
[14] 陈 源, 赖钟雄, 赵巧阳, 等. 福州、三明野生蕉种群遗传多样性的RAPD分析[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37(4): 379-384.
[15] 张 锐. 福建野生蕉资源RAPD分析, 离体培养与SOD基因克隆[D]. 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 2011.
[16] 刘爱忠, 李德铢, 王 红. 西双版纳先锋植物野芭蕉的传粉生态学研究[J]. 植物学报, 2001. 43(3): 319-322.
[17] 唐占辉, 曹 敏, 盛连喜, 等. 犬蝠对小果野芭蕉的取食及种子传播[J]. 动物学报, 2005, 51(4): 608-615.
[18] 孟令曾, 高秀霞, 陈 进. 小果野芭蕉种子散布和不同时空尺度上种子被捕食格局[J]. 植物生态学报, 2008, 32(1): 133-142.
[19] Chin H. Germination and storage of banana seeds[C]. //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New Frontiers in Resistance Breeding for Nematodes, Fusarium and Sigatoka, 1995: 2-5.
[20] 施济普, 张光明, 白坤甲, 等. 人为干扰对小果野芭蕉群落生物量及多样性的影响[J]. 武汉植物学研究, 2002, 20(2): 119-123.
[21] 张光明, 唐建维, 施济普, 等. 西双版纳野芭蕉先锋群落优势种群的生态位动态[J].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2000, 9(1): 22-26.
[22] 唐建维, 施济普, 张光明, 等. 西双版纳野芭蕉先锋植物群落的结构特征及其演替动态[J]. 生物多样性, 2003, 11(1): 37-46.
[23] 陈晓雪. 3种香蕉苗期抗旱特性及抗旱评价指标的研究[D]. 海口: 海南大学, 2010.
[24] 曾惜冰, 李丰年, 许林兵, 等. 广东野生蕉的初步调查研究[J]. 园艺学报, 1989, 16(2): 95-100.
[25] 刘伟良, 王静毅, 黎 明, 等. 海南岛野生香蕉居群分布与居群内植物组成[J]. 中国农学通报, 2007, 8: 476-481.
[26] Ha··kkinen, M, Musa chunii Ha··kkinen, a new species(Musaceae)from Yunnan, China and taxonomic identity of Musa rubra[J].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2009, 47(1): 87-91.
[27] 张光勇, 陈伟强, 刘学敏, 等. 云南省野生香蕉资源收集及保存[J]. 热带农业科技, 2011, 34(1): 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