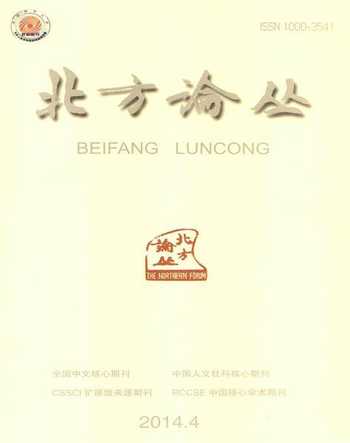“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2014-04-29张纹华
张纹华
[摘 要]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关键词]“九江学派”;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经学与史学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85-05
[收稿日期]2014-07-04
“九江学派”是广东近代重要的儒家学派,“九江学派”的学术思想中包含有相当丰富的经学史学思想。在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的著述中,清晰可见从“半截子”地明夫经史的分合流变,到将经学、史学导向非经学非史学的学术观念,这是分析广东古代学术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在近代出现裂变的重要线索。
有必要指出的是,1882年临终前夕,朱次琦将一生9种编著中的7种焚毁,现在我们看到的朱次琦文献多出自门人简朝亮之笔。“以著述传承朱氏学说”是简朝亮学术生涯的特点,因此,“九江学派”的学术思想多出自朱次琦,但离不开简朝亮的传承与巩固之功。
一、“半截子”地明夫经史的分合流变
经学史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两大重镇。从孔子以“六艺”教育门人与自著《春秋》以明心迹、两汉时期独尊《六经》与史学成为经学的附庸、宋明两代以博大、精微两途直寻孔子,到明末清初以来,王阳明、顾炎武、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在切于人事的“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下,提出“经学即理学”、“六经皆史”的口号,着眼于事实与历史经验,最终将经学导向史学。经学史学的上述分合流变潜藏于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成为分析中国古代学术的一条重要线索。“五学”治学章是朱次琦、简朝亮开馆讲学的内容之一。“五学”首列经学,次列史学,次指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史学旁支掌故学,反映朱、简二人主要是以经学史学的离合关系构建其学科门类的。由于朱、简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
首先,经学的主导地位。将《六经》作为具体历史经验的记载,后人必须从古籍的记录中学习儒道,这是朱、简二人对《六经》的一致看法,也是他们有别于王阳明、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说的主要观点。“《六经》者,古人已然之迹也。《六经》之学,所以践迹也。践迹而入于室,善人之道也。”[1](p.16)朱、简认为,治《六经》重于现实与偏于事,更要会通古人之义,此“义”就是儒家伦理道德。这是他们将经学作为主导地位与分析汉宋明清诸儒治经得失的根本方面。其实,朱、简的审视本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史学。在孔子以前,“六艺”已经以王官之学的形式传播,为孔子所学,孔子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王官之学自成一家之言,变成一种平民学。在汉人那里称为六艺,即《六经》——记载具体历史经验的六种古籍。《易经》属于哲学,《尚书》《春秋》属于史学,《礼》《乐》亦属史学,《诗经》属于文学。如此支离破碎的学术分科,殊非孔子之学。孔子之学在于会通“六艺”,关注整个人类社会。因此,朱次琦主张会通汉宋,“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 [1](p.15)朱次琦认为:“古无所谓理学,经学即是理学也。” [1](p.18)
孔子之学,大备于《论语》,惜汉儒将《论语》作为治经的幼学阶段,汉儒治经实未能深明孔学的真谛。反之,朱熹治经既直寻《论语》,也遍寻孔子之后学与继起 [2](p.30),其《四书集注》显得相当博大。因此,朱次琦将朱熹作为汉学、宋学的集大成,以《六经》、《四书》会通古人之义,彰显孔子之道。“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 [1](p.14)1908—1917年,简朝亮沿着朱熹一生精治《论语》之路,以《论语集注》为善本,兼及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刑昺《论语疏》,申明与修正朱熹《论语集注》,著《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直寻《论语》与《论语集注》,足见简朝亮越明清、会汉宋与溯诸古的治经理念。明儒治经单刀直入,讲求明心见性,经学遂显精微,故《六经》皆我注脚。朱、简二人的关注点殊非《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区别,而是心学家注经是否切于事与达于道。“陆子静,善人也,未尝不学,然始事于心,不始于学,而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善人乎,其非善人之道也。” [1](p.16)清儒治经以训诂、校勘、考证为工夫,此乃治古书,殊非治人事与明道义。故朱次琦说:“古今名家声音训诂,去其违而终之经谊,焉可也?” [1](p.17)简朝亮的《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述疏》等著作,皆以训诂、义理并重求为经学下新注。
其次,经史结合。经学重于理想,必上追三代。史学重于现实,当取法近世,且穷其源。从先秦儒家到明末清初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等史家将经学导向史学之前,将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是经史结合的根本特点。朱、简二人主张的经史结合也是如此。朱次琦认为:“史之于经,犹医案也。《书》与《春秋》,经之史,史之经也。百王史法,其流也。正史纪传,《书》也。通鉴编年,《春秋》也。以此见治经治史,不可以或偏也。” [1](p.17)简朝亮指出:“六艺之文,经学也。《书》与《春秋》,经之史学也。” [3](卷一,p.3)无论是作为经学的医案,还是必须限制在经学的范围内,史学都是不自由的,其不自由在于史学是经学的工具。
经史之本原在于道,经史之会也在于道[2](p.18),这在儒家史学的萌芽阶段便有体现。在“六艺”中,独《春秋》是孔子生平之著。据《孟子·离娄》,孔子指出其编纂的《春秋》的特点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1](p.175)“义”,是指宜,即儒道,故孔子自言:“志在《春秋》。”《春秋》与儒家学说的结合就在于这个道。也就是说,在儒家史学的最早源头,史学必须服务于儒家学说。这是它们可以结合也必须结合的根源。在《朱九江先生讲学记》一文中,朱次琦多次用到“谊”字。“呜呼!孔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谊乖,岂不然哉?” [1](p.14) “经谊,所以治事也。” [1](p.16)“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 [1](p.18) “有古谊然后有古文。” [1](p.18)这里所说的大谊、经谊、经史之谊与古谊,就是指“宜”,即是儒道。儒道成为朱次琦分析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的根本,也是经学史学会通的本原。
通经致用是经史会于道所必然体现的治学精神。将史学的价值定位为经世致用,率先体现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集中反映在所见世的哀、定、昭三朝历史当中。至汉宋,董仲舒之学见汉制,司马迁之学见国要,张载指出,要“以礼治国”,二程则认为,学者必须通世务,均主张通经致用。从明末至清中叶以前,在顾炎武、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推波助澜下,通经致用与社会改革相结合,使千年来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的角色出现大逆转。一方面,朱、简二人将致用作为读书的根本点。“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时而应天下国家之用。” [1](p.16)“所以图报天子养士之意,即所以报国。” [3](卷二,p.13)具体对经学的阐述时,朱次琦则强调通经的重要性。朱次琦认为:“经谊,所以治事也,分斋者歧矣。经学,所以名儒也,分门者窒矣。” [1](p.16)另一方面,朱、简二人强调的通经致用属于中国古代“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模式,他们提倡的经史结合旨在复兴儒学,不是属于明末清中叶以来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通经致用思潮的一部分。因此,朱、简二人虽然认为《尚书》与《春秋》是史之经、经之史,但与章学诚旨在将经学导向史学的“六经皆史”说是有很大区别的。
最后,史学的独立。在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谈论史学的完全独立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随着史家的涌现、史著的产生与史学理论的形成,人们自然而然地必须关注史学,于是,人们对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史学在人类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便越加深入,史学便具备了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独立的可能了。
1.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
在产生了《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等著名史书之后,史学终于赢得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首次将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是《隋书·经籍志》,在经、史、子、集4部中,将史书分为13类,正式奠定经史分途的学术格局,并延至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欲会通儒家大义,不能昧于古,因此,治史必通于经,经学也必待史学之穷其源并止于史。经史互通即朱次琦将史学作为“五学”其中一学的根本原因。朱次琦认为:“夫经明其理,史证其事,以经通经则经解正,以史通经则经术行。” [1](p.15)以经通经、以史通经就是简朝亮阐述经史大意、考订名物典章制度的重要方法。本于经史互通下对史学的重视,反映史学依然是以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的。
掌故学是打通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等的一种新的史学体裁。嘉庆、道光年间,由于近代私家藏书著述丰富与经世致用兴起,经济有补实用,掌故则有资文献,掌故学出现繁兴。近代掌故学始于龚自珍,同时期的俞正燮也极大地促进了掌故学的影响。首次将掌故学作为一种学科来教育门人,并取得显著效果的是朱次琦。朱次琦认为:“《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通《九通》,是谓不通……掌故之学,至赜也。由今观之,地利军谋,斯其亟矣……知掌故而不知经史,胥吏之才也……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则辞章之发也。” [1](pp.17-18)凡关涉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利、文物、制度等均属于掌故学的范围,朱次琦将掌故学摆在一个等同于经学、史学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简朝亮进一步强化掌故学的时政性。“掌故之学则求其可行于今者。古之掌故,序于经,志于史。今之掌故,自国史所书及凡所为政书是也。时务之书皆掌故也。昨之邸报,今之掌故也。” [3](卷一,p.25)古之掌故学与经史相结合,今之掌故学即是国史、政书、报刊,简朝亮将掌故学从中国古代的旧学拉进了新学的领域,与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重视掌故学是相当一致的。王韬建议分十科考试,以废科举,十科中便有掌故学。康有为认为,“故学者不辨士民,不可不通本朝掌故矣。不通本朝掌故,不齿于士,或犯宪典,且不足为民矣。” [5](p.91) 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延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将掌故学作为专门之学教育学生。1903年,张百熙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掌故学与经学、史学等纳入文学科,使掌故学作为一门学术门类奠定下来了。
2.史学理论的传承与丰富
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经历了产生、形成、发展与终结四个时期,对朱、简二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宋代史学与明末清初史学。“资治”意识使宋代史学出现极大的繁兴,与“资治”意识一脉相连的是明末清初发生在史学领域的经世致用思潮。朱、简二人对于史学的阐发与有功于广东近代史学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是源出于此。
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始,宋人的“资治”意识可谓蔚然成风。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地方志的编撰;二是出现奏议集、纪事本末体等;三是注重以史学重振儒学;四是注重研究本朝史与撰写野史笔记。宋人“资治”意识的诸种表现,在朱、简二人的一生中多有表现。朱次琦为乡人冯栻宗编纂的《九江儒林乡志》手定采访条款,朱次琦在肯定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的贡献时,指出《毕氏续资治通鉴》的不足之处,1932年,简朝亮开始著《酌加毕氏续资治通鉴论》,成为简朝亮的未竟之书。朱、简二人的经史互通论,是以儒道为本的,其意即在以史学重振儒学。《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征实录》《晋乘》《论国朝儒宗》《纪蒙古》是朱次琦临终前夕焚毁的7种著述。“国朝”即是朱次琦生活的清王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4](p.112)《纪蒙古》是朱次琦根据1852年出使蒙古见闻所写的著作。因此,朱次琦注重本朝史研究。反之,简朝亮以经明理,以史证事,切于时弊。简朝亮认为:“《书》以道政事,今从事在《书》,不曰是亦为政乎?” [3](卷二,p.28)简朝亮强调指出:“《礼》时为大,夫时者,非谓其时俗也,谓其时义也。” [3](卷五,p.30)简朝亮以回归经典关注他所身处的时代。
顾炎武提出的经学即是理学,着重挖掘与发挥了经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实际上是将经学导向史学。一方面,朱次琦欣赏顾炎武的节义与著作。“顾亭林读书亡明之际,抗节西山。《日知录》遗书,由体及用,简其大法,当可行于天下。” [1](p.16)另一方面,朱次琦明了顾炎武提出经学即是理学的实质,对它进行了修订。“顾氏之言是矣。虽然,性理诸书,剪其繁枝,固经学之佐也。” [1](p.18)宋明理学属于哲学。以理学佐经学与经学即是理学,其意是有天渊之别的。前者承认宋明理学,试图将理学导入经学,以本于儒道实现理学经学会通。后者则是对宋明理学的瓦解与反动,成为清学的出发点,经世致用是顾炎武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本质,只是后来转入了乾嘉经学。正因为朱、顾二人的学术脉络大异,虽然朱、简二人的经学史学思想是取法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但它并不属于清代考证学,也与章学诚、魏源、龚自珍等非正统派将经学导向史学以图实现乾嘉学术大解放是不同的。反之,理学家是朱、简二人的身份。这不能不说在审时度势与真正明夫经史的分合流变这一点上,朱、简二人是比不上章、魏、龚诸家的,也就是在经史分流的最后一站,他们止步了。朱、简二人旨在维护儒家传统,让他们将历史从经学中分离出来是完全没有任何可能的,他们就成了笔者以为的“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流合变的人物。
二、将经学、史学导向非经学非史学
在史官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儒家史学,由孔子、孟子、荀子初步构建了儒家史学的理论框架。孔子在“六义”中独著《春秋》,将儒道会通于《春秋》,遂尤重《春秋》,在儒家思想的发端期已经明显体现经史结合的痕迹。从先秦至明清时期的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等史家出现之前,以经学为主导的经史合流一直以来都是经学史学发展的主要模式。这就使得在厌倦经学,或对儒家伦理道德产生怀疑的情况下,从历史学与哲学的层面使经学导向史学成为了可能。将经学导向史学的这两种路径分别由章学诚、王夫之启引[2](p.32)。这两种路径在康有为的学术中都有体现,但都偏向了现实政治,遂陷入了非经学非史学的境地。
第一,从历史学上将经学导向非经学非史学。经世致用是使从历史学的层面将经学导向史学的根本缘由。在王阳明、顾炎武、章学诚、龚自珍、魏源之前,包括董仲舒、司马迁、二程等在内的汉宋诸儒都十分重视经世致用,他们都以治史的方法治经。真正从历史学的角度,将经学回归于它的本原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认为,《六经》、儒道并不是义理心性,而是具体的历史经验的记载。嘉道咸丰以来,公羊学复兴,龚、魏二人将经世致用指向了社会改革,开启了康有为将经学史学导向社会政治的先河。
嘉庆、道光年间,庄存与、刘逢禄等常州学派的主要人物据《公羊春秋》以维护封建统治。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更以《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发表政治见解,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嘉道以来形成的以《公羊春秋》为中心的今文经学复兴是对乾嘉经学脱离社会实际的反动。庄存与治《公羊春秋》,专求其“微言大义”,企图对封建旧秩序进行调整。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治经,并引出了改制变革的新意。生于末世的龚自珍、魏源则对汉以来的今文经进行了改造与批判。龚自珍治经不主训诂章句,不主谶纬附会,而重在阐述“微言大义”,既将六经还原为历史的记载,也逼近了对封建专制统治这一个严峻主题的思考。从魏源开始,今文经学家大攻《毛诗》《毛诗序》,甚至开始质疑《六经》。摆脱汉代今文经学繁琐无用的学风,将通经致用与改革时弊相结合,嘉道以来的今文经学其实已经与汉代今文经学相去甚远了。
在《教学通义》《民功篇》等早期著作中,已经体现了康有为非常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到了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时,康氏将这种致用精神发挥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治经并不是康有为所长,也非其所愿。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明显呈现的将治经导向治史的倾向,由于康氏只愿在发动维新变法,已经将所有的传统治学家法打乱了。康有为既在刘逢禄、魏源、邵懿辰等质疑古文经甚至认为,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基础上,将古文经全部打倒,也将今文经改头换面,变成宣传变法的工具,使得经学的源头变得让新旧人士都震惊惶恐。与乾嘉经学只求其事实非寻其大义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不求其事实而主观地寻其大义,从史学的源头到释经的方法都失去了可信性,而得出来的所谓“微言大义”即康氏本人的大义。康有为从经学到史学的这种治学路数,将经学的人文精神与史学的科学精神都丧失了。与嘉道以来的今文经学思潮既指斥六经,也主张改革时弊,但未能提出社会改革的蓝图相比,康有为是借助被其改造的今文经学呈现其维新变法的宏伟蓝图。因此,康有为笔下的殊非传统的今文经学,其作为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的身份则更多的是指向社会政治一面,而殊非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
在《六经》之中,唯《春秋》是孔子所著,孔子的“微言大义”重在《春秋》,这是孔子、孟子、董仲舒等诸儒尤重《春秋》的原因。一千多年后,康有为也以此尤重《春秋》,撰写《春秋董氏学》。《春秋》所蕴含的儒道精神依然是康有为关注的重点,经史结合依然是康氏经学、史学的观念,康有为让时人震惊的著作是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作为注脚的。治史非康有为所长,也非其所愿。由“据乱”经“升平”到“太平”,由“君主专制”经“立宪民主”到“共和民主”,康有为将自己的变法维新思想装在了古老的“公羊三世说”里,这个历史发展观又与“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论紧密联系在一起[6](p.109)。同时,康有为认为,“升平”、“立宪民主”是实现“太平”、“民主”的必经之路,否定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飞跃、革命与不连续性,康有为的历史观属于典型的改良主义的进化论[6](p.110)。康有为以“公羊三世说”古老的社会发展模式承载他的维新思想与哲学思想,使作为史学的重要源头《春秋》变成康氏的变法工具。与王阳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以图使“六艺”剥去所有的外人强加于它们的义理心性不同的是,康有为依然是在强化《春秋》的教化功能,并且是以个人的教化取代《春秋》本来的儒家教化。因此,《春秋董氏学》已经殊非传统的《春秋》史著,史学已经非史学了。
第二,从哲学上将经学导向非经学非史学。从孔子著《春秋》开始,史学便成为宣扬儒家思想的工具。在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至明中叶以前,所有的儒学家都将历史的发展统一在性善恶、天命、心体等儒家哲学的范围内。这种以尊德性为主导的道问学,至王夫之的出现遭遇严重的挑战。王夫之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最后的集大成者,在对宋明理学的改造、批判、发展中,王夫之既强调“道”在“器”中的唯物论,也发现以“礼”为架构,以求善、求治为取向的所谓伦理性的天理未能解答与决定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转移的。王夫之这种石破天惊式的质疑,使儒家伦理出现了信用危机,使儒家哲学的本体论与历史意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认识到儒家哲学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一只不可预测的手在干扰着,那么,儒家传统伦理便变得空白无力,将历史的发展独立于儒家伦理之外,逼近于客观的存在便成为可能。但是,王夫之的历史观依然是从属于儒家伦理学的范围,他未能在哲学上将历史意识完全摆脱儒家的道德审判,他依然取法理学,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
历史将取替经学而成为主流,王夫之从哲学上所提出的问题,由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体系的瓦解者康有为继续,并使经学史学的古代传统在近代终结。“以元为体”的发展的自然观与“以仁为主”的博爱的人生观,是康有为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以无为体”的自然观上,康有为甚少关注儒家伦理,他坚持朴素的唯物观,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声光电气等科学名词,与《春秋》“三世说”相结合,强调以宇宙万物来探讨历史规律与社会人生。这是康有为将儒家哲学导向具有近代化气息的地方之一。在“以仁为主”的人生观里,康有为反“礼”主“仁”,并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仁”的内容。传统儒家有等级、有差别之“仁”便荡然无存,正统人士遂将康有为视为洪水猛兽。与博爱哲学连在一起的,是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康有为主张“性无善恶论”,将儒家一直以来割裂开来的性、情、欲加以弥合,反对禁欲主义,主张现世之乐。康有为既将“仁”包含在“礼”之中,打破“仁”、“礼”调和与互补的儒家传统格局,也将求善指向地上之乐,更以此对儒家伦理的改造展现其维新变法的内容,实现所谓的求治。
“以元为体”的自然历史观并没有使康有为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学者,他依然跟王夫之那样,将伦理学与宇宙论相提并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 [7](p.65)所不同的是,康有为以博爱改造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宇宙的看法则增加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同时,康有为没有像王夫之那样热衷于探讨儒家的伦理价值,判断儒家的历史传统并非康氏所愿。因此,康有为没有明确指出只有历史才是儒道的本身,没有在哲学上将史学从数千年来的经学的附庸中摆脱出来。而且康有为将经学史学均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内容,使经学史学导向了非经学与非史学。
考证学、今文经学是清代学术的两股主流。以复兴传统儒学为己任的朱次琦、简朝亮的学术思想不属于清代学术的主流,这是他们没有将经史的分合流变坚持到底的原因。与朱、简二人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以完成朱、简二人没有完成的任务。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并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因此,若从学术层面来看,康有为并没有完成朱、简二人经学史学分流的最后一步。若从政治层面来说,将反对八股文、科举制作为百日维新的内容,并在短短几年内使科举制最终废除,经学最终失去其生存的空间,史学的独立就近在咫尺了,康有为是将史学彻底从经学中摆脱出来的。1901年、1902年,由于反对二十四史都是宣扬儒家学说的工具,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提出要将儒家史学全面打倒。1921年、1926年,梁启超分别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侧重于分析史学的体裁,对于儒家史学思想依然是持批评的态度。从对儒家史学的批评到侧重于研究史学的体裁,梁启超将史学研究引进一个新的纯学术的领域,以经学史学为内容的广东近代学术也宣告终结。
[参 考 文 献]
[1]朱次琦,简朝亮,关殊钞.朱九江先生集[M].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会,1962.
[2]简朝亮,梁应扬.读书堂集[M].广州:广州伏书堂,1930.
[3]范学辉,齐金江.儒家史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康有为,姜义华,吴根樑.康有为全集:第1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7]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作者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中国史博士后)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