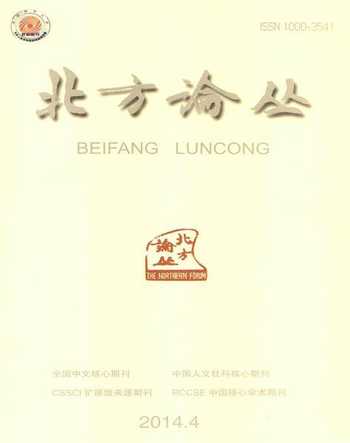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
2014-04-29田恩铭
[摘 要]采摭诗文入传是史书中常见的传记文本的书写方法。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是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史家的采摭往往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以之为媒介继续传播。采摭诗文入传的意义在于:诗文入传构成传主形象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点自《史》《汉》以来莫不如是;诗文发挥文章的政教意义;诗文作为文学文本往往确定传主的文学家身份;采摭诗文入传发挥了保存一代文章的特殊功能。
[关键词]中古史家;采赋入传;历史化语境;文本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35-05
Literatures Wonders Outside its Context:
A Perspective on the Ancient HistoriansPlanting Biographees
Writings in His Biographies and Effectuating Some Classic Literature
TIAN En-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There used to be such a popular trend from Han Dynasty that historian quoted plenty of biographeesodes, poems or prose and planted these quotations into their biographical works, which came into a tradition that it was a must for a historian who wanted to convey his understanding of a particular biographee and the biographees writing style to readers. In the case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plant the biographees writings into his documents. By quoting the biographees' writings, the historians caused these literature texts spread more broadly and come into being classic literature as the historians works spread. There are four aspect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lanting a biographee's writings into his biograpghy: Firstly the quotations can provide a more vivid image of the biographee for readers, which was so essential a practice that we have not found any exceptional examples from all the biographical works ever since Han Dynasty; secondly, the quoted writings worked as a means of expressing the historians moral value and outlook of the world ; thirdly, the quotations worked as a means of identifying the biographee as a professional writer. And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by planting a biographees writings into the biography, the ancient historian preserved and transfer some literature texts to people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Key words:Middle ancient; planting poems or odes or prose into a biography; classicalizing literature texts
[收稿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代胡姓士族与文学研究”(14BZW047);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经典化进程研究”(2014T70277);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中古史传文本中的非写实叙事研究” (2013M530965)。
刘熙载在《艺概》中认为:“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既知其人也。”“读其赋者既知其人”是史家刻画人物形象的出发点,经典文本的介入自然增强了传记文本的文学意味,只是这需要读者予以“知人论世”式的解读,而对于史家来说,这些被采摭的赋作与文本的结合往往暗含了自身的文学观念。如此说来,史传文本所包含的文学观念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书写方面,文本构成中的“成文”介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传记文本中大量地采摭时人诗文入传,对于文学家形象书写和文学观念的传达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书写视角。采摭诗文入传是史书常见的传记文本的书写方法。而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以文学文本而论,《史记》《汉书》《后汉书》主要是采赋入传,而采摭赋作入传与文学文本的经典化进程关联甚深,渐次形成了借助以文论人并进而传达文学观念的书写策略。
一、境中有象:汉代史家采赋入传的考量因素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云:“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若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来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1](p.80)章氏“以文传人”的观点揭示了入传人物的文学家身份与采摭赋作的关系。这段评论大体叙述了采赋入传的意义变化,实际上从宏观视野上看采赋入传对辞赋的经典化也会产生影响,我们不妨就此寻根溯源。
史家之重点在记事、记言,故而编年、纪传之体多有采摭文章入传者,《尚书》《左传》《国语》已经出现。正史之中,初成于《史记》,只是《史记》采文入传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而是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注重写人,录文见其人之性情,尤其并不很重视文章的政教意义。到了《汉书》则大不一样了,本时代政教观念的高扬必然会注入史家所撰的文本之内,例如《史记》和《汉书》均采摭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但是,处理的方式又不尽相同,《史记》是通史,屈原、贾谊因后者之吊文而合传,司马迁仅采摭两篇赋作入传,而《汉书》则不同,除此以外,又采摭其疏奏入传,并以“掇其适于世事者列于传”为标准。《史记》《汉书》均采摭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入传,应该是班固也认为,司马迁所选文本具备了“适于世事”的标准,因袭者首先要确认原创者的观点符合自己的标准,才能取彼以代己。
如果刻意比较一下《史记》《汉书》采摭赋作入传的动机,则可见两者相异之处。《史记》采摭之标准在“太史公曰”中,用章学诚的话说,则“名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亦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而在传记文本中则说:“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本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2](p.3698)将这两段话结合起来,首先可见赋作为一种文体被独立出来,在西汉的被重视程度较其他文体要重要得多;其次,赋的讽喻功能也得到了太史公的认可,故而被采摭入传则源于文体之功能和文学影响。《汉书·艺文志》也有一段关于诗赋之用的阐释: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3](pp.1755-1756)。
显然,班固认为,赋作之讽喻意义日渐衰颓之后,汉乐府取而代之。故而在采赋入传中逐渐树立了一个自觉的标准,如《汉书·贾谊传》:“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如前所述,班固全袭太史公《司马相如传》,采摭文本亦无变化,正在于认同了太史公的见解,所采“尤著公卿者”正是被公卿们认为有意义的文本,而有意义对应的正是“切与世事” 。《扬雄传》也大量采摭其赋作,并张扬其观点以抒发己意:“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故而,扬雄赋作被大量采摭入传。采摭诗文入传从史家的立足点来说存在着实录文献和因文见人的书写意图。从源头上说,《汉书》确立了“正史采文之体式”,“《汉书》继踵前规,复加改良,非但所录经世有用之文倍屣于前,且于剪裁登录之方法,亦远较《史记》为严密理想”[4](p.62)。但从增加采摭的文章来看,还是以诏令、奏疏居多,更多的是处于有益于政事。正如前文所述,汉代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纯粹的雕虫之作主要在娱乐功能上,史家亦多持批判的态度。“《汉书》修订《史记》采文之方式,体肃例严,易于遵循,厥后正史遂递相祖述,奉为定法”[4](p.64),对于实录文献多从政事方面考虑,也符合大一统时代的著史目标。
二、境象之间:范晔采摭汉赋入传与文学经典化的生成
《汉书》采赋入史之方式虽然成为“定法”,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何况班固对于赋体的认识并不是从文学艺术角度展开[5](p.103)。在“质文代变”的过程中,自然还会被后来人所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到了范晔《后汉书》,文学一科已经渐渐独立出来,面对入传人物自然多因一种基于身份认证的自觉意识张少康在《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文学的自觉》中认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中期开始初露端倪,而到西汉后期刘向校书时基本完成”。(参《人文中国学报》第九期,第27页。)张峰屹认为,虽然西汉文学作品“文学意味浓厚”,但还不能说文学已经独立。参氏著《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从立传形式上来说,《文苑传》的出现意义重大,被目为雕虫之技的文章家单独占有了一个单元,某人往往是因为具体文本的影响而厕身其间。采摭诗文入传也就不仅仅是为了政事,而是有了回归文学自身的审美倾向。
《后汉书》设立了“文苑传”,从弘扬史家的文学观念来说,确实具有里程碑性质,“文学”终被目为一科,入选的作者也自然具有了文学家的身份。《后汉书·冯衍传》采摭《显志赋》一篇,冯衍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他“不得志,退而作赋”。《后汉书·班固传》采摭《两都赋》入传,云:“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规,乃上《两京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论述中心仍在赋作所具备的讽喻之功能,又采摭《典引篇》入传,“追述汉德”并“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虽然意在讽谏而文学意味颇浓,传文中亦突出班固以文而得宠 ,走笔至此,文学本位观念也就显现出来了。《后汉书·张衡传》采摭《思玄赋》入传,张衡作辞赋之原因是“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传记的开始部分还提到《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只是“文多故不载”。值得注意的是《崔駰列传》所叙的崔篆、崔駰、崔瑗三代人均长于赋,文本采摭崔篆《慰志》、崔駰《达旨》入传,又突出了崔駰、崔瑗的“善属文”。
《后汉书·文苑传》采摭杜笃《论都赋》入传,“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崔琦上《外戚箴》,“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采摭《刺世疾邪赋》入传。赵壹因“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又为“舒其怨愤”而作《刺世疾邪赋》;采摭边让《章华赋》入传,评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史家采摭的赋作虽多为发愤之作,印证了文人的不护细行,却也保持文学文本的特质。此外,《梁统列传》提到了《悼骚赋》《祢衡传》提到了《鹦鹉赋》故事。马芝《申情赋》、傅毅《七激》也被采摭到传记文本之中。可以说,自《后汉书》设“文苑传”后,采摭诗文入传以追求传记文本的文学审美特征的趋向渐次形成,并且被定格为一种常态,并且能够见出史家文学观的倾向性之所在。
《后汉书》不仅采赋入传,更是在传记文本中记录了作品的留存状况,如《桓谭传》:“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冯衍传》:“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 《班固传》:“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最为详尽的是《蔡邕传》:“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从上述著录中可见,赋体之独立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范晔的这种著录方式并不是最早的,却形成了史传文本集中著录文献的传统。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曾经有所论述,现代学者王瑶、傅刚等人续有申说,郭英德先生《〈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文则追述了自《史记》至《后汉书》的著录变化之过程,对其归类方法、问题排序原则详加勘定,认为从著录次序上“表现出从汉末至刘宋区分文笔的文体辨析观念已趋于明朗”[6](p.88)。自此以后,文学家传记文本述及传主作品流传往往较为翔实,大多以文类及作品篇数述之。由是观之,“文学的自觉”至范晔所处的刘宋时代已然尘埃落定了。
《史记》《汉书》《后汉书》采摭汉赋入传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传记文本自身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是否还具有文学观念史层面上的研究价值?叙事文本中的采摭诗文入传已经成为一种可供研究的现象,由此出发,是否为有利于探讨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毫无疑问,所采摭的诗赋俱为经典之作,经过史家的再度高扬是否会产生经典化的传播效应?至少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构成了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的一条传播路径。
三、境中象外: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经典化生成史的关系
刘宋以后的史家不再以采赋入传为主,随着对文学的自觉认识,诗文俱入眼帘,文学文本的多种文体介入进来,文学经典化进程也因传播空间的拓展而加快了。采摭诗文入传是传记文本书写结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从文学意义上说,《史记》《汉书》《后汉书》主要是采赋入传,而采赋入传亦成为以文论人的书写策略,当然也造成了文因人显的效果。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以“前四史”中的汉代文人传记为中心,从采摭诗文入传考察“文学的自觉”过程;以初唐史家所撰“唐初八史”为中心,从采摭诗文入传探讨文化秩序的重建与采摭诗文入传的关联;以两《唐书》为中心,透过采摭诗文入传形成以“唐宋转型”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除了关于汉代的传记文本以采摭赋作为主,以汉以后为对象的正史传记文本则诗文兼采,这也是文学观念嬗变所形成的格局,这仍然要经历一个渐变的过程。沈约《宋书》并没有设专门的《文苑传》,但是在相关的文学家传记中还是采摭了不少诗文入传,辞赋为数不少且多经典之作。如《谢灵运传》采摭《撰征赋》《山居赋》,都是具有文学意味的作品。尤其《山居赋》作为文学文本采摭入传确认了谢灵运文学家的身份。颜延之则采其《庭诰》入传。总体说来,沈约虽为一代文宗,《宋书》却是本着史家身份确立的书写意图,故而采摭诗文主要也并不在文学之事,还在政事一途。
依史传中“文学的自觉意识”而言,萧子显《南齐书》是一个分水岭。从传记分类来说,王融、谢朓并入一个单元,显然是以文学为划分标准的。虽然文本中采摭王融的作品主要是书奏,传文却突出了他以文学见长的一面,如谓:“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传云:“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 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可见其文名传播之广。《谢朓传》在文本中屡有提及其有文才之句,如“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又如“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敬皇后迁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尤其采摭《赠西府同僚》诗入传,采摭《辞随王子隆笺》文入传意义犹大。《文学传》入传人物虽并不都以文学见长,与《后汉书》相比,传文中更具文学本色。丘灵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齐颇减”, 卞彬的作品“传于闾巷”, 丘巨源“作秋胡诗”,陆厥“五言诗体甚新变”。采摭文章也偏重文学性,如卞彬《蚤虱赋序》、丘巨源《与袁粲书》、陆厥与沈约的论文学之书信等等。传后所《论》,更见魏晋以来文学演进之轨迹。要而言之,至《南齐书》乃有文学家之基本格局,论述亦显文学之气息。《魏书》虽有《文苑》,传文多据《北史》补入,故不具论。
从时序上说,中古时期文学观念在史传之中愈加清晰,采摭诗文的目的也由以有益于时政逐渐多元化起来,可是并没有进入成熟的运作状态。只有到贞观之际,“五代史”才将采摭诗文的考量标准确定下来,史传文本进一步推进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化进程。与前代相同的是,《隋书》采摭诗文入传的目的主要并不在文本自身具有的文学价值,也仅仅作为传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书写内容上往往侧重采摭那些与传主的政事活动形成相关联系的作品。与《隋书》相比,《梁书》采摭诗文入传的特征更为明显,采入作品明显增多,基于文学自身的考量逐渐成为标准,特定时代的文学意味也就在文本中显现出来了。大量采摭诗文入传至少证实了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丰盛,也是对文学家辈出现象的一种诠释。如以人物身份分析,萧梁帝王及其家族作品入传为最多,《梁书》中史臣采摭诗文入传确实展示了本时代文学之既有格局,也将史家的文学观念一并呈现出来。《陈书》更进一步,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格局关系进一步得到加深,入传诗文往往代表了陈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同时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文学观念,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家身份定位变得密不可分了。《北齐书》多采摭本土人物的作品,《周书》则以由南入北的文人作品为主。作品风格上,《北齐书》以学南土的风气为主,《周书》则多尚北地之气质。文学家的作品被采摭的数量、质量往往决定着在本时代的影响力以及文学文本在后代的接受状况。这样看来,采摭诗文入传也是文学格局构建的一个必要的参考因素,影响着文学文本在传记文本中的意义生成。
四、文中象外: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经典生成史的关系
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正是入传诗文的经典生成史上的重要一环,与中古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之形成关系甚深。我们可以从《史记》到《后汉书》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单元,透过采摭诗文入传进入文学接受史的研究视域,实际上是拓展了“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7](p.80)。从而探讨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经典生成的关系、文人传的出现与采摭诗文的关系、抒情文本与叙事传统的关系。中古史家采摭汉代诗文入传往往会将本时代的文学观念书写出来,当下的文化取向能够确定采摭诗文入传的标准。史家采摭诗文入传还能够呈现文学秩序重建的历程。初唐时期是南北文学交融的关键阶段,透过初唐史家采摭诗文入传可以看出地域、士族等因素对文学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艺文类聚》等类书对于采摭诗文也影响颇深;采摭诗文入传关系到了文学秩序的重建[8](p.128)。史家采摭诗文入传展示了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交融。对于文学功能的不同理解,两《唐书》采摭诗文入传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采摭中唐的柳宗元、吴武陵、白居易等人诗文入传方面透露出唐宋文学思想转型的端倪,所采摭文本在文学史或者文学批评史上都被经典化了。自西汉以来,史传文本自以求真为本,但是,透过以采摭诗文入传而形成的文本介入书写能够体现出史家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精神,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所著文本的介入,更是表现出了本时代文体认同和文化转型时期的某些征象。史家的创作形成了一个编码的过程,传记文本就是所编就的产品,这需要阅读者来解码。从传记文本内容上说,因文学经典的介入往往形成了文本的张力,推缓了阅读者的接受速度,进而以文学经典的言说判断文本的内在意义与形象定位,最后推断出史家所持的倾向性。
那么,采摭诗文入传的意义何在?首先,诗文入传构成传主形象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点自《史》《汉》以来莫不如是;其次,诗文发挥文章的政教意义;再者,诗文作为文学文本往往确定传主的文学家身份;最后,采摭诗文入传发挥了保存一代文章的特殊功能。如此看来,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是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通过史家的采摭入传往往确立或者巩固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以之为媒介继续传播。中古采摭诗文入传创造了一个历史化的传播语境,将文学经典因作者形象书写而介入传记文本,文以人存,人因文显,一个文学家的形象方能呼之欲出。周宪在论及文学经典的“现代性编码”时借鉴哈里斯(Wendell V.Harris)的观点,将“历史化”引入经典的功能论述之中。“特别是一些特定的作品在特定时刻具有某种特别的力量,而其他作品则没有,所以经典具有牟总需要解释的历史化力量”[9],这种“历史化力量”往往超越了经典本身的功能,介入历史文本之中于特定时刻发挥出阐释的意义。这样史传文本就与选本、类书、文论、诗话一起构成了文学接受史的一个流动通道,透过这个通道能够还原经典,也可能重新阐释经典。
一旦将采摭诗文入传与文本经典化联系起来,我们对于传记文本的分析也就溢出了文学作品研究的范畴,转而进入了文学观念史的研究领域,自然会引出另一个研讨对象,即史传文本所描绘的文学史图景与本时代的文学经典的关系。传记文本之间的链接很容易展示出史家心目中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的历史现场,这其中与儒家士人的历史担当相关的文本自然会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歌咏的主题”[10]。自从《后汉书·文苑传》出现以来,以史家为中心的文学史谱系的生成不再是奢望,虽然不免因正统文学观念而降低了可信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这句话倒是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只有沿着这样的思路扩散开去,研究者围绕史家针对入传人物所采取的组合方式、传记分组的设计、史传专栏的序论、采摭成文入传展开探讨,从而将这些内容列为文学观念史的研究对象。实际上,通过从整体上阅读传记文本分析其文学意义,然后将传记文本再拆成片段分析其文学史意义,将史传文本所采摭的文学经典放在叙事传统里加以研讨,这必将成为一个有独特的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参 考 文 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吴福助.汉书采录西汉文章探讨[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
[5]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M].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田恩铭.初唐史传与文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
[9]周宪.经典的编码和解码[J].文学评论,2012,(4).
[10]王洪军.玄鸟生商经典化意义及文学场景构成[J].北方论丛,2014,(1).
(作者系吉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