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起人生的画架
2014-04-29陈子诺
陈子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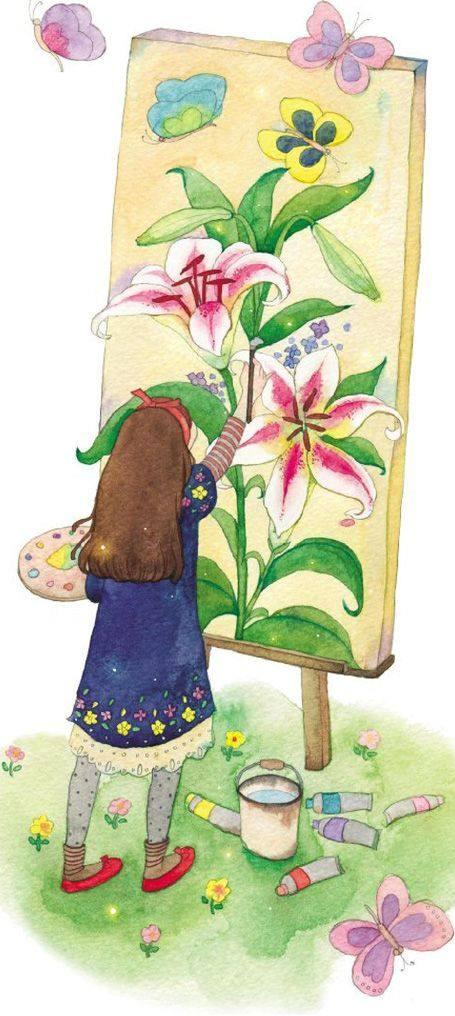
四月的明媚阳光下,我支起了画架,开始画记忆中的金色年华。
起稿
不管画什么都要用铅笔起稿,灰黑的线条流淌在白纸上,像极了简单又纯粹的童年。
小时候我被父母呵护得太好,以致到了三年级还不敢独自过马路。每当父母不在身边,面对大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我憋红了脸也不敢迈出半步。那时,她就会伸出温热的小手抓住我的小指说:“小诺,小诺,我带你过马路。”我就这样被她牵到了马路的那一边。
她似乎是除父母之外,第一个给我力量与勇气的人。
她就住在我家隔壁,只大我三个月。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画画。那年,几乎每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她身边,看她画桌上某个石膏像,或放在边上的一盘水果。此时,她身后的小紫茉莉静静吐露着芳香。
她画画时的沉静与专注让我惊讶,不知不觉中,我也爱上了画画。
明暗
六年级下学期,我的成绩一直在中游徘徊。我仍爱画画,也爱在穿衣镜前跳最新潮的爵士舞。
离毕业考还有100多天,她代表六年级学生在大会上发言,坐在报告厅一角的我望着主席台上的她,忽然就觉得睁不开眼。她是那样的耀眼,不是我所能接近的,莫名的悲伤排山倒海般袭来,原来,我们已隔了那么远。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跟在她的自行车后,戏谑地喊了声:“哎呀,大班长!”她回过头无奈地笑笑,随即正色道:“小诺,你真的要努力了。”我甩甩头,故作潇洒地说了句:“就这样吧。”她咧咧嘴不再说什么,我看见她在夕阳的余晖里越骑越远。
毕业考成绩出来那天,她在电话里问我:“你到底还想不想上嘉一中?”我说了声“不想”后,直接挂掉。毕业考的成绩让我认清了现实,我已做好上普通初中的准备。
令我没想到的是,她下午竟跑到我家来,跟妈妈说要找我。我听了赶紧将房门紧锁。
我把耳朵贴在门背后,听见她反反复复跟妈妈说:“嘉一中的入学考资格来之不易,阿姨,一定要让小诺去参加考试啊……阿姨,小诺只是有些贪玩,她成绩还是挺好的……”
她的话仿佛一束光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照亮了我未来的岁月。我冲出房间,说:“我要去参加,去试试。”
我攥紧了她的手,请求她再给我些勇气与力量。
然后她笑了,眼里却有晶莹的泪光。
那天,我开始了由暗到明的渐变。
上色
清亮但不失厚重的水粉在画纸上铺开,一如我们鲜艳明丽的青春在绽放异彩。
去参加嘉一中入学考的那天清晨,她来为我送行。去考场的校车将要发动时,她挥动双手向我喊:“小诺,加油!”左手腕上戴的是我送给她的白色手表,透明表盘在阳光下闪着晶亮的光,犹如她眸子里的一缕粲然。
虽然最后我考试失利,落选嘉一中,但我和她都坚信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她一起度过了一个悠长而惬意的暑假。我们每天到公园写生,那些鲜活生动的日子宛若一片片金黄的叶子,在记忆的长河中那样耀眼夺目。
我和她都知道9月之前,她将要随父母搬去别处生活,但谁也不提这个话题,只是不停地用色彩表达属于彼此的明媚与忧伤:暖黄色代表快乐,水蓝色表示忧伤,轻盈的浅紫色则是十五六岁少女的浪漫幻想。
我时常会在为线稿上色时幻想,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个叫荷兰的国度找梵·高,找他失落在一片蓝紫色鸢尾花里的那枝暖黄色郁金香——毕竟那是她最爱的花。
别离的那一天,我们站在公园的小河边,她指着那棵我们描画过很多次的古槐树,说:“刚在上面系了祈福的红丝带。若你能幸福,我也会很幸福。”望着在风里翻飞的红丝带,一瞬间我觉得从大树的枝叶间投下来的光影都充满了关心和爱。
……
起稿,理明暗,上色,日光底下我支起的画架上已经有了完成的作品。然而我不确定是否能用拙劣的画笔,一点一点勾勒出曾经那些真实的快乐和忧伤。
那时候,她握着我的手,在童年画卷上画的几笔,宛若春日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前程,温暖了我的心。接下来,就让我背起大大的画板,独自去更远的地方追求梦想吧。
起稿,理明暗,上色——每一幅画的完稿都预示着另一幅画的起笔,正如人生的每一个成功都是下一个追求的开始。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