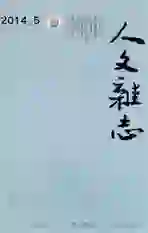盩厔县尉白居易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
2014-04-29徐畅
徐畅
内容提要我们对唐宋城市变革发生以前,中国中古的城乡关系、城乡区别与联系,目前还缺乏明朗的认知。虽然有学者讨论了唐都长安与其近郊地理单元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但专及长安城乡人口流动及相关问题的论著甚少。本文以文人官员白居易为例,关注其元和初年在长安近郊盩厔任县尉及此前后在长安任职的经历、行踪,通过诗文揭示的他的思想、言论、视野,探讨士人的长安城乡流动以及城乡观念,并深入中唐社会变革背景下的长安城市与乡村,从负责“收率课调”的县尉之视角,了解两税法下新的财税政策在基层执行的实况与问题。
关键词盩厔白居易长安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5-0070-13
引言
在唐宋之际城市变革发生以前,从秦汉到唐中叶,城市与乡村,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法律上的地位,在社会文化中的基调,还是在国家礼仪中所扮演的角色,均未有显著区分。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者有感于此,曾提出中国“城乡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框架。Frederick W. Mote, “The C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James T. C. Liu and Wei-ming Tu eds., Traditional China, Prentice-Hall , Inc., 1970, pp. 42-49;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1-154. 中译本: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叶光庭译,收入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12-175页。城乡之别,仅在于自然形态之不同,一般而言,城市四周为夯筑或砖砌的高大城墙所环绕,城墙外有护城河,城内有封闭的坊市,以居市民并展开贸易,而城门之外,是散布的墟、野、丘、渚、川等自然聚落。依物理形态的划分并不绝对,至唐代仍有部分县以上治所没有围墙,但亦有村为“郭”环绕的情况,参见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收入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158-161页。唐王朝建国伊始,官方对乡里村坊的基层建制即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63-64页。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村作为城外百姓居住地通称的地位。而元和年间敕文中将城居民人称为“坊郭户”,与“乡村户”对举,元和四年五月敕:“诸州府先配供军钱,回充送省。带使州府,先配送省钱,便留供军,……宜令于管内州,据都征钱数,逐贯均配。其先不征见钱州郡,不在分配限。如坊郭户配见钱须多,乡村户配见钱须少,即但都配定见钱。”参见王溥:《唐会要》卷58《户部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78页。方肇始中唐以后制度化的城乡分离。以全国最大的城市——首都长安为例,城坊、乡村之区隔仍依唐令,外郭城以外即有散布的乡村,刘再聪依据吐鲁番出土《唐质库帐历》证明长安城内新昌坊与城外小王村、王祁村的分界是延兴门,并考证了西京三苑附近的村落,见其《唐朝“村”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40-43页。郊县之乡村更是星罗棋布。借助石刻材料考订长安、万年两县城外的乡里村名及其地理位置,相关成果很多,如武伯纶:《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爱宕元:《唐代两京乡里村考》,《东洋史研究》40卷3号,1981年,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年,第3-23页。仅爱宕元搜集了京兆府诸畿县下的乡村,见所著《唐代京兆府•河南府乡里村考》,《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國家と地域》,刀水书房,1999年,第163-190页。但京华烟云却逸出了物理上的禁锢,与周边的川原连为一体,遥相呼应,形成文化、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大长安”,本文称之为“长安城乡”,包括长安、万年两县外郭城以外及邻近畿县下的乡村。以地理学区域研究的核心与边缘理论来观察,参考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之导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长安城乡”的一体化,体现为一座城市,因周边乡村提供的人力、物力,自然与人文资源,因平原、高地、河流、山川的拱卫,而具有京邑的核心地位,如陆贽对京、畿关系的理解:“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新唐书》卷157《陆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913页。物资、人员等在城乡之间频繁地流转与交换,物流的情况已有学者论及,张天虹:《物流与商流:唐长安——变动中的都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虽然长安城的流动人口研究也是热点,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参见荣新江、王静:《隋唐长安研究文献目录稿》,《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22辑,2003年,第57-86页。但专论都城与郊乡小区域内人流的论著迄今未见。
2014年第5期
盩厔县尉白居易的长安城乡生活体验
我们注意到,京兆府乡村百姓常因服役、番上宿卫、从事转运等出入长安城市,据史料记载,长安城城池、宫殿、官廨、宅第、寺观、道路等建设,劳力主要来自近畿;如《旧唐书》卷4《高宗纪》:“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板筑三十日而罢,九门各施观。”中华书局,1975年,第73页;卷9《玄宗下》:“和雇京城丁户一万三千人筑兴庆宫墙,起楼观。”第227页。牛来颖认为,长安城市建设中不仅劳力先从京邑及畿内征发,经费可能也主要是来自城市居民所纳之“地子”,见氏撰:《论唐长安城的营修与城市居民的税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110页。开元后拱卫京师的十二万“长从宿卫”,取京兆及近辅州府兵及白丁;北衙禁军,取京旁府州士;《新唐书》卷50《兵志》, 第1326-1328页。连在京诸司执役的诸色职掌人,也是“徧出京兆府”。《广德二年(764)南郊赦》称:“其京城诸司,应配彍骑官、散官、诸色丁匠、幕士、供膳、音声人、执祭、斋郎、问事、掌闲、渔师,并诸司门仆、京兆府驿丁、屯丁诸色纳资人,每月总八万四千五十八人数内,宜每月共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东、关内诸州府配,不得徧出京兆府。”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69,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85页。而文人官僚城内坊里宅第加城外山林别墅的城乡生活模式,在当时也极为普遍。中国古代知识人“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4页。非居于名都大邑,则归于山林溪谷。政治中心长安与城东灞浐、城南樊川、鄠杜、郊县密布的乡村,妹尾達彥统计到唐代不同时期官员在东郊的别庄25处,南郊别庄66处,氏著:《唐代長安近郊の官人别荘》,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刀水书房,1988年,第125-136页。这两重世界,为他们寻求“仕”与“隐”,“兼济”与“独善”,实现人生理想,提供了可进可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