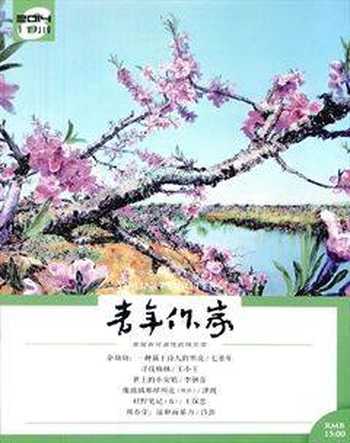成都,从谜语开始
2014-04-29李迪
[成都之谜]
还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谜语,谜面是:“1949年10月1日”。还没看要猜什么,我就笑起来,这是谁出的谜语?真傻!还用猜吗?国庆节呗!大不了多几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会是什么?可是,拿眼往下一找,哇噻,谜底要猜:三个城市名!这回,轮到我傻了。啊?一个日子,猜三个城市名?这……结果,脑壳进水也没有猜到。眼巴巴盼到第二天晚报来,急忙翻看昨日谜底,居然是——
重庆、北京、成都!
还是没明白,为什么是这三个东东?
语文老师说,咱们北京早先就是中国首都,后来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49年10月1日,北京又重新成为首都。所以,重新庆祝北京成为首都——重庆北京成都!
哎呀,真有高人,瞧这谜语出的!
谜底大白。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个城市叫成都。
[听成都人说话]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没去过成都。直到后来,1969年夏天,我上山下乡来到云南农场,两年后又从农场来到驻滇部队,在陆军四十二师宣传队当了文艺兵,认识了来自成都的战友。那天早上,听到两个人说话,一个是唱歌的鲁牛,一个是跳舞的庆生,两个都是成都人,他们的对话,真好听,真好玩,真成都!
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很冷,又是周日,大家都缩在被窝里不起来。只听鲁牛小声叫庆生——
庆生,庆生,我跟你说,昨天装台,我抬着一个木箱直傲牙(咬牙),龟儿好沉!余光里看见前头有个女娃儿也抬了同样一木箱。我好不容易放下,一看那女娃儿是彭玲玲!庆生,二天(以后)你可不要惹她哦,你莫看她瘦哟,她劲儿好大!
庆生好像还没睡醒,嘟嘟囔囔地说:你说啥子!
鲁牛说,我说跟你跳芭蕾舞的彭玲玲,你莫看她瘦哟,她劲儿好大!那天我看到她跑到礼堂那边的茅房切(去)方便,我在宿舍外正跟老乡在摆龙门阵(聊天),玲玲方便完后往回走,晓不得是哪个男兵躲在窗子里拿小镜子反射太阳光晃她的眼。我正摆得高兴,突然后背咚地挨了一砣!我回头一看,玲玲捏着拳头瞪着凤眼狠起吼,鲁牛,你为啥子要晃我!我疼得龟儿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我说,苍天啊!大地啊!我啥子时候晃你罗,哎哟,哎哟!—直到现在,天阴下雨我背上挨的那一砣还疼得很!所以嘛,庆生,你跟她两个跳芭蕾,你跳大春,她跳喜儿,跳就跳罗,你可不要惹她哦!
庆生说,你龟儿子乱说啥子嘛,把我的觉都搅得睡不成。我哪儿会像你,骚鸡公!你听到起,你起床了就切把我的漱口缸整点热水哈,天冷球的很,我牙齿遭不住(受不了)。
鲁牛说,你龟儿想得还美呐,我凭啥子给你整热水?上个星期天,我喊你把我的胶鞋拿到太阳坝子里切晒一下,你都懒球得拿!
庆生说,你妈说啥子哟,昨天浇菜地回来,你尿涨了,跑到哪儿切尿了,你的锄头是不是我扛回来的?你晓得嘛!
鲁牛说,我啷个不晓得,你豆是(就是)动下嘴的嘛,是人家赵青帮扛回来的!你不要豁我(骗我)!
庆生说,你晓不晓得,你那双胶鞋起码三个月没有洗了,不要说让我切拿了,方圆一公里以内的人闻到都得戴口罩!臭死个人!再说了,你昨天给哪个美女献殷勤的,我都瞧到罗,你不把我的漱口缸整点热水,我马上揭发!
鲁牛说,好好,你就莫说了,我这就起床切给你把热水整好放口缸里还不行嘛!
庆生说,你快点切整!
鲁牛说,莫慌,等我把裤儿穿起,总不能光着鸡儿切啊!
听听,成都人说话,多好听,多快乐!
四十多年后,我们这些老战友欢聚一堂,青春成过往,两鬓多染霜。浓妆掩面妇,昔日美娇娘;如今白头翁,也曾少年狂。聚会中,圆号一吹,庆生跟老搭档彭玲玲再跳一曲芭蕾舞《北风吹》。彭玲玲也是成都人,一个演大春儿,一个演喜儿,舞姿不减当年。一招一式,婀娜多姿,把一帮老头儿老太太都带回了浪漫青春。
双人舞最后有一个经典造型,喜儿要站在大春儿的膝盖上,高端洋气上档次。可是,你想啊,毕竟老啦!大家起劲儿鼓掌,加油给力。
彭玲玲上了两次都没成功,庆生鼓励她:再来嘛,来!
彭玲玲说,我怕把你的老骨头踩垮喽!
余庆生笑道,我还怕老婆婆万一掉下来中风那才麻烦哟!
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两个成都人上膝盖成功!
[交上成都朋友]
谁呀?成都画家刘学伦。
当初认识学伦的时候,也是在师宣传队。那时,他手里拿的不是画笔,而是琴,一把中提琴。他在我窗外的树丛下认真拉着,发出鹅叫。
我问,你拉的什么曲子?
他说,亮猪!
什么?
我再问了一遍,才明白他说拉的是《梁祝》。
这也叫《梁祝》?梁山伯祝英台两位大英雄谁放过鹅呢?好像谁也没放过。拉《梁祝》居然拉得像鹅叫,也被招到师宣队来充数,去四川招人的朱队长是不是拎了人家的腊肉?说不定还是青城后山的老腊肉呢!
我冤枉了朱队长。学伦来自成都一书香门第,高挑、白净,鼻梁奇怪地凸起,别具一格。他的特长不是拉琴学鹅叫,而是画画。用笔蘸上颜色能在纸上大闹天宫!所以,在师宣队,他负责画舞台布景。我呢,写剧本。两人配合默契,臭味相投。学伦画的布景真叫绝,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一双球鞋和其他杂物。打扫礼堂的老胡,躬着腰走上去,嘴里嘟嘟囔囔说,是哪个把柜子抬在这儿放着!说着,要把它搬走。手一伸,才发现是画的,眼珠子瞪得掉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学伦先后离开了部队。我回到北京,学伦回到成都。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各自从事编辑工作。后来,他又调到位于成都双流的西南民族大学,成为艺术系教授。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學伦已经成了著名画家。最近看到他画的巨幅国画《金沙祭》,悲怆的场面让我悚然、让我震撼、让我泪从心中涌。前不久,他荣获电影学院最佳优秀指导教师奖,前来北京领奖。我去接他,约好的时间,约好的地点,出站的人流几乎散尽,我却怎么也没找到他。正疑惑,正踌躇,忽然背后有人拍我肩。回头一看,正是他!只见他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像戴了一顶白色的羊绒帽。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会在人流中错过他。因为,我要等待的,我要寻找的,是那个在树下用中提琴认真地把《梁祝》拉成鹅叫的高挑、白净、鼻梁奇怪凸起的“托玛”,而不是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
这一刻,我才觉得什么叫老了。
我们都老了。
但我们都还活着。
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坐上成都“?耳朵”]
我转业回到北京后,因为写作,有了稿费。虽然每千字只有六块,可是,那是什么年代啊!七十年代,钱值钱啊!五毛钱可以大吃一顿!有了钱,我就带着爱人和孩子自费旅游,第一站就来到成都!
那年月,出门没听说谁住宾馆的,什么四星五星啊!大家都穷,都投亲靠友,更没听说过公款消费。当然了,我就住进刘学伦家。第一站去成都,也是因为成都有他!真是好战友啊,夫妻俩把唯一的卧室让给我们住,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外間的小客厅里。学伦家住在磨子桥,一个名字很好玩的老街巷。也许以前那里有座桥?好像没看到。也许,以前桥两旁就是制作或出售用来磨麦子或杂粮的石磨的集中地?好像也没看到。吃的直接就是大米白面,就算有人制作或出售石磨也鲜有成交了。
磨子桥的街上很少见到小汽车,连公共汽车都不多。当时成都老百姓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大家都骑车,马路用不完。出租车是什么?就是在自行车旁边焊一把小椅子,客人坐在椅子上。一车带一人,司机用力蹬车前行。这车有个很奇怪的名字,我是从学伦嘴里听到的。我们出去玩,近处走着去。远处呢?怎么去?学伦说,坐“?耳朵”!我没听明白。什么耳朵?等他带我们来到巷口,叫了一辆改装好的自行车,让我坐上去,我才笑起来。我问,这车为什么叫“?耳朵”?他说谁知道啊,大家都这样叫。我坐上去,晃悠悠,很舒服。又看看小椅子焊在自行车一侧,很像自行车长了一只耳朵,也许这就是起名的原因吧。我把坐后感告诉学伦,他笑着说,不对,不对,谁长一只耳朵啊?说完,他摸摸自己的耳朵。我侧目一看,的确,他长了两只耳朵!这个“?耳朵”之谜,直到去年岁尾,前来成都参加《青年作家》组织的“文学名家看成都”采风活动,诗人叶延滨才为我解开。他从小生活在宽窄巷子,对成都民俗了如指掌。他说,这种“?耳朵”,原先是老公带老婆出门用的,比如去菜市场买菜呀。老公蹬车,老婆坐车,很安逸。为什么叫“?耳朵”,是说老公怕老婆,或者说爱老婆,耳朵根子软,一切听老婆的。成都话管软叫“?”,“?耳朵”就是软耳朵,犹似当下的“气管炎”(妻管严)。老婆说去菜市场,老公说来罗!忙推出“?耳朵”让老婆坐下,又叫一声坐稳,然后使力蹬起车子,全心全意前往老婆指定的地点。这样,一来二去,这种车就被喊成“?耳朵”。再后来,在成都交通工具不发达且人人都穷的日子里,这种专供老婆用的“?耳朵”,被挖掘出载客挣钱的特异功能,于是成都的大街小巷,“?耳朵”车水马龙。噢,我明白了!当年我们坐上去,司机问去哪儿?我们说去杜甫草堂!司机叫一声坐稳,然后就使劲蹬起车子,全心全意前往我们指定的地点。很听话,也是“?耳朵”!还是在此次采风的路上,成都诗人叶浪又补充说,这个“?耳朵”的说法,最初是从农村来的。农村养狗看家,厉害的狗耳朵总是直立着,胆小的狗耳朵就爱耷拉着,被叫成“?耳朵”。何时由狗说到人,由农村进化到城市,时间有待考证。哈哈哈!说罢,叶浪笑起来。笑声是成都口音,带诗人气质。
所以我要用这么一大段来讲七十年代成都的“?耳朵”,是因为成都现在再也见不到或极少见到“?耳朵”了!犹如磨子桥见不到石磨。
可是,当年,“?耳朵”给我们带来多少穷欢乐啊!你想想,两家人,大人加孩子共六口,出行一次就要叫六辆“?耳朵”。六辆“?耳朵”,浩浩荡荡,出没于成都大街小巷,蔚为壮观!而且,很便宜,好像是五毛,还是一块。更为难忘的是,我们一家小住成都期间,磨子桥那个巷口外,从早到晚就停了一大排“?耳朵”。为什么?就为等候我们从巷口出来!那年月,“?耳朵”再便宜,也是奢侈品。坐的人不多,钱很难挣。所以,干这行的,口口相传,说这巷口里住了从北京来的有钱人,一出来就要六辆“?耳朵”!于是,个个推车守候在巷口,从早到晚,排成一排,眼巴巴等我们出来。也蔚为壮观!
俱往矣,这一道成都风景再也不会有了!
当下,守候在繁忙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外排队等客人的出租车,浩浩荡荡,恰似长龙。用北京话说,那叫“扒活儿”,就是等客人。也是一个“P A”,但此“?”非彼“?”!
三十多年过去了,成都像一个老人,慈眉善目白发三千,从远古的金沙向我们走来;成都又是一个青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繁花似锦;成都还是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天府新区眼下还是荒郊野地,可通天大道已在修建中,一个全新的成都将要诞生。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地方,城市与文学发展应该产生很好的作品。
[作者简介]李迪,侦探推理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十余部中长篇侦探推理小说、报告文学,其侦探推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发表后,相继在俄国、法国、韩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