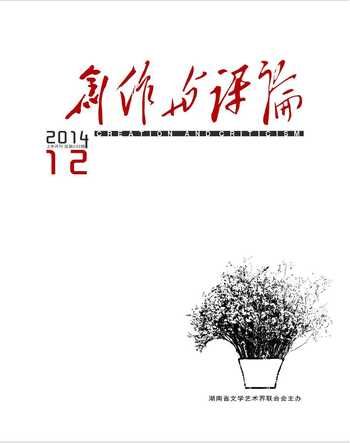民间伦理和乡土文化的深层叙事
2014-04-29柳冬妩
柳冬妩
在广袤的乡野之地,遥远偏僻的山间小村落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发酵之下,往往拥有着无形而强有力的乡村自然伦理和生存法则,乡土自然伦理像一把双刃剑在引领人们由内而外的生存秩序的同时,也对人性造成无形的挤压和伤害,揭露出乡村风物愚昧、麻木的阴暗一面。社会规范有多种形式,而在带着浓重泥土气息的偏远山间村落,民间自然风俗伦理所呈现出的规范和行为约束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它应该是出现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行为规范。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千百年来形成的礼维系并统治着偏远乡村的生存秩序,这种礼杂糅着儒家文化、繁琐的民风民俗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生存秩序与礼所代表的强大的生存逻辑紧密联系在一起,影响着每个人的内在精神秩序。 莫华杰的小说《碑伤》中出现的牛头山这个山间小村庄偏远而闭塞,十分封闭,整个村庄基本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这样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生存环境无疑为牛头山村民的内在精神生活秩序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
作为80后小说的新生力量,莫华杰近年来展现出十分良好的创作势头和爆发力。相比于80后聚焦于青春迷茫与疼痛的文学书写,莫华杰的着力点,明显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莫华杰的小说紧接地气,带着深厚的泥土气息,显得沉稳扎实许多。他以聚焦千年传统文化和传统叙述的方式深入历史,挖掘出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弊端所在。但其小说传统叙事之中却往往带有文本实验性,这一点大大增加了其小说的生动和活力。
《碑伤》延续了莫华杰小说的特质,但相对显得平稳一些。小说用细腻而优美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厚重而轻盈、闭塞而悲伤的乡土世界。连绵潮湿的山雨以及逼仄狭小的山神庙,都渲染出一股压抑窒息之感,这恰好与小说的主题吻合着。传统村落看似自给自足风平浪静的生活,其实暗流涌动。它表面看似平淡自由的生存方式,其实隐隐衬托出民间自然伦理约束下专制高压的一面。《碑伤》呈现的正是这种在民间自然伦理高强度的制约下的人生百态和生命悲剧。小说以刻碑为切入点,通过小孩子阿狗三番两次恳求“我”把他母亲的名字刻在墓碑上的举动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我”作为一个外村人,夹杂在寺庙和两者之间,处于十分两难的境地。“牛头山需要建庙聚仙,一可庇护众生,二可繁荣后人。捐了款的人都可以上功德碑,当然有些家庭出了伤风败俗的人,名声恶臭,即便有心捐款,庙里也不会要,也不会上功德碑。”小说的聚焦点就在此。阿狗的父亲早些年看上隔壁村一个寡妇的牛,和寡妇睡觉,半夜顺手偷牛。结果被人们抓了个现行,寡妇一气之下,说阿狗的父亲不仅偷了她的牛,还强奸了她。刚好赶上严打,当场被枪毙了。牛头山从来没有出过强奸犯和枪毙的人,强奸犯的老婆自然不能上功德碑。小说紧接着就围绕阿狗为了能让母亲上功德碑所做出的努力铺展开来,最后阿狗不幸为此丢掉性命。纵观全篇,阿狗的出现给全文涂抹上了一股温暖又悲情的基调,阿狗的一言一行更是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结尾处被逼疯的徐桃花惨死在山上的寺庙里,人们见到徐桃花在山神庙的神案底下,一副死不暝目的表情,不但没人同情她,反而纷纷指责,甚至破口大骂,责怪她怎么能死在这里。牛头山的人一致认为徐桃花是瘟神,败坏了牛头山的风水,咒她死后不能超生。而山神庙,因了阿狗和他母亲徐桃花的死也只能废弃。人性的愚昧和麻木在这里被刻画得淋淋尽致,轻易间就让人想起鲁迅小说《药》笔下带血的馒头。
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中阐述小说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视点——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式,叙事的无穷魅力某种程度上在于叙述视角的精确把握。《碑伤》中作为刻碑人的我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但文本中时而跳出来的评判话语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说的感染力。在小说的叙事上,叙述者的隐匿与掌控显得尤其重要,在小说中,叙述者是作者在小说中的全权代表。讲故事的这个人不是作者(文本的创造者),而是作者在文学作品中设置的讲故事的人。在叙述语调上的精准把握与否,自然会成为衡量一篇小说质量的标准之一。卡夫卡的小说无论是第一人称的视角还是独特的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其小说叙述的语调都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客观、冰冷而又平铺直叙的叙述语调,仿佛一个冷眼直视的旁观者,令人心生震撼。叙述者像以元叙述零介入的姿态紧贴着故事行走,冷靜客观,不发表任何评价。在小说《碑伤》中,叙述者的语调和情感倘若再隐藏一点,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小说结尾处,“我将刺碑用的铁锤和钢凿,一并埋入了阿狗的坟中。我从此之后不打算再刺碑了,觉得所谓的功德碑,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的手段罢了。然而,真正有功德的人,是无须立碑的。”这句话显得有点画蛇添足,模糊了叙述者与作者的界限。当然,这些瑕疵的存在依然不影响其成为一篇佳作。
题目作为小说的文眼,显示着一个小说家的水准。碑伤,碑之伤,暗喻人性的悲伤与幽暗面。现代社会人最悲哀的是一问一答,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试图去寻找出一个相对应的完美的答案。小说文本意义的无限开放性给作品本身的无限内涵提供了多种可能和不确定性,而作家则应该放下姿态,力图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文学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这样才能激发文学作品的活力与深度。在小说文本中,山神庙和碑这两个道具都弥漫着浓重的象征隐喻味道,这给整部小说涂抹上了多种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山神庙,这个在乡间祭奠叩拜先祖的地方,带有鲜明的个体家族生命图腾的印记。但这种对个体家族生命图腾的崇拜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虚无性。纵观20世纪乡土文学,与家族生命繁衍传承相关的庙宇都呈现其消极保守封建的一面。仔细思索,能从山神庙这寸小之地窥见其精神价值以及村里百姓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困境所在。
“五四小说中的祠堂社庙村规家谱,好比一个个祖先崇拜、尊尊亲亲的家族伦理的文化隐喻,祠堂隐喻新文学作家眼中的“乡土中国”,昏暗阴森,却如铁罩一般冷酷强大地屹立着,代表现代文明的“疯子”则势单力薄,难以撼动,最终还要成为它的祭品。”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吕若涵在《文学中的“祠堂文化”》中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可谓一语中的。而小说《碑伤》中,村里人不约而同地对阿狗和他母亲徐桃花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不屑,则呈现出宗教法制吃人于无形之中的一面。
小说中阿狗以及他母亲的悲剧,除了揭露出人性愚昧麻木的一面,也反衬出民间自然伦理和乡土文化在村里所占据的位置,它几乎根深蒂固,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封闭性和隐忍性作为传统乡土文化的几个突出特点,使得乡土文化形成了一种专制文化,而在封建余孽思想的侵袭腐蚀之下,乡土文化更是具有了一种食人般的野蛮性。个体家庭作为形成乡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在乡土文化占据主导统治地位,并拥有着几乎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的情景下,处于十分压抑和悲哀的境地。小说中牛头山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还没有受到现代都市社会的入侵,村落基本上处于几千年来传统农耕社会的自治状态,山神庙象征着千百年来牛头山在时间的暗流之中所缓慢形成的乡土文化,这种村落在具有传统中国乡土文化共性的同时,也呈现着其独特的一面。阿狗和徐桃花这对母子的出现和行为,顶撞了山神庙所代表的牛头山乡土文化,而这种乡土文化无疑是愚昧麻木、扭曲人性的。然而在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乡土文化氏族文化面前,家族命运和个体命运显得不堪一击。
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在现代工业气息无孔不入的趋势下,民间乡土伦理和乡土文化必将经过新一轮的过滤和构建。莫华杰借一个带有几许民间艺人色彩的刻碑故事,指向时代发展进程中民间伦理和乡土文化的历史内核,颇具批判性和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