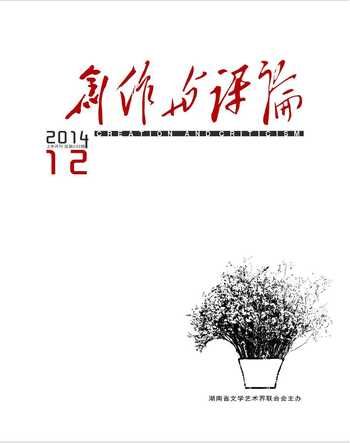烧梦(短篇小说)
2014-04-29林培源
一
盛先生把地图摊开,钟敲了三下。他取下烟斗,磕掉残余的灰烬。窗外日照朗朗,屋里却透出一股凉意。他戴上老花镜,细细察看摊在桌上的地图。这张地图,印制于1992年。那是最近一次修县志时,夹作附录用的。归国前,盛先生将连册地图小心裁下,如此一来,他就有了关于这座县城的“新形象”。盛先生对旧县城并不陌生,他曾无数次翻阅刊刻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县志,将县城的房屋、河道、郊区等铭记于心。乾隆年间的这本县志初版为木刻版,纂修者叫金廷烈,盛先生家中藏有一套(总计六册);另一本县志刊刻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李书吉、王恺修编纂,和上一本相比,足足迟了五十一年。1992年版的县志,则是精装的,配彩图,记录了这座县城的建置沿革、水文地理、文化习俗、发展概况等。他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搜到这本。
三本县志,在时空中排列,如跳跃的音符。
盛先生当然知道,历史不可能呈一条直线,它更像一只线团,线头凌乱,藏匿起人的身世和起源。从这点看,他倒分不清哪一部县志描述的,才是真实的县城?或者说,本就没有真实的县城,一切已经被时间的河流洗刷了,漂白了。只有盛先生知道,记忆不会被漂白。
摊开的地图,纸面光滑,似乎还带着从县志上裁剪下来的温度。
盛先生的手止不住哆嗦了几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注意力更集中些。他的感官还没有适应这种视觉的迁移。现在他所站的,就是他念兹在兹的故土,他抬头望向窗外,灰尘在光线中飞舞。越接近核心,内心越是难以平静。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铅笔,又摸出夹在笔记本里的便签条。眼前浮现出机场里女孩的脸。女孩的字迹,有一种未被时间淘洗和侵占的干净。盛先生捋平便签条,凑近去,从她画的简略路线图上寻找地图上的对应点,再写到本子上。他现在有些后悔,为什么当初不直接拿地图让女孩指认?可惜已经晚了,机场分别后,女孩就登上大巴,继续她未完成的旅行了。
盛先生这才想起,他忘了问女孩的名字。盛先生还记得她脸上的讶异:什么?你六十年没回国了?盛先生笑笑。接着,女孩拿出手机,打开地图软件,照着手机上规划的路线,给盛先生“指路”。盛先生从来没遇过这样的指路,仿佛他们是在一张虚构地图上行走,女孩指完路,就暂时缺席了。
这种缺席,盛先生再熟悉不过了。离乡那天起,他就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某种缺席,缺席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青苔。他至今仍记得,游轮驶出港口那一刻,他望着凄茫茫一片大海,落下了悲怆的泪。涌动的人潮中没有他熟悉的身影。一切隔阂了,连同头顶的天空,也都漏了一角。雨水毫无征兆地倾倒下来,乘客纷纷躲进船舱,只有他愣愣站着,任凭冷雨兜头浇落。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对未来沉重的想象黏上了他。他想知道,那片人人趋之若鹜的土地,真的就美好如天国?信教的母亲临死前,紧紧抓住他的手。告诉他,快走,走了就好。母亲衰弱得只剩一把骨头了,而沉迷于抽大烟的父亲,却永远留在了对岸。
命运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没想到的是,这个玩笑赓续了一个甲子,直至耄耋之年,他才循着当年出逃的路线,又回来了。
笔记本上此刻有了一串汉字:甲午巷、辛亥街、中山路……他玩味于这些街道的名字,认定它们和记忆有着血浓于水的关联。可他越看,越觉得陌生。这是他对旧城的疑问,也是对自己的疑问。1992年版的县志上增添的几个地名,就像新打的补丁,怎么看都很刺眼。不过他也知道,前两本县志诞生于和现在迥异的时代,更改是必然,也是必须,但这种更改来得如此蛮横、粗糙,就像有人拿着粉刷潦草地刷一遍。当初修纂旧县志的人若是见到这一幕,一定会非常震惊吧,尽管他们的震惊与盛先生的震惊,相隔了一百多年。
二
听过盛先生故事的人为数不多,我只是其中一个。
我和盛先生从未谋面,促使我写这个故事的人,是陈宝琪,关于盛先生故事的零星片段,也是她告诉我的。陈宝琪说,盛先生是个谜一样的人,她在旅途中遇过很多人,但从未有一个像盛先生这样令人难忘。她问,你能想象吗?一个人在外面漂了六十年,从没回过一天家乡。我点点头。陈宝琪说,那次纽约飞北京,我和他隔座,他在飞机上翻一本厚厚的图册,看得非常认真,我很好奇,就和他聊起来了。
他穿一套夏装,很正式,看来为了这趟回乡,是做足了准备的。
我问他看什么书,他举起那本厚厚的图册,说是一本县志。我一看,很惊讶说,这是我老家!老先生将信将疑,说,这么说你是我老乡?当我再次确信无疑地告诉他时,他的脸上掠过欣喜,很快,我们讲起家乡话来。他说他姓盛,叫他盛先生就好。他万万没想到会在飞机上遇到乡音和他一样的人——这种机率,比中彩票还小。不过他对家乡的好奇远远超过了对我的好奇,好像我是只望远镜,透过我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他问我老家变化大不大,县城现在是怎样的;我说,县是以前的叫法了,现在是区呢。他就“哦哦哦”地点头,看起来好像很失落。我坐在他身边,看到他的侧脸,他鬓角斑白,说话的语气像在背稿,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偶尔还夹几个英文单词。我们断断续续聊了很久,说着别人听不懂的“鸟语”。那种感觉,好像这些话也搭着飞机在飞。
没错,还一路从纽约飞了回来。
陈宝琪不置可否地笑一笑。
我问盛先生回国的原因。
陈宝琪讲,盛先生说人老了就会这样,像只钟摆,摆过去了又会荡回来。
我问陈宝琪,他一个人回来?
陈宝琪说,当时我也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自己出门,家人不担心吗?他摘下老花镜,像在咀嚼什么,片刻后,他嚅嚅地说,我没有家人。对于我不小心刺探到的隐情,他似乎不大乐意。我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禁忌,很尴尬,不敢再问下去。所以也就不知道他是一直独身,还是结过婚又离了。
這是陈宝琪结束漫长的旅行后,我们再一次见面;上一次见,是她去敦煌之前。她不像我,总是窝在同一片狭仄的土地上,半步没踏出门;她闲不下来,你永远猜不出她下一步要去哪里,毕业后她没有工作——她家境很好,似乎也用不着工作——兴起了就拉只行李箱出门,到处去疯玩,近的去过东南亚,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远的就是欧洲了。这次去美国,她持的是个人旅游签证,从纽约曼哈顿,到佛罗里达,再到加州,着实把半个美国走了一遍。每次她出门,撂下一句“我出去几天”就人间蒸发了:不回短信,也不打电话,也不经常上网,偶尔更新微博,也是自拍照,加一个定位。她就像一只飞得很高很远的风筝,我怕的是哪天线断了,这只风筝就再也飞不回来了。
像往常一样,她喜欢和我讲旅途中的见闻,但这次她兴致勃勃讲盛先生的故事时,我打断了她。我问,你就不能好好待着吗,为什么总要走?她沉默一阵,抬起眼说,没办法啊,人各有命,也许我生来就该这样。她的话中,有为自己开脱和辩解的成分。至于我,我是不信这些宿命论的说法的,包括盛先生一把年纪归乡这事,我也持怀疑态度。一个人离乡很久,久到已经断了关联,却还要拼了命像只归巢倦鸟一样飞回来,个中缘由一定很复杂,并非一句“人各有命”解释得清。再说了,归乡便归乡,这之后呢?
陈宝琪刻意绕开话题,继续说道,从来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和我谈起家乡,虽然他讲的我不是很理解。以前旧社会的人背井离乡是件天大的事,有时还关乎生死;现在就不同了,人很容易就离开家乡,又很容易就回来。盛先生讲他十几岁时坐邮轮逃难到国外,母亲死了,父亲又下落不明。我听着,就像是在看电影,很传奇的样子。他说,离乡的感觉像树断了根,他这次回来,就是想回来看看树根底下的土是否还在。
因为问题被冷落,我有些埋怨,但细想之下,还是决定顺着陈宝琪的话头问下去。
你说他是第一次回来,既然迟早要回,为什么会拖到现在?
陈宝琪说,八十年代末他准备回来的,但那阵子国内形势不太好,计划就搁浅了,没想到这一拖就拖到了现在,哎,有时人很奇怪的,一个念头起了,就算隔了千山万水也要回来。
这个隔了千山万水也要回来的盛先生,真真与众不同。就我所知的大部分“华侨”,都是那类心系故乡,热心参与公共事业的人,个个出手阔绰,福荫子孙亲戚,名字也经常出现在乡村建设、兴办教育的芳名录上。只有这个盛先生不一样(也许他谈不上“华侨”),暌别故土六十载,就像突然冒出来的一棵老树,就这么横着将枝干伸过来,投射一片惨淡的阴影。
陈宝琪的话让我感慨,人不能没根没底地活着啊。
陈宝琪摇摇头说,也不对,有些人注定一辈子飘来荡去,是没根的。
我想说,比如你?但终究没开口。我知道她这句话另有所指,是在形容自己。也许在盛先生这位老番客身上,她无意间照见了什么。我想,这就是她对盛先生好奇的原因。这位盛先生和老家之间,就像离了土的树根,到底隔的不是岁月,而是人心,至于是什么人心,大概除了他自己,就没人知道了。
我说,盛先生为什么后来还找你?
这个问题似乎戳中了什么,陈宝琪的表情有了变化,她咬咬嘴唇,好像即将说出的是个天大的秘密,过了片刻,她压低声音说,盛先生找我是为了……帮他烧梦。“烧梦”两个字从她嘴里冒出来,像一道诡谲的符咒。说完,陈宝琪直勾勾地看着我。她一定没想到吧,这个词勾起了我莫大的兴趣。我追问道,什么叫烧梦?
三
那天盛先生用的是公用电话——他没有手机,也不用电脑——至于他怎么找到陈宝琪的,陈宝琪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机场分别之后,盛先生问旅行社要到了她的号码。
陈宝琪怎么也想不到,盛先生会将她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
那天天热,盛先生换了件短袖汗衫,棉麻布的,穿在身上松松垮垮。他搭三轮车穿行于烈日底下。踩三轮车的师傅背部湿了,他和盛先生聊起来,问他,探亲啊?盛先生想了一下,回答,是啊,返来看看。师傅又问,现在变化大着哩,以前城里没这么热闹的。盛先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师傅聊着,日头太毒了,好几次他都失神忘了接话。
到了红绿灯路口,盛先生焦急地四下张望,很快,他望见身着短袖和牛仔裤的陈宝琪站在不远处。他让师傅靠路边停,下了车,给钱,朝陈宝琪招招手。陈宝琪撑一把伞,走过来扶他。盛先生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能行。
陈宝琪带着盛先生,进了一家糖水店。
天气太热了,盛先生从住的宾馆出来,就如掉入一只巨大的火炉。陈宝琪这才发现,对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说,热天如此难捱。她递了张纸巾给盛先生擦汗,问他想吃点什么。盛先生说,都可以。陈宝琪于是指着菜单,介绍道,这个是龟苓膏,那个是双皮奶,还有这个,是草粿。也许“草粿”一词的发音吸引了盛先生,他聚精会神盯着菜单上那碗黑色凝状物,食指扣一扣说,就这个吧。陈宝琪自己要了一份烧仙草。盛先生好奇,烧仙草?陈宝琪解释道,就是台湾的一种甜品,等下给你尝尝。盛先生若有所思地点头,两人之间陷入沉默,陈宝琪看到他举目四望,表情始终不太自然,仿佛这间糖水店,是一处异域。
陈宝琪心里有隔阂,尤其在接到盛先生电话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它替代了先前旅途中的默契。不过几天罢了,陈宝琪惊诧于这种关系的微妙变化。她觉得眼前这位老先生身上一定藏了什么秘密,又捂着不说,令人如坠云雾。盛先生倒是不紧不慢,他这个久未归家的好奇番客,看着店里来往的人,像要把鲜活的一切刻进眼底。陈宝琪想起先前他说过六十年没回来,还有他询问家乡情况时透露出来的热情。这一来,陌生感便从他的眉梢、呼吸和眼神中淌了出来。
盛先生问了陈宝琪的名字。摘掉老花镜之后,他的双眼更浑浊了。陈宝琪这次看得明朗,他的眉角是微翘的,额头上方花白一片,老人斑墨点一样,缀洒在颧骨和腮帮之间,眼袋像干枯的皱巴巴的蝉蛹。他比印象中要老许多,皮肤像风干的蜡纸,人不瘦,但很虚弱,好像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陈宝琪怔怔地看,恍惚间想起自己那已不在人世的祖父。这种感觉十分奇怪,一个活着的人,令她想起死去的人。祖父如果还健在,也是盛先生这个年纪,不过相比起来,祖父就幸运多了,他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一生。
她望着眼前的老人,想到他孤苦无依的样子,心底那颗皱巴巴的核桃,紧缩了一下。
盛先生从公文包掏出一叠旧照,搁到桌面上。陈宝琪从未见过这类照片,上面都是旧县城的物景风貌。放最上面的,是一座塔狀建筑物的照片,塔状建筑物孤立在一片荒草地上,远景似乎是颓垣断壁,因为不够清晰,陈宝琪只能勉强判断出大致的轮廓。盛先生说,这个你没见过吧?陈宝琪摇头。盛先生手指落在照片右下角,陈宝琪看到,上面写着“八角楼”,她一下子恍悟了:原来这就是老辈人说的“八角楼”呀!县城真的有过这样一栋建筑!陈宝琪吃了一惊。接着,盛先生如数家珍般,把这些存在或消失的建筑与遗迹,一一指认给陈宝琪看。盛先生就像一个考古学家,陈宝琪也不知,这种热情和细致是从哪里来的,说他是老番客,却也一点不像。几十张照片,有的是从书上扫描的,还有的残破不堪,不知从什么报刊上裁下来的,它们走马灯似的从眼前晃过,勾勒出一幅逝去年代的图景。
陈宝琪长这么大,从未想过她生活的地方和历史这么接近,或者说,她从未意识到,其实她就活在历史中。以前她多厌倦这里啊,觉得它落后、愚昧,远远没有别的地方那么有意思,这里的人也是,拘泥于小地方的自恋,还看不起外地人。这些年她四处旅行,走得越远,对这座小城越是生疏,也从未好好想过,老家就真的一无是处吗?她以前认为,人要四处走,看不同的风景,见不同的人,这样就会活得明朗一些,快活一些。然而就在这一刻,在盛先生的讲述中,某种她以前所不理解东西,箭矢一般越过时间,一下子击中了她。
盛先生讲,我在国外当过一段时间教员,这些照片大多从图书馆影印的,见到老相片,就像看到家乡,看得越多,就越想回来,可是又很怕,这种感觉你能理解吗?我好像得了一种怪病,不回来的话,就治不好了。
说着,盛先生抽出压在最底下的照片。这一张很新,像刚洗出来的。盛先生幽幽地讲,这是我以前的家。陈宝琪凑近去看,这栋民国建筑的外墙剥落了,但依稀可见昔日的光彩。整座大宅乱糟糟的,悬挂的衣物、横亘的破旧家具、还有坐在门口洗衣的妇人,一切都显示着破败。盛先生说,这里也不是我的家了,现在住着几户外省人。我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看,拍了照片。我向附近老人打听父亲的下落,问了好几个,终于有人告诉我,土改时,我父亲不愿把名下的土地充公,被批斗了,他后来被人发现时,已经上吊死了。我这几天睡不好,一躺下就做噩梦,梦见我父亲,哎,也许我,我不该回来……
盛先生说起这段过往,眼底潮濕。谁能想到,他竟然隔了几十年才得知父亲死讯!这几天他四处打听父亲死后的下落,没有人知道,那时地主死了就死了,没人在乎他的身后事。
陈宝琪想安慰他,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了。
盛先生继续讲,我在城区到处走,找了你帮我指路的几个地方,路上没一个我认识的,车来人往,我走过去,又走回来,一天天就过去了。很多熟悉的地方已经没了,骑楼倒了,宫庙也找不到,小时经常跑来跑去的街巷,现在都铺了水泥。这个地方太陌生了,就像打碎了一只碗,拼不回来了……我晚上躺下去,还梦见以前的老县城,人也好,物也好,都在,像放电影。我母亲每周都上教堂,我父亲喝醉酒骂人的声音也还在,他们都还年轻,但是往往梦做到一半,天就落雨了,非常大,然后什么都冲走了,连我自己也被冲走了……
陈宝琪听他讲这些,一点点吃力地补缀他梦里破碎的画面。窗外日头很猛,盛先生的声音,好像翻刻的录音带,有一种摩挲人心的力量。相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讲这么多话。他也许被这个梦折磨太久了,不得不说出来。现在,更因触及到真切的土地和人事,那些原本可以隐藏起来的渴求乃至恐惧,就全都像爆米花,一粒粒飞迸出来。
讲到激动处,盛先生的语速快了,嘴唇翕动,眼底尽是浊泪。陈宝琪忽然间无所适从。她没想到,盛先生的悲戚水墨般晕染开来。她被这濡湿的气息团团围住,手里紧紧捏着纸巾,一时慌乱,竟忘了递给他。她其实很想说,这个世上没什么是不变的,人会老,城会老,什么都会老。安心接受改变,才能活得自在一些。然而这些她始终不忍说出口,它们于是化作石灰,堵在她心底烧着,灼得人疼痛。
糖水店的食客,好奇地看这对老少。陈宝琪躲不开别人的注视,只好将目光投射在盛先生身上。盛先生沉浸在讲述中,偶尔抬手抹一抹泪,全然忘了此刻是在哪里。陈宝琪的背脊沾上了一股黏糊糊的悲悼,吃到嘴里的烧仙草,好像有了苦涩的味道。时间停滞了,声音也静止起来。盛先生像一个玩具被人损坏的小孩,很心疼,又很无奈。陈宝琪只好默默地握住他干枯如树枝的手。陈宝琪相信,沉默可以传递温度,带来慰藉。这是她在祖父溘然辞世时学到的。这时,祖父的脸幽幽浮出来,影影绰绰的,和盛先生的脸叠合,有了鲜明的轮廓。
陈宝琪感到一阵难过,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些?她在心底暗暗骂了句该死。
过了很久,盛先生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慢慢地回过神来,默然地抹掉脸上的泪。陈宝琪看到,他的眼窝塌陷了,须发黏腻,像水洗过。陈宝琪怎么会想到呢,这个老番客心底藏的秘密,原来是悲伤。这悲伤水一样淌出来,淹没了陈宝琪。她看到盛先生的嘴唇在发抖。天很热,他的额头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她这时才发觉,盛先生什么都没吃。
他想起了什么,自顾自说,我回国前刚做了心脏手术,我已经老了,不能把这些坏的记忆带走。说这句话时,他的眼里透着绝望,似乎心底有什么东西死去了,像一个死胎,排不出去,一直在悲鸣。
四
世事变迁,县志中的故乡已不是故乡,盛先生记忆中的故乡沉下去了,化为灰烬。当盛先生要求陈宝琪陪他去找神婆时,一阵阴寒爬上陈宝琪的脊柱。她向来是不信这些的,小时候患过一次很严重的湿疹,浑身痛痒,看过医生,几天不见好。祖母看不下去,坚持要去问神,求一道符回来烧水喝。陈宝琪记得,因为这事,母亲和祖母争得面红耳赤。她记不起那时湿疹治好了没有,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味蕾上符水的记忆却不肯退去,总时不时地沁出来,撩动她。那是她第一次对这里的一切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就像一种慢性病,时长日久,终于显出并发症来。
现在这个老先生,竟然要她做向导去找神婆!
盛先生再一次重复道,我想把这些东西统统忘掉。这句话让陈宝琪不知如何是好,她摸不透,这个老人家一直渴念回来,现在却又……
盛先生说,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我没多少时日可活了,这样折磨,太痛苦了,还不如忘了好……
可是,怎么忘?忘了就会好吗?这是陈宝琪的疑问。
盛先生目光浑浊依旧,微张的嘴唇预示了痛苦的残留,他好像被抛在陷阱中逃不了的猎物。
陈宝琪想说一些话来安抚他,三番四次开不了口。沉默横亘在中间,不知怎的,她眼前闪过网上看过的一则消息,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便将它复述出来——
前几天新闻里讲,人的记忆就跟电脑内存一样,是可以删除的。荷兰有个科研团队一直在研究人的大脑,实验结果显示,记忆是可以从大脑的“储藏室”取出来的,然后再通过神经回路再次浮现。从大脑提取的记忆可以人为“干涉”。只要把握好正确的时机,对大脑进行轻微的电击,就能将特定的记忆破坏,这样,人就能忘记痛苦的过去了。
陈宝琪故意讲得很慢,好像这样,就能扭转盛先生的想法了,谁知盛先生听完,目光暗了下去。他默然垂首,视线不知落在什么地方。顷刻后,他抬起头来,目光确凿无疑地表明:比起冷冰冰的科学,他更信乡间巫术。
盛先生说,以前乡下的神婆懂一种特别的疗法,叫“烧梦”,我做孥仔那阵,厝边头尾谁患了重病,或者撞了邪,凡是遇到不好的事,都会请神问卦。最灵验的一招,就是这个“烧梦”了,有点像招魂,不过和招魂不一样,这是把人的晦气往外赶,烧掉,就像清明扫墓烧纸钱一样……
陈宝琪静静地听,心揪得紧紧的,她惊讶于盛先生的迷信。她糊涂了,盛先生千里迢迢回来,最后只能求助这种愚昧的方式?再说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记忆又不是野草蓬蒿,说除去就能除去的?来年春风乍起,野草蓬蒿,该疯长的还是一样疯长。
我以为回来就会好的,回来就没事了,没想到更严重了……我失眠好几天了,我的心脏不好,随时都会死,我不能把这些坏的记忆带走啊!
盛先生深陷于绝望中,像掉入泥淖中死命挣扎的马匹。
陈宝琪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她可以就此脱身,告诉盛先生,没用的,不能迷信。好几次她都想说,她不认识什么神婆,也不知道什么“烧梦”。可是话到喉头,硬生生咽了下去了。她知道自己拒绝不了,不能坐视不理,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老人受此折磨。最后,几乎是在破釜沉舟,陈宝琪说,我带你去,带你去烧掉这个梦。
她知道,一旦做了救命稻草,是不能輕易折断的;同时她也清楚,无法保证圆这桩心愿。我非常理解这种矛盾的心情。陈宝琪大概也没想到,她会做这种“荒唐”事。在后来的讲述中,陈宝琪透露了一个秘密,她说,我一头雾水,只好问我阿嫲,骗阿嫲说朋友的妈妈想去“巡家门”。“巡家门”,潮汕方言,指向算命师求告一年运程,往往是针对一户人家所作的算卦和占卜。我阿嫲就讲,水磨那边的阿娘算命准,找她一定没错。
在乡下,算命阿娘的名头比镇长还响,别人可能不知道现任领导是谁,但若问起算命阿娘,绝对无人不晓。
水磨离县城几十分钟的车程,下车一打听,很快就找到算命阿娘的家。算命阿娘因擅长算卦占卜替人消灾而远近闻名。她住的老宅,水磨石地板,门口摆了盆栽,普通人家的装扮,但内里另有乾坤。自从陈宝琪应承下帮他之后,盛先生安静了不少。他讲了半天话,人也累了。去的路上,他靠在车座上,呼呼睡着了。陈宝琪望着这个老人,很心疼,他睡得那么熟,脸上是安详的,但这安详中,却带着盲信与麻木。陈宝琪忽然想,如果真的能烧掉这个梦,但愿他可以安安心心的,不再苦痛。
踏入老宅那一刻,盛先生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他站在老宅前,举目凝视,像一个即将迈入寺庙的香客,但这里既不是寺庙,也没有和尚,这里有的是一个算命阿娘。他脸上怯怯的,仿佛即将踏入的,是一处诡秘的所在。
坐在老宅里的人全都静静地候着,没人敢高声说话,一切就像古老的仪式,所有人遵循仪式的规矩,只怕惊扰神明,最后落得个受罚的下场。隔开一道竹帘,陈宝琪看到算命阿娘的神坛,还有坐在神坛下方的“顾客”。据说以前一条“时日”才二三十,现在涨价了,要六七十;一家若是几口人,算一次就要几百块。陈宝琪隐约听见一老妇人说话的声音,丹田气十足,一字一句,有板有眼。盛先生看来心情平复了不少,他像个耐心候诊的患者,安静地坐在塑料椅上。陈宝琪被这安静感染了,她看着屋里的人,看着盛先生,好像明白了什么,她自己也是凡人,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人在无望时,唯有求告于看不见的力量。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盛先生。陈宝琪扶他走进去。掀开竹帘,迎面一股香灰呛得陈宝琪差些打喷嚏。算命阿娘的老宅,是那种旧式洋房,地板是水磨石的,大厅和天井相连,有两间客房,其中一间,就是算命阿娘设的神坛。陈宝琪打了个寒噤,目光有意无意地躲着算命阿娘。
光线有些暗。落座之后,陈宝琪很紧张,好像问神的不是盛先生,而是她。她惊讶于盖在神坛上的繁复织锦,燃烧的蜡烛和香枝,和这间刷得粉白的房间格格不入。神坛上的香炉堆满灰,此外,还有纸和笔,一把闪着寒光的刀(陈宝琪不知为什么会有刀)。其中最惹眼的,就是供在神龛上的菩萨像了。传说算命阿娘是被观音娘娘附身的,乡下人简称她“阿娘”。落神时,她不是一个普通妇人,而是神明化身,从她口中说出的,字句如金,攸关性命。陈宝琪心头乱糟糟的,她想知道,菩萨真的无所不知吗?她会戳穿我这个无神论者吗?想到这些,她紧紧握住盛先生的手臂。她后来说,算命阿娘怎么能在两种身份间自由变换呢。开坛前,她是一个微胖的、眉开眼笑的老妇人;观音附体后,就是知祸福卜凶吉的神仙。
盛先生开口,阿娘,我有事相求。
话音刚落,算命阿娘带着命令的口吻,提起笔说,念你的时辰八字。
盛先生解释道,阿娘,我不算命,我是来“烧梦”的。
算命阿娘的手僵住了,搁在半空,死鱼一般的眼白翻出来,吓得陈宝琪汗毛倒立,有种被人戳穿了什么的惊恐。她撞见愠怒凝聚在算命阿娘眉间——就要爆发了。
陈宝琪坐立不安,她只有一个想法,想拉着盛先生逃离这个地方。
盛先生重复道,阿娘,我不算命,我想“烧梦”,烧我最近做的梦。
盛先生僵持着,好似在挑衅算命阿娘的权威。陈宝琪眼看坐在对面的老妇人即将动怒,她壮起胆子,哆哆嗦嗦讲,阿娘,对不住,我……
算命阿娘忽然搁下笔,莫名大笑起来。她的笑尖利而凄惶,搅得房间里空气荡起微澜。陈宝琪注意到,她的表情一霎间换了,忽然低眉顺目起来,声音也不同了。观音附身了。陈宝琪头皮一阵发麻,仿佛这方神明与凡人共处的空间,真的有一个超越了实体的存在悬于其上。而所有的症结,都来自这个被噩梦缠身的老人。
这一次,观音娘娘的声音讲,梦可烧,烧了就回不来了,可要想清楚哇。
五
就像对症下药,“烧梦”前,要明确两样东西:梦的细节,以及烧梦者想烧去的部分。算命阿娘推过来一张纸。盛先生在纸上写下什么,陈宝琪看不清。从算命阿娘的反应来看,她似乎并没有帮人烧过梦,然而眼下的阵势,又无疑指向某种神秘途径。
空气中有股粘稠气息,不知不觉,陈宝琪已经被吸附进去了,就像一粒灰尘。眼前的算命阿娘,神情肃穆,沉默中透出凛然。陈宝琪看着盛先生,他花白的头发,在光线中浮动。她以为盛先生还要讲那个旧梦,谁知道这一次,他讲的是另一个,一个全然陌生的梦。
以下便是陈宝琪转述的盛先生的梦——
我梦见自己搭乘的邮轮(应该是我十几岁离乡时搭的那艘)遇险翻船了。我醒来时躺在海滩上,身后是海。日头很毒,我爬起来,朝着内陆走去。我看到的人皮肤都很黑,小孩子不穿衣服四处跑。我无意间闯进一条大街。大街人来车往,两边很多店铺。我继续走,越走越困惑,两边都是骑楼,骑楼底下,有米铺,有衣帽店,有卖吃的,还有棺材铺……男女老少,皮肤黑,牙齿白,好像混种人。大街灰扑扑,高音喇叭在放音乐,听不清放的是什么,好像是地方剧。拐进一条小巷,我见到井边一个妇人,妇人背着孩子,蹲在井边洗衣服。我走过去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警惕地看我,说,你连这里都不知道?我又问,那条街叫什么?妇人皱眉,说,你连巴毛街都不知道?我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第一次来这里。妇人的口音,是潮汕话和其他不知什么方言的混体。我听得懂,但是音调不同,有些词必须努力分辨才能听清。那条“巴毛街”让人捉摸不透。后来我才明白,“巴毛”就是过山鲫,是那种可以在陆地上用身体爬行和翻跳的小型亚洲淡水鱼。想通这点,我才恍悟,巴毛以顽强生命力著称,离了水还能存活,是当地人的图腾,是他们信仰和崇拜的神。这个不知叫什么的小城,由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组成,听口音,有的是福建人,有的是潮汕人。他们和我一样,是在海难中存活下来的。他们与当地人结合、繁衍,在这里扎了根。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再次走进大街,一群持枪的人将我围住。他们把我打晕,吊在城墙门口。等我醒来,我才意识到,是背小孩的妇人告的密。他们把我当成入侵的间谍处死。我听见底下民众高喊,他们抛弃了我,还派人来侦查,烧死他!烧死他!声浪一阵盖过一阵。我就要死了,汽油浇到头顶时,我看见不远处有坟堆,所有墓碑都朝着来时的方向。
盛先生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穿来,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恐,充斥于光线晦暗的房间。
他怅然地讲,如果那时候跳海死了,该多好啊——
陈宝琪被这个异乎寻常的梦吓到了,她不知道,这个梦盛先生真的做过,抑或只是某种幽暗心境的投射?她想不通,也无法想通,也许梦和盛先生的经历一样,带着传奇。
算命阿娘听完,眉头皱起。她和盛先生之间,隔了一重看不见的幕帐。片刻后,她拎起神坛上的那把刀,刀离开桌面时扑起一阵香灰,算命阿娘表情狰狞得狠,空气中似乎有什么魑魅魍魉横冲过来,撞在她身上、脸上。只见她右手握住刀柄,左手张开,遮在唇边。陈宝琪隐隐预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眼睛闭了又张开。这时,她看到刀搁在算命阿娘伸出的舌头上。刀尖碰上一截粉红色的舌头,几乎就在同时,刺啦一声,舌头割裂一道口。算命阿娘眼疾手快,抓起神坛上的一叠黄纸,贴住舌头,再拉下来,手沾血,在符纸上凌乱涂抹着什么。盛先生的身子震了一下,像是灵魂出了窍。陈宝琪几乎要吓晕过去,她靠在盛先生身上,偏过头,不敢看这血腥的一幕。喉头泛起酸气,她捂住嘴,险些吐出来。
一切进行得太快了,超乎陈宝琪的想象。也不知过了多久,她从惊惧中猛睁开眼。盛先生像是被催眠了,表情木然,身体微微发颤,飘浮在另一个时空。她不敢伸手碰他,生怕一不小心,就将盛先生的魂魄撞得粉碎。算命阿娘做完这套繁复的仪式,脸上恢复了平静表情,她安然无恙端坐在太师椅上,嘴唇既没有流血,也不见任何痛苦的迹象。陳宝琪看到她闭上眼,口中念念有词,她手里的符纸烧起来了,在空中舞动,符纸上的血字,被火舌吞噬了,陈宝琪嗅到一股气味,混杂了血腥和香灰。一个又一个的赤红的血字于火光中腾起,跳跃,纷乱如梦。顷刻间,纸符化作一堆薄薄的灰烬掉落下来。火光照亮房间,也照亮神龛上慈眉善目的观音像。
陈宝琪知道,这个梦烧终于完了,盛先生也该醒了。
陈宝琪讲述时,把我也拉进了那个光线晦暗的房间。她说,不知为什么,烧梦结束之后,她心底有些东西复苏了,就像过了一冬冒出嫩芽的树,窸窸窣窣,一直往上长。她没讲盛先生最后去了什么地方,我也没有问她。
因为我知道,就在故事结束时,盛先生正提着行囊,踟蹰在另一条归乡路上。
林培源,1987年生,广东汕头澄海人,现为暨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2007、2008年,连获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12年获首届广东省高校校园作家杯中篇小说一等奖,已出版《薄暮》《锦葵》《欢喜城》《南方旅店》等四部长篇小说,在《青年文学》《西湖》《萌芽》《作品》《最小说》《广州文艺》《文艺风赏》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