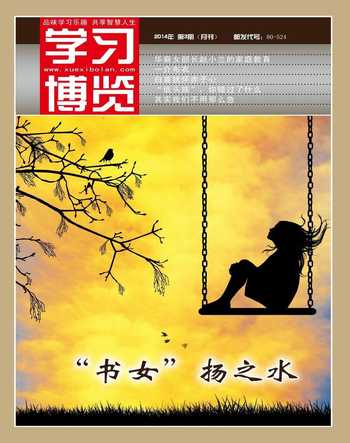白首犹怀赤子心
2014-04-29元年春
元年春
上世纪50年代初,邵燕祥发表诗集《歌唱北京城》和《到远方去》,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其中触及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很快受到批斗,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1979年至今,邵燕祥写了大量“回归常识”的诗和杂文,“用犀利之笔,还原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还屡屡为过往公开忏悔。他回顾“文革”说:“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2007年,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他写道:“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個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章诒和认为,“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
1980年,在“江青四人帮两案”的审理中,由律师张思之带领的辩护小组,为姚文元、李作鹏、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件罪行。张思之为异端辩护的职业律师生涯就此开始。上世纪90年代初,他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1995年,他代理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2003年,他以76岁高龄代理“郑恩宠”案;2004年,他代理“黎元江”案……这些著名的“必输的官司”,让张思之赢得“从来没有赢过一场”的大名声。虽然“屡战屡败”,他打包票说:“如果你能从我败诉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一句话是我讲错了,我都认输。”他认为:“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2000年,他出版《我的辩词与梦想》,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在中山大学,一些学生听了袁伟时的历史课,经常跑过去问他:“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作为历史学家,袁伟时主张“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2006年,《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周刊刊登袁伟时的长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引起主流媒体哗然,《冰点》被迫停刊整顿,袁伟时被称作“叛徒”。其实,过去十多年,袁伟时挨的骂并不少。不少学界中人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更有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灵魂的拷问》等都引起强烈反弹。面对谩骂,他“一笑置之”,相信“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他对未来保持乐观,因为“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
在经济学界,张五常是公认的产权理论大师,科斯、弗里德曼、阿尔钦等学界泰斗说他是“百年来只此一人”。张五常向来狂傲不羁,甚至看不起诺贝尔奖,公开宣称:“我的文章中至少有六七篇100年后还有人读,哪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样说?”他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明世事”,因为他自己逃过荒,做过生意,卖过古董,搞过艺术展,打过官司,当过分析员,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82年,张五常离开美国回到香港,出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系系主任。他要带领学生和同事做“时代弄潮儿”,因为“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之后的近30年里,他充分利用了他所处的难得的时间和地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自己“百无禁忌,不滞于物,自我陶醉,于传统和世俗有所不合”。因不满于“经济学气功师”、“西方经济学低劣搬运工人”的横行霸道,他经常“危言耸听、以惊麻木”。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2006年11月,83岁的邹承鲁院士逝世。中科院在讣告中罕见地评价他为“刚直不阿的斗士”。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科学家为核酸营养品做商业广告、企业虚夸“5年克隆全部人体器官”、院士涉嫌论文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邹承鲁一次次严厉批判。2003年,在中国科协年会上,他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他还认为,科学上的评价要讲究可靠而不是快速。他喜欢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
“中国不缺我一个历史教授,但是缺少做环保的人。”梁从诫说。1993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他在环保上身体力行:名片用废纸复印而成;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坚持用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为宣传环保,他四处演讲。有一次,全场只有5名听众,他笑着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的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在一次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斥责北京市某领导说:“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在川西某县城,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元。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点燃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这一幕深深印在很多人心中。作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自嘲说,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010年10月,梁从诫逝世。上千人参加告别仪式,地上几乎未见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