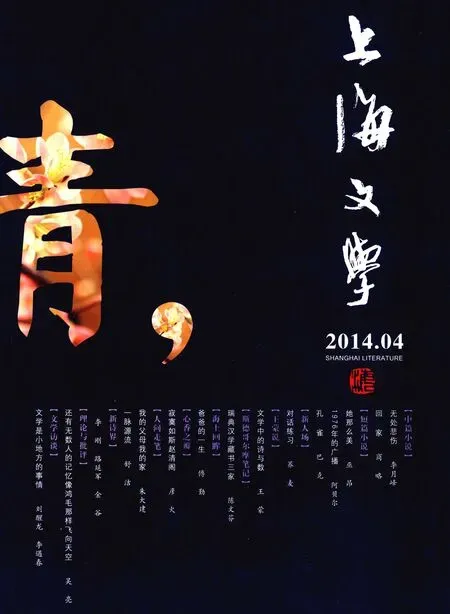文学中的诗与数
2014-04-29王蒙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前天,刘炯朗教授讲“数里有诗,诗里有数”,对这个问题我特别感兴趣。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报道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兴宅的一个观点,“最好的诗就是数学”。当时很多人质疑,认为这是故作玄虚。可是,他的这句话却把我迷住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有的特别烦数学,比如汪曾祺,别人问他,你为什么写小说,他回答因为我从小数学就不及格。我呢,从小就特别热爱数学,沉湎于数学,但是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临出门前,我女儿对我特别不放心,她说你出去讲什么都行,千万别讲数学,因为你那个数学是初中二年级水平以下的数学。但是由于受到了刘教授的感染,哪怕讲完以后被暗杀,我也非讲这个数学不可!
我要讲的是我心目中的文学与数学。虽然今天早上我查了一些数学表述和“词儿”,但来不及了。我的一些表述可能不那么准确,尽管如此,我想提几个思考题,大家共同思考。第一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华文化中“数”的意义。在中国,“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十百千万亿,不仅仅是数学的概念,还是人文的概念,是哲学的概念,是政治的概念。为什么是政治的概念?一个朝代不行了,我们常说它“气数已尽”。“气”说的是一个朝代的政治生命力,“数”说的是时序,比如一个朝代历经五百六十八年,五百六十八就是它的“数”。不仅汉族文化讲“数”,新疆文化也讲。伊斯兰教语言里,有一个词叫“天饷”,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老天爷都会给一个“饷”,也就是汉语里定数的意思。譬如你的“天饷”是四十四年,四十四年后你就拜拜啦。他的“天饷”呢,一百零六年,譬如巴金先生。所以这个“数”的意义非常大。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权力制衡、多元制衡。做到没做到另说,起码它的理论是这样。中国没有多元制衡的传统,但中国有没有平衡呢?中国的平衡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中国人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多元制衡,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很难做到。但是“不为已甚”,留有余地,掌握分寸,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其实很可怕,培养我竟要用一百年的时间,当然等不到你培养完,培养成果就没了。可是为什么还说“百年树人”呢?因为只用三十年的时间来考察一个人是不够的,他河东的时候是这样,一到河西的时候又突然变成那样。大家不要笑,这种事情很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要用三十二年才能考察清楚一个人。当然,不必等六十年了,六十年之后他又河东了。
中国的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八千,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数字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是人生观。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中国人很崇拜一,天下定于一。所以原来的中宣部部长叫陆定一,中国还有一个VIP叫符定一。二,二的意思就更重要。毛泽东喜欢二,叫做一分为二。但是二带有反叛性,说一个人有二心。如果皇帝说一个大臣有二心,那这个大臣的脑袋恐怕要保不住了。现在人们说二,还包含“stupid”的特殊意思,但哲学家庞朴主张一分为三,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物不仅会从统一的一面变成互相对立的两面,而且由于对立两面的斗争,会产生第三面新的东西。四,四和方正有关,大方无隅。我不一个个说。六,中国人喜欢说六,六六大顺,这和几何学有关系,一个圆里面可以内接一个正六边形,连上它们的对角线后,又变成正三角形。七和巧有关系。八和什么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人们常说“八面玲珑”。九,九九归一。九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数字,是不得了的。有一次我在北京看到一辆车,车牌号上都是八。人家告诉我这辆车的车主是一位退休的领导人,于是我就手痒,口痒,老想给他献一个策论。建议他把车牌号换成九。你说你都已经下来十年了,还八个什么劲呀,你就九就完了。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几率,就是命运。我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在北戴河看到一个小贩。这个小贩在路边通过和路人做游戏的方法赚钱。怎么做游戏呢,四种颜色的球,比如红黄黑白,每种球五个,共二十个。在做游戏前,小贩会让你仔细把这二十个球看一遍,然后把它们放到一个很清洁的布口袋里。你闭上眼睛,从里面摸出十个球来。如果你摸出来的颜色组合是五五〇〇,比如黑五白五红零黄零,或者黄五黑五白零红零等等之类,小贩就奖励你一架莱卡相机。如果你摸出球的颜色组合是三三四〇,那奖品就降一个等级,譬如一盒万宝路香烟。如果摸出球的颜色组合是三三三一,那就奖励一个更小的礼物,譬如只是一个小小的书签。但是,如果你摸出球的颜色组合是三三二二,那就要罚你给小贩一块钱,如果是一二三四呢,罚你五毛钱。很多人乍一看游戏规则,得奖的情况有三种,罚钱的只有两种,很快就被吸引过去了。纷纷走上前去闭上眼睛抓球,抓一次,三三二二,交一块钱;抓一次,一二三四,交五毛钱。就这样抓了半天,最后终于有一个人得奖了,奖品才是一个小小的书签。在座的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回去拿麻将牌做实验,条子万字筒子,还有风,一共四样,湊齐二十张后可以摸摸看,很快你就会发现三三二二和一二三四出现的几率比较多,五五〇〇最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数学家梁昌洪先生听完我的故事后,首先进行理论推算,然后用电脑做了一百万次随机模拟,最后还组织一百四十名学生进行了六千一百八十次现场抓球实验。这三个方法都试过之后,得出的结论一致。虽然我个人总感觉三三二二比一二三四出现的几率要多,但是梁先生告诉我,从数学计算的结果来看,三三二二和一二三四出现的几率是一样的,都是百分之三十二,两个加起来大概是三分之二。几率最小的是五五〇〇,大概是十万分之三。起初我感觉五五〇〇出现的几率和飞机出事故的几率差不多,但是民航很紧张,向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说,十万分之三,要真是这么大的几率,那谁还敢坐飞机?实际上,飞机出事故的几率比这个数字要小得多,到底小多少,我也闹不清楚,但愿我们不要碰上这样的事就好。虽然飞机出事故的几率比五五〇〇的几率还要小上一百倍或者一千倍,但它仍然存在,即使这样,也有人碰上,这就叫命运,是根本没法子的事情。那么三三二二和一二三四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第一,命运它并不那么极端,有相当的公正性。三三二二最公正了,因为2.5,2.5,2.5,2.5这种情况不存在。一二三四看上去不公正,但是实际也很公正,因为它排除了两个极端,一个五,一个零。人生虽然不太公正,但它是排斥极端的。另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要求绝对公正是不可能的。假如在这二十个球的基础上,每个颜色增加一个球,抓出三三三三颜色组合几乎不可能,几率大概也非常小。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在主宰着你的命运,这种东西不见得公正,比如当你碰见五五〇〇了,或者比五五〇〇还邪,那恐怕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但如果不是五五〇〇,三三二二和一二三四还是过得去的。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数学就是命运,几率就是命运,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排列组合就是结构。譬如说ABC这三个字母,你可以把它们变成ACB、BAC、BCA、CAB、CBA,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排列方法。其实,在长篇小说和多幕剧里,排列组合是任何做结构的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雷雨》。《雷雨》里主要有八个人物,周朴园,鲁妈,繁漪,四凤,周萍,周冲,鲁贵,大海。《雷雨》它充分利用了排列组合。你看,周朴园是鲁妈原来的情人,是周冲和周萍的爸爸,是煤矿工人鲁大海的老板。鲁妈,是四凤的母亲,也是周萍的母亲,又是周朴园原来的情人,是鲁贵现在的妻子。周萍,是周朴园的儿子,是繁漪的法理上的儿子,又是繁漪的情人,是周冲的哥哥,又是鲁大海的死对头。我不一一地说。我们想一想,这样一个排列组合的结构,多么紧凑,多么整齐,多么吸引人。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排列组合是尤其重要。一般来说,能省一个人物就省一个人物。千万不要作品中冒出一个人物,说完一句话后,就甩手走人消失不见了。假如作品中出现了一个人物,就要考虑他和第二个人物的关系,还要考虑他和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直到第n个人物的关系。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想说,数学悖论就是人生悖论。数学里面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悖论。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说谎人悖论”,形式就非常多。譬如,有个人说,“我说的话全是谎话”。这就充满了悖论,当我说我说的话全是谎话的时候,这个话本身是真话还是谎话?如果这句话本身是谎话,也就说实际上我说的话很多不是谎话。如果我说的话明明都是谎话,那我说的这句话不就是真话了吗?说谎话就是说真话,说真话就是说谎话。还有“堂·吉诃德悖论”。这个名称,我记得过去看书的时候没这么说过,这里姑且引用一下。说有一个村庄很不讲道理,每天早上第一个进城门的人,都要被守城门的士兵抓起来问一句话,如果他说谎话,就把他烧死,如果说真话,就把他淹死。有一天,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卫兵把他抓起来问,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来被烧死的。这个回答又是一个悖论。如果士兵把这个年轻人烧死,那证明他说的不是谎话,是真话,但应该被淹死。如果士兵把年轻人淹死,就又说明他说的是假话,实际上应该被烧死。所以说,真话就是假话,假话就是真话。再比如欧洲还有这样的故事:柏拉图指出,苏格拉底说的全都是谎话。然后,苏格拉底回答说,您说的是正确的。同样的道理,不同的形式,还是前面的问题。另外还有罗素的“理发师悖论”,理发师宣布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他究竟给不给自己理发?这样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的比我还多,道理很简单,当你肯定一切的时候,你肯定不肯定否定呢,当你否定一切的时候,你否定不否定你的否定呢?悖论,与其说是数学的悖論,不如说是人的语言的悖论,人的思维的悖论。悖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它说明人的一切认识都给自己留下了麻烦。再有刘教授前天提到的“距离悖论”。这些悖论都说明人的思维,人的思想,人的主观的判断与世界的运转是有差距的,你永远都不可能判断一切。所以人生有时候很悲哀,你自以为你想得已经天衣无缝了,实际上仍然漏洞百出。
当然了,文学作品中也有直接写这种人生悖论的,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把数学的悖论往人身上写。小说中写美国的战争期间,空军部队有一个规定,如果有人不想继续当空军参加战斗,需要申请退役,并且只有当你得了神经病才能申请退役。但是你只要正常地申请退役就证明你没有神经病,部队也就不准你退役。这样的方法据说被中国广东的一位想要辞退员工的老板学会了。老板是怎么说的呢?老板对员工说,我们现在都是民营企业,别以为我们会养着你,你得自己有创造能力,我们才能继续聘用你。这个工人回答道,我有创造能力,你看我辛苦劳动,给企业赚了这么多钱。老板却说,既然你自己有创造能力,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我的企业,自己出去打拚赚钱就可以,下个月起就不用来上班了。悖论在很多地方都有,不仅仅是逻辑上的,方法上的,而且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1958年,我被补划为右派,也碰到过这样一个悖论。当时我们有一个规矩,你必须承认你反党,才能证明你态度变好。你如果说自己不反党,这本身就是反党,因为党说你反党了你说自己不反党,这说明你现在就在反党。我记得和我一起被划为“右派”的人中,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同志,他老说一句话,“我们认下这壶酒钱吧。”什么意思?就是你认不认,你都得认。可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位协和医院的医生,虽然大家对他进行了很多次批评、教育和帮助,但他迟迟不“醒悟”。有一次我对他说,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反党,党都指出你反党了,是不是?你就承认自己反过一次吧。他说你对我帮助太大了。可是到了第二天,他说,我想了一夜,还是觉得我没反党。当时,就有人急了,骂道,“你混蛋,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你没反党!你没反党你怎么着,你是革命者吗?你是英雄吗?党错了吗?党说你反党了,你说你没反党,难道是党反了党了吗?”生活里面充满悖论的,有时候多学点数学知识会更好。
第五,我想说,无限大,一个“一”,一个“零”,这就是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哲学的最基本的观念。我对老庄特别有兴趣,我认为老子的道就是无限大,无限大就是上帝。一切的根源就是它,它永远不会增加,也永远不会减少。无限大的意思,是一条直线在无穷大的前提下延伸,它就是圆,是永恒。无限大恰恰和“零”是相联系的,因为正无限大等于负无限大,这种特点只有零才具备。还有一个“一”和“零”。“一”就是有,老子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生于有就是“一”。我注意到,现在很多电器的开关上都写一个一字,一个零字,一就是接通了,零就是take off,没有接通。无穷大对人的魅力太大了,我不想细说了,细说容易露馅,就把我数学知识不过硬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现在我假装连无穷大的知识都懂了,其实我懂得非常有限。中国古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无非无,无非非无,无非有,无非非有”,我一直没有查到这几句话的出处,但我觉得特别棒。无非无,无不是绝对的无,无是能够生有的无。有也不是有,有可以变成无。我有时候在想,零才是无穷大。什么叫人千古了,什么叫人永恒了,就是当他去世了,当他的存在变成零的时候,他就进入了无穷大。所以零和无穷大是挨得最近的数字。根据我初级的英语水平,我知道“zero”是零,但是我去观看体育比赛的时候注意到,大家常常不说zero,而是说nothing,比如“one to nothing”就是一比零所以零的观念是人生的观念,是世界的观念,而不是简单的mathematics的概念。这样的人生观念和世界观念贯穿在我们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有人说《红楼梦》里“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是要求小说结束的时候里面的人物要全部死光。高鹗写到最后,小说中还留下几个人,因此有人责备高鹗是千古罪人。我不这么看,宝玉出家了,黛玉死了,史湘云守寡了,迎春死了,妙玉被掳走了,这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很多人不懂得无非无。假如《红楼梦》中一大家子人坐着超音速客机,从法国巴黎飞向美国纽约,突然飞机失事,大家都死得干干净净,实际并不悲哀。还有,我记得看《小兵张嘎》,有一个场景是,小兵张嘎的奶奶被日本人杀了,张嘎一个人在那哭。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很悲哀。但是如果小兵张嘎和他奶奶一块被日本人杀了,反倒就不悲哀了。所以“零”、“一”和“无穷大”的关系,正是所有小说、戏剧最吸引人的地方。
最后我再讲点几何学。几何学和文学的关系更多。我老觉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几何学。“大漠孤烟直”是垂线的关系,两个直角,一条纵的直线,一条横的直线。“长河落日圆”,是切线的关系,落日圆圆地落在一条河上,它和河相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有相似形,常常有对应,常常有投影的关系。譬如说《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和甄宝玉,其实就是相似形。假如,你要多写几个人物,比如宝玉,还有宝玉second,宝玉third,都是相似形的关系。另外,还有投影的关系。老红学家常常喜欢说,袭人是宝钗的影子,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这些人物之间的相似和不相似,某些相似,这和我们几何学上很多概念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归结一下,为什么数学和文学这么亲近,因为它们都是用精神缔造的世界,是用智能缔造的世界,一个人在高度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活动中,会感到一种喜悦,会感到一种升华,会感到给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家园。在数学的活动中,他也同样会体会到这样的感受,這是高度的精神活动的一种享受。不仅如此,数学和文学的很多思维方法是一样的。当你面对一个数学难题,死活解不出来的时候,本来是从右往左走,可以试着从左往右走,很可能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文学也是如此,有时候,你这么写死活写不下去了,但是突然换一个角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数学和文学,都训练人想像的能力,训练人专注的能力,训练人激变的能力,训练人换角度换路线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又喜欢数学又喜欢文学,从数学里能体会到许多文学,从文学里又体会到许多数学,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就说到这,谢谢大家。
互动部分:
学 生:我是一名90后,读书的时候我常常感到现在很少有伟大的作品,当代的作品没有鲁迅那个时代的作品好,顾彬先生曾说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我有些类似的感受,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老师怎么看。
王 蒙:我补充两点。一,“伟大”这两个字在中国富有某些神话的色彩。比如我们会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但一般都不说邓小平是伟大的领袖。而且我们常把它道德化,带有一种精神的弥赛亚的性质。拿文字来说,有一个词master,“大师”。这个词在中国就不得了,第一你要“伟”,要“大”;第二,还要“师”,要“万世师表”。所以看来,是对精神领袖的一种要求。但在英语里,说master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是一个乐队的指挥。有一次,他到一个小商店排队买东西,突然售货员认出他,然后就喊“master,master,过来过来”然后,我的朋友就享受了不用排队的待遇。我想说的第二点,比较重要,我们说这个作家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时,往往会倾向于古典主义的,悲情的,决绝的作家。写喜剧的作家伟大不了,写悲剧的就能伟大。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代性,modernity,modernity实际在消解伟大,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古典主义的时候,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把多少悲情写到了作品里面。可是现在呢,现在人人都可以写,都可以在网上写。在网上订合同,每天要写三千字,或者一天写一千五百个字,这样你才能赚钱,别人才不会忘记你。那么现在文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现在的时代也可能有很好的作家,也可能有很好的意义。但它的意义和雨果的那个时期相比,和巴尔扎克那个时期相比,和鲁迅那个时期相比,会发现他们起码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要死要活,现代人理性多了。市场经济里,会看到人比过去务实得多。你们心目中的伟大作家,不光是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有的外国人问,谁是中国现在的鲁迅?那么我请问谁是法国现在的巴尔扎克和雨果?谁是英国现在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谁是现在的雪莱和拜伦?谁是西班牙现在的塞万提斯?如今的时代已不是经典主义的时代,所以有人预告,文学要灭亡。文学灭亡是胡说八道,但是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心态?昨天有人问我,什么时候,能有人再写出一本《红楼梦》?我告诉他,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再写出一本《红楼梦》!因为文学是不能copy的,英国也不可能再有一个莎士比亚。有的话大家也会讨厌他,我们现在要用一种新的观点来探索今天精神上的果实和成品。
学 生:很多作家创作时会用悖论的技巧,我觉得悖论也是一种美,比如《围城》里的一些悖论,王蒙先生,您怎么看文学中的悖论?
王 蒙:悖论,在逻辑思维里,在数学里,是令人不安的一个命题。但在文学中,恰恰是文学的材料,是文学的源泉,是文学非常喜爱的东西。我们经常在文学的作品里看到感情的悖论,看到三角关系,看到四角关系。很多人都渴望从一而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现在有一首歌,唱到“不需要天长地久,只需要曾经拥有”。这不就是悖论了。尤其是很多电视剧,肥皂剧,一旦用了悖论,它可以弄出很多集,写作者至少可以得到五十万的写作费用。你看,要是连悖论都没有,那就连钱都赚不上。悖论既可以是悲剧,也可能是喜剧。现代人常常把悖论看成是喜剧,把悖论看成是对自己的嘲笑,对人生的调侃。这也牵扯到刚才谈到的伟大作家的问题。现在写伟大爱情的人越来越少了,什么是伟大的爱情,过去“殉情”才是伟大的爱情。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没有死,那他们的爱情没有伟大到哪去?如果故事最后,两个仇敌尽释前嫌,家庭问题都解决了,两人牵着手,白头到老,朱丽叶每天晚上还给罗密欧打一盆洗脚水,还进行一点足底按摩,那能是伟大的爱情吗?伟大的爱情是用死作代价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也是这样的,如果林黛玉嫁给了贾宝玉,还给他生了俩儿子……现在的人越来越聪明,不那么容易去为爱情而死。但是假如一个人要死了,把眼睛一闭,心想我要归于永恒,归于无穷大,我现在既是零又是无穷大,也是一种选择吧。所以这个世界在变,我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现在对现代性质疑的人非常多,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不是让你死,而是让你活的更好的文学作品,也挺好,也挺舒服,起码有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