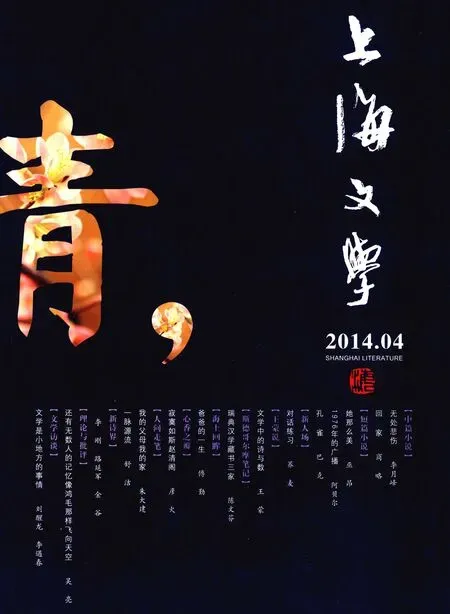1976年的广播
2014-04-29阿贝尔
阿贝尔
1
家里人都不在,小乡一个人躺在厅房的长板凳上听广播。广播里一个女的一直在唱歌,小乡在等她把歌唱完,好听广播员讲话。广播员也是个女的,声音并不好听,但小乡就想听她说:“长桂人民广播站,下面播送通知。通知:今天晚上——在桂香楼院坝里——放映——战斗故事片——《渡江侦察记》。”桂香楼就是公社。《渡江侦察记》小乡已经看过三遍了,但他还想看。“下次不要照手电,如果共军发现,大炮一轰,连老子一块儿下大江喂鱼!”这句台词,小乡和他的伙伴都背得滚瓜烂熟了。上一次放《渡江侦察记》,散场后走岩子头下来,几个人抢着背这一句台词,九胜只顾嘴里没顾得看路,一趴扑下去把门牙都磕脱了。
没有等到那个女的唱完,歌声突然停了,但广播员迟迟不讲话。小乡听见外面下雨了,雨落在竹梢上唰唰响。厅房里的光线也暗了下来,挂在楼口柱头上的广播箱看上去已不再是红颜色,紧靠板壁的婆婆的棺材也布满了暗影。小乡一下坐起来,望着广播箱,心里催着广播员快快讲话——不讲话放一曲音乐也行,只要出一点声音,他就不会太害怕。
从记事起,那口棺材就放在厅房靠板壁的一侧。小乡知道它是给婆婆准备的。婆婆并不老,也很少生病,所以一直被闲置在那里。说是闲置,也只是针对棺材本来的用场——装死人。实际上它从未空闲过,不是用来装麦子就是用来装谷子,有时还装点花生、核桃什么的。把花生、核桃藏在棺材里自然是父亲的主意——他怕几个孩子偷吃。把花生、核桃藏在棺材里,的确很难让人想到,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去动,也动不了笨重的棺材盖。
小乡走过去打开门,希望看见婆婆站在院坝里,筲箕搁在石凳上正在歇气,筲箕里的青菜还在滴水,或者看见有人正从他们家院墙外面走过——赶着水牛,披着蓑衣……可是没有。院坝里不见婆婆的影子,院墙外面也安安静静,听不见一点脚步声。小乡经常在黄昏看见有人牵着水牛经过他们家院墙,还有人挑着水桶或者背着一大背柴草。他看不见他们的脸,只看得见他们的脑壳顶顶。他们的身体被挡在石墙后面,只是脑壳顶顶在移动,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受了操控的木偶。牛经过的时候,除了甩起来的尾巴便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石墙垮出一个缺的时候,才看得见牛背,才看得见人的大半个身子。
雨下起事了,不大,嘀嘀嗒嗒的。
小乡正要拉上门到园子里去找婆婆,广播又响了。有人在讲话,说的是北京话,口气很硬扎,一听便知道是一个大官。但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周总理——周总理已经在前几个月死了。广播里的电流声很大,一直在铮铮地响,小乡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广播里的人讲的是什么。他想知道讲的是什么,便咚咚咚顺着楼梯爬到楼口,把耳朵贴在广播箱上,可还是听不清,广播箱里的电流声更大了,铮铮铮——铮铮铮,像锯锯镰一样割耳朵。小乡本能地将耳朵躲开,怕从广播箱里真的伸出一把锯锯镰。小乡听清楚了两个词:“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活动”。小乡隐约知道了一点——北京出大事了。小乡伸手去摇了一摇广播箱,小乡知道,铮铮铮的电流声是因为广播里哪个地方不通畅。小乡不止一次看见父亲拿了竹竿去剟广播箱,去剟街沿上的电线,几剟几剟广播里的声音就好了。有时候父亲在打算盘或者在编背篼,就叫小乡到楼口去摇广播箱。小乡不知道他们家的广播箱挂在那里多少年了。小乡问他大哥,他大哥也不知道。从记事起,他们家的广播箱就一直挂在楼口。开始的时候,阴天都能看见上面刷的红油漆,慢慢地便只有出大太阳才能看见了。箱上扑满了灰、蛛丝和竹叶,顶上还结了厚厚一层油垢。
小乡摇了摇广播箱,铮铮声倒是没有了,只是广播里的人也不讲话了。他又摇了几下,广播里的人还是不讲话。他有点烦了,有点讨厌这个广播箱了。他拍了它两巴掌,拍了满手的灰尘和油垢。有一只很小的红蜘蛛被他拍死了,粘在手板儿上。
小乡下了楼梯,在门背后找了一根竹竿,学着父亲的样子剟了剟广播箱,又剟了剟和广播箱连在一起的电线。广播响了,但杂音更大了,根本无法听清里面在说什么。剟电线的时候,有些够不到高,小乡抬了凳子站到了婆婆的棺材上。棺材还没上漆,上面铺着麻布口袋和烂蓑衣。
这么一个木头箱,这么一根从外面牵进来的铁丝,却让小乡恨也不是爱也不是。有时候,这个木头箱的确是可爱的,它唱歌,它讲故事,它播送放电影的通知……有时它更是神奇的,用一个喜悦或者悲痛的声音念出一长串大人物的名字。时间久了,有些名字在小乡的脑壳里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听见前面的名字便晓得后面要念的名字,比如周建人、许德恒、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赛福鼎……也有讨厌的时候,也有恨的时候,就像现在,响着响着突然不响了,响着响着就冒出铮铮铮的杂音来。有时候,小乡感觉那一根连着广播箱的铁丝也连着他——连着他身体里的某个地方,控制着他。
小乡扛着竹竿从屋里出来,学着大人的模样查看着那根和广播箱连在一起的铁丝。铁丝走屋檐下的板壁上穿出来,左拐,牵到了隔壁他大爸家,右拐经过两匹挑,与石墙那边林犬家的广播相连。小乡举起竹竿刨了刨屋檐下的电线,电线弹起来,弹落了上面的蛛丝和扬尘。在一匹挑与屋檐之间,有一个燕子新做的窝,小乡拿竹竿刨电线的时候特别小心,生怕碰到了。小乡不喜欢燕子,但他怕燕子骂他——几只几十只燕子一起骂他,他会感觉到被孤立了。
小乡扔了竹竿,爬上石墙,一截一截查看头上的电线。石墙两边是高大的樱桃树,叶子长得很繁茂,果子长得很繁盛。刚下过雨,叶子湿漉漉的,滴着水。小乡听父亲说过,电线挨到竹子或者树了,广播也会冒杂音。石墙上的电线没有挨到树,但它挨到了树的叶子和一些细枝枝。有一段电线几乎就是从叶丛中穿过的,小乡想爬上去刨开却够不到高。
小乡从石墙上跳下来,捡起地上的竹竿去刨樱桃树上的那叢枝叶,却怎么也刨不开——刨开了,竹竿一拿开便又合拢了。小乡管不了那么多,他举起竹竿朝那些枝叶打过去。他有一点失控,打得有一些过火,打掉了一大蓬樱桃叶和细枝枝,连同很多青樱桃。他有一点兴奋,好像听见屋里的广播又在讲话了,他越打越兴奋,一竿一竿没完没了地打着,也不管打到的枝叶跟广播线有没有关系。
石墙那边林犬的老妈开始骂人了,一边骂一边朝墙根走来。听见骂人,小乡扔下竹竿,一趟子跑进了屋。
广播真的又响了,木头箱里的人真的在讲话,而且只有很小的电流声,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小乡听不大懂,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兴奋。他躺在长板凳上,连心跳都加快了,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一股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电流,在他刚开始发育的身体里制造出了一种紧张的、有所期待的快感——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小乡望着楼口那个木头箱,望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牵进来的与木头箱连在一起的铁丝,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从这个广播箱出发,顺着这根铁丝一直走,去找到那个唱歌的人、那个讲话的人以及那个播送通知的人。
2
小乡挨家挨户去查看了广播线回来,家里人都不在。走的时候婆婆还坐在门槛外面的石凳上做针线,手指上戴一个很大的上面有凹点的黄铜顶针。现在石凳上空空的,片篼子也端进了屋。
小乡在婆婆坐过的石凳上坐下,仰身过去靠着后面的板壁,说不清这一趟子是把他跑累了还是跑饿了。
向后仰的时候,小乡看见院墙上的樱桃已经在变红了,但红透的很少,且都是在向阳的树顶,大多还是屁黄屁黄的。樱桃一年一熟,小乡还是头年吃过,早已忘了是什么味道。不过,他还记得头年清树的情景。头年樱桃熟得早,“五一”刚过,树上就全是树叶了,几颗剩在树顶的樱桃都红烂了,从竹林飞来的鸟还与他争抢。他像猴子一样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用勾搭棍儿将鸟赶走,再把樱桃勾下来抬嘴衔住。
小乡查清楚了,不管是高头院子的广播还是底下院子的广播,通通都接在一根铁丝上,这根铁丝是从晒坝边九胜家房背后的青杠林里牵过来的。现在还拿不准的是,这根铁丝是顺路牵过来的,还是翻桅杆坪、走桂香楼梁上牵过来的。他本来想钻进青杠林去看看,谁知在鲁疯子家核桃树底下碰见了他父亲,他父亲把他吼了一顿。他父亲跟几位女社员背着喷雾器,正往竹林盖走,看见小乡脸黑得像锅底,一发话脖子上的青筋便像蛇一样颤动起来。小乡记得从岩方前头到竹林盖,一路上都栽有电线杆,上面绷着电线。在晒坝里,小乡看见保管员胡玉培正在搭蚕架,想走过去问一问生产队的广播线是走哪里牵来的,又没敢。小乡怕胡玉培反问他,你一个碎娃娃家,问这个做啥子?他不晓得该怎么回答。胡玉培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又是党员,没准他会盘问小乡问题的动机。
小乡起身跳下街沿,穿过院坝和竹林,来到那棵最向阳的樱桃树底下,掌着树爬上了院墙。他先在院墙上看了看人,看了看树顶正在红的樱桃,这才像只小猕猴般上了树。
在树下看得见红了的樱桃,上了树反倒看不见了。小乡不怎么敢去扳头上浓密的枝条——枝叶间全是屁红屁红的樱桃,稍不注意那些枝条便会弹起,把樱桃弹落,有时还会把枝条扳断,父亲回来一眼就看见了。他不敢扳还是扳了,扳开了一层枝叶,依然看不见红樱桃。他很无奈,伸手摘了几颗黄樱桃喂在嘴里,感觉味道还不错,便又摘了几颗。
从樱桃树上下来,小乡感觉他真是饿了,肚子里不只是咕噜叫,还有猫抓。有什么可吃的?他在厨房里转了转,翻遍了碗柜和案板的每个角落,也没看见有什么吃的,连一点剩菜剩饭也没有。
小乡突然想到了花生和核桃。他知道他们家还有花生和核桃,过一段时间婆婆便会在他们睡了之后取出来剥,剥了又在锅里炒。婆婆炒花生米、核桃米的时候,小乡还没睡着,隔着蚊帐也能闻到炒花生米和核桃米的香味。有时候炒焦了,他也能闻到焦糊味兒。他很难得看见整粒的花生米和核桃米,更别说吃了,偶尔吃到的都是用菜刀轧过的或者用尖窝子舂过的花生泥和核桃泥,不是被包在抄手里就是撒在花卷里。
小乡一直感觉他们家有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他们小孩子看不见、找不到的地方,家里好吃好喝的东西全都藏在那儿,只有父母和婆婆三个人晓得。小乡很想找到那个地方,放学回家见婆婆不在,他都要去找一找。他找过父母的睡房,找过父母睡房里的米缸和两门柜。他找过婆婆的睡房,找过婆婆睡房里的面桶。他还爬上楼,找遍了所有的箭竹子笆笆,连挑梁和瓦缝都找过了。他不只用眼睛和手找,也用脑壳找,他有空就会去琢磨那个神秘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他甚至很注意听大人说话,希望能从他们的话里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有一次,小乡从婆婆嘴里听到了一个叫“海底”的词,他暗自兴奋了很久,想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海底”了。然而,海底究竟在哪里他并不知道。跟婆婆下河淘菜的时候,小乡想直接问婆婆“海底”是什么、“海底”在哪里,又怕大河的水声太响了婆婆听不见。他只好悄悄地跟踪婆婆,盯她的梢,看煮好的瘦肉和炸好的鱼肉是从哪里端出来的,他生病吃药时吃到的饼干糖是从哪里取出来的……不久,小乡终于找到“海底”了。一个又黑又脏的清代老柜子,老柜子有两个大抽屉,取下抽屉,里面便是“海底”。老柜子就搭在婆婆的床当头,上面放着面桶,小乡平常也都只是翻翻抽屉,没去想抽屉下面。
然而,“海底”也不是那个神秘的地方。当小乡学着婆婆把抽屉一个一个取脱放在地上,把脑壳和手伸进去的时候,感觉到了深深的失望——摸遍了整个海底,也没有摸到一颗花生、一个核桃。他只摸到了一壶白酒,闻到满海底都是酒香。他把白酒取出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现在,小乡晓得家里藏核桃、花生的地方了,那就是婆婆的棺材。他想吃核桃花生,又不敢接近。他对棺材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恐惧,在他的感觉里,棺材的形状、颜色和气味,带出的都是对死亡的暗示。可是现在,饥饿感让他忽略了恐惧,他走到了婆婆的棺材边上。小乡知道,他是绝对抬不开棺材盖的,但还是试着抬了一抬。他用尽了力,也没能把棺材盖抬动。有一次,小乡看见大哥和二哥把棺材盖抬动了,抬开了一条缝,可以伸手进去。从那条缝看进去,能看见什么呢?小乡在想,是不是一张皱皮柑子一样的脸,或者一只发蓝的手?
小乡在院坝里看了看天,一趟子跑到路口,他想找个人帮他抬开棺材盖。天还是蓝的,只是錾子岩顶上挂着几片薄云,太阳已经移到了陶家山,离落山还有两竹竿,河对岸大山的影子已经移到河水中央。小乡在晒坝里找到九胜,叫九胜跟他去他们家吃核桃、花生。
四月下午的阳光有如清晨一般明丽,只是多了一点恍惚。村子里看不见人,看见的全是一树一树繁盛的樱桃。有鸡站在院墙上,伸长了脖子啄食矮枝上的樱桃,头上的冠子在树枝的映衬下红得像毒蘑菇。两个少年从晒坝出来,走过用铧铁做的吊在已经不再发芽的老樱桃树上的钟(生产队的人便是听了它的响声出工、开会、分东西),走过胡清林家路口和胡宇林家路口,时不时跳跳,吓飞了正在院墙上啄食樱桃的公鸡。石板路上树影斑驳,阳光点点,两个少年的影子也斑斑驳驳。
九胜没有吃到小乡家的核桃、花生,也没能帮小乡抬开棺材盖。两个少年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也没能让棺材盖动一动。九胜嘟哝着嘴走了。小乡跟着走到路口,饿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他记起了吃中午饭的情形,已经挑在筷子上的肉,被突然闯进屋的下院子一个比他大的女子抢过去吃了。
小乡坐在路口,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人,可他却是个“一把手”,有一只手在小乡还没有出生时就被炸弹炸没了。小乡一边往肚子里咽口水,一边看太阳落山。太阳只剩下半边了,太阳光一轮轮地旋转、鼓胀着,发出好几种平常很难得见到的颜色,有紫色、有橙色,还有绿色。
在橙中带绿的光线里,保管员胡玉培走挑水路上来了,背上背着好几张簸箕——那些簸箕被刷洗得干干净净,水也晒干了。小乡喊了声“胡玉培表叔”,喊的声音很小,别人根本没听见。“胡玉培表叔!”小乡大声喊了一声。这一次,胡玉培听见了,靠着石墙停下来,把背上的簸箕放在石墙上,直了直腰。
“胡玉培表叔,可不可以帮我取个东西?我抬不动盖子,取不出来。”
“取个啥子东西?在哪里取?”
“在我婆婆的枋子里取,是核桃和花生。我肚子饿了。”
胡玉培看着小乡,没再说话。他熟悉小乡婆婆的枋子,前不久还当着小乡婆婆的面夸过那个枋子,说那个枋子硬扎,料选得好,做工更是莫说头。小乡想,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人,是不是也害怕枋子。
胡玉培背上簸箕走了,小乡转过头看了看他的背影,有点不相信这么个人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小乡又等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队长王生喜,他提着一个鸡啄米的闹钟从龙嘴子回来;一个是拉板板车的王司机,从城里拉粪回来,他们都不愿意去帮小乡取东西。
就在小乡感觉绝望的时候,哑巴牵着一头牛从挑水路上来。“哑巴,可不可以帮我取个东西?”小乡走上去拦住他问。小乡想,哑巴说不来话,总听得来话。
见小乡跟他说话,哑巴笑了,一边笑一边唵唵地叫。小乡从哑巴手里要过绳子,直接把水牛牵进了他们家院子。哑巴跟着进了院子。
小乡走到婆婆的棺材边一阵比画,哑巴总算弄懂了小乡的意思,正要弯腰去使劲,小乡的婆婆回来了。小乡的婆婆背着一背带秸的胡豆,走得爬腰爬腰的。婆婆问小乡又在搞什么鬼,把胡豆倒在了厅房中间。看见哑巴从屋里出来,婆婆笑了笑。
“把哑巴叫进屋,又想搞啥子鬼?”哑巴走后,婆婆问小乡。
“我肚子饿了,想找个人帮我把枋子盖盖抬开。”
从木格窗看出去,还能看见院墙后面哑巴的脑壳顶顶和牛甩起来的尾巴。
“砍脑壳的,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找人动那个家伙!你老子晓得不打死你?”
“婆婆婆婆,我晓得枋子里有吃的,你给我取点出来嘛!”小乡的口气是乖顺的、讨好的。
“我哪敢给你取?你老子晓得了要骂人!”婆婆又背着背篼出门了。
小乡哭了,婆婆佝偻的背影在他的泪眼里变得越来越模糊。他睡在厅房的胡豆里,又一次想起了吃中午饭的情形——下院子那个比他大的女子抢吃他筷子上的肉的情形。小乡剥了一把生胡豆,没往嘴里喂,他哭得更凶了,泪水滂沱。
就在这时,楼口的广播突然响了,播放起一支相当好听的曲子。听见广播响,小乡一下子不哭了,也不伤心了,一下子来了精神,从胡豆里跳起来,叮叮咚咚爬上了楼梯。
晚上公社有电影——《难忘的战斗》。
听到有电影,小乡的肚子也不饿了,腿杆也变得有劲了。
小乡拿着一条长板凳出门的时候,河对岸的整匹山和他们的整个村子都已经落入阴影,只有錾子岩还晒得到太阳。金黄的日线像一根不规则的锯条,在长满灌木的岩壁上投下一个一个的锯齿。
3
小乡在隔壁路口遇见林犬,他也拿了板凳去看电影,怀里还抱着个馍馍,一时腾不出手来拿。小乡走上去帮他拿,让他把板凳扛到肩上。
“我們早点去占位置,免得大人来了莫地头坐。”林犬把板凳搁在肩上,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拿回自己的馍馍。
馍馍是二道面的,有点黑,但比小乡婆婆蒸的还要大,看上去面发得很暄和。
小乡有点舍不得把馍馍还给林犬,林犬也看出来,一直伸手等着。
“给我别一坨得行不?”小乡看了看林犬,又看了看林犬伸在他面前的手。
“你想得倒美!”林犬说。
“就一小坨,核桃光光大一小坨。”小乡说得可怜巴巴的。
“你想得倒美!”林犬又说了一句,从小乡手里一把抢回了馍馍。
小乡没有生林犬的气,他已经在想像里咬了一大口馍馍,走到晒坝里去喊九胜的时候,嘴巴里还有麦面的香味。
九胜大方,从家里偷了花生出来给小乡和林犬吃。林犬不吃别人的东西,也不给别人吃他的东西,但这回他吃了九胜的花生,还揣了几颗在包包里舍不得吃。也许是受了九胜的感染,林犬破天荒给小乡掐了一坨馍馍。
“我们每家子的广播线都是从哪里牵来的?都是连在哪里的?”走到鲁疯子家的核桃树底下,小乡问九胜和林犬。
“这还用问?肯定是从北京牵过来的,连着北京的!”林犬把握十足地说。
九胜说林犬说得不对,应该是从桂香楼牵过来的,因为公社有个广播站。
九胜没了门牙,说话不关风。
林犬急了,马上问九胜:“如果是从桂香楼牵过来的,我们是咋个听到北京的声音的?”
小乡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对又都不对,他也纳闷得很,如果他们生产队的广播线不是从北京牵来的,北京的声音又是如何装到他们家楼口的广播箱里来的?他觉得这件事比他们想像的都要复杂,只有一根电线杆一根电线杆地去搜,才弄得清楚。可要是这电线杆一根一根一直栽到北京,总不可能搜到北京去。
小乡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九胜很赞同,林犬反对。林犬说:“要搜你们去搜,我要走大路,快去占个好位置。”
谁不想占个好位置?放映机旁边的位置,离银幕不远也不近,能清楚地看见讲话的公社书记——他刚刚喝过酒,能清楚地看见和书记坐在同一根板凳上的女知青——扎着两条马尾辫,中途还可以看放映员倒片、换片——倒错了再倒过来,换错了再换回来,不会干着急。再说,一根电线杆一根电线杆地搜也花不了好多时间,如果电线是从桅杆坪牵过来的,说不定比走大路还要先到。走桅杆坪算是走捷径,一路上还可以跑,只要看清楚广播线就行了。
小乡找到了全村广播线的总线,发现还真是从桅杆坪牵下来的。那些电线杆太矮了——电线自然也绷得矮,被青杠树的枝叶完全遮蔽了,只有到了冬天,青杠树落光叶子的时候才会露出来。
三个人一口气跑到坪口,放下板凳坐在上面歇气。林犬心里不愿意却跟着来了。坪口的那根电线杆像是要高很多,上面的电线看得清清楚楚。
已经是傍晚了,但天还没有打麻影子,錾子岩背后更高的山峰上还看得见一绺黄斑斑的太阳。涪江两岸是变得更暗了,河滩、草地、山崖、山坡、桑田、竹林、瓦屋……变得最暗的是錾子岩脚下的锅坨漩。天空的颜色变深了许多,但几座大山的山峰都还是亮丽的,西天的几处云彩显得格外绚烂。
他们没敢在坪口久留,沿着堰盖上放牛人和刨水人走的小路一路奔跑,时不时去留意堰盖上或者堰盖下的电线杆。有时电线杆离堰盖很近,小乡就跑上去摸一把——小乡对电线杆和电线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和莫名的感激,觉得是它们把外面的世界带到了他的面前。有时电线杆离小路很远,中间与他们隔着好几块麦田,甚至隔着一片坟林或一条大沟,几乎看不清上面的电线,小乡只有靠歇在电线上的麻雀来确认电线的存在。
在坟林窝窝,三个人都被一声吆喝吓住了。过了坟林窝窝不远便是桂香楼梁子了,下了梁就是公社。他们从记事起就听说,坟林窝窝闹鬼,听見那一声吆喝,三个人都以为真的遇到鬼了,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坟林窝窝时有新坟,白晃晃的花圈在桅杆坪便能看见,不要说小孩子,就是大人大白天路过也会感到害怕。
小乡正要拔腿跑,听见九胜说,小乡,是你大大。
小乡抬头看,果真是他父亲——背着喷雾器,走在树林边的田埂上,像是刚从树林里钻出来。
“狗日的几个,咋个在这儿?”小乡的父亲朝他们喊。
“我们去看电影,桂香楼今晚上有电影。”林犬说。
“看电影咋个不走大路?”小乡的父亲一边说一边朝他们跑过来,背上的喷雾器上下跳着,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喷雾器的盖子好像也没有拧紧,里面没有打完的药水溅了出来,随着晚风飘进了三个孩子的鼻孔。
小乡看见父亲跑过来,本能地拔腿便跑。他顺着堰盖跑了好久,一直没敢回头。他父亲在喊他,九胜和林犬也在喊他,他什么都听不见。
4
这天放学得早——邓老师的男朋友来了。九胜约了小乡去公社医院捡废针头。在小乡眼里,邓老师的男朋友有电线杆那么高,每次从他身边走过都要刮起一阵风。他从一辆停在公路边的长途客车上下来,提着一个旅行包,径直去了邓老师的寝室,并不到教室里来找邓老师。邓老师透过没了玻璃的窗户看见他,脸倏的红了,讲课的声音也开始发紧。
说是去公社医院捡废针头,其实是在公社医院旁边拱桥下的垃圾山里捡废针头。九胜熟悉那些针头,一眼就能看出哪种是一号针头,哪种是二号针头,哪种又是三号针头。
椒园子的男生经常去拱桥下面捡废针头,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用废针头的针屁股做了一个啄啄炮。三号针头小,针屁股只能装三根火柴头的火药;一号针头大,可以装八根火柴头的火药,响声自然最大,跟放火炮一样。他们用窗户上的风钩做啄啄炮的手柄,把针屁股绑在风钩上,装好了药再扣上。
拱桥沟刚涨过水,把拱桥下一山山的垃圾冲走了。小乡和九胜把剩下的一点垃圾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根废针头。他们翻出的全是药瓶打碎后的玻璃碴、浸了水的标签纸和又脏又臭的纱布与药棉。
没捡到废针头,小乡想,要是医院里哪位阿姨能给他一根就好了。小乡和九胜走进医院,趴在注射室的窗台上偷看——注射室里没有一个人,白瓷盘里各种型号的针头都有。
小乡和九胜没敢进注射室,他们从医院的后门出来,径直去了桂香楼。天阴阴的,已经下了好几天雨了,仍没有放晴的意思。小乡不经意地抬头,看见了桂香楼口子上的天堰——横跨在公路上的一条渡槽,滴滴答答地往下淌着水。
在桂香楼转了一圈,没有看见有桂花树,也没有看见有楼,小乡心想,这么个地方,怎么叫桂香楼?他为“桂香楼”这个名字纳闷好久了。是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桂花树,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栋楼?他不晓得应该问谁。没有桂花树,皂角树倒是有一棵,就在公社背后的坡上。
九胜提议去捡废电池。小乡晓得哪里有废电池——就在皂角树底下的坡上,他去捡过好几回了,每一次都能捡到。小乡不明白那个地头为啥有那么多的废电池,公社的人为啥都把废电池丢在那里。他不相信他们的心有那么好,晓得他喜欢废电池便特意丢在那里。记得他捡到的电池都是火车牌的,有的里面电还没有用完,捏起来还是硬邦邦的。
这一次,他们在皂角树底下又捡到了,一共是七节,三对单一只,只是捏起没有以往的硬,有两只已经流水了。他们捡了石头,就地坐下来开始砸废电池,准备把每一节都砸开,取出里面的炭芯。他们喜欢那一根根漆黑的炭芯,喜欢拿炭芯在石头上、树上、墙壁上、乒乓台上写写画画。
“九胜,我问你一个问题。”小乡砸着砸着废电池说。
“你问嘛。”九胜停下来,看了小乡一眼,等着他问。
“你真的认为生产队的广播线是从公社牵起去的?”小乡问话的语气和表情因为过于严肃和正式,反倒显得有一点滑稽——他把废电池炭芯上的墨粉糊到脸上了。
九胜没有回答小乡的问题,说:“小乡,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邓老师的男朋友每次过来,会不会跟邓老师睡一床?”
小乡听了,突然显得很生气,严厉地说:“任九胜,不许你这么说邓老师!”
九胜看着小乡,十分不解,他吹了口气,埋下头接着砸他的废电池。缺了门牙的九胜看上去样子有些滑稽。
小乡没完,又对九胜补充了一句:“也不许你这么想邓老师!”
不许别个这么说邓老师、想邓老师,小乡自己在心里却已经想过几百遍了——他知道邓老师的男朋友早就跟邓老师睡一床了。每次那个人来过,邓老师的眼睛都是哭过的,脸色也是惨白惨白的。
下雨了,小乡一个人跑了。他先是跑到了何聋子家的早晚门市部前面,接着又跑到了供销社的砖房子当头。雨很快就下大了,屋檐水一下子便拉伸了,雨声轰鸣,响成一片,每一栋房子前面都是飛流的雨帘。同时,刮起了风,飘飘雨飘到了屋檐下,飘进了门窗。他的衣裳很快便湿透了,成了水坨坨。
小乡从一个屋檐下跑到另一个屋檐下,跑了四五个地方都无法躲雨。他把一只凉鞋跑掉了,把另一只凉鞋的耳子跑断了。他把断了耳子的凉鞋提在手上,满脸雨水,像是大哭过。
透过雨幕,小乡看见山根里的一栋老式青砖平房当头上接了一个柴棚,就不顾一切跑了过去。
一把捏不住的雨水,混淆了从房子里牵出的好几根电线。
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小乡本能地朝窗户里看了看。雨下得更大了,屋檐水已经淌不住,一股股地分流到了街沿上,分流到了窗玻璃上。透过雨水横流的窗玻璃,小乡看见了一个正在播音的女广播员的侧影,隐隐约约,有些模糊,在一股股雨水的流淌中变换不定,她很漂亮,很年轻。小乡停下来,趴在窗台上,偷偷地看。雨水一股一股地从窗玻璃上流下来,小乡用嘴去吹,用手去抹,都不管用。他的背上也在淌水,分不出是从屋檐上流下来的,还是从他的湿衣服上淌下来的。
有一会儿,窗玻璃上的雨水改变了路线,小乡看清楚了正在播音的女广播员。她真的年轻,跟他的邓老师一样年轻;她真的漂亮,比他的邓老师还要漂亮——她是瓜子脸,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下巴。她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坐在一把旧时的太师椅上。她的碎花连衣裙很宽大,盖住了太师椅一边的扶手。面前搭着一张三屉桌,桌上放着一只扎了红绸缎的麦克风。小乡听不见她播音的声音,但看得见她张嘴、闭嘴。她每张一次嘴,盖在太师椅扶手上的连衣裙上的碎花就会颤动一次。
小乡时常听大人说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叫王英书,但他不知道王英书原来有这么好看。小乡用从废电池里取出的炭芯,在路边的石头上、桑树上、别人家房子的当头上,写了很多很多的王英书、王赢输、王影疏、王颖舒、王淫书、王盈书。
它们当中,小乡最喜欢的一个是“王影疏”。
5
地震了,天天下雨,从八月下到了九月。
地震过后,小乡家的广播就没再响过。从石堆上爬过去问林犬,林犬家的广播也没响了。过去,小乡家和林犬家隔着高高的院墙,现在,地震把院墙震垮了,变成了一堆一堆的石头。
小乡约上林犬,跑到晒坝里去问九胜,九胜家的广播也不响了。晒坝里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空,晒着一簟一簟的麦子、核桃或者花生,而是搭满了抗震棚。
“地动的时候广播还在响不?”林犬问九胜。
九胜记不到了,转而问小乡。小乡说,地动的时候他正站在茅坑边上撒尿,差点栽到茅坑里。至于广播响没响,他也不记得了。不过,当天晚上广播一定是响过的,三个人都记得。小乡清楚地记得他的“王影疏”说“长桂人民广播站,今天第三次播音开始”时的情形——当时天还没有黑,錾子岩上面的星星已经在眨眼睛了,他刚从龙嘴子回来走到路口,“王影疏”播音的声音又一次唤起了他对那个雨天侧影的想像。想像中,他的身体里第一次跑过了一匹小马。
在漫长的余震不断的雨季里,没有广播听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大人们都抗震救灾去了,雨一停,婆婆也出门到园子里为全家人准备吃的去了,大哥二哥已经长成了大人。小乡整天睡在厅房的晒簟里,看着屋外一阵一阵的雨,听着各式各样的雨声,有时候感觉太沉闷、太无聊了,就顺着木梯爬到楼口去看广播箱,摸广播箱,盼着广播突然响起来。
广播不响,听不见北京的声音,听不见“王影疏”的声音,小乡有时也会去想“王影疏”,想比他看见的侧影更多的东西,比如她是哪里的人、多大了、耍没耍男朋友,以及那些不好说出口的更为隐秘的东西——她略显宽大的碎花连衣裙和连衣裙里的身体,甚至远不止身体,还有从雨水迷蒙的窗玻璃里透出的一种不确定的光芒——纯洁而迷离,带一点淡蓝。
当然,有时候小乡也会去想上次因为父亲半路杀出没来得及弄明白的广播线,它真的如林犬说的那样,是从公社广播站牵过来的吗?
想“王影疏”的时候,小乡总是不记得“王影疏”的声音——传递到他们家广播箱里的声音。其实,“王影疏”的声音并没有多好听,甚至可以说算不上好听。当然,小乡听见的是“王影疏”传递到他们家广播箱里的声音,未必就是“王影疏”原来的声音。也许“王影疏”原来的声音就像小乡在雨天看见的侧影一样美,是那些污迹斑斑的电线把她的声音变成了小乡听到的那个样子。
小乡总是在傍晚时分想起“王影疏”。他睡在厅房的晒簟里,晒簟一直都只打开了一半,另一半还卷着筒。大人们都不在家,婆婆也到后门外山根里接渗水去了。不管门外下没下雨,不管雨下得大还是小,天光都非常地暗,越来越暗,小乡能看见从大门外面钻进来的一坨一坨的麻影子,就像是有人在天空这个巨大的砚台里磨墨,墨在一点点加重、加浓。
小乡一个人睡在晒簟里,突然感觉很害怕,他希望广播响起来,哪怕只是唱歌(没完没了地)也好。当然,如果有人说话更好,如果有“王影疏”说话更好——长桂人民广播站,下面播送一个通知……
这么想,小乡抬头看了看楼口的广播箱。楼口一团漆黑,广播箱也是一团漆黑,只有瓦缝里还看得见一丝丝光。
小乡把视线从楼口移下来,移到了婆婆的棺材上——婆婆的棺材也是一团漆黑,或者说是一团棺材形状的黑影。
小乡感觉越来越害怕,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默念:“广播快响,广播快响,广播快响……”
有时候即使天下着雨,天光也会略显明亮——黄昏还有一会儿才到。小乡一个人坐在晒簟里,仅仅是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害怕。楼口刚刚罩上一层暗影,广播箱还显得很清晰,婆婆的棺材四周只是布上了暗影,棱角都还清清楚楚。小乡会在隐隐的害怕里想“王影疏”,想“王影疏”身上那些隐秘的、他一无所知的可能的东西。好几次,小乡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他在广播线的这一端,“王影疏”在广播线的那一端,他们就像是长在同一条藤两端的两个瓜。小乡很喜欢他的这个错觉,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陶醉,陶醉感暂时消除了隐隐的恐惧感。过去,小乡也想邓老师,但在他和他的邓老师之间却缺少这么一根广播线。
小乡在晒坝里的抗震棚外面碰见九胜,问他想不想听广播。九胜说想倒是想,就是听不到了。小乡说,听不到是因为桅杆坪的电线杆倒了,我们找几个人去竖起来。
找哪几个人呢?他们首先找到了林犬。林犬正在竹林里的水里捞柴捡山核桃吃,对小乡的想法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当着小乡和九胜的面,一连砸开了三个山核桃,里面都是朽的,且奇臭无比。他们又去找了几个比他们大的孩子,他们都不愿意去,他们只是想听广播。小乡瞧不起他们,鼻孔里哼哼走了。在青皮树底下碰见小英和丽芳背着南瓜从园子里回来,听小乡和九胜一说,倒是背篼一搁跟他们去了。
桅杆坪的电线杆都是好好的,一根一根立在长满刷把签和水葵的秧田盖上。电线杆上的电线也都是好好的,上面还歇着几只麻雀。他们顺着电线的方向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坟林窝窝。有一根电线杆倒了,但没有完全倒下来,上面的电线也没有断。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根电线杆?”九胜问小乡。小乡也不知道,說:“我们先把它竖起来!”
两个人走过去开始往起竖电线杆,自然是竖不动。电线杆虽然是香椿树做的,但对于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太重了,何况还被两端的电线紧紧地拉扯着,几乎要悬起来了。
小英跑过去帮忙,半天找不到掌手的地方,反倒踩了一脚泥。丽芳也跟着跑过去,比小英还要惨,两只脚都陷在了稀泥里,直到小乡过去帮忙才拔出来。
“我们一定得想法把电线杆抽起来。”小乡说,“说不定回去就能听到广播了。”
九胜也很想听广播。好久没听到广播,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在九胜和小乡的想像中,外面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大事情的地方。这个外面,不是指桂香楼,不是指县城,而是指他们从未去过,甚至不敢想像的地方,比如北京,比如越南,比如朝鲜,也包括美帝和苏修。他们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啥样子。他们往上只走到过县城——准确地说是走到过县城西门外面,往下只走到过古城——跟大人去锤碎石,他们全部世界的方圆仅限于三十里长的江河两岸。他们和外面世界的唯一的联系就是眼前的这根电线。
天难得放晴了一会儿,眼看雨又要来了。四个人坐在堰盖上想办法,四个人的眼睛里都是茫然。四个人都是一脚的泥,一身的泥。
“雨又要来了,我们回去!”丽芳说。她不是怕雨,而是怕堰盖上不远处柏树林边上的那些坟。说话的时候一回头便能看见新坟上被雨水泡垮的花圈。
小英也想回去,只是不好意思说。
“我想不到啥办法,你有吗?”九胜问小乡。
小乡没听见九胜的问话,他的眼睛落在远处的堰盖上——哑巴牵着一头牛在堰盖上吃草,牛一边吃草一边甩着尾巴驱赶蚊子。
一闪念,小乡有办法了。他没有把办法讲给大伙儿听,便径直朝哑巴跑过去。他们坐的地方与哑巴隔着条沟,堰渠绕到了沟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见小乡的身影。等到小乡从对面沟里钻出来,嘴上、脑壳上全是泥。
小乡停在哑巴面前,又比画又说,比画了好一阵,哑巴才弄懂他的意思,牵着牛跟他走过来。牛舍不得堰盖边上的青草,走两步就要停下来啃两口,哑巴不得不用手里的绳子使劲抽它。
牛拉过来了,拉到了那根倒伏的电线杆旁边,九胜和丽芳几个还是不明白小乡的意思。但哑巴明白,他将手里的绳子一头绑在电线杆上,一头套在牛身上,绑牢,还试了试,然后唵唵唵地叫站在电线杆旁边的丽芳和小英走开。哑巴扯了根桑条赶着牛往前走,牛走了几步,刚刚把绳子拉伸,四个蹄子便陷在了稀泥里,怎么抬也抬不起。哑巴有些生牛的气,拿起桑条使劲抽打起牛的屁股。牛挨了打,奋力拔出蹄子,尥起蹶子来。
猛地,倒伏在地里的电线杆被拉了起来,但很快又倒下了,且比之前倒得更为彻底,把上面的电线也挣断了,连电葫芦都摔碎了。
6
天晴了,秋意也有了,注意看,河对岸半山上已经有了秋色。
天晴了,也只是不再没完没了地下雨。天阴阴的,连一点昏昏太阳也照不见,铺着铁灰色的云,只是天变高了,天边变远了。
漫长的雨季里,水稻都生了虫,稻田里长满了稗子。
大河涨过几次小乡从未见过的大水之后,也慢慢平静了下来,但河水还很浑浊很丰沛,捧一捧水在手板里看得见悬浮的沙粒、树叶、木屑和草根。
小乡开始下河坝捞柴,天天泡在水里,没有时间去想听广播的事情了。
小乡在河坝里看见一个人,一个年轻女人,很像是“王影疏”。小乡不敢确定。“王影疏”怎么会跑到龙嘴子河坝里来?怎么会来背水捞柴?
分明是“王影疏”,小乡却不敢确定。她穿着粉红色的雨衣,雨衣的帽子搭下来遮住了眼睛,小乡无法看见更多。她的下巴很清楚,是小乡在公社广播站的窗户里看见的下巴,还有她整个面颊的轮廓和气质,是小乡一看便能够感觉到的。
河坝里的人太多,小乡撵着“王影疏”看了很久也没能把她看清楚。刚要看清楚,不是被一个披蓑衣的人,就是被一个送饭的人走过来挡住。小乡本来还想看看她雨衣里穿的是什么衣裳——是不是那条碎花连衣裙?
走到石灰窑,小乡没敢再跟着“王影疏”往前走——远远地,他看见了背着喷雾器正在稻田里给水稻打药的父亲。
望着远去的粉红的背影,眼泪一点一点从小乡的眼睛里渗出来。
回到水边,小乡没心思捞柴,他收起刚插下的柴网扔在柴堆上,慢吞吞地回了家。家里没一个人。天晴了,但院坝里还是泥泞,檐沟里的青苔已经厚厚一层,街沿的石头缝里长出了水蕨。
推开门,小乡看见婆婆不知什么时候掰了玉米倒在晒簟里,有青有黄,有两个青玉米滚落到了晒簟外面婆婆的棺材旁边。
小乡走到棺材边把玉米捡回来,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楼口上的广播,接着撕开玉米,掐了掐。玉米还很嫩,直往外冒浆。他肚子饿了,想吃烤玉米,跑进厨房去看灶孔里有没有火。
灶孔里还真有一点火,一点中午的火石子,被婆婆埋得好好的。小乡用火钳掏开火石子,把撕好的玉米丢进去,只听见一两声玉米被火烤的响声。他坐在灶门前等了好久,都没有闻到烤玉米的香味。他刨了刨灶孔里的玉米,发现火熄了,干脆用火钳把玉米夹了出来。他在玉米上只找到三颗熟的,掐下来喂到嘴里。三颗玉米把小乡的潮气(食欲)惹发了,又想到了婆婆的棺材。不过,他好久都没有吃到婆婆包的核桃抄手和炒的花生了,不知道棺材里面是不是还有。生产队的核桃已经打了,堆在保管室还没晾晒,至于花生,今年就别想了,都叫八月的那河大水冲得干干净净,花生地都变成了乱石滩。
小乡希望棺材里面还有。即使没有,他也想看个究竟,看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都是啥样子。
找谁帮他抬开棺材呢?这一直都是让小乡困惑不解的问题。不能叫大人看见,不能叫大人晓得,找的人又得有大人的力气……他最好的朋友就是九胜,但九胜肯定抬不开那么笨重的东西。他想到了哑巴。
小乡从他们高头院子走到底下院子,路上没碰见一个人。晒坝里也不见一个人。路下园子里,远处田坝里,也看不见一个人。整个村子出奇地安静,从樱桃树上掉下一片叶子都听得清清楚楚。鸭子吃饱了虫子,在排水沟悠闲地扇动翅膀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还有晚风吹过竹梢的声音,细得像蚕子在吃桑叶。
在保管室,小乡还真听见秋蚕吃桑叶的声音。
哑巴家的院子里蓄了很深的水,就像一口水茅坑,又脏又肥的鸭子在里面潜着水捉虫吃,它们扁平长长的犹如撮瓢一般的红喙一点不像是从它脑壳上长出来的,倒像是人工安装上去的。哑巴不在,他家的圈门却大开着。
九胜和林犬也不在。天阴阴的,铅云铺展得很平整很均匀,从天光看不出一天的早晏。小乡在路口站了好一阵,也没有等到一个人。
进到屋里,小乡一个仰板倒在了晒簟里。他顺手抓过一包青玉米,撕开啃起来。青玉米很嫩,一颗颗都还是浆,味道甜甜的,带一点腥味。青玉米浆的味道,让小乡想起“王影疏”。这一次,他想起的是穿粉红色雨衣,雨衣帽子遮住眼睛的“王影疏”。
小乡扔了啃了一半的青玉米,一头爬起来,咚咚咚地爬上木梯。他没有去碰手边的广播箱,而只是盯着它。他突然生出一种预感,预感到广播会突然响起。
广播真的响了!奏起了一支奇怪的曲子。一直都奏着那么一支曲子,一遍又一遍,好像那支曲子是一条河,一直要流到大海。小乡也不知道自己是希望这支曲子停下来呢,还是就这么一直奏下去。他并不想听“王影疏”播音的声音,相比她的声音,他更希望看见她的样子——不管是穿碎花连衣裙坐着的侧影,还是穿粉红色雨衣的背影。
小乡站在楼梯上,在等那支曲子结束。他希望有人出来说话。
小乡在楼梯上站了很久都没等到音乐停,便慢吞吞一框一框地从木梯上退下去,站在地上望着广播箱。他又有了一种预感,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想到了,没敢继续想。
小乡回到了厅房的晒簟里,他听出了广播里播放的是哀乐。他的预感更强烈了,有些不敢相信——那个人不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吗?
小乡感觉又累又饿,好像已经活了一辈子,好像自己的肚子从来都不曾吃饱过。他慢慢地,慢慢地朝着晒簟里的玉米堆仰了过去,很快就迷迷沉沉地睡着了。他做梦了,梦见自己上了桅杆坪,一根电线杆一根电线杆地朝前搜寻,一直搜到了桂香楼。坟林窝窝里并没有让他害怕的新坟。他发现电线并不是到了桂香楼的广播站就终止了,而是继续往前延伸。他继续一根电线杆一根电线杆地往前搜寻,过了县城,出了河谷,到了平原上。在一根电线杆下面,他看见了黄河。最后,他搜寻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很多电线,他不晓得是哪一根。
小乡只睡了一小会儿就醒来了。他是急醒的,也是饿醒的。就在他起身准备找东西吃的时候,看见婆婆的棺材盖是斜开的。天光变暗了一些,婆婆棺材的四周又布上了暗影,棺材盖斜出的那道长长的缝隙也是一道暗影。他站起来,走出晒簟,走到了棺材盖斜出的那一道缝前面。他现在想的不再是核桃、花生,而是婆婆。婆婆上哪儿去了?婆婆会不会就睡在棺材里?
谢天谢地,小乡松了一口气,婆婆没有在棺材里,棺材里只是装了半棺材麦子。小乡侧身把一只手伸进去,插在麦子里,摸到了几颗花生。小乡换了个地方摸了摸,又摸到了几颗花生。他猜一定是婆婆舀麦子忘了盖上棺材盖。
小乡回到晒簟里吃花生。吃花生前,他先把花生摆在一起,一颗一颗数了一遍,就像是一个仪式。
就在小乡剥花生的时候,突然,广播里有人说话了,是北京的声音,不是“王影疏”的声音。他听不太明白,廣播里用了很多很多的形容词,都是很长很长的句子,就像是一出大戏的过门。他把手里的花生放下去,站起来望着楼口的广播箱。
天光更暗了,像是又到了傍晚。外面没有下雨的迹象,只有微风吹动竹梢的声音,也没有脚步声。
小乡相信北京的声音会从头再播一次。他等着从头听起,把事情听明白。他重新拿起一颗花生来剥,剥开发现全是朽的。他换了一颗再剥,还是朽的。他一口气把所有的花生剥完,全是朽的,有的已经蛀成了粉末。他把朽花生一颗一颗捡起来揣在包里,想一会儿出门时把它们扔得远远的。
老屋里的暗影在叠加,就快要看不清楼口的广播箱了。神龛下方,全家人获得的一张张奖状也变成了暗影。
广播里终于念完了最后一个形容词堆砌的长句,小乡听清楚了一个成语,“永垂不朽”。
“毛主席死了!”小乡惊叫了一声,心一阵狂跳一阵发紧,他仿佛突然变得不会呼吸了。
小乡再一次走出晒簟,咚咚咚地爬上楼梯,盯着面前黑糊糊的广播箱。可是,广播里说话的声音消失了,渐渐放大的是一阵阵刺耳的电流声。接着,戛然而止。
小乡从楼梯上下来,外面已经擦黑了。他回到晒簟里,斜靠着那些半黄半青的玉米躺下。这时候,他感觉到的不再是饥饿,也不再是害怕,而是孤独——伴随着莫名的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在充满霉味的空气里,有淡淡的青玉米浆的味道弥散开来。他又一次想起了“王影疏”,想起了那个穿碎花裙的坐着的侧影,下意识地将一只手伸进了裤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