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庆:不忍一生被这样抹去
2014-04-22张振涛
张振涛
李元庆:不忍一生被这样抹去
张振涛
由于杨荫浏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没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过的人大多会犯个小错误,把杨荫浏视为这个单位的“掌门人”。其实,杨荫浏只是学术掌门人,主持机构运转的行政领导人是李元庆。他被杨荫浏的大名遮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杨荫浏与李元庆,让外界充满好奇,无数人围绕他们做过文章,但好像一直没有把两个人的地位说清楚。在机构运转的当量上,两人应该相提并论。为了不再把类似“错误”延续,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人都有个心愿,为李元庆编辑一本漂漂亮亮的纪念文集“以正视听”。迟迟未能如愿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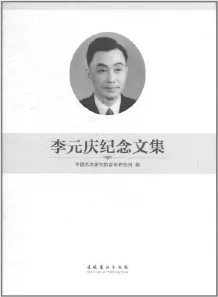
《李元庆纪念文集》书影
2004年夏,定居香港回北京办事的中国音乐研究所老前辈孔德墉先生,邀我与刘东升一聚。席间不知不觉间扯到这个话题上,我就把愿望说了出来。刚说完,立马后悔提起这件事,真是“一言出口,驷不及舌”。因为孔先生兴奋莫名,立刻开始探讨如何具体操作。孔德墉和刘东升,都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老人,一直有为老所长做点什么的愿望,这把火一点就着。老人们聚会时也一致认为,编辑《李元庆纪念文集》是实现心愿的最佳途径。2007年,孔德墉慷慨答应全部经费由他承担,并希望于年底就编辑完成。有了出版经费,才算有了把心愿付诸施行的条件。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孔先生出钱,我们出力。与刘东升谈妥,他负责约稿,我负责出版。好在老同志一听此事都积极响应,纪念文章没多久就汇聚起来了。本来只想把纪念文章汇集一起,编辑过程中,我又有了新定位:何不趁此把李元庆的所有文论汇集一编?不利用这次出版,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难说了。原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李元庆论文集《民族音乐问题的探索》(1983年),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与他的地位很不相称。
方案立刻得到刘东升的赞同。2007年12月17日,孔德墉、刘东升、范慧勤、周昌璧、夏明珠、李煞和我,会聚一堂,重新确立《李元庆纪念文集》体例:第一部分照片,第二部分李元庆的全部文章和作品,第三部分纪念文章。
当时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就读硕士研究生的徐明哲,向我征求学位论文选题意见。我灵光一现:写李元庆。前有戴鹏海编的《李元庆年谱》,中有李元庆论文集《民族音乐问题的探索》,现有老同志的纪念文章,只需把李元庆剩下的著述和作品汇集起来就能呈现整体轮廓。这么好的课题和前期准备谁不答应呀?徐明哲欣然接受,并立刻着手收集资料。查找复印,登记著录,不负所望,她几乎找到了李元庆所有的文章和创作歌曲。2009年4月2日,文化艺术出版社责编王红拿来了《李元庆纪念文集》的校稿。看着李元庆全部资料汇为一编的那份舒坦,大大超越了仅有纪念文章的喜悦。

1954年,杨荫浏(右)与李元庆合影
李元庆的生平大家写了许多,我不多啰嗦,只想谈谈他转向民族音乐研究这一点。年轻时代学习大提琴的人似乎应该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改变他的是1941年到达延安并进入“鲁艺”的机遇。他是参加过《黄河大合唱》(1940年)、《白毛女》(1945年)初演等一系列现代音乐史上重大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是坐在那个“不成编制”的乐队中的乐手之一。李元庆、张贞黼拉大提琴,身边有拉小提琴的时乐濛、李季达,吹笛子的李焕之等。这些不成编制的乐手却让新中国大乐队组建成了正规编制。“鲁艺”对李元庆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影响,人生从此重新定位。1942年他参加编辑《民族音乐》,开始脚踏实地接触民间音乐。后来到张家口“华北联大”任音乐系教员,认识了河北的民间艺人。李元庆一生最著名的学术论文《管子研究》就在这个时候奠定了基础。虽然以后再没时间让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这篇被音乐学界评价为近代“乐器学经典”的范文,已经可见其功力。借用梁启超评价谭嗣同的话说:“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
1949年9月,李元庆被委派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组建“研究部”,新事业扬帆起航。此后,他一直主持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直至生命结束。他确立的持续数十年的路线图,内在理路异常清晰且固定不变,即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的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资料中心与学术机构交叉重合,彰显了掌舵人的学术眼光和政治视野,并因此而在整个音乐界播名。新中国的学术机构谱系中,中国音乐研究所是独具特色的一个。从此,中国音乐学成为了一项事业、一门科学。
李元庆一生成就了两件大功。第一是创立与建设中国音乐研究所,第二是乐器改革。第一件事,音乐图书馆、乐器博物馆、音响资料馆的三大建设,确立了这个单位在整个学术界的核心地位。第二件事,如果把20世纪乐坛上的“乐器改革”视为学科史上的一首壮歌并让整个音乐界受惠是并不过分的话,那么不管正负面影响如何,都应该称为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举措。具有远见卓识又深爱传统音乐的领导者,为两大奇功投入了毕生心力。“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人之人情所欲居也。”
一个人活了一生,做了许多事,难免得罪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负面评价,唯有李元庆没有,众口一词,一致赞誉。这听起来像神话,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谈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大家必然会提到他的名字以及那句评价:“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年龄越大对同辈越少敬意的杨荫浏,却自始至终对李元庆表露出少有的敬意。纪念文章中,杨荫浏使用了一系列修辞学上的正衬法,使人感到李元庆在他心中的地位。列举一事,以见杨荫浏记忆中与李元庆开始共事时的细节:
1950年我们就开始进行采访工作,我们在天津首先想到的是就近采访北方的说唱音乐。我们古乐组的同志有曹安和、储师竹和我三个人,每周去天津的劝业场听几次说唱,有单弦牌子曲、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等等。元庆很支持我们的工作,考虑得很细,他嘱咐我们凡是为工作外出,一切开支都可以报销,以免在试行低工资阶段加重我们个人的生活负担。
这番话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位单位负责人对专家工作的认同,更是从实际层面体察同事难处、全力呵护的细微之处。假如“业务同伴”没有能力领会“行政搭档”的贴心和细心,那么,“行政搭档”用来向“业务同伴”展示默契的用心和慧心,也就难以铭记于心,而这点点滴滴,都能引起两人之“会心”。于是,两人“更相引重,始终无间”。李元庆与杨荫浏仿佛就是内在思想的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研究所仿佛就是外在现实的李元庆与杨荫浏。
朱熹说,学人转化风气,一方面通过写作传播学养,一方面做出风范让别人习模。李元庆以身作则,以文章传播学养,以行为树立风范。作为领导者,他干预了那个时代的风气,让许多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歪风邪气没有进入这个单位。他是有人格魅力和特殊禀赋的人,待人宽厚,和蔼可亲,目光炯炯,在中国音乐研究所里就是个发出巨量热源的磁场。一个伟大人物能够给整支队伍带来共感,不是靠权威,而是靠信任,靠通过自身言行立刻能够让人领悟的信心。那是每个人都可以正面接受的信息。颜回论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话用在李元庆身上同样恰如其分。人们常说,一个单位到底能不能搞好全在“一把手”,特别是“政治运动”一茬接一茬的岁月。“得一善人,部内苏息;遇一不善,合州劳弊”。李元庆掌控大局,“民仰以安”,使得机构没有像许多单位那样搅成酱缸,陷入无休止的内讧。中国音乐研究所遇到李元庆是一大幸事!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人遇到李元庆也是一大幸事!
话转回来,2008年6月18日,我与孔德墉、刘东升、周昌璧,又聚在一起商量《李元庆纪念文集》的“序”。大家认为,请周巍峙先生写序最合适,不光是因为他的身份压得住阵脚,还因为他是最了解李元庆的人。但考虑到周老90多岁的高龄,实在不好意思张口。19日上午,我和孔德墉、李煞一起拜访周巍峙,谈到《李元庆纪念文集》的编辑进度,周巍峙立刻兴奋地回忆起与李元庆一起的故事。我得寸进尺:“您可不可以写点东西?”没想到,周先生竟然一口答应。
周巍峙的序言,是我做了数十年编辑最难忘的文字。它给人的不是震撼而是心酸,不长的文字远远超出应该说的。尤其谈到李元庆受委屈的那件事。“男儿有泪不轻弹”,谁想到这位在众人面前清爽乐观、半辈子致力于传统音乐资料收集的领导者,竟然在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时,找到老朋友大哭一场。这则真实的故事恍如鞭笞一段被诅咒的时光。周巍峙序言中那些好像是对几十年前的老朋友诉衷肠的话,仍然像是对今人发问。个体与集体之间没有对视权利的岁月,一旦某人“以组织名义”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就会产生令人窒息的可怕后果。李元庆之死归根究底是死于某些人的病态话语与不寒而栗的惊悸。一句话砸在头上,堵到心口,竟然到了置人穷途、夺人健康的程度。然而,历史总是在使一些人功成名就的同时让另一些人名誉扫地,如同让岳飞名扬千古的同时让秦桧遗臭万年一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历史已让明枪暗钺的讥讽闭嘴了。这本纪念文集就是历史评价,就是后人心中的那杆秤!
文集中作者们的认真,使我深感此书的分量,它凝聚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聚集于一个单位中的一群人的磨难和思考。如雪白发覆盖着一群老人沉重的头颅,其中积沉着许多沉重记忆。作者们如数家珍地追述着与李元庆一起走过的道路,也梳理着自己生命史中的一段温暖与纯真。无须说,这是本书呈现的第一共同主题。
《李元庆纪念文集》出版时,照例开了个会。2010 年3月27日,老人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主持会议,副院长刘茜、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张子康前来致贺,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孔德墉、刘东升、李凌子(李元庆女儿)、夏铭珠(儿媳)、文彦、何芸、范慧勤、周沉、周昌璧、张淑贞、简其华、王秋萍、李文如、乔建中、伍国栋、居其宏、冯继轩、蔡良玉、万昭、秦序、王子初、金经言、项阳、李岩、李玫、吴凡、齐琨、林晨、陈燕婷、王英瑞、孙晨惠、李洪峰、张春香、吉盈颖、都本玲、张婷等出席了会议。外单位的客人有:陈自明、王震亚、汪毓和、毛继增、俞宜姿、金湘、于庆新等。责任编辑王红和两位编辑徐明哲、李煞也在场。
北京和中国音乐研究所是上述人员工作过的地方,现在大部分人也还住在城市周围,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见面了,但只要聚在一起,就有欢声笑语。
一个人不可能被所有人记住,但同处一个单位而相互联系的一群人却会永远记住曾经处于集体归属感中心的核心人物。李元庆被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人同心欣仰,但对于包括如我在内的下一代人来说却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应该从前人的记忆中拼接起一位在艰难时局中摸不清方向只好以凭着一颗良心和负责心把握住了正确方向而且开天辟地、英姿勃发的领导者形象。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办公室的钢琴上,我一直摆放着杨荫浏、李元庆、缪天瑞、黄翔鹏的“标准照”。岁月风霜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但他们都定格在最令人敬仰的那一刻。李元庆看上去永远是眉清目秀,风神潇洒,这个太过英俊的“美男子”形象常常令人想到那个诞生了诸多伟人而且个个伟岸的时代,真的是英雄辈出而且人人得天惠风。我们对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般学术地位的人永怀感恩,因为,他用自己的双肩荷载了那个时代的沉重却让同事们轻松。
责任编辑/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