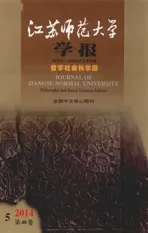论20世纪欧洲哲学思维模式的转化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2014-04-17简圣宇
简圣宇
(广西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广西南宁 530022)
论20世纪欧洲哲学思维模式的转化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简圣宇
(广西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广西南宁 530022)
主体性;主体间性;交互;存在论
自胡塞尔开启主体间性思想探索之门以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对主体间性思想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因为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主体性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其总是倾向于人为地构造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中心,并意识到主体意识无法在没有参照系的孤立状态中独自形成,必须在自我主体与他人主体的互联互动过程中动态形成,即,主体的形成所仰赖的,恰恰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为了深入理解20世纪欧洲哲学思维模式的这一历史性转化,必须充分重视胡塞尔及其后的哲学家对主体间性的研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体性哲学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显,笔者在《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形成、演变及其困境》一文中已经对此展开过分析[1]。从笛卡尔以“我思”为起点构思和阐释其主体性哲学开始,欧洲的主体性哲学便开始了其形成、演变以及遭遇困境的进程。在主体性哲学演变过程中,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其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始终无法摆脱“唯我论”的阴影,即过分强调自我的主体性,这种对“自我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实际上是将单个存在的自我主体放置在原来“上帝”的地位上,所以,虽然欧洲的现代主体性哲学是以质疑中世纪以来的经院哲学那种贬低人性而推崇“神性”(或可称为神的“无限主体性”,或者“超主体性”)的弊病为开端的,但最终却使学者们发觉,其实主体性哲学只是将过去神学中那个主宰一切的被称为“神”的主体,置换为“唯我论”中的“自我主体”。表面上,上帝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但实际上,真正的人性复苏却远未完成[2]。
主体一词来源于拉丁语“subjectu m”,意为“基础”、“基质”,即其是一种作为依据和基质的中心存在。于是相应的,主体性思维模式力图构建的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独白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个话语中心,除此之外的所有次级话语都被作为“他者”而边缘化。这种等级秩序将自我主体抬高到之前神学哲学中的“上帝”的位置之后,之外的其他主体和自然界就被视为异己的“他者”而遭排斥。由于认为自身是全知全能和不证自明的(比如“我思”不容置疑的绝对合法性),所以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愿再去跟其他异质主体进行对话和自我反思。其他主体发出的声音在这个等级秩序中被排在次级的位置上。而一旦成为次级话语,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中心话语的附庸。这些“次级话语”对于中心话语构建的意识形态,只能全盘接受,至少仅能消极认可。一旦次级话语试图以自己的独立意志参与话语的建构,拒绝仅仅作为中心话语的消极回声,就会被高高在上的自我主体视作异质话语而加以贬低、排斥乃至消灭。
《国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由于不尊重主体间的差异,缺乏来自其他主体的异质话语的挑战,单一的主体性将日渐丧失在思想撞击中获得新发展的机会,走向僵化孤立、偏狭自大的死胡同。当代各个哲学、美学学派所警惕和反对的所谓各种“中心主义”,如生态美学所反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所反对的西方中心主义、女性主义所反对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等观念,都是狭隘的主体性哲学思维模式演化的必然产物。
过度膨胀的自我主体,有着沉沦于封闭独白的必然趋势。之前神学哲学那种反对对话,强调自身全知全能的历史局限性不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在现代主体性哲学中变本加厉。于是,如何既破除主体性哲学思维模式的桎梏,又不至于重蹈客体性哲学思维模式的覆辙,就成为学者们认真思索的问题。主体间性的思维模式,正是学者们在进退维谷时,射进幽暗深谷的一道希望的曙光。
一、单子的共同体: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
胡塞尔虽然是主体间性思想的奠基者,但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学说正在开启迈向主体间性的时代大门。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此:胡塞尔是在试图建构更加纯粹、理性的主体性时,逐渐意识到主体性的缺陷而走向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的。
这也暗示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微妙关系:主体间性作为主体性的救赎,为主体更加全面、自由和健康地展现本质力量创造了平台,避免了只有一个单一主体在独白而其他主体则被客体化的危险。
笛卡尔的“我思”命题对胡塞尔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胡塞尔接受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维,其许多核心观点都与笛卡尔有着密切的关联。面对欧洲哲学的危机,胡塞尔也力图为哲学寻找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点,他赞同并发展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创建了现象学“本质还原的方法”。1911年,胡塞尔在德国哲学杂志《逻格斯》上发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认为,20世纪欧洲精神文化的危机,就在于缺少统一的目标,不再追求无限的理性,因而哲学要负担起自己作为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的既往重任,指引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历史目的在于成为“所有科学中最高的和最严格的科学”,代表“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认识之不懈追求(以及与此不可分割的是对纯粹而绝对的评价与意愿之不懈追求)”,但哲学还没有能力将自身建成一门真实的科学,因为“还缺乏那些在概念上得到明确界定、在意义方面得到完全澄清的问题、方法和理论”[3]。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对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基础、方法和整个思维态度进行批判,在严格科学的意义上对哲学进行彻底重构。哲学若要成为严密、普遍的科学,就需要设法进入自身的对象领域。胡塞尔认为,其途径便是“中止判断”(Epoché),或曰“悬置”,以及“加括号”(Einkla mmerung),把自然的思维态度乃至认识对象都暂时悬搁起来,中止逻辑判断。在对待客体的独立自在性问题上,应当存而不论,即“存在的悬置”;在对待历史所给予的观念和思想的可靠性问题上,也应当存而不论,即“历史的悬置”,经过这番悬置之后,才可以用“纯粹意识”直接面对事实本身,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本质还原的方法”。在胡塞尔晚年,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里依然回响着这种理念,他认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了其对生活的意义,哲学和科学应该揭示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4]。
可见,在认识论领域追求绝对可靠的基点的理性主义思维,贯穿胡塞尔的学术生涯。在《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一书里,他提出“凡是知识都是存在者(Seinde)的知识”[5],也就意味着,应当批判实证主义那种“人屈从于外在世界”的客体化倾向,而去确立人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不过,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是建构在心理学意义的经验主体之上的,在笛卡尔那里,这些“沉思”是在用自己的心灵的“我”(Ich)代替自我(ego),以心理学的内在性代替自我学的内在性,以心理学上的内在知觉代替自我学的自身知觉[6]。
为此,需要进行现象学的改造,摒弃心理学残余,将一切有关外在事物存在的经验排除掉,而在内在的意识范围内把握自我,把“我”从经验主体改造为超验的“纯粹自我”。作为诸习性之基底的自我,其本身是“自身自在地存在于连续的自明性之中的,因而是在自身中连续地把自己构造为存在着的”[7]。主体总是处在不断地自我构造过程中,但又以“习性”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
单个主体在充分具体化中就是一个莱布尼茨式的单子,“我对我自己存在着,并不断地由作为‘自我自身’的经验明见性而被给予我”[8]。认识论关涉两种关系,一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认识主体与其他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主体只是单子,那么各个单一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何在?假若世界上只有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单子主体,那么他们是如何能够发展出自我意识的呢?须知,主体意识无法在没有参照系的孤立状态中独自形成,必须在自我主体与他人主体的互联互动过程中动态形成,即,主体的形成所仰赖的,恰恰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
于是,在将自己的理论进行细化的过程中,胡塞尔意识到自己正在陷入“唯我论的自我学”,在“第五沉思”中,他提出:“当我这个沉思着的自我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而把自己还原为我自己的绝对先验的自我时,我是否会成为一个独存的我(solus ipse)。而当我以现象学的名义进行一种前后一贯的自我解释时,我是否仍然是这个独存的我?因而,一门宣称要解决客观存在问题而又要作为哲学表现出来的现象学,是否已经烙上了先验唯我论的痕迹?”[9]
各个主体之间不能像莱布尼茨式的单子一样相互疏离、孤立,以单一主体的状态存在,而只能是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形成自我的共同体,这便是胡塞尔在认识论领域内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他指出:“无论如何,在我之内,在我的先验地还原了的纯粹的意识生活领域之内,我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连同他人在内,按照经验的意义,可以说,并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O bjekten)的世界。然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验,有他自己的显现及其统一体,有他自己的世界现象,同时,这个被经验到的世界自身也是相对于一切经验着的主体及其世界现象而言的。”[10]胡塞尔把这种单子共同体称之为“先验的交互主体性”。
在交互主体那个共同的意向性世界中,他人由于具有已定位的被给予性方式而成为一个“中心项”。“在意向性中,他人的存在就‘成了’为我的存在,并且按照它的合法内容,它在其充实的内容中就得到了解释”[11]。在主体间性的领域内,他人不再是作为他者的他人,而是另外一个自我(“他我”),一个与我一样的主体。自我主体,与“他我”通过意向性的综合作用,在纯粹自我的范围内理解和体会彼此的存在,在“我的现实和可能的经验”里的统一体,各个主体的存在是“共此在”(Mit-da)。此时,自我主体之外的主体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个“陌生主体”(Frem dsubjekten),相反,“他人就是我本身的一种映现(Spiegelung)”[12]。于是,本来不可通达的东西便得到了共现。
在主体间性领域,各个主体之间交互存在着,他人主体与“我”是对等的,都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再是“非我”的外在关系,而属“我”的内在关系。“我”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他人中的一个人,正如他人的躯体存在于“我”的感知领域,“我”的躯体也存在于他人的感知领域,人可以统觉地成为他人,理解他人的同时而又更加深入地切入到他的本己性视域中去,因而,共同的视域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开放性视域。
理性,是主体性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立场,使他从二元对立的思维出发,力图将人与自然区隔开来,把主体的存在割裂为对立的“经验性的存在”和“精神性的存在”,然后赋予“精神性的存在”以优越性,认为“理性”高于一切具体存在。此外,这种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还把意义丰富的“理性”简单化了,把自然科学的理性当成了“理性”的全部,而这种价值理性缺席的简单化“理性”是危险的,它将逐渐滑向狭隘的“工具理性”:如果以这种异化了的、非人格的“工具理性”对待主体,那么人的存在就会被当成物理事实来看待,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那种独具韵味、不可替代、丰富多彩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被忽略掉,人的主体性在被高扬的同时也在被片面化、狭隘化,并且最终被异化,另外,还在主客关系上片面强调主客对立和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撕裂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关系。
胡塞尔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仍然沿袭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本是站在主体性思维的角度思考意向性结构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却逐渐意识到自己所依据的思维模式自身就存在着自我孤立的悖论,即,主体性思维所依据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演化过程中无论是从何种维度考量,都必然导致诸主体之间的疏离乃至分裂。于是,他一方面试图克服欧洲的精神文化危机,另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把感性经验从主体存在中“括号”出去,还从认识论思维出发,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来对待。这最终导致其理论体系出现了内在矛盾,而这种内在矛盾又为欧洲哲学日后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胡塞尔本欲从笛卡尔的主体性“我思”出发,去追寻更为纯粹的主体性的思想,但在最后却开创了主体间性的思想;本欲高扬能够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普遍理性,但其最终却深切关注具有开放性、原生性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使其思维开始逸出冰冷机械的认识论局限,朝向具有人文关怀的存在论。所以,汪堂家先生不禁感叹:“笛卡尔和胡塞尔一头一尾界划了主体主义的传统。”[13]
二、走向主体间性: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思考
自胡塞尔开创了主体间性的理论道路之后,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也以各自的研究视角,对主体间性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而当代和当下的哲学、美学研究,也逐渐突破“主体性”思维的局限,而迈向“主体间性”的广阔视域。
海德格尔认为,欧洲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千年之弊:遗忘了“存在的意义”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为此,他指出自己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意义的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14]。
为了回应胡塞尔理论的局限性,海德格尔以“此在”(Dasein)作为自己追问“存在”意义的出发点,他认为“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和“存在论上”就具有优先地位,人的存在是主动的、主体性的,而非无意识的、客体性的。“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来领会自己本身……生存问题总是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但是,“此在”在此并不是独自存在的,“此在”在本质上是“存在世界之中”[15],即与世界上的他人“共在”,但是海德格尔也进一步认识到,现实领域的主体间性是难以充分实现的,日常的“此之在”,往往是“此在的沉沦”[16]。
为了探究实现主体间性的本真状态,海德格尔在其美学思索的后期,更是直接阐述了人通过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来“诗意地栖居”、“天地人神”四元世界和谐共在的思想:“命名的呼唤召唤物进入这种到达。——那被命名因此被呼唤之物,自身聚集为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这四者原初统一于相互存在之中,在四元之中。——天空、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的统一的四元,居于物的物化之中,我们称之为世界”[17]。处于与社会世界中的他人、与自然世界中的大地苍穹、与艺术世界中的艺术作品等,在“意义世界”内彼此相遇、共同存在的,这种状态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状态,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状态。海德格尔的“四元说”,实际上标识着他对胡塞尔不彻底的主体间性的反思,希望唯我独尊的主体性在哲学的思维结构中退场。
伽达默尔则在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基础上,把注重“主体-客体”关系的传统解释学改造为强调“主体-主体”关系的现代解释学,他提出,理解不是将文本的意义进行复原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交流而生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即是主体与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两者共同形成一个“自内而运动的大视域,这个大视域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包容我们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解释者带着自己的特定“视域”进入解释活动,将自己置入文本的历史视域之中,“通过我们把自己置入他人的处境中,他人的质性,亦即他人的不可消解性才被意识到”,文本的视域与理解者的视域两者融合为一。当两者融合为一时,就能在生产性的理解中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于是,“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18]。
由此可见,在伽达默尔那里,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认识论的主客认知关系上升到存在论的主体间的平等理解的存在关系,这样,作为主体的人对文本就不是单向度的认识和解释,而是与之进行交流、沟通,于是“视域融合”成为主体之间而非主客之间的融合,两者此时超越了自身原先视域的局限,共同创造出全新的、具有更加广阔视域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接下来哈贝马斯在批判继承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构想后,将其阐述为交互主体的世界。他在海德格尔等人的语言学转向的带动下,建立了“普遍语用学”理论,提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把人的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试图通过交往行动来化解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人性的异化;在保证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自身个性的同时,以平等的对话来达成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包容他人,不是把他人融入自身,更不是排斥他人。没有差别地尊重每个人,也应该是尊重另一个国家的人或是有自身差异的不同民族的人。他还由此提出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交往行为来建立社会规则:“同社会劳动的结构相比较,角色行为的结构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交往行为的规则,即主体相互之间公认的和习俗上得到保障的行为规范,不能归结为工具行为或者战略行为规则。”[19]
为此,他为自己的话语行为理论提出了四大有效性要求,包括可领会性、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这样就可以克服主体性哲学的唯我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主体间性:“通过揭示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和囿于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范围之内的‘自我’的连锁关系而克服了主体哲学”[20]。他的这种理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现实领域,主体间性的实现是不充分的,而且他在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同时,遗忘了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关系。
此外,德国宗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也从自己信仰主义的角度丰富了主体间性美学思想。他提倡以存在论的主体间性关系来替代认识论的主体性关系,即以“我-你”(I-T hou)关系来替代“我-它”(I-It)关系;认为“正如每一关系不能离弃‘我’,关系必须伫立在‘我’与‘你’之间。应当根除弃绝的非是‘我’,而是惟我独尊之虚妄本能。一旦‘你’转成‘它’,关系之普照性即威逼世界,关系之惟一性即排斥外有”。于是,“你”不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他者,而是与“我”亲密无间、相互交流、彼此信赖的另外一个主体。“我”只有与“你”相遇,才能真正成为自身,才能获得广阔的视界。“人不是依赖于其自身的关系而只是靠着与另一个自我的关系才变得健全”,“人观照与他相遇者,相遇者向观照者敞亮其存在”[21]。
这种主体间性的“我-你”关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之间。在马丁·布伯看来,“我所言及的正是活生生的人,你与我,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世界;这里没有所谓孑然独存之自在的‘我’,自在的在”[22]。于是,从布伯开始,对主体间性的阐释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当代主体间性思想的理论架构日渐明朗化,而主体间性思想也日渐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思维依据。
三、在对话中建构主体间性:巴赫金设想的开放性结构
在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是一位重要却又常常被遗忘的人物。他在文艺学上的成就如此卓著,以至于他“复调”理论的光芒将他在主体间性哲学上的成绩给掩盖了。这有点类似于我国的沈从文,人们多知道他是小说家,却不了解他在服饰艺术研究方面的丰厚成就。
巴赫金没有打算以严整、宏大的体式来建构关于主体间性的理论体系,而是提供了建设思路,他设想了一个开放性结构,不是一次性将主体间性理论阐述得完满、无懈,而是在这个结构中促进平等的交流,力图在诸主体的对话中逐步建构主体间性——只要框架足够坚实,那么其中具体的阐释空间是灵活多元的,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
海德格尔曾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里提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之独在是一种残缺的样式[23]。海德格尔强调了诸主体存在的主体间性内涵,凸显出诸主体共同此在在世的不可分离。
而巴赫金在其早期论著《论行为哲学》中,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存在即事件”,俄语为“бытие-событие”。其意在强调“存在”(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是具有能动性、参与性、生成性的人的行为世界、事件世界,人必须以作为存在的整体去亲身参与和加以体验,“唯有这样的行为才充分而不息地存在着、生成着,是事件即存在的真正活生生的参与者,因为行为就处于这种实现着的存在之中,处于这一存在的唯一的整体之中”[24]。在俄语中,“事件”(событие)一词由“共同”(со-)和“存在”(бытие)构成,虽然“事件”(событие)不是“同在”(со-бытие),但巴赫金在其论著里往往是从“同在”(со-бытие)的层面来谈论“事件”(событие)。毕竟,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各种存在因素的交汇下产生和发展的。可见,“存在即共同存在”的命题,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主体不是作为单子主体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主体间性的关系之内,自我主体与他人主体共同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巴赫金后来在《长远时间》里还拓展关于“事件”(событие)的阐述,将世界视为在诸主体间积极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共同存在”而非“现成的存在”[25]。所以,“事件”这个概念在巴赫金的主体间性理论里,还容纳着诸主体在互联互动中保持未完成、不断发展状态的内涵。
单个主体的存在,天然包含着不可消除的缺陷,若想尽可能达到存在的完整性,就需要诸主体的共同存在,因为主体间的交流沟通,可以构建文化共同体,从而延续过去、面对当下和开创未来。为此,巴赫金提出了“外位性”(Вненаходимость)的概念。他提出:“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他人无法进入的位置。现在我身处的这唯一之点,是任何他人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时间和唯一空间所没有置身过的。围绕这个唯一之点,以唯一时间和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展开着整个唯一的存在。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远都不可能做。”[26]既然自我主体与他人主体都是唯一的,那么世界作为诸主体的共同存在,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心,而应当是处于平等对话中的多中心状态。其中,诸主体相互之间并不融合,而是一种对话性的协调关系,这应当是探讨哲学基础问题的基本框架。
“外位性”作为巴赫金主体间性理论的重要概念,其所蕴含的广阔意义就在于它肯定了不同的主体之间(包括现实的人际关系和诸文化间的关系等)作为一种异质共存结构的合理性。单个主体总是用于其视界的独一无二性,而既有对他人的视域优势,又天然带有自己的盲点和局限性。同样,由某区域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形成的文化,也会是瑕瑜共存的,而有盲点和局限性的文化也会对生活在该区域、该时代的具体的个人产生影响。
理解,就需要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展开彼此互动,而对话就是为理解而服务的沟通媒介。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独白思维不同,对话思维追求彼此之间平等对话的沟通方式。每个主体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个体世界,并在这个具有局限性和时间性的个体世界里展开自己的存在——我在此,你在彼,不同的主体构成了不同的中心,并且以此构建出自己对于共在世界的印象、思考、判断。当代世界的思想界对哲学思维的思考,其实延续的就是巴赫金的这种思路。只有以外位性的立场来思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异同,才能在敞开和坚守两极之间保持好平衡,从而拥有一个宏阔、开放的视野。
四、小结
主体间性思想发展至今,时光已流转过近一个世纪。而这一个世纪,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期。从局域网,到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我们进入这个全新的时代之后,“交互(inter-)”在社会学领域前所未有地普及,主体间性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狩猎、农耕、工业化等时代,而我们所处的当下,正是一个全新的“交互(inter-)”时代的开始。
主体间性思维并非是简单化地排斥主体性,因为那将违背其初衷,倒退回自我客体化的前主体性蒙昧状态,而是在主体性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扬弃。毕竟,主体间性的建构,需要以一个个具有自由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主体作为基石。主体间性思维所反对的是主体性的独白化:在把自我主体不证自明地设定为存在中心的同时,压制和覆盖其他主体的异质声音。可以说,主体性只有在主体间性思维中才能洗去虚妄的独白属性,得到更加充分的净化和提升;而主体间性则是通过把诸多单个主体性联接成交互主体性,将主体性提升到新的历史和哲理高度。梅洛—庞蒂就曾指出:“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27]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马丁·布伯等,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在社会学、认识论和存在论领域内逐步丰富和发展。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主体性思维模式最核心的局限性:其总是倾向于人为地构造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中心,并意识到主体意识无法在没有参照系的孤立状态中独自形成,它必须在自我主体与他人主体的互联互动过程中动态形成。一言以蔽之,主体的形成所仰赖的基础,恰恰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
没有哪个学派的理论是能够一次性达到完美程度的,作为诸主体的他们各有缺陷和局限性,但正是这些带着片面的深刻的异质理论,一方面能够从自己别具一格的视域出发,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深层潜能,在理论的花圃中展现出“春花秋月,各呈其韵”的态势;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彼此之间的辩驳、对话中,既从对方理论体系中得到借鉴和启发,又成为对方以资参照、反思的思想资源,从而为学界进一步丰富、细化主体间性思想提供新的契机。
[1]简圣宇:《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形成、演变及其困境》,《前沿》,2011年第5期。
[2]杨春时教授依据欧洲主体间性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区分了三个领域,厘清了与此相对应的三种不同的涵义主体间性概念: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一)社会学(包括伦理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其最早在伦理学领域内提出,近现代后则扩展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学领域。像康德、黑格尔直至马克思、哈贝马斯等都在社会学领域涉及到主体间性问题。(二)认识论领域的主体间性是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最早涉及到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但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的,只涉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因此只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三)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是指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由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海德格尔后期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更为彻底的主体间性理论家是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此外,雅斯贝尔斯和马塞尔·马尔丹也提出了与马丁布伯类似的主体间性思想。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即存在论和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从根本上解释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4][6]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101页。
[5]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张廷国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
[7][8][9][10][11][12]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E·施特洛克编,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1、193、122、125、125、149、128页。
[13]汪堂家:《自我的觉悟:论笛卡尔与胡塞尔的自我学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4][15][16][2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6-17、202、146-148页。
[17]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1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
[19]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20]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1][22]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7、231、5、11页。
[24][26]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卷,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1页。
[2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27]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页。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Mode of Europe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From Subjectivity to Intersubjectivity
JIAN Sheng-yu
(General Education Department,Guangxi Arts College,Nanning 530022,China)
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interaction;Ontology
Since Husserl started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study,Heidegger,Habermas and other scholars began to try to enrich and develop the inter subjectivity thought from different angle.Scholars realize clearly the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of subjective thinking model.They tend to construct a solipsistic center deliberately and know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cannot form alone in isolation without reference.After all,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cannot do without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subject and other-subjects.That means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 relies on intersubjectivity instead of subjectivity.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hilosophy thinking mode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we should pursue our studies from Husserl to subsequent philosophers for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ought.
B505
A
2095-5170(2014)05-0086-07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4-10
本文系“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阶段性成果。
简圣宇,男,广西南宁人,广西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