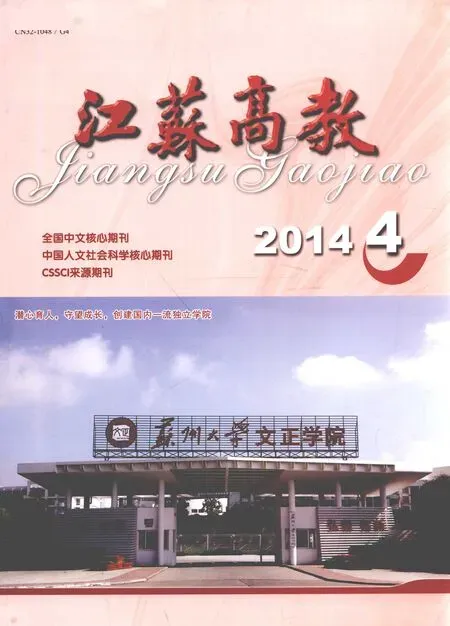论高校二元权力结构下的学生权利救济
2014-04-17邢鸿飞芮令辉
邢鸿飞,芮令辉
(河海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98)
根据关于高校权力的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我国高校实际存在着两种权力,一种是实施如制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活动、开展教学研究的权力,一般被认为是高校学术权力。还有一种是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管理等活动的权力,属于高校行政权力的范畴。
一、二元权力结构下的高校权力与学生权利冲突及其表现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是法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长盛不衰的重要研究对象。到底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抑或是二者的平衡,各种学术观点层出不穷。权力的滥用容易导致腐败、专制,损害个体的权利。权利的滥用也同样会导致对其他主体所享有权利的损害。从这个角度说,权力和权利都需要制度加以规范。
基于当前我国高校中行政权力过于膨胀、学术权力不当侵害学生权利的现实情况,通过对权利的救济来限制、规范权力是一项明智的选择。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生了诸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等一系列学生起诉学校的案件,这些案件生动地体现了高校学生权利与不同的高校权力之间的冲突。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虽然都被视为行政案件,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与学生权利发生冲突的权力是有区别的。同时,虽然这些冲突在高校领域经常出现,但现实中我国并没有完善的解决机制加以应对。下面结合这两起案件,针对二元权力结构下的高校权力与学生权利冲突现象做一分析。
田永起诉北京科技大学源于北京科技大学曾以田永违反学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人员发现后,学校对田永作出了按退学处理的处分。在田永毕业时,学校依据之前对田永的处分以田永已丧失学籍为由拒绝向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派遣手续。该案的法院判决在实践中明确了高校在管理某些事务中所享有的行政主体资格。法院认为,高校虽然不属于行政机关,但是法律法规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在高校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性质的行政法律关系,所以,司法权对此可以进行监督。高校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如《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对学生进行管理,一旦学生违反了这些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分。本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所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处分,是典型的高校行政权力行使的行为。学生如认为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自然可以通过我国现行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来得到救济。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博士学位、不颁发毕业证案,虽然也是由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处理,但是其与田永案存在明显不同之处。此案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基于对刘燕文博士论文的审查,在投票中反对票多于赞成票,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刘燕文不服该决定,将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被告起诉至法院。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高校对于学生有学籍管理的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授权,有权决定是否授予学位。法院认定此类权力是由法律授予的,具有行政权力的属性,司法权可以进行监督、审查。但是在重审以及二审中,法院以刘燕文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起诉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法院判决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个案件所涉及的关于学校行政权力和学校学术权力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据此判决。
在该案中,学校拒绝为刘燕文颁发毕业证、授予博士学位是基于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而做出的行为。准确来说是学校行使学术权力的行为,基于学术权力行使的特殊性,行政权力以及司法权力应当尊重学术权力主体——学科、专业内的专家、学者及所组成的集体对学术的专业问题所作出的判断。
因为,学术研究是研究者们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而进行的研究,研究过程及其研究结论的得出均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对于学科内的专业化问题,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无法直接判断。在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都应当对学术权力保持一定程度的尊让。只要学术权力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司法权和行政权都不能加以干预。只有在学术权力的行使存在程序瑕疵的情况下,司法权和行政权才可以以违反程序正当为由加以干预。因此,当学生权力可能受到学术权力侵犯时,对学生权利是否真正受到学术权力侵害的实质性判断,只能由相应专业的学术团体进行判断,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只能从程序权利的角度对学生权利进行救济。通过这种区别化的救济方式,既可以对学生权利进行救济,也是对高校学术权力的一种尊重,符合高校独立自主进行学术研究的特性,有利于高校的学术发展。
二、高校二元权力侵害学生权利的救济方式
(一)二元化救济方式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当高校学生权利受到来自于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主体之外的普通意义上的法律主体侵害时,可以通过民事、刑事等一般性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时,高校学生所享有的维权手段与普通法律关系主体的维权手段无异。当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侵犯学生权利时,其具体救济制度的设定应考虑上述两种侵权行为的不同性质,赋予学生区别化的救济方式。所谓区别化救济方式,就是当高校二元权力,即高校行政权力、高校学术权力与学生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根据高校行政权力、高校学术权力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构建不同的学生权利救济模式,通过不同途径来化解学生权利与高校二元权力之间的冲突。构建区别化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方式,旨在兼顾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个体权利的保护,正确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从而最有效地解决高校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
(二)行政权力的运行与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方式
由于高校行政权力具有公权力的属性,对其作用的对象产生直接的影响,“故须严格遵守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此项行政的发动与行使,除不得与上位阶的规范相抵触外,尤须有明确法律授权基础,始得为之,同时亦须遵循程序法上的相关法规,不得任意为之”[1]。但现实情况下我国高校行政领域却不尽如此,行政权力的膨胀与越位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学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行政主导的管理体制,权力分配不对称,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弱化,行政权力总是处于有利地位,致使矛盾难以解决。”[2]这不仅需要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也需要对高校行政权力侵害的权利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济。法律对权利进行保护和救济是制约公权力的有效方式。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利越多,就越能有助于公民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越能构成对公权力行使的有效制约,从而促进选择法律成为国家和民众共有的生活方式[3]。
基于高校行政权力的法律属性,可以构建一个包括行政权和司法权都能参与的权利救济模式。高校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法律的规制,但不能因此一味要求限制高校行政权力的发展。高校去行政化并不是将行政权力从高校中剥离,而是在不违反上位阶的法律规范的情形下,规范高校行政权力的行使,充分发挥行政权力在高校治理中的优势,以促进高校的发展。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我国高校管理实践中,存在着行政申诉制度,该制度对学生申诉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是学生权利救济最为重要的行政救济方式。尽管在当前权力机关公信力受到置疑和指责的大背景下,学生对于该制度并不信任,但是为有效阻止学生对该救济方式刻意回避的非正常判断,让学校的行政管理部门穷尽行政权,可以考虑通过构建行政申诉前置模式加以解决。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行政申诉制度,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规定行政申诉的强制性前置,将学生因受高校行政权力侵犯而产生的行政纠纷交由高校先行救济。这既是出于我国现实法治环境的考虑,也契合充分发挥行政权力作用的法律理念。司法权应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宜过早干预高校行政纠纷的解决。当学生对于法定前置的高校行政申诉程序作出的处理结果仍然不服时,可以根据规定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再次申诉;只有对再次申诉的处理结果不服时,方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对争议事实可以进行实质性判断,有权依据法律法规对高校行政权力行使的实体和程序性问题进行全面审理。
(三)学术权力的运行与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模式
学术权力有其专业性,学科知识的深度和复杂程度不适宜由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进行判断。虽然高校中部分行政人员同时也是学科内的专家甚至权威,但是该类人员对学科专业问题进行判断时应基于其学术人员的身份,与其行政职务无涉。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认为,“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高校以培养专业人才、进行学术研究为其存在目的,学术自由是高校的生命。尊重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进而尊重高校学术权力的行使是发展现代化高等教育的题中之意。高校学术主体是高校追求高深学问、研究高深知识的基本依靠,给予高校学术主体足够的自治权限和自由,是推动高校不断进步进而通过知识的转化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必由之路。但是,历史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4]。诚然,“在存在着自主性权力领域的地方,掌权者可能会愿意服从一些具有某种法律性质的自发约束”[5],但是仅仅通过权力主体的“自发约束”并不能使学生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构建一套制度化的救济模式不仅可以突破这一权力规律,而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学术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可以更有效地确保学术权力的运行。对于高校学术权力侵犯学生权利,应秉持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理念来对学生权利进行救济。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缺乏当学生权利受到学术权力侵犯时的救济途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只规定受理受到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学生申诉,并没有涉及学术事项的救济方式。司法机关在学生面临学术权力不当侵犯时也因为没有明确的依据而陷于尴尬境地,这一尴尬局面突出地体现在了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一案中。为此,我国必须根据学术权力的特性构建相应的权利救济模式,以兼顾学生权利的救济和学术权力的行使。
国家可以通过完善《高等教育法》或者至少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明确高校学术权力侵犯学生权利时的救济模式。首先,高校应当建立一个公正独立的学术纠纷处理机构。该机构的成员应当由学科专业内的权威专家组成,出于公正的考量,该机构的成员可以考虑聘请本学科、专业内的外校权威专家。出于程序公正的考量,本校与该学术纠纷有涉的专家学者应当予以回避。学术纠纷处理机构的成员应当根据自身的学术水平对有关学术问题作出独立的判断,不受其他外来因素的干扰。鉴于权威专家的意见可能出现相左的情况,从相对公正的角度考虑,可以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当对于学术问题判断结果出现较大争议的情况时,可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由专家们讨论之后,甚至可以听取外国同行权威专家的意见后再作出处理结论。
其次,当学生认为其受到学术权力侵犯时,应当先向学术纠纷处理机构申请救济,即高校学术纠纷处理机构的处理是学生获得救济的必经阶段,是学生要求进行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而且,当针对学生的处分涉及学术权力行使的内容时,学生仅能以程序瑕疵为由向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寻求救济,至于涉及学术内容、专业性的判断,只能交由独立的学术纠纷处理委员会进行处理。学术纠纷处理机构的判断结果具有终局性,除非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学生不得对学术纠纷处理机构的处理结果再次申请行政救济或者司法审查。
再次,当高校对学生的处分依据同时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行使两种情形时,学生不满该处分申请行政救济的,高校应当将此申请交由学术纠纷处理机构先行处理,然后依据学术纠纷处理机构做出的处理结果维持或者变更处分,在确保涉及学术争议的内容获得解决后,学生方可申请行政救济乃至司法救济来解决高校行政权力行使所产生的纠纷。
最后,学术纠纷处理机构处理纠纷的所有过程应当公开。当然,这是一种事后公开,必须将学术纠纷处理机构处理纠纷的依据、流程、结果等内容,通过纸质或网络的形式予以公布。
[1] 翁岳生.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4.
[2] 袁祖望.高校行政权力的弱化与强化[J].江苏高教,2004,(3).
[3] 徐爽.以权利制约权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基本权利立法实践的发展[J].政法论坛,2011,(6).
[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5.
[5]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