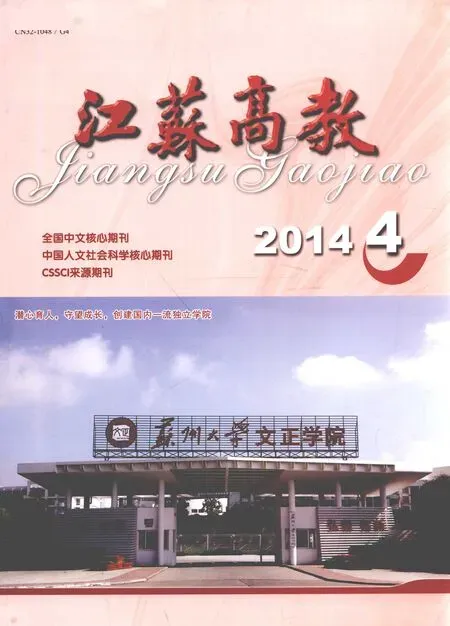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路在何方
2014-04-17潘林珍王燕妮
潘林珍,王燕妮
(1.泰州学院纪委,江苏泰州225300;2.南京邮电大学高教研究所,南京210003)
创新人才培养已成为当前我国大学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倡导培养创新人才以来,大学教育者从未停止过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究和实践。例如,从招生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到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大学都进行了革新,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或工程”;同时重视学校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校园文化环境对培养创新人才的影响。但我们不可忽视对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对创新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和既有制度,归根结底是传统社会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社会阶层结构制约了我国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
教育回报的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当前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也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和制度影响。新中国建立后,逐渐形成了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行政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社会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
这样的社会结构使大学被置于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大学逐渐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这种丧失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功能性的。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鲜明的“中央集权”属性。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直接抑制了大学的创新能力。正如美国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指令下,我国大学过高估计了提高技术才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品质的培养,甚至一度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原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现。但现在的情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更为滞后。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1]。这种现象在日益复杂的大学组织中尤为明显。在大学外部,大学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几乎都来自于政府。行政部门通过管干部、管人才、管工程项目和经费、管科研、管学科和专业、管课程设置、管教材编写等对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使近年来政府对高校的控制不松反紧,更加全面和深入,呈现全能主义的趋势。在大学内部,其资源也主要根据行政级别来配置。不同的行政级别掌握着不同的权力和资源,级别越高,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就越多。大学内外部的各种权力不断干预着甚至是侵犯着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并最终使得教学和科研不得不成为行政权力和利益的奴隶。哈耶克认为,“为一定政府或专门化机构所控制的,带有一定指定性或针对性目标的研究,由于失去了选择研究问题的自由,难以产生新知识的主要源泉,而在为拓展知识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基础研究中通常并无固定的论题或题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通常都是由于否弃传统的学科分工而带来的”。因此,“在知识的普遍进步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且不可预见的重要成就,一般来讲并不产生于对具体目标的追求之中,而是产生于对各种机会——亦即每个个人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天赋能力、特定环境和社会交际等因素之间的偶然性组合所创造的机会——的把握和运用之中”[2]。也难怪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天天喊“培养创新人才”,但创新人才培养效果不是很理想。而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很少提什么“提高学生创新素质”,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创新、创业人才,还出了不少诺贝尔奖得主。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问题所在:这些名校的校园文化是崇尚真理、追求卓越,谁拥有真理谁就会得到尊敬,谁的创新理念好,谁就在学术和教育上有发言权。
如果说,社会体制模式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更多是宏观的、外发的影响,那么社会阶层结构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则是微观的、内生的。虽然改革开放使得社会阶层结构从“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变为“国家—社会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但正如孙立平所言,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3]。
首先,中产阶级的缺失使我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缺乏相应的阶级基础。马斯洛认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种需要都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它们构成不同的等级或水平,并成为激励和指引个体行为的力量。并且需要的层次越低,它的力量越强,潜力越大,在高级需要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中产阶级是指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因此,他们既有创新的条件又有创新的动力。对传记资料的统计分析表明,创新人才更可能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子女也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的主要来源。然而目前我国中下收入的人口占绝大多数。年轻人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是当今社会不可否认的事实。当青年人生理和安全等低层次需求还未充分满足,在为谋生而奔波忙碌的时候,自我实现、创新性等需求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样,大学创新教育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最终只能被忽视甚至不自觉地被抵制。
其次,中产阶级的缺失使得我国现阶段社会呈两极分化趋势,社会阶层结构仍属于金字塔形。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具有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典型特征。一是金字塔的框架等级森严、上下分明。于是“畏上”、“敬上”、“崇上”便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意识和行为模式。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结构上层(即教师)产生敬畏之心,从而使学生与教师形成服从与操控的互动。学生们只会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他们不需要产生和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二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强调的是“大一统”,即统一于“金字塔”的顶点。“大一统”强调的是整齐划一,而排斥个性差异。大学作为社会单元,也自然仿效这一模式,不仅自身依靠金字塔组织结构加以运行,连培养的人才也强调“统一规格”。然而创新与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充分发挥个性,才能培养创新能力。只有使每个学生都先成为自主的、独立的人,才有可能形成创新能力,创造出成果。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说,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不只是大学本身的问题,而更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作为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改变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政府首先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要缩小社会分化,积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培育发达的中产阶层,造成在社会分层阶梯上,最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在数量上都减至绝对的少数,中等阶层占有绝对优势的格局;另一方面尊重大学的独立法人和办学主体地位,有限干预大学发展,运用法律、政策、监督和评价等手段对大学进行宏观管理,使大学真正成为按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法人单位。
[1] 孙立平.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J].瞭望,2009,(36).
[2]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177.
[3]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