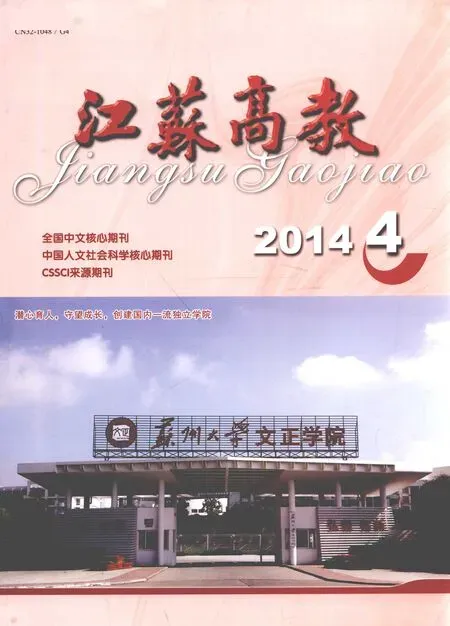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关系
2014-04-17方泽强
方泽强
(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昆明650092)
有一段时期,教育学与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被描述为“暧昧的关系”[1],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甚明确。同样,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似乎更不清晰。一些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学一直在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发展自身,是其它学科的“殖民地”和“跑马场”。与此相反,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开放性是高等教育学科重要而鲜明的学科特征”[2]。真相究竟如何?难道高等教育学除了开放地引进应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外,就没有反哺其它学科并做出贡献吗?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高等教育学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关系。
一、高等教育学与哲学的关系
1.哲学对高等教育学的哺育:“人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哲学是关于人、自然、社会、世界等方面“最一般”的学科。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社会的本质是什么、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都在哲学家的思考范围内。对于哲学,狄尔泰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的繁荣和宗旨都是要使教育学成为广义上的关于人的形成的学说。”[3]从“哲学的繁荣和宗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一门以人为核心和根本的学科。如此,哲学就为高等教育学的存在奠定了“人学”基础。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高等教育学是研究如何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学科,首先必须对人以及人的本质形成基本“洞见”,而哲学恰恰能为高等教育学提供“人”方面的知识。在哲学史上,“人”的形象问题先后经历了中世纪的“宗教人”,到16世纪的“自然人”,再到18世纪的“理性人”、19世纪的“社会人”以及20世纪初“文化人”的变动。这些变动引发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从培养牧师转向培养哲学王,又转向培养科学家、人文学者等。实践已证明:哲学中关于“人”的知识一旦变化,高等教育学关于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知识就需要调整。
进一步地,哲学不只向高等教育学提供了人才培养的“现在目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人才培养的“将来目标”,“将来目标”成为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中“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方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人的问题,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只是出自“本能”或“社会的风俗习惯”,处于自然境界;做事出于功利要求,处于功利境界;做事出于服务社会,处于道德境界;做事符合整个宇宙的法则和人类的利益,就达到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产物。”[4]冯先生的人生境界观为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高等教育的育人活动提供了具体目标指向。在当代,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正在走向“普及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因此,高等教育在培养人的方面将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应努力将受教育对象培养成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如果由大学培养的人才都只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那么,高等教育就没有履行好职责。所以,高等教育学应把哲学中关于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追求,并对如何实现此目标规定具体内容和活动。就此而言,哲学为高等教育学如何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知识养料。
2.高等教育学对哲学的反哺:“实践”并“拓展”哲学命题。从知识性质看,哲学是一门形而上的学科,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形而下的学科。形而上的学科意味着该学科的知识抽象性较高,一定程度上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形而下的学科意味着该学科的知识具体性较高,一定程度上充满着现实主义色彩。因而,哲学中关于人的发展的种种预设目标能否实现都需要高等教育实践的检验以及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归纳,这种“检验”和“归纳”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学对哲学的反哺。例如,哲学史上曾有关于“理性人”的假设,这种人性假设一度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指导理论;然而实践中发现,理性尽管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人除了理性之外,还具有感性、冲动等属性,完整的人应是集理性、感性于一身的人,而不能因为对理性的追求而忽略甚至否认其它属性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大学在培养人的过程中不只重视对受教育对象理性方面的培养,而且兼顾其它属性的培养,从而深化了关于人的认识。由此可见,哲学中关于人的“形而上”的知识是否科学正确,有赖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检验。通过检验和归纳,高等教育学形成了关于“人”的完整知识,修正哲学中“理性人”的理论假设。
此外,哲学虽然提出了关于人的发展目标预设,但目标如何具体化、如何实施以及实施步骤、实现路径应是怎样等内容需要高等教育学进行创造。这种创造就体现了高等教育学对哲学的反哺。举例来说,马克思哲学的“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如何落实到高等教育实践中?这需要高等教育学对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发展目标进行分解、细化,提出具体化的内容以及可操作的方法、路径,形成可行性的行动方案并落实于实践。这种具体化的内容和行动方案就是高等教育学“自我创造”的知识,而非由哲学自动生成。显然,这种知识是对哲学理论的具体化拓展,为哲学注入了新的知识养料。
二、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1.心理学对高等教育学的知识输出:“人”内心发展的知识。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理现象,探寻心理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高等教育学则是关于高级专门人才如何教育和培养的学科。所谓教育,简约地讲,就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相比之下,“内得”比“外得”更重要。因为在本质上,教育(人才培养)就是个人将“外得”内化于身心而“有所得”的过程,高等教育层次上的人才培养也是如此。“内化”是一种心理活动,存在着一般规律。如果人们能够掌握这种心理规律,依规律来指导内化的过程和各个环节,那么人才培养过程就具有科学性。就此而言,心理学能为高等教育学提供人的内心生长、发展等方面的知识,促使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更加科学有效。在历史上,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之所以被视为“科学教育学”,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借用心理学的知识来构筑教育学的理论,从而使教育学具有科学性。
这里有必要指出,不能盲目认同个别研究者提出的“用心理学取代高等教育学”的观点。首先,心理学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人的内心活动方面的知识,人的心理活动只是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中涉及到的一部分内容而非全部,而高级人才的培养还涉及到生理、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心理学无法取代高等教育学。其次,心理学无法对高等教育事实的原因和结果作出充分解释,而这一点是开展教育活动最关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心理学对教育领域现象的研究,即使是学习心理的实验研究,不过是对心理或教育心理事实进行实验研究,它的成果对于整个教育实践活动来说,也还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知识。换句话说,这种研究并没有承担起对教育的责任,并没有描述教育现象和研究教育事实的因果关系。”[5]另外,“解决教育问题的技术,可以由心理学、社会学、技术科学等提供,而价值方向的澄清和指明,必须由教育学者来进行。”[6]不难发现,实践中只有高等教育学才能对高等教育事实因果关系进行说明,对高等教育核心问题进行处理,而其他学科对此是“乏力”的,就此而言,高等教育学不可能为心理学取代。
2.高等教育学对心理学的知识供给:特殊情境化的心理知识。心理学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心理方面的知识积累和发展。自心理学17世纪建立以来,学者们只敢宣称他们“有限度”地获得心理活动的知识,大致掌握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有学者就指出,“心理学一般都会谈到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据称它反映了人的遗忘规律,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知道一个孩子在某一天内到底遗忘了多少知识。因此,任何对这遗忘曲线的运用都是近似的、非完全的。”[7]就此而言,心理学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关注不同情境下不同人群的心理活动现象,为心理学增添新的、具体化的知识,为深化对心理学一般规律的认识添加更多的“脚注”。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学能够为心理学提供特殊情境化的心理知识。以高校课堂教学为例,在大学课堂中,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如何互动、大学生如何进行研究性学习等“情境化”活动与中小学的课堂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大学主张学术自由,师生在知识探索方面具有平等权利,大学生与大学教师容易形成民主平等式的师生关系,相比之下,中小学尤其小学更多呈现出教师权威主导式的师生关系。另外,大学主张学习自由,大学生学习知识是在外在约束力相对较弱的氛围下进行,以利于探究新知识。相比之下,中小学学生一般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具有较强的外在约束力。就上例而言,大学生与教师的心理互动、大学生学习心理活动的特殊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学中“学术自由”、“学习自由”理念的践行造成的。在此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学为心理学提供了特殊场域中师生互动以及学生心理活动方面的素材。这显然有利于心理学进一步探索心理现象,深化对心理运行规律的认识。
三、高等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1.社会学对高等教育学的贡献:“社会关系”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学科。对社会学而言,“公平”是其核心价值追求,“关系”思维、“系统”思维是其观察社会问题的独特方式。高等教育学则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和发展。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化的知识动物,也是社会化的符号系统”[8]。高等教育中的人活在一定社会中,所以高等教育学需要社会学的知识。另外,就“物”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高等教育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所以高等教育学也需要社会学的知识。
具体而言,在人的发展层面,社会学为高等教育学提供了人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社会关系方面的知识。高校是一个小型的社会,高校中的每个人、每群人都处于某种“社会地位”,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如何扮演好不同的角色,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应保持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事实上,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和组织理论就被高等教育学引进,应用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从而使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人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和状态,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保驾护航。在社会事业层面,社会学为高等教育学提供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知识。举例来说,如果高等教育学没有学习运用社会学的公平理论,那么,在指导高等教育发展时就可能疏于考虑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机会问题,这样,高等教育就可能成为拉大阶层差距、引发阶层对峙和社会动荡的工具。反之,高等教育学能把社会学的“公平”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实践,就会重视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提出有效措施加以保障,这样,高等教育能够在促进阶层流动和分层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2.高等教育学对社会学的回报:“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份。美国学者查尔斯·维斯特指出,“大学的存在,是为了向后代传授知识,并产生新知识、新思维、新见解。”[9]可见,大学和高等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基于此,关注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应把大学以及高等教育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由此,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为社会学增加了“知识份量”。此外,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学为社会学提供了特殊场域的“社会关系”方面的知识,丰富了相应的社会学理论。例如,组织按照科层制“高层管理低层、低层服从于高层”的社会关系运行一般能取得高效率和高效益,但该制度在大学内的运行存在特殊之处。“大学组织主要由具有高深知识的学术人员组成,以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为目标……专业学术人员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地工作,他们对组织的强制权力有一种天然的抵抗,他们的工作也很难受他人的控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组织中,科层机制的等级权威、规章制度以及市场机制的物质利益刺激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10]“大学组织散结合的系统,尽管它也多多少少具备科层组织的一些特征,但严格来说它不属于科层化组织。大学组织所承担的主要是高度专业化的学术活动,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学生的学习都带有相对的自主性,他们不太欢迎非专业人员对在自己归属的专业领域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指手画脚,因此来自职位的权力即使是合法性的,但未必是有效的。”[11]由上可见,在大学这种从事知识生产、发展和创造的机构中,科层制的实施要结合学术发展的规律运行才可能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具体来说,大学场域中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要形成“平等合作”的关系而非“绝对化服从”的关系,学术人员也要形成“平等交流”的关系而非“管治与被管治”的关系,如此,大学运转才是良性的、有效的。必须指出,这些特殊化的“社会关系”知识是高等教育实践所产生的,属于高等教育学的知识范畴。高等教育学中的这些知识无疑能进一步丰富科层制理论,进而为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知识养料。
[1] 李政涛.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从知识、科学、信仰和人的角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75-82.
[2] 徐楠,李莉.论现代高等教育学科的开放性特征[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22-125.
[3] 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196.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92.
[5] 唐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60.
[6]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85.
[7] 李政涛.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从知识、科学、信仰和人的角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6-137.
[8] 宋太庆.知识革命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6.
[9] [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M].蓝劲松,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
[10] 金顶兵,闵维方.论大学组织中文化的整合功能[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93-96.
[11] 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