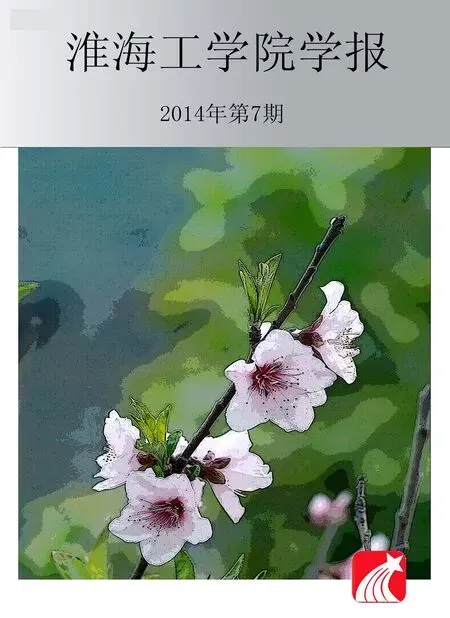转型时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乡村人际关系探析*
2014-04-17阳清
阳 清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在进行物质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建立在个人感情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具体状态[1]。随着我国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农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外地打工或做生意,但又并未在城市里扎根,这个群体被称之为外出务工人员。然而在市场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了他们人际交往的变化。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外出务工人员与家乡原有的人际关系的变迁,描述其现状,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一些修复和发展他们与原有乡村人际关系的建议。
一、转型时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乡村人际关系的现状
(一) 亲缘关系
1 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关系也不同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家庭结构是一种成员长幼有序的差序格局”。传统农村家庭遵守默认的“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的伦理规范,但是现在这种和谐融洽的场面不复存在,关系变得微妙化。一是亲子关系的变化。过去在农村,“养儿防老”是一种惯性的思维,赡养老人也是子女自觉遵守的一项义务,但随着人们理性化行为的发展,“老人无用”的思想开始抬头,有些子女认为父母老了已没有多大价值,不愿意赡养老人或因需负担而嫌弃、辱骂老人。传统社会中老人因智力而具有的权威,在快速更新的信息时代已丧失其价值,其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则是更加注重与下辈的亲子关系。在城市文化的熏陶下,外出务工人员开始越来越注重子女素质教育,同时又因为外出务工心怀愧疚,对子女的需求是有求必应,不加辨别。但由于相处时间过少,他们与子女的关系还是比较疏远,子女对父母的概念更多是停留在称呼上,情感依恋不强。二是夫妻关系的变化。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或因为在城市见多识广,或因为两地分居,离婚的现象相比于过去明显增多。另外,更多的农村妇女走向城市,承担家庭中的经济角色,随之妇女自主意识得到提升,社会地位提高,农村妇女不再是一味地服从丈夫,而是有自己的想法,但往往又缺乏沟通协商的技巧,这就造成夫妻吵架事件频发。
2 家族观念的变化 重视血缘关系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一大显著特点,为了应付自然生产,他们往往抱团而居,因此很多村庄往往由一个姓氏成员发展而来。村内大凡有重大活动,如婚丧嫁娶、盖房建屋等,同姓的本家都出钱出力,并依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帮助的力度不等。但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外出务工,相处时间减少,兄弟姐妹关系淡化。虽然兄弟姐妹关系还是重要的血缘关系,遇重大事情,他们仍然是背后的支持网络,但没有以前亲密。过去大家都在农村务农,农忙时会义务性地换工,每逢兄弟姐妹生日都会相互走动,但是现在由于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隔离,只有过“正生”(老家习俗:逢十即是正生)才会相互请客。除了过年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平时联系也不多。一部分兄弟姐妹还因父母的赡养分工及财产分割问题而关系不和。另外则是家族观念的淡化。过去由于农村生产力低下,迫于经济生产的需要,家族成员不得不依靠家族互帮互助而生存。另外,传统农村社会中,法律观念淡薄,当外族入侵时,主要依靠家族的凝聚力来捍卫本姓氏成员的利益。由此以来,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甚是密切。但现在外出务工人员都是分散地在外地打工,家族观念淡化,往往注重的是自己小家庭的利益,由“大家族”转变为“小家庭”,出现“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 地缘关系
1 邻里关系的变化 邻里关系在农村中承担着特定的社会义务:生产上互济,生活上守望相助,对晚辈的社会化,但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外出人员增多,邻里功能大为削弱,邻里关系更多成为“地理”上的概念[2]。历史传承下来的“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正在丧失,邻里之间的交往变得工具化。一方面是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利益化。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经济利益成为社会利益的中心,人际交往中追求利益的理性主义开始凸显。那些在外面挣了大钱或是谋得了一官半职的人是门庭若市,邻里街坊是找各种理由与他攀上关系,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为自己所用。另一方面则是邻里关系的冷漠化。功利化的交往目的导致外来务工人员与一些弱势的邻里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过去村庄里的老弱病残都会得到邻里的尊重和帮助,但是现在大家像避瘟疫一样刻意去疏远这些弱势的邻里,乡村中那种扶残救困、温情脉脉的传统美德正在被“利益”所冲散。另外则是邻里交往的表面化。过去邻里之间还承担重要的情感支持功能,谁家心理憋屈,随便可以拉一个邻居倾诉心肠,但是现在随着交往时间的减少,邻里之间的信任感降低,越来越少地敞露内心世界,交往内容更多是事务上。
2 与村组织、村干部关系的变化 过去,大家都在家务农,对村集体有比较高的归属感,也很认同村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村内重大事务,大家会积极响应队长的号召,一起开会,商量讨论,并且尊重村内干部的权威,信任他们的行为。但现在外出务工人员常年在外,他们没有时间与精力来过多地关心村集体事务,与村组织的关系疏远。另外随着在城市发展,外出务工人员见识增多,对村干部的权威认同下降,又因部分村干部群众意识淡薄,办事透明度低,村内政务财务不公开,进而造成外出务工人员与村干部关系的恶化。一方面是客观上对村内公共事务的漠视,与村组织关系的疏远;另一方面则是主观上对公共事务强烈的知情权,但又普遍缺乏表达,而村干部并未意识到村民这种需求,这就造成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失望与不满,最终形成了外出务工人员与基层政府之间疏离、对村干部不信任的状态。
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乡村人际关系变化的原因
(一) 社会流动造成空间距离上的隔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在城市巨大拉力的作用下,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为农村带去先进观念的同时,也使以村落为单位的村民分散化。过去一个村落里的成员因生产需要是一个紧密的团体,而现在各自散落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角落,团体被零散化。人际关系的建立是以人际活动为内容,而人际活动又以一定的相处时间为前提。在社会流动这种背景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不管是与同是外出务工的村民还是留守在农村的村民相处的时间都比较少,自然而然交往频率下降,以前的感情因时间而淡化,而现在又没有时间来重建感情,进而导致交往深度的浅化,邻里之间的交往内容多停留在事务层面上,难以达到情感上的相互支持,人际交往趋于表面化。
(二) 谋生方式的不同造成农村社会分层
在社会学意义上,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社会分层根源于社会差别的存在[3]。农村人口大部分外出务工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促使农村由同质化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异质化的社会结构,由单一的职业角色转变为多元化的职业角色。过去大家都在农村种田,经历相似,财富相差不大,而现在大多数农村人口都外出务工,在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中,有些人自主创业在外做生意,有些人则是出卖自己劳动力进厂打工,这一方面造成邻里之间相互依赖程度降低,彼此不再因生产那么需要彼此,关系因客观条件而逐渐疏远;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进而引发农村社会分层,他们因财富的多少由过去平等的地位演变为高低有序的社会地位,这易引发村民的失衡心理,因嫉妒等不良心理而影响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同时因经济思维的深入,利益成为行为的主导力量,村庄内又会出现“强-强”“弱-弱”两大集团,最终形成因差异而隔阂化和因利益而功利化的复杂局面。
(三) 文化上道德的失范及习俗的衰落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逐步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城镇社会转化,村民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开始怀疑传统的以“人情、伦理”作为基础的行为规范,但由于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村社会尚未完全进入现代社会,城市中那套以“理性、利益”为基础行为规范又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社会,于是就出现了道德失范的现象,即一个社会既有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而新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的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的'真空'阙如[4]447-448。这就造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在乡村人际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在实际交往中受市场经济理性思维的制约表现出目的性与功利性,但同时又无法完全摆脱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带有浓厚的伦理性。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中承担一定的功能,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5]12。农村社会一些传统节日及习俗也有其功能,其重要功能之一即是联络感情。但现在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农村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衰落的趋势。以笔者的家乡为例,几年前,正月里去左邻右舍家拜年,人们会围坐在一个桌子旁,一边“挂红”一边聊天。那种场面其乐融融,欢声笑语。而现在,那种串门的“恭喜拜年”似乎完全演变成一种仪式,像完成任务一样,很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本该如此”而如此,拜年的时候不会再在别人家小坐一会儿,不会轻易去和别人攀谈,更多时候是前脚进,后脚出。由此可见,这种习俗上的衰落减少了人们相处的时间与机会,无形中也拉开了村民之间的心理距离。
(四) 市场经济导致价值观念的改变
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受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熏陶,注重等价交换,强调物质利益。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他们由于相对贫穷,易出现狭隘的金钱主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化,以能否为自身带来经济利益作为交往的标准[6]。当他们把这一套行为价值观念内化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其经济性与工具性会表现在他们日常的人际交往行动当中。当回到农村,由于行为模式的惯性他们仍会不自觉表现出世俗化与功利化,并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不纯洁的思想带回村庄,冲击着原有的淳朴民风,从而逐渐地用经济理性化的工具性关系替代了传统农业社会中那种互帮互助、以感情为纽带的人际关系[7]。
(五) 现代化建设造成人与工具的异化
外出务工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大多外出务工人员已将过去的土砖房改造成现代化的红砖房,室内根据经济条件也配备档次不同的现代化设施,电视电话一应俱全。但正如弗洛姆所说,“人类逐渐被自己所创造的商品所囚禁,沦落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却忽视了人类存在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8]4。本来,我们所创造的物品如大众传媒等是用来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上的需求,然而,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这些东西所占据,以致我们反而忽视了身边的人,疏于与他们进行交流,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仍然以我熟悉的家乡为例,当我们都是土砖房的时候,邻里之间的来往是自由的、随意的。但是自从大家建起了红砖房,室内搞了装修,家里有了电视机,我们更愿意选择在家看电视,也不会轻易去邻居家串门。就这样,乡村社会中人们的心理距离被我们的生活工具硬生生地拉开了。
三、构建外出务工人员乡村和谐人际关系的对策
传统乡村关系是以情感整合起来的,而现在则是一种理性整合。帕累托认为,“情感”是一种剩遗物,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而“理性”是一种派生物,是变化的;因而以情感为纽带构建的农村社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以理性为纽带构建的农村社会是不稳定的,是充满风险的[9]。外出务工人员与原有乡村的人际关系表现出理性化、工具化、冷漠化、疏远化,从经济角度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也需警惕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状况长期发展下去,外出务工人员将沦落为“永远的游子”,在自己的故乡找不到归属感与安全感,最终会异化作为“人”的社会本性。因此,我们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有机地将传统“人情”与现代“理性”相结合。
(一) 传统文化调节与现代法律调节的有机结合
文化道德根植于其生存的土壤,同时又反过来影响、规范、整合生存于这块土壤的人们的行为[10]。传统农村社会强调的“人缘、人情、人伦”以及尊老爱幼等礼治秩序为村民的行为提供了一种范式,有其重要的调节功能。因此我们应吸收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之精华部分,不完全抛弃,重视其规范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发扬传统文化,维护传统习俗节日,充分发挥习俗的情感交流功能。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理性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传统乡村伦理型社会也在向法理型转变,法律是法理型社会中最主要的调节方式,因此农村也应重视法律在法理型社会的调节控制作用,有机地将传统乡村的本土性与城市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性结合起来,防止发生道德失范的现象,从而引导乡村社会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
(二) 建立全社会的新型人际交往规范体系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高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货币以其强有力的穿透力侵入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人们一切行为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反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这种个体的过于理性一方面易导致社会成员心理病变,另一方面可能导致社会集体的非理性。因此,在当前全社会人际交往价值观多元化、良莠不齐的情形下,我们应倡导建立一套全社会的新型人际交往准则,坚持平等友好、坦诚相待、守信互利等原则,以满足人际交往的情感需求为主,兼顾交往中的利益,促使全社会良好氛围的形成。这样,外来务工人员在学习新型现代人际交往规范的同时,也不至受到城市不良人际交往观的冲击而出现价值错位的现象。
(三)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社会评价体系也不尽合理,财富成为衡量个人价值及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因此,人们大多还停留在追求物质利益的阶段,迫切地追求金钱财富。又因为社会分配制度不完善,社会流动空间有限,这就造成了贫富差距与马太效应,人们为了上升到社会结构中的高层,人际交往开始变得功利化与目的化。因此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各项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分配和社会流动公正公平化,人们可以通过正规公开的渠道获取社会资源,而不是依靠社会关系网络,这样人际交往的利益化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同时,人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开始从追求物质利益上升到追求精神价值,不再一切往“钱”看,注重人际关系的情感需求功能,人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融洽多。此外,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地就业,这就为他们在共同地域工作生活提高了机会,避免外出务工的零散化,有利于促进他们相互了解,从而实现人际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王巍.浅析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村人际关系[J].三江论坛,2006(12):23-26.
[2] 宋国恺.转型期中国农村人际关系探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76-79.
[3] 徐婷.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综述[J].中国市场,2011(9):114-117.
[4] 郑杭生,李强.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一种探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5]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 闫丽娟,胡兆义.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J].长白学刊,2007(6):108-112.
[7] 王枫萍.韦伯理性化思想的解读及其对我国现代化的启示[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72-476.
[8] 弗洛姆.寻找自我[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9] 杨群宝.农村人际关系的淡化和构建和谐农村社会[J].决策管理,2007(1):48.
[10] 宋国恺.转型期中国农村人际关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