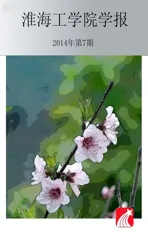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考辨及新解*
2014-04-17梁新军
梁新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一
什么是文学?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自从“文学”这个术语诞生以后,它的内涵和外延就始终面临着不确定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总是对其有不同的理解。然而,正是这种内涵的复杂流变和共时性存在的多义性,才形成了文学的独特魅力。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也就在于它始终存在的难以被界定的神奇魅力。但是,也恰恰如此,无数学者才萌生了一劳永逸地定义“文学”的巨大热情。在西方,自1759年莱辛发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以来,斯达尔夫人又在1800年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由此,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得以产生。在中国,新文学概念则源于晚清从日本引入的现代学科观念,直到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方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产生了,可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当代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其《文学性》的开头便抛出了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一是因为全人类范围内的文学是丰富多样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当然可以对其有独特的理解和界定;二是尽管人们可以有自己多元化的理解从而对文学抱持一个最开放的立场,也总是有一小部分人孜孜不倦地试图为人类千姿百态的文学寻找到一个确定性的概括,从而企图在根本上揭示文学的特征(比如乔纳森·卡勒就认为,“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文学的定义,而是要描绘文学的特征”)。最早做出此项努力的,大约要算20世纪初期活动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了,这其中的代表罗曼·雅各布森曾这样说过:“文学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 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152在这里,雅各布森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学性,即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根本特性。雅各布森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使文学从复杂含混的文化整体中独立出来,从而推广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加深人们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和认识。雅各布森的贡献是无可非议的。人们要想深入地认识文学,当然首先要把文学从众多的语言文本中区别出来。只有首先区别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对其做科学的研究,从而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它。其他的形式主义者沿着雅各布森的思路,也表明了类似的看法,比如什克洛夫斯基就认为,“诗歌的话语是经过加工的话语,散文则一直是普通的、节约的、容易的、正确的话语”[2]77,这里诗歌成了文学文本的典型代表,而散文则归属于普通的话语文本,由此什克洛夫斯基强调了诗歌话语的特异性,从而凸显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总之, 如果加以归纳,俄国形式主义派的文学性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语言本身的突现方法,文本对习俗的依赖以及与文学传统的其他文本的联系,文本所用材料在完整结构中的前景[3]24。在这里,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了文学的根本特质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关于文学性争论的先河。
二
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延续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标准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区分,他认为“诗歌语言不是一种标准语言”,“对诗歌而言,标准语言是一种背景,用以反映因审美原因对作品语言成分的有意扭曲,也就是对标准语言规范的有意违反”,“正是这种对标准语言准则的违反,这种系统的违反,使诗歌成为可能;没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没有诗歌可言”[3]17-27。他的观点显然比前者更深入了一步,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诗歌话语特异性的观点。虽然必须承认,他们对文学性的探索是富于成效的,他们的见解确实深化了对文学语言之独特性的认知,然而,俄国形式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布拉格学派关于文学性的看法,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文学语言以及表达手段的突现这一方面。
但是,几十年后,乔纳森·卡勒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说:“关于文学即新颖化的观念,有一点需要保留说明。在语言领域,文学的效应不仅表现在奇特的形象和组合方面,还表现在高雅的语言方面。”[4]25他认为,“把某文本的文学性效应局限在语言手段的表现范畴之内,仍然会碰到巨大的障碍,因为所有这些因素或手段都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出现在非文学文本之中”[4]25,“语言的突现不能成为文学性的足够的标准”[4]27,因为其他文本中也可能会有类似的语言突现现象。在反思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观点之后,他提出了自己对文学性的看法,即“这些结构的融合——即按照传统和文学背景的规范建立起统一的功能性相互依存关系——似乎更应该成为文学特征的标志”[4]27。他认为有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的融合需要考察,“第一层次把在其他言语中没有功能作用的结构或关系融合在一起”[4]27。他进一步解释:“因为文学文本不是传递具体信息的语言形式,而与异化的交际环境相联系,在这种异化形式里,语言的细节和结构的重要性居于传统的支配地位,文学语言从多种渠道表达它的意义。”[4]28这里卡勒的意思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地方在于,它的语言细节以及由此丰富的细节建构起来的整体性的语言结构。“第二层次的融合是指整部艺术作品的融合”[4]28,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贯穿作品的统一性,理应是文学性的基本内涵之一。第三层次的融合是“作品针对文学背景以及它与文学手法、习惯、体裁、读者赖以阐释世界的规则和范式的关系等,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意义”[4]29,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这个层面,文学文本总是对某种隐性解读给予评论”,这个文学文本宛然成为了一种“自省语言”,“一种不知不觉中(因其异化交际的形态)就自己的意义行为发表出某种高见的语言”[4]29。
纵观乔纳森·卡勒对文学性的理解和阐释,不能不佩服其深刻的洞见。他的作品统一性的观点(即整部艺术作品的融合)显然吸取了英伽登的艺术作品的“形而上的质”的看法。总体来看,虽然他的观点表述较为抽象晦涩,但他对文学性的认识确已超越了几十年前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了。以其视角来看,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看法确实略显机械和偏狭。乔纳森·卡勒是后现代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此篇论文显然已经自然地把文学性置于后现代语境之下进行观照,这时期文学文本所体现出的“文学性”早已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划定的那个范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提出“文学是对文学本身的批评,是对它所继承的文学概念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性是一种自反性”[4]30。这里,他的意思是文学不再只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之物,而是一种对传统的反叛。我们不得不承认,卡勒的此种新解,强烈地体现出一种后现代精神,他所理解的文学已然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更广义的文学了。我们知道,自后现代主义兴起以来,文学的疆界便呈现出扩张的态势,一些体现着强烈后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不仅成为热烈讨论的对象,甚至有些还被追捧为文学经典。从后现代主义角度重新审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是乔纳森·卡勒此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三
在此之前,我们知道韦勒克也曾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他对文学本质的看法。他首先沿着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思路,区别了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及日常语言的不同,他虽然认为这是困难的,但还是认为“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实用意义上的区别是比较清楚的”[5]14。进而他根据自己条分缕析的梳理和翔实有力的论证,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性观,即认为“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5]16。他进而又解释了如此界定的缘由,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非文学的所有区别,“篇章结构的个性表现,对语言媒介的领悟和采用,不求实用的目的以及虚构性等”[5]18。但是如此的界定还不能使他完全满意,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5]18详细考察韦勒克的文学观,显然他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他的谨慎的表述和立论也是经得起推敲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文学理论》中所显示出的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精辟的洞见,以及扎实有力的学术风范,都显示着他的观点几乎是不可挑战的。
然而,韦勒克的文学观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文学思想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影响,他本人就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尽管跟其他的新批评学者有不同意见,但总体而言,他的关于文学性的看法,并没有超出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设定的框架和思路,只不过他力求超越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偏狭,试图更全面综合地界定何为文学作品的共同特性罢了。当然,到底能不能从丰富多样的文本中抽象出一个特性来,仍然是大可怀疑的事。
史忠义在其翻译的《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中的译者序里也对文学性做了较为深入的历时性考察。他认为西方学者针对文学性的种种定义,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形式主义的定义,这主要以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观点为代表;第二类是功用主义的定义,也即是文学语言是一种突现的语言,文学语言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强烈的自我指向性;第三类是结构主义的定义,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乔纳森·卡勒的观点;第四类是文学本体论的定义,即认为文学语言的参照物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幻想中的人和事;第五类定义涉及到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即文学语言的陈述条件与某些特殊的条件相关。依次批判性地梳理了西方学者对文学性的几种定义之后,他仔细分析了其利弊得失,提出了自己的对文学性的看法。他认为,“‘文学性’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存在于形象思维之中。形象思维、文学幻想、多义性和暧昧性是文学性最基本的特征”。作者进而解释了他的定义,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他的定义的合理性。纵观作者对以往几种文学性定义的梳理和批判以及所提出的观点,可以说他确实指出了前几种观点的偏狭之处。他整合了前人的各种观点,系统梳理并建构了自己的观点,创造性地以一种新的视角更新了文学性观念,对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文学性确有较大启发。然而,在对文学性的梳理和重新界定上,史忠义虽然用力极深,但其总结仍然略显笼统,不够明晰精炼,他虽然关注到了创作主体的意向方面(形象思维、文学幻想),也关注到了文本特征方面(多义性、暧昧性),但只以此两个维度来归纳文学性显然是不够的。
彭峰在其文章《论文学作为艺术的几种方式》中,也将以往的文学性观归纳为三种方式:形式主义方式、本体论方式、程序主义方式[6]。所谓形式主义方式即指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性观,本体论方式是指现象学家英伽登的文学性观(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纯意象性对象),程序主义方式则是指“文学性存在于接受者的阅读当中”这样一种文学性观。程序主义的逻辑依据是没有阅读就没有文学,因此文学性理应存在于读者的阅读当中,并体现在其阅读的态度中。这种程序定义法不再是“根据艺术的特征和功能来进行定义,而是根据某物成为艺术作品必须经过的程序来进行定义”[6]53。彭峰的文章精炼地总结了文学性论争史上的三种不同观念,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文章只述不论,只梳理、阐释前人的看法,而未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观全文,作者并没有提出自己对文学性的看法和立场。
因此,本文想在彭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何为文学性,并尝试建立自己的文学性观。事实上,对文学性作一个明晰精炼的、富于学理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认为,文学性是一个复合型的有着多重内涵的概念形态。为了更明确地阐释这一点,这里需要引入广义文学观的概念。
四
何为广义文学观呢?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本体论。这里的“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批评派及韦勒克所提出的“狭义文学观”,即把文学定义为审美的语言文本。广义文学观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文学观,它主要区别于以雅各布森、俄国形式主义者和韦勒克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它并不否定文学作为一种狭义的审美性语言文本存在的客观性,反而它囊括与包容了这一存在的事实,进而它还力争涵纳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的新样态。我们知道后现代语境下文学文本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各种新样态,这是“后现代性因素”在文学中的一种必然反映。时代不同了,文学也在新时代获得了更新和演变,这种语境之下的文学当然要用新的文学观来概括。当然,这种新文学观并不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简单的颠覆和反叛,而是内在地把传统文学观囊括其中。它是以往各种文学观念的自然延伸,在某种程度上固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立场和姿态,但并不与传统水火不容。它更多地是对传统的一种延展、生发,它使文学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这种新时代下的文学,即处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自然要用一种区别于以往狭义文学观的广义文学观来理解和认识。旧有的文学性观念理应得到更新,或被重新界定。本文认为,文学性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创作主体的对其作品的“文学性”追求,即创作主体的“文学”动机,这是依照文学文本的先在的“文学”意图来界定文学性的;二是文本层面上的文学性,此种层面上的文学性不应只体现着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专有特征(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观),也应包含文学文本与其他语言文本间的共通之处,即文本层面上的文学性不仅应是一种对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或结构形式的特征的概述,也理应涵纳其与其他语言文本间的共通之处(真理性),文学文本从来不只是仅具有审美性因素的语言文本,它也是天然地贯穿着真理性因素的一种文化文本,所以审美性和真理性都应是文学性的应有内涵;第三个层面上的文学性,体现在接受主体对文学作品的感性认同和理性接受上,文学接受者是怎样认识“文学作品”的,怎样描述所阅读的“文学作品”的,这本身就体现着文学性的另一个维度,即接受者一方赋予“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这里文学性不仅体现为一种特有的文本特性,也体现为文本接受者的认可。
总之,文学性理应贯穿在这三个层面上,它是一种复合型的、多层面的概念形态,它不单单体现为一种狭义的文本特性,也包含另外两个层面:创作主体一方的“文学性”追求、接受主体一方的“文学性”追认。文学性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概念形态,涵纳了三个维度上的文学特性:创作主体的、文本形态的、接受主体的。事实上,这种文学性观某种程度上也正和迪基(Dickie George)的艺术体制理论不谋而合。迪基认为,“某物要成为艺术作品需要经过至少两个程序:首先,它必须是艺术家有艺术意图地创作出来的;其次,它必须获得艺术界的认可”[7]34。与其不同的是,本文的文学性观在第二个程序上指接受者(广义的读者)的认可而不只是文学界(文学研究者)的认可。
本文的文学性观涵纳并超越了以往的各种文学性观,也有别于后现代语境下对文学性的一般理解(卡勒的文学性观),它是对以往的各种文学性观的提炼与升华,但又不同于史忠义的普遍升华说。本文的“文学性”,明确宣称是后现代语境下由广义文学观而生发提炼出的具有更高统摄力的“新文学性”,它克服了表述的模糊和逻辑的松散,明确了其本身所涵纳的三个维度,并以凝练而富于学理的语言将之系统性地表述了出来。
参考文献:
[1] LEE T L,MARION J R.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Four Essays[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5.
[2] 维·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M]//茨维坦·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 扬·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M]//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4]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M]//马克·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5]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 彭锋.论文学作为艺术的几种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13(3):48-54.
[7] DICKIE G.Art and the Aesthetic: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M].Ithaca,N Y:Cornell UP,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