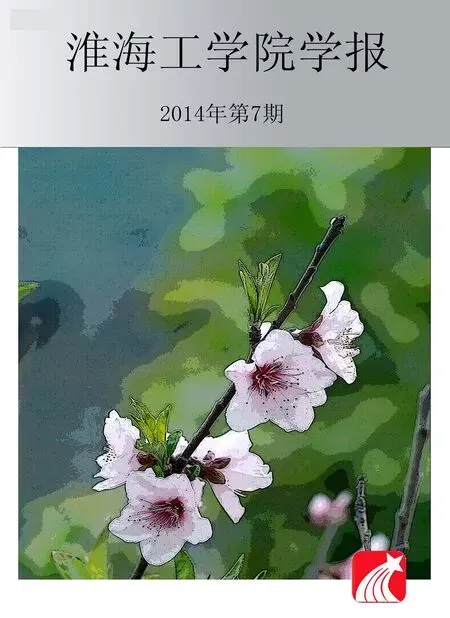浅析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2014-04-17孔文静
孔文静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人权概念首次进入我国宪法,使保障公民权利成为一项原则性规定。2013年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人权保障理念,明确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结合起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一项重要任务。虽然我国在立法方面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各种权利保障,但由于长时间受“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侦查等阶段有罪推定、滥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等现象屡禁不止。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不平等的地位,使得其权利很容易受到侦查机关的侵害。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保护具有必要性。
一、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增设的人权保障制度
(一) 辩护制度
首先,将律师介入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并且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其次,扩展辩护援助对象;再次,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辩护人的权利,如阅卷权、申请回避以及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向侦查机关了解情况、提出意见的权利等。规定辩护律师除特殊案件外凭“三证”就可会见当事人,并且保证辩护律师不被监听。
(二) 强制措施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取保候审的情形,即“羁押期限届满而案件尚未办结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取保候审”。在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方面增加了辩护人的角色;其次,在监视居住范围方面,增加了逮捕转为监视居住和羁押期限届满后符合条件的适用监视居住的情形。规定“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办案场所进行”,是强制措施中人道主义的体现;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机关的拘留通知义务以及拘留的原因、拘留的场所等等;关于录音、录像问题,规定了“可以”和“应当”两种情形;对于逮捕,第91条规定了逮捕通知的时间,规定逮捕后的羁押地点并且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家属的知情权等。
(三) 证据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和禁止自证其罪原则。第55条、56条、57条、58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合法取证的要求,切实保护了被追诉者的基本人权;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了禁止自证其罪的原则,这一制度是对国外“沉默权”的借鉴,旨在承认、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制度的不足
(一) 律师帮助权不够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的介入时间提前,有利于减少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变相羁押”等侵权现象的发生,但律师的会见权在当前的律师会见制度下仍然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持续时间和次数并没有作明确规定。第二,新刑事诉讼法提出“会见不被监听”,但却没有明确禁止侦查人员派员在场。第三,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会见仍须经过批准。这就给侦查机关滥用职权、阻碍会见提供了机会。第四,有关律师权利救济的规定不够明确。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律师对处理不服的申诉复议的相关规定。第五,新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但对辩护律师收集证据的程序有相当严格的限制,这就给律师调查证据增添了不少压力。
(二) 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存在缺失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控诉机关承担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明义务,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否定了通过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但是该法第118条明确犯罪嫌疑人有“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不得保持沉默。这一条款的保留,导致“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很难得到保障。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够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禁止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这实属不彻底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第54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有很大的裁量范围,所以,很难把握。另外,新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方式只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而对于纠正意见是否采纳,以及不采纳后应如何处理等救济措施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还不够完善。
(四) 具体的强制措施仍然存在问题
具体而言,强制措施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第一,我国法律对拘传规定得较为笼统,对于任何拘传、两次拘传的时间没有做详细的规定。这就容易导致非法拘传的出现,如进行多次拘传,甚至令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愿去填写时间,更有甚者,侦查人员直接代替犯罪嫌疑人去填写。这些行为都严重威胁到了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第二,取保候审方面:在对保证人与保证金的规定上,新刑事诉讼法赋予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决定保证金金额的权力。这就很容易促使决定机关滥用权力。第三,监视居住方面:首先,新刑事诉讼法虽然扩大了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但是变相羁押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加长犯罪嫌疑人受到控制的时间;其次,关于监视居住的“住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在指定居所执行”,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法律漏洞。第四,对于拘留过程中的录音、录像问题,将其分为“可以”录音、录像和“应该”录音、录像两种情形,但是“可以”二字便为执法人员应该录音、录像却不录音、录像的情况提供了可能。第五,关于逮捕,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无法通知的情况以及如何处理并未作规定,这就为“秘密逮捕”提供了可能,仍是一个法律漏洞。另外,新刑事诉讼法仍没有规定延长羁押次数的上限,这些都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 完善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第一,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这样可有效减少非法讯问的情况发生,而且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犯罪嫌疑人内心的紧张。第二,赋予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录像的权利。新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了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根据控辩平等的原则,也应赋予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录音、录像的权利,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实践中难以证明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或其他暴力方法取得证据的问题。第三,适当取消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相关限制,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充分的自由权,从而便于律师广泛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第四,取消律师会见的批准制度,确立秘密会见制度,从而保证会见权之立法意图的实现。
(二) 树立非法证据排除、无罪推定等理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贯彻无罪推定理念,首先要明确毫无例外地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其次要赋予犯罪嫌疑人有限的沉默权,这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因为我国宪法第35条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规定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因此,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三)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相关制度
第一,建立适用强制措施的审查机制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对非法实施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权利。侦查机关对于强制措施适用的选择,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比例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加强对侦查阶段采取强制措施的审查和控制,建立相应的审查机制,不仅能够对侦控行为起到监督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也是一种救济机制。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遇到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或者超期羁押等侵犯其人权的行为时,不会再无人问津。第二,建立侦羁分离制度。我国长期以来看守所归公安机关管,导致公安机关身兼两职,既是侦查机关又是羁押机关。这样一来就纵容了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现象的出现。建立侦羁分离制度,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分离出来,将羁押权利赋予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管理,并且明确此机构的职责,使其与公、检、法三机关各司其职、彼此独立。那么,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会见难等一系列与侦查机关办案有关的问题将大大降低。
(四) 完善立法,弥补法律漏洞
对于立法尚不足的地方,需要查缺补漏。第一,刑诉法对于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应该作出明确规定,可以规定保证金为非法所得的百分之多少的比例或者具体规定各种被追诉的罪名所对应的取保候审的金额。第二,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录音、录像,不经录音、录像而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不得作为证据适用。第三,立法应该完善变更强制措施的具体规定,并赋予犯罪嫌疑人相应的救济措施。当公安、司法机关作出不予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时,应该向犯罪嫌疑人作出书面答复并说明拒绝理由。第四,立法应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制度。比如,确立最长羁押期限以及延长羁押的次数,超过此期限或者超过延长期限的次数,犯罪嫌疑人将被无条件释放;用立法的形式确立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中的生活条件,比如伙食、睡眠、居住条件等等应明确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并且要有必要的救助保障,如自由会见律师等等。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于刑事诉讼活动有监督的权力。基于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这种监督主要表现在审查批捕、监督逮捕执行、审查起诉等方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应当立即执行并送达执行回执,如果未能执行也应当送达执行回执并说明未能执行的原因。加强和改进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使其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 郭明文.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J].河南社会科学,2006(4):80-83.
[4] 仲丽娜.试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法律中的确立及完善[J].学术交流,2006(10):61-63.
[5] 张红侠.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J].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4-37.
[6] 陈云龙.检察机关侦查指引权及其实现机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2):6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