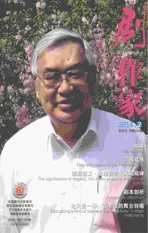没落失意者的挽歌——论契诃夫对田纳西早期剧作的影响
2014-04-17莫惊涛
莫惊涛
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曾经轰动过百老汇舞台,对世界其他民族戏剧,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剧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美国南方为背景,写南方的没落和对逝去的美好时光的眷恋。他作品中充满的那种淡淡的忧伤、朦胧的诗意以及那些在一系列困境中苦苦挣扎、不合时宜的人,都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剧作家契诃夫,想到他笔下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忧郁和诗意,想到那些同样沉迷于往事,在平凡琐碎的生活和严苛的社会环境下依然心存理想和美好的人。威廉斯在《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人们常说,劳伦斯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最大。是的,劳伦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让我喜爱的人物,但是契诃夫的影响更大。”[1]
1935年夏天,由于备受神经衰弱的折磨,威廉斯不得不到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外祖父家中休养。在这里,契诃夫的三本书信集和两部剧作《海鸥》、《樱桃园》深深吸引了他,令他陶醉,以至于使他忘记病痛。这种从最初的阅读中体验到的的快感和共鸣,强烈渗透到威廉斯的情感和思绪中,对他一生的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契诃夫剧作中那种淡淡的忧伤,那种蕴含着时代巨变的平平淡淡的生活,那些精神和肉体被撕裂的想过美好生活而不得的人,都深深感染了威廉斯,进而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尤其是在他早期的作品《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中,我们仿佛触摸到了《海鸥》和《樱桃园》的影子。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在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身上,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时代的变幻中谱写了一曲没落失意者孤独与梦幻的挽歌。
在两人的剧作中,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首先就是他们的作品都取材于平凡的日常化的生活,都在家庭生活表面的波澜不惊中折射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其次就是那些色彩鲜明的人物,那些身体虽沉沦于地上,而灵魂却不甘堕落、高蹈于空中的失意者与寻梦者。在契诃夫的剧作中,他们是以生命去追寻“梦的戏剧”的特里波列夫;是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最终却身心俱疲的尼娜;是樱桃园中没落的、善良的郎涅夫斯卡娅。在田纳西的剧作中是身在仓库、心向大海的汤姆;是像玻璃一样晶莹剔透却纤弱自闭的罗拉;还有一心向往纯洁高雅却命运凄惨的贵族小姐布兰琪。这些拥有美好梦想和热情而无法实现的人,这些在时代挽歌中渐行渐远的人是如此的相似,让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两位剧作家在创作灵感上的共通性,即题材选择的相似性和人物设置的同构性。
一、题材选择的日常化
对于题材的选择,剧作家往往都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偏好。有的擅长写生活中的暴风骤雨,直面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现实主义大师易卜生和阿瑟·米勒;有的长于研究人生和生命的奥秘,思索道德的价值,如梅特林克;而契诃夫与田纳西则喜欢撷取普通人的生活,很少以重大历史事件、严峻社会问题等宏大故事为题材,他们或写世纪末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或写南方中下层社会中不得志的小人物,尤其是契诃夫笔下的那些没落贵族以及田纳西所塑造的那些失意的南方女性更是栩栩如生、鲜明感人。
契诃夫一向主张按生活本来的面貌描写生活,他特别注重对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用契诃夫自己的话来说,“人物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2]在他看来,人生伟大的喜剧和悲剧都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厚层下面。他的作品主要写知识分子,就是通过他们最寻常的生活展示出他们的无奈、挣扎和失落。
《海鸥》是契诃夫所创作的不朽作品之一,它是一部关于爱情、关于艺术、关于危机的剧本。然而它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家庭的农庄里,剧作家的思想则通过一对少男少女(特里波列夫和尼娜)的梦想展开。尼娜是一个住在湖边的美丽的可爱的少女,受特里波列夫一家人的影响,她整天梦想着光荣,梦想着舞台。在尝试了初次登台的滋味后她结识了特里波列夫母亲的情人——名作家特里果林,从此命运骤变。尼娜以全部的热情爱上了特里果林,为此不惜违抗父母的意志,脱离家庭跑到他所在的莫斯科去。可惜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维系的时间很短暂,不久特里果林就玩厌了她、抛弃了她,重新回到他的老关系阿尔卡基娜身边去了。身受重创的尼娜在悲凉中成了一个外省的女演员,在长期的奔波演出中,她渐渐成熟起来,真正意识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光荣、不是名声,而是信心和使命。
特里波列夫也有自己的梦想,他既梦想着光荣,也梦想新的艺术形式。他写了一个别出心裁、言语古怪的剧本,由心爱的尼娜上演给亲友们看。没料到遭到母亲等人的嘲笑,羞愤之下,特里波列夫下令闭幕不再演出。这还不是最难过的,最痛苦的是不久之后他还失去了至爱的尼娜。饱受打击的特里波列夫曾试图自杀,被救后他虽仍然进行创作,他的小说也被刊登在首都的杂志上,但对尼娜的爱和创作上的困惑依然困扰着他。最终在无法留住尼娜、目睹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后特里波列夫举枪自杀,他的生命,也像他的戏剧一样,中途夭折了。
剧本的情节简单,题材寻常,表面上就是两个青年人的青春、爱情和梦想。可是通过他们的磕磕绊绊,通过他们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我们却可以深深体味到他们的憧憬与快乐,挣扎与苦闷,可以从中意识到:那种最初的、早期的幻想的美,仅仅是可能的美而已;只有那经历了挫折与痛苦,真正认识了一切但仍然有信心的美,才是真正的恒久的美。
《樱桃园》是契诃夫临终前的天才作品,它通过贵族庄园樱桃园被拍卖这一事件,抒写了一曲新生活来临前没落贵族无可奈何、感伤失落的挽歌。然而在作品中我们却发现,在契诃夫笔下,樱桃园被拍卖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件却被放到了暗场加以处理,舞台上呈现的全是剧中人物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片段。我们看到的是旅居巴黎的郎涅夫斯卡娅归来,亲人久别重逢后的拥抱、亲吻和叹息;看到的是得知樱桃园即将被拍卖后他们多愁善感的童年回忆;看到的是樱桃园拍卖当天举行的滑稽的心不在焉的舞会以及加耶夫念念不忘的台球和安尼雅、瓦里雅等人的爱情,还有忠心耿耿的老仆人费尔斯听不清楚的嘟嘟囔囔……可正是这一幕幕的日常生活场景让我们思索:就是这日复一日的琐碎与空虚把那些贵族老爷、太太的激情和意志消磨殆尽,使得他们在历史大潮涌来时无所适从,只能在叹息中黯然退场。就像樱桃园的失去一样,他们的衰弱与失意纵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却也让人感到留恋和惋惜。
威廉斯是美国南方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美国南方为背景,写南方的没落,写南方中下层社会中不得志的小人物。他作品中的场景与人物,都无显赫可言,也于历史事件无关。可他同样在日常化的生活中,通过人物梦想的失落向我们展示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人物命运的挽歌。
《玻璃动物园》是威廉斯的成名作。它明显带有剧作家自身家庭境况和自己青年时期痛苦生活的影子,因此威廉斯称它为“回忆剧”。剧作写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溫菲尔德一家三口人的生活状况,写了他们的梦想、追求与失落。母亲阿曼达出身于南方的富庶家庭,当年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如今被丈夫抛弃,带着一双儿女窘迫度日,当年在蓝山的回忆成了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儿子汤姆是个渴望冒险、渴望大海、渴望自由的仓库保管员,可为了母亲和姐姐,却不得不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家庭和仓库中苦苦煎熬;姐姐罗拉身患残疾,心灵脆弱,羞于见人,惧怕外面的世界,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丈夫,只好躲在家中,与玻璃动物作伴。此外还有一个外来者吉姆,当年学生时代的明星,如今汤姆的工友。剧作就在一家人寻常的生活中展开,可就在汤姆的电影院、罗拉的独角兽、以及阿曼达过时的吊钟型女帽和黄纱裙中,我们却看到了他们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希翼,看到了他们试图挣脱又无力或无法挣脱后的凄楚与悲凉。
《欲望号街车》是威廉斯极富盛名的代表作,曾一连上演八百五十五场,打破了美国戏剧演出的最高场次记录,为威廉斯赢得了纽约剧评奖和普利策奖。声名显赫的剧作也不过取材于贵族小姐布兰琪前往新奥尔良探亲的经历。布兰琪出生于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家族,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但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她早已今非昔比,在经历了一系列家庭惨变和自身沉沦后,她早已伤痕累累、一无所有,却依然生活在美好的臆想中,念念不忘南方的文明和昔日的贵族生活方式,认为自己依然高尚优雅、纯洁无比,仍然幻想着凭借这些去收获一份浪漫的爱情和安宁的家庭。可现实绝非想象,在妹夫斯坦利的自私、野蛮和粗暴的阴影下,布兰琪的梦想很快破灭了,整个精神世界也随之崩溃,最终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在家庭的矛盾纠纷中,在不同精神世界的抗衡中,布兰琪的失败预示了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南方文明的脆弱和渐去渐远的哀歌。
二、人物设置的同构性
在品读两位剧作家的作品时,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除了取材的日常化、家庭化外,他们的剧作在人物设置上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中,无论是人物关系的架构还是人物的性格特点、情感际遇以及命运走向,都与契诃夫的《海鸥》和《樱桃园》非常相像,我们甚至可以很容易找到相对应的人物关系。
在《海鸥》和《玻璃动物园》中,家庭成员的设置非常相似。两个家庭都存在着父亲的缺失;母亲(阿尔卡基娜和阿曼达)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都靠回忆中的辉煌来慰藉眼前的落寞;儿子(特里波列夫和汤姆)都是未来的作家,他们都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和羁绊,和母亲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隔膜;都有两个美丽的、拥有美好梦想的姑娘(尼娜和罗拉),都有一个外来的“闯入者”(特里果林和吉姆)唤醒了她们孤独的灵魂,但随之带给她们的。却是更大的迷茫和失落。
首先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没有父亲的形象,而且在他们其他的作品中也多存在着父亲角色的缺失,即便出现也从不是主角。或许这与他们痛苦的童年记忆,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和父亲爱恨相交的关系大有关联。在契诃夫最为著名的四部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海鸥》和《樱桃园》里都是没有父亲这一角色的;《三姊妹》中的父亲不过是关于莫斯科回忆中的一个幻影;只有在《万尼亚舅舅》中出现了父亲的形象——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可他却是个庸庸碌碌、愚蠢透顶、没有心肝的寄生虫。在威廉斯的作品中也多存在着父亲角色的缺失。《玻璃动物园》中的父亲溫菲尔德先生不过是挂在墙上的大幅照片,再有就是阿曼达穿在身上的他留下的宽大的浴衣以及罗拉常听的留声机。可正是他的缺失或逃亡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空虚、混乱和苦难。在这里,剧作家借父亲的缺席预示了“美国梦”对人们的背弃,表达了在现代文明下家庭作为最后精神避风港的幻灭。
剧中两位母亲的形象(阿尔卡基娜和阿曼达)更是极为相似。在和儿子的关系上,她们各自都有着深深的隔膜,两部剧作中最尖锐的冲突都是发生在母子之间。阿尔卡基娜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任性的女人,是一个名声被宠坏了的演员。她过于陶醉在自己往昔的成功中,陶醉在那种肤浅、表面的幻象里。她对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在哈尔科夫,别人多么热烈地接待我,送给我多少礼物”。“我多么善于装扮,我穿得是特别好看的衣服”。对她来说,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已变得不重要了,不过是名声和浮华,早已失去了它的诗意和创造性。所以在精神上,阿尔卡基娜始终在嘲讽儿子的艺术探索,甚至连他的作品都从未看过。而阿曼达对汤姆的文学理想也是嗤之以鼻,认为儿子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在仓库里工作。在物质上,两位母亲也非常相似。阿尔卡基娜对儿子非常吝啬,有七万元存款却整天叫苦,说连给儿子买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而阿曼达与汤姆也经常围绕着房租、电费等日常开销发生冲突。在爱情上,两个女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喜欢卖弄风情,都具有表演天赋。公众场合阿尔卡基娜总是不忘炫耀自己,而阿曼达则数次提及当年一个下午接待十七个男客人的辉煌壮举,企图用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来忘却面前的痛苦,来换得心理的平衡和安宁。但是时代的冲击和自身的缺陷却使她只能黯淡下去。
此外,剧中的两对年轻人特里波列夫和汤姆、尼娜和罗拉在性格特点和情感际遇上也多有相似点。先看特里波列夫和汤姆。在《海鸥》中特里波列夫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文学青年,他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他不承认母亲阿尔卡基娜所献身的戏剧,认为是些可怜的、没价值的戏,说现代的戏剧是陈规旧套,是偏见。对知名作家特里果林的作品也同样不认可,觉得俗套,让人厌恶。他渴望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其实,特里波列夫否定的不仅仅是阿尔卡基娜和特里果林所代表的艺术观念,也不仅仅是因为对尼娜的爱情和他们相对立,而是在内心深处他就否定现存世界的秩序,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灵魂是如此的寂寞和无法安顿。所以,即便是在成功之后,他也没有从孤独和忧郁中走出。他始终害怕陷入艺术的陈规旧俗中,理想与梦幻中的东西是那样遥不可及,他依旧是一个失败者和失意者。再加上爱人尼娜的最后出现加速了他的这种幻灭感,最终只好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玻璃动物园》中的汤姆是个诗人,在仓库工作清闲时就偷偷躲进盥洗室写诗,因而被工友称之为莎士比亚。汤姆的性格特点,更多的表现为他的诗人气质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他虽然表面上浑浑噩噩,但内心却多愁善感,热血沸腾,“每当我拿起一只鞋,想到人生的短促和自己的无所作为就感到不寒而栗”。他渴望冒险,渴望到海上去扬帆远航;他羡慕魔术师在不动一颗钉子的情况下就能逃出封闭的棺材,因为对他来说家庭的重负就如那口棺材一样。和特里波列夫一样,汤姆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和我想要做的有多大距离!”可家庭的责任又让他无法逃避,只好经常去电影院在影片的光怪陆离中满足自己的幻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两个人在苦心经营的同时,都感到了精神上的失意和孤苦无依。
另外相同的是在两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两方面的激情:除了艺术之爱,还有女性之爱。在特里波列夫表现为对尼娜的执着爱情。尽管尼娜离他而去,可两人最后见面时他的爱情表白是那样深挚动人:“尼娜,我骂过你,恨过你;我撕过你的信和照片,然而我时时刻刻都知道我的心灵是和你永远连在一起的。我没有能力叫自己忘记你……我呼唤着你,我吻过你走过的土地;不论我的眼睛往哪儿看,我都能看见你的脸,看见你那么温柔的微笑,在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刻照耀着我的微笑……”在汤姆则表现为对姐姐罗拉的深深眷恋和怜惜。在陌生城市的街头,那些彩色的玻璃小玩意儿让他的牵挂喷涌而出:“哦,罗拉,罗拉,我本想把你丢下,但我比原来更忠于你。”这两种爱可以说是他们心灵中的两个顶峰,是他们梦幻的根基,也是他们孤独的源头。在《海鸥》中特里波列夫留下了,离开的是尼娜;在《玻璃动物园》中罗拉留下了,离开的是汤姆。但无论谁去谁留,横亘在心中的,都是那青春的孤独和梦幻,都是热情燃尽后的忧郁和凄楚。
尼娜和罗拉都是剧作家钟爱的女性,对她们的美丽都极尽描述。尼娜的美是热烈奔放,即便是整天自我欣赏的阿尔卡基娜也不由得赞赏,认为拥有那么美的容貌和声音却埋没在乡下简直是犯罪。而罗拉的美是娇弱脱俗,“像一块在阳光照耀下透明的玻璃,放射出一种不真实的瞬息即逝的光辉。”在特里果林和吉姆进入她们的生活之前,尼娜和罗拉都生活在各自的私人世界里,尼娜如一只快活单纯的海鸥;罗拉则沉浸在玻璃世界的晶莹剔透里。但在这个私人世界里,都有一个男人隐身其中。尼娜是那么崇拜特里果林,特里果林在她面前犹如一个崭新的世界,好像通过他,某种未知的无人走过的新路就在她脚下。而罗拉则一直在心里暗恋着中学时代的同学吉姆,就像尼娜记住了特里果林所有的作品一样,罗拉也珍藏着和吉姆相关的文章、节目单和剧照等。在吉姆到来之前,罗拉封闭、自卑,像玻璃动物一样敏感易碎,是吉姆让她认识到自己的美丽和与众不同,就如吉姆所言:“他们平平凡凡——像野草一样,而你——你是蓝玫瑰!”吉姆给了罗拉自信和勇气,罗拉不再羞涩了,罗拉会跳舞了。如同特里果林给了尼娜一个演员的梦想一样,吉姆也给了罗拉一个爱情的梦想。
但梦想毕竟是梦想。当特里果林的感情冲动化为乌有之后,当吉姆承认自己的唐突之后,尼娜和罗拉面临的就是梦想破灭之后更加沉重的孤独和失落。尼娜就像那只海鸥,本想高蹈于波浪之上,却一下被生活剪断了翅膀。但幸运的是尼娜并没有绝望,在梦幻的碎片中她仍能看到亮丽的光泽,在随剧团四处奔波中她更加成熟了。她对特里波列夫说:“我思想着,思想着,于是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一天比一天坚强了。”而一向脆弱的罗拉也变得坚强了,当吉姆不小心打碎了她钟爱的独角兽时,她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哭,而是说:“我并不太偏爱这个,这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件小事。”她把那只珍爱的已经变得平凡了的独角兽送给了吉姆。罗拉对玻璃动物态度的改变可以折射出她心灵的变化,她不再像蜗牛那样缩在自己的壳里了。吉姆的离去同样使罗拉失望,但剧中写到:“她咬紧她那颤动的嘴唇,然后勇敢地笑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历了情感的风暴之后,罗拉也许会像尼娜一样,勇敢地走出自己的玻璃人生。
如果说《玻璃动物园》对《海鸥》的借鉴还只是表面的人物关系的相似,在具体的分析比较中,我们会发现《欲望号街车》对《樱桃园》的学习则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它们不仅在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相似,如郎涅夫斯卡娅和布兰琪,罗伯兴和斯坦利,而且两部作品都以古老庄园的失去为线索,以善良、优雅的贵族女子的命运起伏为主线,以此向我们昭示了旧的、美好的事物在残酷现实面前所遭受的摧残以及它们在新时代面前必将逝去的哀歌。在人物共同的命运中,我们会明显感觉到后者带有前者的影子。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辞世之作。在这个剧作中,作为现实主义的戏剧大师,契诃夫在简单平凡的情节中揭示了深刻的主题。他以樱桃园主人的更替为题材,反映了俄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其中美丽的樱桃园几乎就是主人公郎涅夫斯卡娅的象征,它的命运就是主人的命运。关于这个剧作,契诃夫曾说过:“在这个剧本中,中心角色是女性,是一个老年妇女,她的一切都在昔日之中,而在今天她什么也没有。”[3]
剧作从郎涅夫斯卡娅从法国归来开始。她善良、单纯、慷慨,但除了挥霍浪费、寻欢作乐外,几乎什么也不会做。她在法国呆了五年,先是挥霍无度,后靠举债度日。而在此之前,她也是“瞎糟蹋钱”,在丈夫死于酗酒,儿子又不幸溺死后,她随情夫私奔,没想到情夫在把她的钱“抢个精光”后又抛弃了她,以至于她想服毒自杀。最后她只好变卖了在芒东的别墅,一身空空地回到了即将被出卖的樱桃园。美丽的樱桃园充满了她童年的回忆和往昔的荣光,她甚至说如果要卖,那就连她自己一块儿卖。可就在这种困境中,她依旧挥金如土,与加耶夫一起进城用午餐,雇请犹太乐队来演奏举行舞会,在家里的老佣人几乎没饭吃的情况下,还给醉醺醺的流浪艺人一个金币……更可怕的是,她没有丝毫责任感,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寄生性,意识不到自己是靠别人来生活的。所以她才会在落寞时孩子般地回忆“童年,纯洁的童年”,会感伤地称呼那些家具:“亲爱的小柜子”、“亲爱的小桌”,会在离去时对出卖的庄园说:“再见,亲爱的房子,年老的爷爷”,“啊,我亲爱的、精致的、美丽的花园!……我的生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永别了……永别了!”这些温情的伤感在如此困境中实在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当然在契诃夫笔下,郎涅夫斯卡娅又是非常善良和充满诗意的。她年轻时曾帮被粗暴的父亲打破鼻子的小罗伯兴清洗和包扎,并同他开玩笑说:“到你结婚的时候伤就会好的。”这种和善的态度使罗伯兴一直感恩不尽。郎涅夫斯卡娅对老仆人费尔斯也是关心的,在离家之前的一件心事就是如何安置好病重的费尔斯,在安尼雅告诉她已将费尔斯送进医院后才放心。她也的确钟爱自己的樱桃园,清晨那段对樱桃园的致意是那么美,那么伤感,可是这种多情挡不住樱桃园被拍卖的命运。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它的新主人竟然是以前庄园农奴的后代,新兴的资产商人罗伯兴。剧终斧子砍伐树木的声音是那么沉闷、凄凉、悲怆,犹如朗涅夫斯卡娅重回巴黎后的命运,犹如一首没落贵族渐行远去的挽歌。
《欲望号街车》是威廉斯早年最富盛名的作品。在剧作中他塑造了布兰琪这一典型的美国南方女性的形象。在威廉斯幼年生活的时代,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同时,种植园主为掩盖剥削的真相,臆造了浪漫的优美的“南方神话”,它渐渐成了南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神话”常常展示给人们这样一幅平静柔美的画面:温和的老主人仁慈又威严,在田间劳作的黑人快活又忠实,美人风情万种,绅士彬彬有礼,空气中充满了浪漫的爱的气息。这种氛围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内战前南方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了显示自己与北方佬的不同,故意夸大了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来自战后,当时的南方非常需要一种支撑人们思想的信念。于是,人们便把生活加以浪漫化,给原本平淡的生活罩上了一层理想的光环。
在这种田园设想中,南方女性是种植园神话的核心。南方传统以家庭为中心,重视家庭利益,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则是家庭的中心。在人们的想象里,她们往往被描绘成虔诚、正直、优雅、好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作为众人的典范而倍受尊敬。尤其是那些未婚女子更是引人注目,传说中她们大都具有美丽的容颜,纯洁又娇弱,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婚前,她们可以有很多的追求者,追求者越多说明这个女子的魅力越大。每天在如诗如画的庄园里谈情说爱,和众多的追求者周旋几乎成了她们日常生活的主题。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广为人们接受,但与真实的生活相比却有很大的差距。婚后,作为妻子和母亲,女主人往往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她们既要料理家庭琐事、照顾子女,又要竭力维持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社交场合做一名淑女的典范,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和操劳中很多人一生也达不到南方神话中所描绘的那样高的境界。尤其是在南北战争后,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北方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开始无情地冲击南方优雅的骑士精神和浪漫风情,这时,南方固有的传统观念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在物质优势丧失的同时,它既不能保存自己原有的文化思想,更不能保护在这样的氛围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南方女性。
田纳西剧作中所描写的正是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南方女性。正如《田纳西·威廉斯》这本研究专辑中所说的:“所有这些形象都是对具有和维多利亚时期相联系的文化和高尚行为而又遭受挫折的妇女的研究,这种文化和高尚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不复存在。这些女性比家庭主妇和爱叨唠说闲话的更优雅一些。伴随这种淑女的优雅也产生了一种矫揉造作,这种矫揉造作有时只是一种热情……她们都脱离了周围的环境,生活在自己臆造的世界里,做一个关于她们魅力的温柔感伤的梦,或是一个关于她们过去的和男人成功周旋的梦。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她们自身的矛盾,她们觉察不到自己不合适的举动。”[4]《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琪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布兰琪·杜波伊斯,在法语中意为白色的森林。她美丽、高雅、敏感又脆弱,她一出场,身上就穿着洁白高贵的衣服,束着一条柔软的腰带,和周围肮脏嘈杂的环境极为不协调,剧本的舞台提示说:“犹如一只纤弱的白蛾。”她早年生活在一个有着高大白色圆柱的庄园,享受着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时光,是个喜欢幻想,娇巧又躁动不安的美女。除了仪态万方、举止高雅外,南方的传统还要求她洁身自好,做一名淑女的典范,这就使得她一直崇尚纯洁和美好。但十六岁时她深爱的丈夫因被窥破是同性恋而羞愧自杀,这成了她终身挥之不去的阴影。再加上因父母相继去世,庄园无法维持而不得不出卖给别人,她那种悠闲的生活也随之而去。为摆脱恐惧和孤独,她开始在“欲望”的驱使下纵情声色,靠不断与陌生人幽会来弥补生活的空虚,结果在当地声名狼藉无法容身。后来又因为和一个十七岁的男生厮混被学校开除,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教职,最后她不得已来到了具有现代文明的新奥尔良妹妹家。在这里,往日的情愫使她无法面对肮脏的现实。她用纸质的灯笼罩上灯泡,尽量让自己躲进阴暗里;她一次次的借助水疗妄图洁净自己、缓解神经和压力;她编织一系列的谎话来蒙蔽他人也蒙蔽自己,想以此来躲避现实,隔绝自己;她想让妹妹斯蒂拉和自己一起离开斯坦利离开“陷阱”,不成之后又想竭力改造妹妹的生活环境;她想让米奇娶自己,哪怕暂时过上有所依靠的生活……可是在强悍、粗野、无情地追求肉欲和物质利益的斯坦利面前她还是很快败下阵来。她的逃避无法解决这一对立和冲突,她的努力遭到的只有嘲讽、迫害和更深的伤害,最终她只能退出这个世俗的现实世界,遁入她永远的庇护所——精神病院中。布兰琪的悲剧命运,向观众揭示了一个同样深刻的主题,那就是:在工业化商业化的大潮中以布兰琪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已在斯坦利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折磨和蹂躏下逐步走向崩溃。正如威廉斯自己所说该剧表现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弱肉强食,野蛮和残忍的强者蹂躏了温柔和优雅的弱者”。[5]布兰琪正是这样一个脆弱的、不合时宜的旧南方的牺牲品,她以自身的坎坷和不幸,书写了一曲旧南方的挽歌。
和两位命运凄惨的女性不同,在两位剧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安于现状的胜利者,那就是《樱桃园》中的罗伯兴和《欲望号街车》中的斯坦利,正是他们的强大和胜利昭示了前者的没落和失意。
在《樱桃园》中罗伯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与多愁善感、不讲实际的贵族老爷太太不同,他是个从乡巴佬起家的人,务实、冷静、明智,梦想着能像巨人一样拥有广大的创造气魄。他说:“有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我就想到:‘主啊,你赏赐给我们巨大的森林、广袤无垠的原野、辽阔无际的疆界,生活在这种地方,我们也应该像巨人一样神通广大才行啊……’”因此,他一心扑在事业上,从早到晚忙着给自己、给他人管钱,甚至连爱着他的瓦里雅也顾不上。另一方面,尽管他有“纤细而柔软的指头,像艺术家的指头一样”,他有“敏锐而细腻的灵魂”,但是他的生活纲领却是和诗情画意截然相对的。在朗涅夫斯卡娅心目中美丽的充满童年回忆的樱桃园,在罗伯兴眼中不过是一块可以砍伐利用的宝地。正如他极力劝说朗涅夫斯卡娅的:“而且我敢说,再过二十年,别墅的住客一定还会增加好几十倍的。现在,他们不过在露台上喝喝茶罢了,可是以后总有一天,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一份地来耕种的,那时候,您的樱桃园就要变得兴旺、富足、茂盛了……”所以在购买樱桃园这一事件中,罗巴辛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特点。虽然他声称自己爱朗涅夫斯卡娅比对亲人还亲,但为了他的宏伟大业,还是不惜重金立即买下樱桃园。尽管当他看到朗涅夫斯卡娅失声恸哭,也觉得尴尬不堪,噙着眼泪说:“啊,但愿这一切早些结束,让我们这种支离破碎的不幸的生活快点改变一下吧。”但这种感伤并没有妨碍他立即开始砍树,开始他的宏伟计划。且在朗涅夫斯卡娅离开前就开始动工,完全置私人感情于不顾。正如剧中特洛菲莫夫形容他的那样“是一只碰见什么就吃什么的猛兽”,说罗伯兴这种人之所以需要,是为了“新陈代谢”,是为了完成短促的历史作用——尽量帮助破坏那已经衰亡的东西。的确在生猛肯干的罗伯兴身上完全体现出没落贵族被取代的必然。当然,契诃夫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罗伯兴和旧时代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不可能成为未来的代表,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特洛菲莫夫和安尼雅身上。
在《欲望号街车》中,斯坦利则是与布兰琪相抗衡的现实世界的代表。他是一个普通的钢铁工人,说话粗鲁,态度野蛮,时常把鲜血淋漓的生肉带回家来。在贵族小姐布兰琪看来他简直就像是一个石器时代的野人,“他的举动像禽兽,他有禽兽的习气!他吃饭、举动、说话都像禽兽!”他自称是“这一带的王”,谁也不能违抗他的意志,具有十足的暴力倾向。他有两个特点:一是纵欲,一是爱钱。他把钱看作是通往幸福之路的关键,认为只有钱才能满足他生活的需要,得到生活的享受。很明显,他与布兰琪是截然不同的人,所以她一在他家露面就引起了他的反感,甚至是敌对情绪。他憎恨布兰琪,一方面是他认为布兰琪挥霍了应该属于他的妻子家的财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憎恶她的高雅,她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优越感严重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他必须要把她拉下来,就如同他曾经将斯蒂拉从白色的柱子上拉下来一样。为此,这个男人使出了浑身解数:摔碎了布兰琪正在听的收录机,撕下了她特意罩上的纸灯罩;无数次的言语侮辱,暴力恐吓;还花费心思去采购员肖那儿刺探布兰奇的隐私,调查她的丑闻,并告诉了对布兰琪有好感的米奇,导致他们关系的破裂;随后更进一步借布兰琪生日之机,送她一张返程的车票,把她驱逐出门;更甚的是在妻子住院期间强行奸污了布兰琪,彻底摧垮了她的精神。就这样,这场南北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冲突最后以斯坦利的胜利告终,同时也意味着以布兰琪为代表的南方贵族的彻底败落和消亡。它就像一首凄楚的挽歌,揭示了南方种植园文化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悲剧。
一个是时代更替中贵族之家分崩离析的挽歌,一个是工业文明冲击下贵族小姐穷途末路的哀歌,借此两位剧作家想告诉我们的:尽管美的逝去会让人觉得哀伤和惋惜,但当历史风云变幻时,如果还紧紧抓着固有的、传统的东西不放,势必会遭到毁灭的命运。唯一不同的就是在《樱桃园》中虽然郎涅夫斯卡娅落寞离去,但在安尼雅、特罗非莫夫等人身上剧作家却预示了新生活的光辉和亮色;而在《欲望号街车》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剧作家对美逝去的痛惜和对旧南方的深深怀恋。
当然,在对两位剧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威廉斯对契诃夫的学习和借鉴除了题材选择的日常化和人物设置的同构性,他们的剧作在艺术手法上也颇有相似之处。尤其是诗意氛围的营造、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及心理刻画的手法在他们的创作中都非常突出,成为他们揭示人物内心矛盾、推动情节发展与深化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但是由于个性气质的相似和直觉上创作手法的相似,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谱写了一曲没落失意者孤独与梦幻的挽歌,同时又不乏希望的光辉,并以此告慰个体在生命悖论中的挣扎与无奈。
注释:
[1]Tennessee W illiams, Memoirs [M],Carden City:N,Y,Doubleday,1975, p41.
[2]《契诃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3]朱逸森,《契诃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4]陈凯,《从田纳西的三部名剧看美国南方女性的悲哀》,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5]谢榕津译,《当代美国剧作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