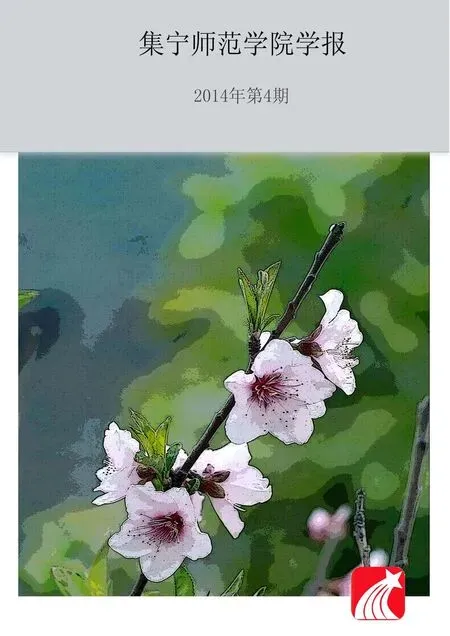明末丛林寙败之考辨与析疑
2014-04-17刘晓玉
刘晓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河南 郑州 451000)
明末丛林寙败之考辨与析疑
刘晓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河南 郑州 451000)
明末佛教丛林窳败,积重难返,一方面佛教僧团内部修持不力,持戒混滥;另一方面国家设教未尽善,政令反复无常。揆诸史实,国家不恰当的宗教管理方式正是导致明末佛教丛林窳败的直接原因。
明末;丛林窳败;政令析疑
明末的佛教僧团领袖以智旭、圆澄为代表,他们以振济颓纲为业,著文痛陈佛教丛林内部师徒无谊、戒仪不张、修持不力的种种窳败之境,今人据此可明晰当时佛教僧团之状况。若欲探究当时佛教丛林衰败的根本原因,还必须将之放诸于中国政权大于教权的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以此审视进而辨析国家宗教管理政策对佛教丛林造成的直接影响。
一、丛林积弊难返
明末四大士之一的蕅益智旭(1599-1655)曾在自传中言及:“二十七岁,遍阅律藏,方知举世积讹”,①当时律师少有师承者,精严律学、严持律仪更是无从谈起;所谓教门也只是依文解义,图一时言辞快意,未在心地上悟入知解;而禅宗门人要么狂罔无知,要么落入知解偏见,更有盲修害炼者落入窠臼而不自知。而智旭所哀之事,一则,本无佛心佛行之人借佛法图名求利;二则,缺乏远识,无参究向学之心;三则,自高自大,轻视净土修行。智旭针砭的出家者笈笈于名利以及禅、教、律三宗之士的种种偏谬之处反映出了当时佛教丛林的问题。非独智旭,与其同时代的曹洞宗湛然圆澄禅师(1561-1626)也曾撰《慨古录》一文,描述了当时“去古日远,丛林之规扫地尽矣”②的佛教僧团寙败景象。
其一,师资关系。“是以前辈师资之间,亲于父子,今也动辄讥呵”,③师徒间关系不睦,信任度不高,一方面缘自为师者品行不端,有载“今之师僧,见弟子有英俊之资,便乃关门就养,不许其动步。何也?恐近好人,不附于我也”,④为师者品质低劣,难怪学者疑惮;另一方面缘于为弟子者非真心向学,不知礼敬师长,“今时沙门,曾不见为真灯故,回礼为师。或慕虚名,或依势道,或图利养,或谋田宅,或于本师闻气,弃旧从新,回礼于他,旧师眇然视为闲人”,⑤如此拜师,掺杂了太多的现实功利。另有求学者,“或师范诫训过严,或道反议论不合,便欲杀身以报之也,或造揭帖,或捏匿名,徧递缙绅檀越,诱彼不生敬信”下,⑥如此行径毫无师徒情谊可言。
其二,僧品低下。圆澄指出当时丛林中“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⑦这些人出家动机不端,只为了逃避世俗压力而寄佛门谋衣食。在圆澄看来,正是这些人混入佛门才造成了僧品芜杂、丛林败落的局面。
其三,学养低下。住持、首座乃僧团的领众者,其修为高低直接决定了僧团的整体素质,乃至佛教的兴衰。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明末佛教丛林领众者的整体素质令人堪忧。根据明朝的皇家礼俗,在新皇即位之初,会遴选童子作为他的替身出家修行,所建皇寺梵刹,也由这名童子担任主持。如果说在皇权干涉下,由童子担任住持的现象属特殊情况,影响范围还不大,但若根据圆澄所述的情况,可知当时佛寺住持整体素质之低下:“前代住持,必推一方有道德者,有司推举,朝廷勅住,或为世主知名,持诏演道,由是千百共居,人不之疑。今也不然,才德一无所有,道学有所未闻,世缘颇足,便名住持,致使丛林衰落,礼义绝闻。更兼官府,不辨清白,动辄行禁,使真道者退身不就,而不肖者百計攒谋,佛法愈衰,丛林愈薄。复有屑屑之徒不知大体所开,才出家来,苟图声誉,以为己任,急急于名利之场,或私创山居,或神庙家祠,男女共住,或典赁民房,漫不可稽”。⑧有真道者退身不就,主持之位成了钻营之辈追逐名利、地位的方便,长此以往,佛教怎会不衰败呢?
其四,悟解不力。过去的讲僧因各依教判,所以才有所专精,今之讲僧看似无经不解,无典不通,实则专精悟入的程度不及前人。“古之为宗师者,高提祖印,活弄悬拈,用佛祖向上机关,作众生最后开示,学者参叩不及处劝其日夜提持,不记年月,然后悟入。今之宗师依本谈禅,惟讲评唱。大似戏场优人,虽本欲加半字不得,学者不审皂白,听了一遍,己谓通宗,宗果如是易者,古人三二十年参学,竟为何事,岂今人之根,利于古人耶?由是而推,今之谈宗者,实魔所持耳”。⑨依圆澄所见,当时所谓修禅之宗师照本宣科,落入文字功夫者众,真正悟入心地者鲜有其人。
其五,不谙律仪。戒为三学之首,持守戒律乃出家僧人的本分,然值明末之际,佛教律典久已废弛,出家受戒者大多不谙律仪,整个僧团在戒律守持方面不尽人意。据圆澄所述,“古之出院者,为众所弃,名同死罪,律制被弃比丘,不与同宿,犯波逸提,被弃者愧,不敢立于人前。今时沙门,视丛林为戏场,眇规矩为闲事,乍入乍出,不受约束”。⑩依“八敬法”,纵然是百岁比丘尼见到二十岁的新戒比丘,也应礼敬供养,然当时丛林中出现的“拜女人为师”、“女人受沙门礼”的现象不仅反映了佛教戒律“八敬法”的废弛,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比丘尼在佛教僧团中地位的提高。而“波罗夷”、“波逸提”属比丘、比丘尼所应持守的基本戒条,其中“波罗夷”还属戒律中的最重之罪,一旦违犯,将被永远摈除在僧团之外。所以根据文献记载的明末丛林的持戒情况,可以推知当时的僧人要么是不通律典,不谙律仪,要么就是无视戒律,知戒而不持,想必不通戒律而难持戒者众。
二、政令反复无常
英宗正统年间,因皇帝个人的侫佛倾向,国家开始更改宗教政策且有违明初的政令精神,是明代宗教政策随意变更的开始。英宗之后的诸帝常因个人宗教倾向和政治认识的不同更改前朝法令,宗教政策表现出一朝被废,一朝复兴的特点,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
洪武朝是明朝国家宗教政策制定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家对待佛教的基本态度取向,国家管理佛教僧团的僧官制度,有关度僧的数额、度僧的条件、寺产数额等相关政策也都在这一时期订立完成。从具体的条文可知,明太祖时期对待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控制加利用,一方面,严格限制出家人的数量、性别、年龄以及僧俗之间的交往,避免其对社会生产,政治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又愿意扶植佛教的发展,以图利用其“阴翊王度”、“暗助王纲”的政治效用。太祖之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也基本延续了洪武时期的宗教政策和态度倾向,只是其中的永乐皇帝表现出了对西藏喇嘛教僧人的特别尊崇,但是这三朝在度僧给牒方面都是理性且有节制的。
由英宗执政的正统朝和代宗执政的景泰朝是国家宗教政策由理性、节制向非理性、不节制演变的转折点。正统元年至正统六年间,国家度僧,数额巨大。与明初相比,国家度僧政策之所以发生转变,乃因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侫信佛教,他以其个人因素影响了当时的国家政策。到了正统后期,国家又相对加强了对佛教的管束,并多次强调“通过考试”乃得度的条件。至景泰朝,代宗也如英宗一般崇佛,自景泰二年(1451)起,国家变更度僧制度,僧人得度的条件不再是通过考试,而是缴纳钱粮,之所以实行此政策乃因正统十四年(1449)国家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蒙古瓦剌军掳走。此后连年不断的边疆战事和政治赔款造成了国家军费、粮草的紧张,为弥补亏空、供给钱粮,国家实行鬻牒度僧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标志着自洪武时期开始实行的给牒蠲“免丁钱”政策的废除。
自宪宗成化朝到世宗嘉靖朝为明朝中期,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国家在度僧、控僧、寺产等方面的宗教政策又有重大调整和演变,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明朝后期的佛教发展走向;嘉靖之后隆庆、万历两朝直至崇祯亡国为明朝后期,这一时期以神宗统治的万历朝时间最久,占近五十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直接决定了明朝末年的佛教环境和境遇,是明末佛教最为重要的时期。
三、设教肆意无度
圆澄于《慨古录》中提出的“国家设教未尽善”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宗教集会,二是度僧制度,三是僧官制度,四是赋役制度,以下将逐一对其进行分析。
其一,禁止丛林讲经集会。明初,国家并未禁绝丛林集会,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还专门颁旨令“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僧俗善人许令斋持戒牒随身执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他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⑪值明中叶嘉靖朝时期,民间白莲教一度活动猖獗,为防止白莲教徒利用宗教集会混入其中,挟惑媚众,危及政权,嘉靖二十五年(1546)政府下达禁令,要求“聚众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⑫。红、白莲教属于宗教外衣包装下的反政府组织,其神秘且颇具煽动力的表现形式使得生存于乡野之中的下层民众易受蛊惑,历来为政府所禁绝,国家为了防范白莲教,故而禁绝了一切形式的宗教集会。
其二,废除考试度僧制度。明初,洪武十年(1377)国家定例《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经为僧人必须通达的经典,若欲出家为僧者,必须先参加国家组织的试经考试,通过者方给牒披剃,不过者责令还俗,⑬直至明正统年间,国家也是通过考试给牒度僧,沙汰沙门。值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曾令“僧道赴四川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⑭,从而打破了先朝考试度僧,免费给牒的制度,至明末则以“立例上银”为定例了。⑮较为严格的考试度僧制度,不仅是国家控制人口流失,保障社会生产、人口繁衍的有效举措,也维护了佛教僧团的纯正性,而纳银即可得度的政策,最终造成丛林“无名之流,得以潜之,然则此之流类,满于天下”的局面。⑯
其三,僧官选拔制度流弊甚大。作为官僚制度的一部分,明代的僧官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洪武元年(1368),太祖皇帝曾命浙江之东西五府的名刹住持,聚集南京,于天界寺设立“善世院”,掌管天下僧务,当时德高望众的原璞禅师,独出方略具有条叙,所提纲文、条款在全国推行,⑰这是明代僧官的雏形,整个制度、纲领的构建完全由僧人参与完成。值洪武十四年(1383),礼部颁旨曰:“释道二教流传已久,历代以来皆设官以领之。天下寺观僧道数多,未有总属,爰稽宋制,设置僧道衙门以掌其事”,⑱至此明代正式设立了掌管僧务的政府机构。具体部署是:在京城设置僧录司,掌管天下僧教事。设善世二员,正六品,左善世、右善世;阐教二员,从六品,左阐教、右阐教;讲经二员,正八品,左讲经、右讲经;觉义二员,从八品,左觉义、右觉义。在外布政府、州、县,各设僧纲、僧正、僧会,分掌其事。其中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教事;各州僧正司,设僧正一员,掌本州僧教事;各县僧会司,设僧会一员,掌本县僧教事。整个衙门的设置,沿袭宋制,官不支俸。⑲出家人既要遵守佛门戒律,同时还要受到国家律令的管束,界限就是所涉事务属僧对僧事,还是僧涉俗事。所谓“在京、在外僧道衙门,专一简束僧道,务要恪守戒律阐扬教法,如有违犯清规不守戒律,及自相争讼者,听从究治,有司不许干预。如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情,重者送问,在外即听有司断理”。⑳从明初制定的典章来看,僧官对教内事务的管理还是拥有较大自由的,举凡出家僧人户籍的考查,经文考试的组织,度牒的审核、发放等相关事宜都由僧官处理。㉑然而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当时的僧录司右善世南浦,左阐教清让两位僧官涉嫌在京城正式度牒审查资格中舞弊贪污,当时的礼部尚书胡潆上奏遣给事中、御史、礼部官各一员,公同考审。㉒自此之后,明代僧官就失去了自行审核出家资格的权限。
其四,出家反累于俗。明初“太祖于试度之外立例:纳度上银五两,则终身免其差役。超然闲散,官府待以宾礼”,洪武十九年,又“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设砧基道人,一应差役不许僧应”,㉓“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烦难答应官府,并在此人。其僧不许具僧服入公听跪拜”。㉔可见,按此典章行事,明初的僧人不仅没有劳役之苦,还可受官家礼待。出家人赋役制度的改变,始自嘉靖三十九年起(1560),出家人不仅要按例纳度上银,还要缴税、承担徭役,㉕所谓僧事、俗事无不牵涉其中,出家反累于俗。
结语
由上辨知,自明代中后期始国家的宗教政策常随着帝王的个人倾向代有变更,在整个过程中排佛的士大夫、受宠的僧官、侫佛的宦官、崇佛的帝后各种力量牵涉其中,制定政策急功近利,更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对一些宗教问题的处理也过于简单、粗暴。应该说在以维护政权为第一要义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佛教始终是处于被动地位,国家宗教管理的不恰当正是导致明末佛教丛林窳败的直接原因。
注释:
①〔明〕澫益智旭大师自传,《灵峰宗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⑮⑯㉔〔明〕圆澄,《慨古录》,《卍续藏经·册65》,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分别引自第366页,第367页,第371页,第374页,第373页,第369页,第368页,第371页,第373页,第368页,第368页,第368页。
⑪⑬⑱⑲⑳㉓〔明〕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大正藏·册49》,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分别引自第929页,第928页,第939页,第931页,第931页,第934页。
⑫㉕〔明〕徐阶,《明世宗实录·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3年版。
⑭㉒〔明〕孙继宗,《明英宗实录·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3年版。
⑰〔明〕如惺,《大明高僧传·卷3》,《大正藏·册50》,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609页。
㉑〔明〕葛寅亮,《卷2钦录集〈金陵梵刹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36册),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220页。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Doubts concerning the Buddhist Corruption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U Xiao-y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He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Zhengzhou 451000,Henan)
The severe corruptions in the circle of Buddhists are hard to be chang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1368-1644)for the two reasons-one is the ineffective spiritual practice of Buddhists and the misuse of Buddhist disciplines and the other,the capriciousness of governmental decrees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 system of that dynasty.By referring to the related historical facts,it is known in the paper that the inappropriate mode of the national religious management is directly contributive to the cause of the corruptions in the circle of Buddhists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late Ming Dynasty;corruptions of Buddhists;analysis of the doubts of governmental decrees
B21/2
A
2095-3771(2014)04-0058-04
刘晓玉(1983-),男,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宗教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