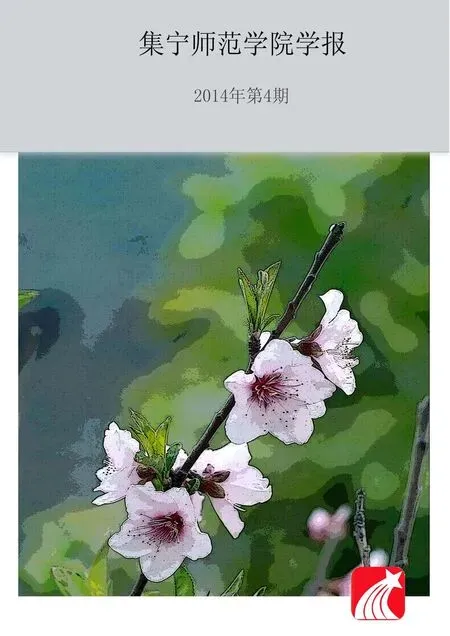清末察哈尔右翼地区的移民垦荒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014-04-17何学慧张军王英维
何学慧 张军 王英维
(集宁师范学院政史系,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清末察哈尔右翼地区的移民垦荒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何学慧 张军 王英维
(集宁师范学院政史系,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清统一蒙古之后,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推行“新政”。新政期间,调整了对蒙政策,代之以“放垦蒙地”,使持续了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不攻自破。内地民人大规模迁入蒙地,察哈尔右翼的前山地区成了规模较大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盲目垦殖,粗放经营,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致使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清末新政;察哈尔右翼;放垦蒙地;生态环境
清代察哈尔地区是我国北部边疆游牧少数民族活动的主要区域。1675年(康熙十四年),清政府将察哈尔编为左、右翼各四旗,实行总管旗制。分布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是察哈尔右翼四旗。
清政府统一蒙古地区之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稳定边疆地区的政治秩序,实行封禁政策。从顺治开始,历经康熙、雍正等朝,清廷颁布了一系列内地汉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①谋生的禁令,但屡禁不止。据《口北三亭志》记载,1724年 (雍正二年),“自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②察哈尔右翼四旗垦地已达29709顷。③乾隆年间,移民趋势持续发展,内地民人冲破禁令出口外垦荒谋生,致使察哈尔右翼的前山地区已成为规模较大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清末,内地民人向察哈尔右翼地区大量迁徙定居,达到高潮。内地民人的大规模迁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区域农业的发展,满足了牧民的粮食需求,同时也解决了大量出塞饥民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内地移民对该区域大规模垦殖,采取粗放式经营,使脆弱的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④
一、清末移民垦荒政策的实行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逐渐调整了对蒙的封禁政策。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每年需支付赔款二千余万两,本息相加,共支付高达 4.5亿两的赔款。这个空前庞大的数额使原本捉襟见肘的清政府财政更加枯竭,再也无法恪守旧制,于1901年1月29日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决意变法,施行“新政”。在察哈尔右翼四旗推行的“新政”主要是“移民实边”政策。“移民”就是将内地的大批汉族农民移向边疆地区垦殖;“实边”就是通过屯垦充实边防,抵御外敌入侵。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招牌,真正目的是想通过“移民实边”政策,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填补早已枯竭的财政。正如山西巡抚岑春煊对蒙地奏请开垦以筹款项所言:“臣维现在时局艰难,度支竭蹶,兵费赔款之巨,实为历来所为未有。……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地方旷衍,甲于朔陲。……若垦十之三四,可得田数十万顷。”“如开垦则对国家经济有益”,“是利国也”。⑤
清末政府“移民实边”放垦政策的推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迫于内地人口与土地的压力。清朝人口增长迅速,到鸦片战争前已突破4亿大关。在1887年至1912年的25年中,人口增加了21.03%。⑥人口的增长必然要求土地相应地增加,在1887年至1914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11.84% ,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仍很严重,人多地少致使人浮于地,游民充斥。⑦清末流入察哈尔地区的内地民人以山西人为主,直隶、河南、山东人次之。据记载,察哈尔地区“连日所经均系新辟之区域,居民多系山西大同一带渐次移来。侨寓年代,至远亦不过二十年以内。”⑧证明在清末放垦期间迁至察哈尔地区的汉民多数来自山西。当时,山西省人口逐年激剧增长,大致情况为:1661年(顺治十八年)有5758407人,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有6602921人,1724年 (雍正二年)有8246435人,1762年 (乾隆二十七年) 达到10239907人,突破1000万大关。此后,山西人口继续增长,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突破1200万,1783年 (乾隆四十八年)突破1300万,1812年(嘉庆十七年)突破1400万,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突破1500万,1856年(咸丰六年)突破 1600万,1877年(光绪三年)达到了16433000人的高峰。⑨在人口激剧增长的压力下,山西内地土地数量已不能供给激增人口所需的粮食。正如康熙所言“今太平已久,生齿甚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今在口外种地度日者甚多。”⑩于是,“移民实边”新政在蒙地推行后,极大地促进了移民的进程,内地大量过剩人口像潮水般涌入未经大规模开发的察哈尔右翼地区,使清前中期持续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不攻自破,取而代之的是“放垦蒙地”。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清政府委任兵部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负责开放察哈尔八旗及其属于西盟的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的蒙地垦务工作。贻谷赴任后,即着手组建察哈尔垦务机构。5月,在归化城设立督办蒙旗垦务总局,随后又设立办理管辖察哈尔右翼垦务事宜的丰宁垦务局;设立负责管辖察哈尔左翼的张家口垦务总局;设立负责管辖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垦务的西盟垦务总局。由此可见,放垦规模之大,正如贻谷本人所说,“经画三千余里,操纵二十余旗”。⑪10月,为了加强统治和推行垦务“新政”,保证放垦顺利进行,又将丰宁垦务局分为二局,一个是丰镇垦务局专管正红、正黄两旗的垦务;一个是宁远垦务局专管镶红、镶蓝两旗的垦务。同时,还在各旗建立了垦务局会办,具体负责各旗的垦务。
清末(1902—1911)10年的大规模蒙地放垦,贻谷率先全面放垦察哈尔土地,而察哈尔右翼又为最早放垦之地。为了加快放垦步伐,垦务局制定了统领全局的《察哈尔右翼垦务办法》章程。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清旧垦。察哈尔右翼地多数是私垦地,这些私垦地由地商“肆行其包揽侵渔之计”,大部分不交押荒和地租,需要速行清理。二是招新垦。明确规定王公牧厂 “将地归官勘办”,由各旗总管绘图注明若干苏木纵横里数及已垦未垦大致情况,并派员查勘,除“酌留随缺地及公共牧厂外,余均一律交出开放,该旗不得过问”。三是恤蒙艰。考虑到“蒙旗之穷日甚”,另加一些新办法以示体恤。“新放地,拟于每亩收押荒二钱外,加收办公银一钱,以六分作官局经费,四分作该旗协同办垦公费”。四是明确押荒升科办法。此办法参照山西省垦地的旧章,以360弓为一亩,每亩收押荒银2钱,办公银1钱;耕种3年后升科,其升科正项(王公马厂及官荒空闲地)每亩均征银1分4厘,遇闰每两加银2分,每正银1两随征耗银5分;王公牧厂每亩随征私租银4厘,官荒空闲地每亩亦加征归公私租银4厘,以充口外七厅经费。五是去地商、户总名目。“从前地商、户总有经手未报之地,无论已垦未垦,均饬遵照现办章程即行交纳押荒,以凭分别升科”。⑫
在《察哈尔右翼垦务办法》制定后,具体问题落实难以到位,头几个月办垦迟缓,为此,垦务局又出台了《现办情形及嗣后办法》作为补充,其主要内容是:①采取调动、控制八旗总管措施;②无定章前,先行查报缺、牧并区别民、蒙地价,给民户加价,以明示“恤蒙艰”;③打击地商。同时,在《清厘旧垦章程》中压缩了放垦期限,严定期限是:察哈尔右翼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9月1日起,每20日为一限,令三限呈报。⑬察哈尔右翼参照《垦务办法》章程,于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5月1日,由贻谷下令察哈尔蒙地一律交垦务局勘丈放垦,开始对荒地的垦种情况进行调查。规定已垦之地3个月内完成交纳押荒银,次年升科;新放未垦之地交纳押荒银后,试种 3年再升科。⑭并奏请将王公牧场除留下一定数量的牧丁养赡之地外,其余的“一律报效开垦”,⑮光绪予以批准。于是,察哈尔右翼四旗除留下官兵随缺地、公共牧场、牧丁养赡地等外,其余一律接受垦务局的勘丈,全部放垦。察哈尔右翼地区的放垦,是清理旧垦与开放新垦同时进行的。所谓“旧垦”就是“放熟地”,在清前中期的私垦官放中,察哈尔右翼地区特别是丰镇、宁远厅的大部分牧地已变为农田,至此时察哈尔已开垦土地约有2万顷,⑯大部分都是熟地。正如贻谷所言:“不垦牧地则无可垦矣,各旗所报半私垦熟地也,不垦熟地,则可垦亦无几矣。”⑰所谓“放新垦”就是指新放垦的土地。在察哈尔右翼地区放垦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旧垦地,征收押荒银和升科银,使地户不能逃避租赋,对蒙汉人民实行民族压迫和剥削。为此,丰宁垦务局还制定了具体放垦征收的实施办法:一是经官府批准的放垦,每亩交3钱押荒银;二是奉文准放而旗厅未丈明指交的,每亩交4钱押荒银;三是未经许可而是佐领、兵众等,年饥指地借银而无力偿还的,每亩按5钱交纳;四是地商、民人和蒙古兵弁,私买私卖的而佐领并不知情的,令其各还各债,实在无力偿还的,按每亩6钱核算给地。⑱这是对私垦地户逃避押荒、升科而私得利所采取的一种补偿措施。
通过以上“放垦蒙地”措施的实施,在察哈尔地区,无论是清丈旧垦还是开放新垦,都进行的较为顺利。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察哈尔右翼垦务局共放垦2.4万顷,其中,放过生熟各地1.4万顷,未经放垦地1万顷。至1904年(光绪三十年),察哈尔右翼垦务局共办结地13447顷8亩,总计共放地23879顷36亩。⑲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察哈尔八旗及其境内官私牧厂土地,已基本上清理丈放完毕。其中,察哈尔右翼四旗放垦土地约2.48万余顷。⑳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贻谷被革职时,察哈尔左右翼共放垦258456余顷。㉑据记载,清末(1902—1911年)10年间,开放察哈尔、绥远蒙旗土地79843顷,合532280公顷,㉒放垦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致使察哈尔右翼四旗地区形成“垦地日旷,牧场益狭……蒙民之生计日蹙”㉓的局面,现如今的商都、化德地区原有的畜牧业经济被农业经济所取代。
二、清末放垦后土地沙化严重
察哈尔右翼地区处在北纬39°30′—43°50′,海拔高度1000—1500M,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0℃—6℃,多风干旱,年平均风速2.5—5.0米/秒,年降雨一般在150—500毫米之间,年蒸发量1740—3000毫米,是中国北部边疆最重要的草原生态系统之一。到清末的全面放垦之前,该区域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牧民向来是以放牧为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曾是察哈尔草原的真实写照。
长期以来,以畜牧业为主的察哈尔右翼地区,放牧是对地表植被的自然利用,破坏性较小,再加上草原广阔,回转余地较大,可以避免牲畜对草场的过度啃食,从而有利于维持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平衡。但是,清以来随着内地民人蒙地垦荒的不断推进,移入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一方面允许和鼓励蒙古王公自由招垦,另一方面出面主持开垦事务,劝诱蒙古王公报垦土地,导致牧地渐少,耕地日增,使昔日一望无际的草原只剩下不连片的孤岛。牧民由于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草场而濒临破产,迫使他们不得不将游牧生产与粗放的农耕生产结合起来,渐渐地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到清后期,察哈尔右翼四旗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开始瓦解,农耕已成为该区域的主要经济。20世纪初,今乌兰察布地区大青山的后山地区已形成“沿途多汉民耕种,渐成村落”“路旁多垦地,蒙汉杂处”㉔的局面。
不可否认,蒙汉交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该区域的经济开发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是,清政府对涌入蒙地的民人缺乏统筹安排、统一规划,往往大多集中于适宜耕种的所谓“荒地”。在清末10年的放垦过程中,所放垦的“蒙地”被视为是蒙古地区的荒地。所谓“荒地”,是相对于内地农民而言,对可耕种而不去开发利用的未耕种土地的称谓,即将许多优良牧场当作“荒地”。但对于牧民来讲,被视为“荒地”的大面积草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只有寸草不生的荒漠才是真正的荒地。然而,清政府在“天下大利必归于农”的主观意识驱使下,以收取“押荒银”应付庚子赔款,填补赤字日巨的国库,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为直接目的,而不顾牧民利益,大规模地加以招民放垦。大规模地开垦草地,使地表植被改变了原来的生态结构而被改造式利用,草原景观被破坏,防风固沙功能亦丧失,直接导致自然生态失衡。
清末以来,由于过度农垦引起的沙化更加严重,最终形成察哈尔右翼沙漠化的典型区域。新垦土地把大面积草原植被剥掉后,一年仅有90天左右有粮食作物生长,冬春秋长达8—9个月是裸露的,在风的作用下,即可将表土吹蚀,极易沙化,沙尘天气频繁出现。《朔方道志》和《清史稿》都记录了清末以来的沙尘暴。1853年(咸丰三年)3月10日午后,西北有黄黑气二道,忽起忽落。有顷,黄气消失,黑气直冲天际,向东南飞奔二三里许,顿时黑暗,对面不相见,虽燃灯烛,光彩尽蔽,久之黑转红,房舍人物尽似血染,旋即狂风大作,砂砾飞扬,入夜渐息。1876年(光绪二年)秋7月29日午后,丰镇地区忽然平地雷声大震,风遂起,飞沙走石,尘雾漫天,将十一湾村民场墙移北于南相距数十步,略无倾欹,碌碡卷去半空,落村南小沟,数十人憾之不出,禾稼吹去无数。㉕4-5察哈尔右翼地区的沙化区主要分布在今乌兰察布市的后山地区四子王旗、商都、察右中旗、察右后旗 4个典型区域,几乎是“一年开荒,二年吃点粮,三年变沙梁”。开荒一亩,沙化三亩,农牧两伤,不可避免地形成“农业吃掉牧业、沙子吃掉农业”的恶性循环,生态退化益发不可收拾。
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被垦蒙地不像内地农民那样精耕细作,而是采取“广种薄收”式的粗放经营。据《绥远农垦调查记》记载,绥远后山人种地“高处倾斜地,表土极薄,已成粗砂土壤。此盖由农人智识太低,土地毫不施肥,甚至收获时,将作物连根拔出,收回以充燃料。”㉖这种不但不施肥料,收获时还将庄稼连根拔起的习惯,对于保护地力非常不利。耕种几年,土壤腐殖质减少,肥力降低,地力减弱,于是又将“土地之贫瘠者弃之可也,再租他地之肥沃者种之,”㉗大片土地被撂荒。察哈尔羊群大马群一带,“垦户恒多领种土地,云数年后以其产量递减,遂弃置不顾,任其复荒”。㉘丰镇厅北的一些地方亦出现了已开垦,而又复变为荒地的现象。陶林厅一带,汉民也因光绪末年封建剥削加重,弃地潜逃,“近来弃田地避赋税而去者,所在多有”。㉙这些撂荒地,因地表植被已被破坏,土壤肥力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无植被覆盖的撂荒地经过干旱风季,下伏沙质沉积物被大风吹扬而起”,㉚造成撂荒地越多、越快,沙化的速度越快、程度越严重的局面。
此外,在清末全面放垦期间,随着内地民人不断地垦占草场,察哈尔地区出现了农牧争地的局面,而竞争的结果却是农进牧退。察哈尔八旗南部草原的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草场面积的缩小,使产草量减少,而草场承载负担越来越大,加重了草场的载畜量,结果造成“草畜矛盾”。过度放牧随之加剧,部分草场长期过载,远远超过草场资源的负担,这种掠夺性经营,极易引起草场植被的退化,使土地失去保护,更加速了沙化进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所垦之地多系土质肥沃的草场,绥远后套佃农“逐好地耕种,有如逐水草而居之势。盖后套以水利当先,若某处于今年夏季伏天溉有良好田地,明年则移来种植。”㉛“仅仅剩下更低劣的牧场供畜牧使用。随着牲畜数量的增加,植被以更快的速度退化”。㉜据调查,在连续原始放牧的情况下,到第二年7月中旬,植被覆盖度由无放牧的42.1%下降到3.1%,群落高度由22厘米下降到4厘米,地表沙质土壤几乎完全“暴露”,㉜最终变成流沙移动、尘土飞扬的荒漠化土地。可见,移民垦荒导致了农业、牧业两线沙化的局面。农区面积越大,牧区沙化的趋势就越显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事实上,在贻谷放垦期间,灾害就不断发生。大水成灾,蝗灾连年发生,蝗虫“多有厚至三四寸、七八寸者,长宽自数里至二十余里不等,弥望无际,人难插足。”一经闯入各种田苗,“茎叶无遗”。㉞察哈尔地区在1906年“自春徂夏雨泽愆期,六七月间亢旱尤甚,田苗萎坏”。㉟这些灾情的发生是人类一味的、无休止的向自然索取,超出了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
三、结束语
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清末内地民人不断进入察哈尔右翼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蒙民对粮食的需求,丰富了牧民的物质生活,但大规模地垦殖,严重地破坏了草原生态。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否认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清政府的“移民实边”、“放垦蒙地”的政策和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方式,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只有遵循自然法则,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才能避免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长期生态损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发展,真正造福当地人民,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注释:
①《大清会典事例》(卷166),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②㉞黄可润修纂,《口北三厅志》(卷一地舆),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均引自第446页。
③⑬⑱⑲政协乌兰察布市委员会,《乌兰察布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分别引自第266页,第331页,第333页,第334页。
④参见闫天灵,《关于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社会影响问题的相关研究》,《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衣保中,张立伟,《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
⑤《岑春煊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光绪谕折汇存》,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⑥吴春梅,《贻谷与内蒙古垦务》,《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
⑦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⑧陆邦彦,劳亦安编,《内蒙纪行》(第11册),《古今游记丛钞》(卷四五),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4页。
⑨参见政协乌兰察布市委员会,《乌兰察布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山西通志》(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46页。
⑩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壬午,《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
⑪苏德,《关于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蒙古史研究》(第7辑),2003年。
⑫⑭贻谷,《垦务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1),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分别引自第30—31页,第32页。
⑮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钦差垦务大臣全宗》(卷一)。
⑯赵之恒,《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⑰贻谷,《蒙垦陈诉供状》;参见政协乌兰察布市委员会,《乌兰察布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
⑳参见苏德,《关于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蒙古史研究》(第7辑),2003年;赵之恒,《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㉑贻谷,《蒙情续供》,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51页。
㉒乌兰察布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乌兰察布盟志》(中),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877页。
㉓马福祥,《蒙藏状况》,蒙藏委员会1931年版,第13页。
㉔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
㉕参见张宇主编,《守望家园——内蒙古生态环境演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㉖曾雄镇,《绥远农垦调查记》,《西北汇刊》(第1卷),1925年第8期。
㉗唐启宇,《西北农垦计划私议》,《西北汇刊》(第1卷),1925年第5期。
㉘赵世荣,《调查察哈尔羊群大马群垦务日记》,《东方杂志》(第13卷),1916年第10期。
㉙转引自政协乌兰察布市委员会,《乌兰察布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近代农业史》(卷二十),成文出版社,第356页。
㉚朱震达等,《中国沙漠概论》,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㉛李纪,《后套农业近况》,《农业周报》(第1卷),1931年第17期。
㉜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㉜傅守正主编,《构筑北疆绿色屏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7页。
㉟贻谷,《绥远奏议》,吴春梅,《贻谷与内蒙古垦务》,《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第238页。
The Impact of the Immigrants' Reclamation of the Chahar Right Ar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E Xue-hui ZHANG Jun WANG Ying-wei
(Dept.of Politics and History,Jining Normal University,Jining 012000,Inner Mongolia,China)
After the Qing Dynasty(1644-1912)unified Mongolia,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prohibiting reclamation in Mongolia.Facing the domestic troubles and foreign invas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implemented"New Deal."During the New Deal,the government adjusts the policy of prohibiting reclamation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in Mongolia without the effect of being attacked,and changed to the policy of cultivating Mongolia.The result is that the people in the central areas moved into Mongolia in a large scale,and the front hilly area of the right Chahar became the larger area of both farming and pastoral lands.People's behaviors at that time-blind reclamation and extensive management-went beyond the self-adjusting ability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itself,thus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ragile grass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New Dea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right area of Chahar;allowance of cultivating Mongolia right;ecological environment
G03
A
2095-3771(2014)04-0028-06
何学慧(1968-),女,副教授,硕士。张军(1971-),男,副教授。王英维(1977-),男,副教授,硕士。该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察布荒漠化防治问题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NJZC13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