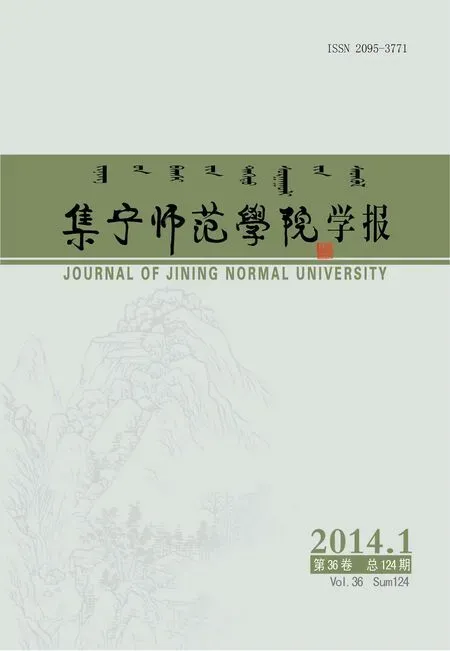诠释学语言问题中存在与表现之间的关系
2014-04-17郭冬梅
郭冬梅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加达默尔 (Hans-GeorgGadamer, 1900—2002)的哲学解释学理论遭受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他的“相对主义”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由于时代的距离,还原作者的意见是不可能的,解释只是对文本的解释,它不解释作者,也不解释历史。这样可能会陷入一种相对主义的状况,因为人们在理解的过程中对历史流传物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那么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或者说哪些理解是正确的呢?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同时其中牵涉了诠释学语言问题中存在与表现的问题。解释的历史性即是表现的多样性,多样性如果与真理性的关系不能处理好,就将导致相对主义。
加达默尔对工具主义语言理论和符号论语言观进行了批判,在工具主义语言理论看来,语言只是工具,人类可以用语言这种工具达到对事物或者真理的认识,这种观点滥觞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其错误在于将形式与内容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语言并不是意识借以同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与符号和工具——这两者无疑也是人所特有的——并列的第三种器械。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①符号是用于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加达默尔认为语言不是手段,语言是包围和缠绕我们的世界因素。语言不是符号,而是一切能用语词表达的存在物的基本媒介。相对于“符号”,加达默尔更认为,语言是原型的“摹本”,在“摹本”中,原型得到表现和持续存在。他认为知识和语言、语词和事物、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语言内在于思想和存在,即语言和存在是统一的。“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而且同时也正是存在使自身在语言中被理解。
但是历史流传物总是在历史中被理解和解释的,亦即它的本质总是需要在不断的历史中表现出来,流传物的这种偶缘性却给了本体论的诠释学一个难题:存在与表现在历史流传物中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们是区分还是不区分的呢?面对着同一个历史流传物,处于不同传统中的解释者,乃至在统一传统中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解释者总是要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即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而在加达默尔看来这是流传物的自我表现),这些表现与流传物的存在之间的一致性必须得到论证。
首先,加达默尔认为凡是能被理解的东西并不存在于自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它的理解过程的统一性中,也就是说存在于表述的语言之中。“能被理解的只是语言“,“语言表达的东西绝非不具语言的先予物,而是唯有在语词之中才感觉到其自身的规定性。”②我们无法直接到达流传物的存在,必然地要借助于语言,只有在语言中流传物的存在才能不断地显示出来。问题是在流传物的表现过程中,解释者境遇的不同必然导致的是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表现与存在是相区别的。例如对《哈姆莱特》的解释自作品出现以来就是千差万别,形式主义者对它的解释与精神分析者对它的解释绝对是不相同的,给人的感觉是作品的真实存在与表现是相区别的,到底哪个表现才是真的呢?加达默尔认为:“来到语言表达并不意味着第二存在,某物表现为的东西都属于其自身的存在。”③他在语言中的表现正如在镜子中的表现一样,乃是自身的现象,解释的多样性并不分裂成众多性。表现仍然是自身的表现,是同一种存在,表现与存在是一致的。艺术品的存在并不是同它的再现或它显现的偶然性相区别的自在存在,艺术作品同它的效果历史,历史流传物同其被理解的现在乃是同一个东西。凡是语言的东西都具有思辨的统一性,一种在它的存在和它的自我表现之间的区别本身,事实上是无区别的区别。“对流传物的每一次领会都是历史地相异的领会——这并不是说,一切领会只不过是对它歪曲的把握:相反,一切领会又都是事物本身某一方面的经验。”④这时我们就很明显看到了,存在与表现是没有区别的区分,这是诠释学本体论语言理论的一个悖论。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加达默尔必须面对的,他于是又将目光转向了古希腊,在柏拉图关于“美的理念”和“善的理念”论述中找到了答案。
柏拉图对美和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善是看不见的,它只是对行为的判断,它不能自身显示出来,而且善经常具有欺骗性,我们经常为德行不纯的摹仿和假象所欺骗。某个人做的某个行为可能会表现出是善的,但实际上却可能是恶的。但是美却不一样,它具有一种最终的显明性,美的存在与美的表现是没有区别的。为了发现真实的美,我们不需要研究美的现象背后的东西,因为美本身表现在这每一种现象中,每一种现象都是美的,每一种现象都是真的。加达默尔把美这种可直接把握性与善的不可把握性加以对立,把美的这种特性称为美的优异性。他说,“美自身就有光亮度,因而我们也不会受到歪曲摹本的欺骗,因为只有美才享有这一点,即它是最光亮的和最值得爱的东西。”⑥在美和善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美是由自身得到表现的,它的存在直接呈现出来,美使得理念与现象得以中介。“美相对于善的突出之处在于,美是由自身得到表现,在它的存在中直接呈现出来。这样,美就具有一种能够给出美的最重要的本体论功能,即能使理念和现象之间进行中介的功能。”⑦在各种各样的事物中我们看到了美,我们看到的也是美的存在本身,而且美与不美的事物之间的明显界限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中得到了确认。真实的美与表现的美是无区别的,美就在美的事物中,它通过美的事物使自身得以显示。
同时,美还有一种 “光”,“美具有光的存在方式”。我们知道,光能够使他物成为可见,从而使自己成为可见,而且只有通过他物成为可见才能使自己成为可见。光能够使看和可见之物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没有光就既没有看,也没有可见之物。太阳因为光使自己为人们看见,同时也使世界万物为人所见,这就是光的性质。美也具有这种光,美同样也是使自己呈现在它的现象里,不仅在表现的事物中呈现,而且只有在通过感官可见的事物中才能存在。
在柏拉图的关于美的论述中加达默尔看到了美的理念与存在的相通之处,当然这种存在不仅仅是审美的艺术作品的存在,还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存在。“如果我们把美的本体论结构描述为一种使事物在其尺度和范围中得以出现的显露,那么它也相应地适用于可理解领域。使一切都能自身阐明,自身可理解地出现的光正是词语之光。”⑧也就是说,在历史流传物中,也存在一种光,这种光就是词语。存在表现自身,通过揭示能被理解的存在物的历史过程中,语言就是可理解物能表现自身的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语言并不是狭义上的语言,而是指思维的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是普遍的。但是语言要为人们所知,就必须借助于说的语言,即词语。存在自己说话,并且用符号表示出来。词语就是从存在身上流溢出来的,因此每一次的表现都是存在,而且存在并不会因为流溢而自己减弱。存在在词语之光中表现自身,词语之光就像真实那样反映它,正如美是在它使之成为美的东西中被启示。
从光的形而上学建立的美的显现和存在的显现的对应关系中,我们能够认识到两点:一是美的显现方式和理念的存在方式都是自成性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自成事件的。这意味着事物自身的行动在理解过程中的决定性,话语的形成就是事物本身找到语言表达的思辨事件。“关于事件或事物的行动的讲话都是从事物本身出发提供的,明显的东西总是一种被说出的东西:一项建议,一个计划,一种猜测,一种论据或诸如此类。”⑨我们在解释的过程中并没有赋予可理解物什么东西,是它自己在诉说,我们做的只是在倾听。二是诠释学经验,也就是对流传下来意义的经验,具有直接性。在解释的过程中,意义永远是直接地向我们呈现的。它使自身在明显之中,就像美一样,它不能也无须证明。
加达默尔在援引柏拉图的理论中看到了解决问题的道路。在柏拉图那里,美作为善在其中得以表现的方式是在它的存在中使自身显现的,即表现自身的。这样表现自身的东西因为是表现自身,所以是不能同自身相区别的。它不是对自身来说是一物,而对他者来说是另一物,他也不是通过他物才存在的东西,它自身在闪光。柏拉图关于美的形而上学弥补了理念和表现之间的裂缝,正是美自身既设定了这种对立也使这种对立得到扬弃。这种观点也解决了在解释学语言问题中存在和表现的这种悖论。在加达默尔看来,理解是对真理的“照面”,照面本身是在语言的解释过程中进行的,这就使得语言现象和理解现象是存在和认识的普遍模式得到确认。我们在历史流传物所理解的东西是存在的一个观点或方面,然而它们都是真的,都是关于存在的真理的现象,因为表现自身和显现是存在的本性。因为它解释自身,所以它的解释不是某种不同于它的东西,存在在它的表现中得以表现自身。
我们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流传物的时候,我们是被卷入了解释的事件之中的正如被卷入游戏中一样,整个解释的活动就是语言游戏。在《真理与方法》的结尾处,加达默尔又将视角转回到了“游戏”,这个曾经被加达默尔赋予本体论意义的概念。游戏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这是加达默尔美学思想的核心。他强调艺术和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艺术家和游戏者,而是艺术和游戏本身。游戏始终是游戏本身,此外无它。它不来源于什么,也不为了什么,更不利用什么手段。游戏的意义始终是在它每时每刻的不断生成之中,这里游戏概念超越了文学艺术作品了,整个历史流传物的解释都是语言的游戏。加达默尔认为,游戏不再为理性给予的一个尺度所规定,不再是我设立对象,不再是人作为主体来观照对象,而是被存在所规定,确切地说,是对存在的理解。当理解进人的存在领域,就会让人的一般自我理解的经验,其中特别是艺术审美经验成为人的存在的揭示,而语言则是解释存在的必然途径。
注释:
①〔德〕加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②③④⑥⑦⑧⑨〔德〕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引自第615页,第615页,第612页,第623页,第623页,第625页,第628页。
⑤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