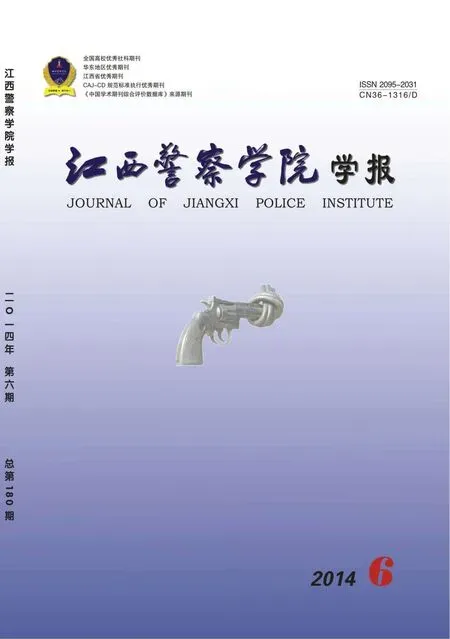“婚内强奸”犯罪化问题研究
2014-04-16江奥立
江奥立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3)
“婚内强奸”犯罪化问题研究
江奥立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3)
“婚内强奸”应该如何定性,学界分歧甚大。各种意见围绕“婚内强奸”犯罪化是否存在观念障碍和技术障碍展开自身的论述。具体而言,夫妻家庭地位的道德评价构成“婚内强奸”犯罪化的观念障碍,实际操作所内含的风险以及“婚内强奸”有罪判决的社会效果构成了“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技术障碍。事实上,对夫妻家庭平等地位的强调能够消解其中的观念障碍,否认实际操作中的风险与犯罪化证成之间的关联性、明确“婚内强奸”非犯罪化者论据之间的矛盾性,亦能消除其中的技术障碍。在“婚内强奸”犯罪化路径的选择上,“婚内强奸”构成“强奸罪”是合适的选择,但是,“婚内强奸”与普通强奸罪之间存在差别,应在量刑上有所区分。
婚内强奸;犯罪化;男女平等观;社会效果;强奸罪
一、问题的缘起:实务迷茫与理论分歧
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同床原属恒情,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丈夫可以违背妻子的意愿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对此,实务做法不一,学界意见相异。一方面,实务部门虽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其坚守“婚内强奸”无罪化立场,试图与理论通说①通说认为,“夫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的确立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就构成了夫妻双方认可和确定的共同生活的重要内容。如果把夫妻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丈夫不顾妻子意愿强行与其性交作为强奸罪处理,不仅为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取证带来一些困难,而且不利于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内部关系的稳定。当然,如果丈夫为满足性要求而对妻子实施其他行为(如虐待、伤害、侮辱、诽谤等),构成其他罪,则应另当别论,构成什么罪按什么罪处理。”参见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96.保持一致,但是,在现实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实务部门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的案件法院最后作出无罪的判决,有的案件法院则作出了成立强奸罪的判决。法院认定的不一致性足见“婚内强奸”在刑事评价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学界对“婚内强奸”是否成立犯罪分歧甚大,至今仍无定论。大体来讲,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一)否定论
持否定论者一般认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相互存有配偶权,基于配偶权夫妻之间存在同居义务,因此,即便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也应该基于配偶权的存在而得到豁免;婚内强奸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普通强奸,适用此重罪并不合适;从语义上来讲,夫妻之间合法的性关系难以用“强奸”来评价。[1]更有论者指出,所谓“婚内强奸”在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中,一个都不符合。[2]
(二)肯定论
持肯定论者一般认为,该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丈夫只要具备犯罪能力,当然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3]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表明了女性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渴求,刑法理应加强对女性权利的保护;[4]各国在对“婚内强奸”的态度上经历了“丈夫婚内强奸豁免权”的坚守到废弃,这意味着“婚内强奸”犯罪化是立法以及司法必须面对的趋势;[5]即使承认“丈夫有与妻子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这一前提,也不能必然得出 “丈夫有使用暴力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这一结论。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过长的逻辑距离以致这种推理事实上是无法完成的。[6]
(三)区别论
区别论认为不能对“婚内强奸”行为做“一刀切”的处理,应视情况而定,其中存在时间区别论和手段区别论两种观点。在时间区别论者看来,应当以夫妻双方是否存在感情破裂的情形作为判断的标准,具言之,“婚内强奸”如果发生在能够表明夫妻双方确实存在感情破裂的场合里时,丈夫才构成强奸罪。能够表征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典型情形有长期分居、离婚诉讼审理阶段等,但不局限于此。[7]手段区别论在承认“婚内强奸”成立强奸罪的基础上,为了避免该重罪对家庭结构造成过大的冲击,提出 “婚内强奸”构成强奸罪仅限于以暴力作为手段的情形,换言之,迷奸等非暴力的奸淫行为并不成立强奸罪。[8]
在本文看来,“婚内强奸”犯罪化并不存在观念和技术上的障碍,否定论所举的理由事实上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区别论虽能照顾到民众的感受,但这种纯功利的解决之道缺乏法理和规范上的依据,总体来讲,肯定论是值得赞同的。在“婚内强奸”犯罪化路径的选择上,现有的“强奸罪”完全可以规制此类行为,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婚内强奸”的入罪化并不合适。下文着重从观念和技术的角度,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同时以对“婚内强奸”作详细的规范上的展开。
二、问题的基点:“男女平等观”在“婚内强奸”研究中的坚持
(一)西方国家的认定
在西方,最先为“婚内无奸”代言的是英国法理学家黑尔勋爵,其在文中写道,“丈夫不可能亲自对他的合法妻子犯强奸罪,因为他们相互的婚姻允诺与契约,妻子已经在这类契约中将自己贡献给丈夫,这是她无法取消的。”[9]对此,当时几乎所有的英国法官都接受了丈夫“婚内强奸豁免权”的结论。黑尔爵士关于“婚内强奸豁免权”的主张对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1977年为止,美国有29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丈夫不能因强奸妻子而被起诉。[10]除此以外,1975年联邦德国刑法典也明确强调强奸罪中的性交是指“婚姻外的性交”。随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要求提高家庭中的地位的呼声愈发高涨,一些国家在反思本国司法传统时发现了“婚内强奸豁免权”的不合理性,于是,一场观念上的肃清大规模的展开。1991年10月23日,在婚内强奸豁免权发源地的英国,上议院在审理皇室诉R一案时,作出了废除婚内强奸豁免权的历史性裁决:妻子只要表示离开丈夫的企图(如搬离家庭),便已经撤销“婚姻承诺”,有权控告丈夫强奸。金斯爵士指出:“现代妻子不再是丈夫手下逆来顺受的性奴隶,而是平起平坐的伙伴。”自此,英国男子才也不能因婚姻关系而肆无忌惮地强迫与其妻子发生性关系。深受英国司法传统影响的美国,也逐步消解因“婚内强奸豁免权”带来的不合理的局面。“根据一个最近的调查,2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地区)已经废除了所有性犯罪的规则。在剩下的州中,一些司法辖区已经废除了特定暴力强奸犯罪的婚内免责规则,而保留了其他性犯罪的免责性”[11]有着悠久的“婚内无奸”历史的德国,在之后刑法的修正中,也将强奸罪中“婚姻外”这一特征给取消,[12]这为“婚内强奸”构成强奸罪提供了规则上的支持。
(二)我国的传统认定
在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男性对女性的管理无异于对财物的管理,在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尽管婚内常有强迫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但从来不可能因此而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这种“婚内无奸”观念在封建时期尚属合理,在讲求个人权益与平等的今天,“婚内强奸豁免”则已经没有存在的空间。一方面,丈夫与妻子之间首先是以平等人的关系展开的。有观点认为,同居义务作为配偶权的内容,是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结婚就意味着夫妻双方共同选择了同居的权利义务,如果不愿承担此项义务,当事人可以选择不结婚。”[13]然而,婚姻不是强奸者的通行证,夫妻关系也绝非是将一方依附于另一方的结合。事实上,婚姻对男女双方也并非毫无限制,夫妻关系的成立意味着性伴侣的特定化,男女任何一方都不得在与其他异性发生性接触。强奸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女性性的自由选择,包括对象的选择和是否发生性行为的选择,婚姻关系限制了前者但没有限制后者,否则,夫妻之间的平等关系将无从谈起,女方在家庭中附庸于男方的状况将难以改善。另一方面,“婚内存奸”否定者认为,“鉴于包办婚姻以及夫妻在家庭中地位不平等的现象,至今还在一些地区严重存在,以致丈夫不顾妻子的意愿而强行与之发生性交的现象还较多,如果一概以强奸论处,则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情况。”[14]司法部门似乎也较为赞同这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南》中就曾指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同居和性生活是夫妻之间对等的人身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内容,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和性生活的法律承诺。因此,从法律上讲,合法的夫妻之间不存在对妻子的性权利的侵犯,相反,如果妻子同意与丈夫以外的男子发生性关系却构成对合法婚姻的侵犯,所以,如果在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不顾妻子的反对,甚至采取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与妇女进行性行为,不能构成强奸罪。[15]最高检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丈夫用强制手段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不作刑事追究,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对于多起重大恶性婚内强奸案件,检察部门都未以强奸罪起诉。[16]然而,以家庭稳定为由否定强奸罪的成立事实上并不合理。虽然强奸罪不是自诉型犯罪,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案件案发的可能性极小,如果夫妻之间尚存有一丝感情,这类案件都不可能被揭发。这从客观上就限制了“婚内强奸”犯罪化可能社会家庭稳定带来的冲击。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发现,从“婚内无奸”到“婚内有奸”的认识,事实上是封建传统思想到现代人权思想的转变,同时也是夫妻隶属关系到夫妻平等关系的转换。女方在夫妻关系中始终处在弱势的一方,如果法律认可“婚内无奸”,实则是将女性的家庭附庸地位给合法化,女方要想摆脱其弱势境地的愿望将更加难以实现。不可否认,当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发达,家庭仍负有很大的社会职责,但是“婚内强奸”案发的可能性极低,这在客观上消减了犯罪化给家庭稳定带来的冲击力。因此,在本文看来,将“婚内强奸”犯罪化是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的。
三、问题的重点:“婚内强奸”犯罪化不存在操作上的隐忧
将“婚内强奸”犯罪化一直被认为存在实际操作上的隐忧。一方面,婚内强奸犯罪化会使中国的已婚男性如履薄冰,女方随时可以告发男性,使男性陷入无妄地诉讼中,任何一次夫妻间的交合都可能会使丈夫锒铛入狱;另一方面,即使确实存在男方强奸女方的情况,但婚内强奸为卧室内二人之事,女方的只言片语又无法成为定罪的唯一依据,因此,这类案件的取证成为难点。除此以外,“婚内强奸”非犯罪化者还认为将此类行为入罪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曾举出一系列数据,如“1989年到1999年大规模进行的‘性文明’调查表明:在夫妻性生活过程中,丈夫强迫妻子过性生活的占调查总数的2.8%,受害妇女绝对人数有几百万之多。”[17]“北京的一份调查发现,43.3%被丈夫殴打的妇女紧接着遭到性暴力的摧残。”[18]借此说明“婚内强奸”仍是中国社会较为普遍的情形,犯罪化运动可能会带来犯罪率提高、监狱监管压力增加等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论者还指出,西方国家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家庭的社会责任并不大,个人权利的张扬似在情理之中。但是中国的国情有所不同,家庭仍负有较重的社会责任,因此,刑事判决应尽量避免对家庭稳定造成冲击。
在本文看来,这些操作上的隐忧多数是被虚构出来的,在现实中不可能成为问题。首先,两性的结合并非儿戏,除非感情完全破裂并且女方别有用心,妻子诬告的情形几乎不会出现。以“婚内强奸”犯罪化会使男子惶惶不可终日为由,否定犯罪化的合理性并不妥当。其次,一个行为是否是犯罪行为,主要在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取证的难易程度是事实认定的问题,本身并不能成为否定犯罪化的理由,事实上,刑事实务中不乏取证困难的例子,如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等,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从来就没有因此否定犯罪化。最后,对于“婚内强奸”的取证不能仅靠女方的片面之词,而应该重点考察行为时的客观资料,如行为发生时的地点、时间、行为人采取的手段等,同时结合事前事后的事实,如夫妻双方平时的感情、事后被告人的态度等等,进行综合判断。
另外,认为“婚内强奸”犯罪化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第一,“婚内强奸”的发生极其隐秘,除非当事人自己曝光,否则这类案件几乎不可能被揭发。这倒不是说未揭发的“婚内强奸”就不构成强奸罪,而是为了指出这类犯罪隐蔽性的特点客观上限制了打击面过宽的可能,因此,以犯罪化后将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打击面过宽、监狱监管压力增大等为由,否定“婚内强奸”构成强奸罪,显然不妥当;第二,“婚内强奸”非犯罪化者提出的论证理由事实上存在冲突。一方面,论者认为“婚内强奸”的取证非常困难,将“婚内强奸”犯罪化会出现操作上的困境。另一方面,论者又认为,从中国社会现状来看,“婚内强奸”尚属普遍现象,如果将“婚内强奸”犯罪化,势必会出现犯罪率上升、打击面过宽的结果。仔细斟酌这两个理由,我们便能轻易地发现两者的矛盾之处,既然“婚内强奸”取证困难,这类案件最后确定为犯罪的可能性便极低,加之上述提到“婚内强奸”隐蔽性的特征,这些都在客观上限制了打击面的扩大。此时,论者又如何以打击面过大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婚内强奸”非罪化者追求论据的数量而忽视论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此种做法欠妥当;第三,古谚曰:家和万事兴,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家庭的稳定与和睦。“婚内强奸”非罪化者担心刑法的强行介入会人为地拆散一个家庭,使原本就存在隔阂的家庭失去了复原的可能,进而对中国家庭的稳定造成冲击。在本文看来,这种论述是欠周全的,理由在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稳定与和睦的现实,使得受害的妻子更愿意选择去原谅丈夫,在这种场合下,刑法几乎无法发现犯罪的事实,客观上也限制了介入的可能。在妻子执意要控诉丈夫的恶行的情形中,夫妻之间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感情可言,所谓“家庭”也只是一具空壳而已,此时,刑法的介入自然不会存在“婚内强奸”非罪化者口中所言的“拆散一个家庭”。综上,我们发现,刑法的介入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对社会家庭稳定的冲击是有限的。
四、问题的难点:“婚内强奸”犯罪化路径的选择及展开
将 “婚内强奸”进行犯罪化客观上存在多种路径,具体来讲有修改刑法和解释刑法两种意见。在本文看来,刑法研究的重心在于“解释”而非“批判”,解释者只有在穷尽既有条文展示的所有可能性以后仍得不出符合正义理念的结论时,立法修改的建议才有必要被提出。[19]刑法条文的解释应该注重社会文化流变的现实和刑法当时所处的法环境,通过考察以上两个方面,我们认为,将“婚内强奸”涵摄于“强奸罪”并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具体来讲,应该从以下三点切入予以证成。
(一)夫妻“存”奸
这里涉及刑法解释方法的问题。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立法者对可罚性的行为进行总结并明确化,刑法解释则是在立法者给定的框架内进一步明确。刑法中概念有核心含义与边缘含义所组成,一般来讲,从社会人的角度出发,对核心含义的掌握往往不存在问题。然而对边缘含义的解读,时常因人而异,此时,需要借助外界的解释工具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并明确模糊的含义。一种方法试图从概念的历史含义中确定概念的边界,通常以查词典、翻阅传统书籍等等方法展开,这是一种朝后看的解释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则是在承认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 “时间距离”①在理解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阈,一个是文本的视阈,另一个是理解者的视阈。文本有其自身的视阈,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历史存在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理解者也有其自身的视阈,它是由理解者自身所处的历史境遇所赋予的。这样一来,两个视阈便存在差异,伽达默尔对此称之为“时间距离”。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的特征对概念的边界做符合当下观念的解释,这是一种往前看的解释方法。在本文看来,任何概念的展开都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法律的稳定性要求立法者必须具有前瞻性,事实上这种前瞻性只能通过立法的模糊化和解释的时代性来实现,否则,坚持使用几十年前的概念来说明当下的事态显然会认为的缩短法律适用的寿命。“语言是开放的,它的意义边界并不存在警示的标志;语言本身无法实现自我界定,确定性系由社会实践所赋予。”[20]时代进步的过程亦是社会观念流变的过程,我们应该尊重当下的主流价值观,以此作为确定概念边界的参考系。
“婚内强奸”犯罪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夫妻之间是否存在“奸”的问题。有学者从“奸”概念本身着手,认为夫妻之间不存在“奸”的行为,否则,夫妻之间就是合法通奸行为,这显然说不过去。[21]“强奸”一词确实包含了对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描述,“强”表明通过手段强迫女性服从,“奸”表明手段行为实施后与女性发生性关系。上述观点显然认为只有被道德所谴责的性关系才是“奸”,同居义务是夫妻之间必然的内容,自然不存在“奸”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被法律所否定的行为必然为道德所不齿,“奸”本身就带有法律或道德的否定性评价,如果夫妻之间发生正常的性关系,当然不能称之为“通奸”,但是,如果丈夫在违背妻子意愿的情况下,强行与之发生关系,本身就受到法律否定性的评价,此时将性关系称之为“奸”当然不存在问题。因此,“强奸”中的“奸”是在“强”的基础之上对性关系所做的描述,是指受到法律或道德否定性评价的性关系。
(二)“婚内强奸”犯罪化不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
有观点认为,夫妻之间存在同居的义务,此种义务阻却强奸罪的成立,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尽管我国不承认婚姻关系的契约性质,但同居权的相对性却是十分明显的,即夫妻任何一方同居权的实现皆有赖于另一方的配合”事实上,[22]将夫妻性生活作为同居义务的法定内容存在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将夫妻的同床义务并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依《婚姻法》第三条的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第四条的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夫妻之间确实存在法定的同居义务,但其内容只限于相互扶助、相互忠实。婚姻的缔结使得男女之间产生了忠于对方的义务,具言之,男女双方只能选择与对方同床,不能与其他人同床,婚姻关系限制了男女双方的选择权,但没有限制一方按照自己意愿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其次,如果认为婚姻关系使得男女双方产生了同床的权利义务,这里就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混乱。一方面,男女一方有权利不发生性关系,但另一方面,在面对对方要求行使权利时,有负有了不可拒绝的义务,这两种关系显然是矛盾的。最后,如果认为夫妻之间存在同床的法定义务,如何追究违背义务后的责任是存在问题的。有观点以域外的规定为由,认为夫妻之间不履行同居义务时应迫使其履行。“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法国民法典》第214条第四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使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又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这些规定针对的是夫妻之间相互生活、相互扶助的义务,夫妻一方拒绝发生性关系,不能因这些规定要求法院判决强行与另一方发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婚姻法》不仅没有明确规定同床的法定义务,而且从《婚姻法》的发展史来看,其更倾向于将同床的法定义务排除在外。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是在1980年颁布的,并在2001年的时候进行了修订。从修订的内容来看,《婚姻法》更加重视夫妻在家庭中的平等与和睦。如在新婚姻法第3条第二款中添增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内容;新增加了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增加了43、45、46条关于如何对家庭暴力追究法律责任的条款。这些修正无不是在强调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与受谴责性,虽然“家庭暴力”的范围仍旧备受争议,如是否包含冷暴力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性暴力显然是家暴的典型的表现方式。如果认为同床义务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这就意味着主张权利的一方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要求义务方履行自己的义务,换言之,夫妻一方强迫对方发生性关系只是在要求对方履行义务,并不构成强奸罪。很显然,将同床义务认定为法定义务的后果是,《婚姻法》为禁止家暴、提倡家庭和睦的努力化为泡影。
(三)“婚内强奸”具备刑事谴责性,但需要与普通强奸相区别
从法治国的理念来讲,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条文所描述的类型并存在主观上的罪过时,刑法不应该拒绝适用。通过上文的论述,将“婚内强奸”犯罪化并不存在构成要件要素解释上的问题,亦不存在违法性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存在故意,刑法就应该加以评价,换言之,通过形式违法(构成要件符合性)和实质违法(违法性)的客观判断后,只要行为人对此有罪过,该行为就应该接受谴责,这是形式法治的题中之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形式法治本身也存在内在风险,即可能会带来法理与人情之间的冲突。为了弥补这一点,刑法理论开始自身理论的改造。最先关注刑法中法理与人情结合的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此,有学者指出,“期待可能性是对在强有力的国家法律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23]在适用方面,该理论认为,刑法在科责他人时不应仅仅关注行为人是否存在罪过,还应考察行为人行为时的客观情状。这种规范责任理论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开始承认人的意志相对自由的结果,客观环境对人的行为存在或多或少的限制,人类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自己预想的行为。正是这种客观限制有强有弱,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期待可能性不仅存在着有无的问题(是否阻却责任),而且还存在程度问题(是否减轻责任)。”[14]据此,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形式上符合犯罪的行为开通了出罪或减罪的通道。但是,期待可能性理论毕竟是对行为的期待,行为人的要素并没有被充分的考虑,因此,这种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德国刑法学界在建构犯罪构成理论时,发展了“行为人的答责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行为人在具体的犯罪事实中具备不法与有责时,还需要考虑刑法对行为人是否有预防的必要,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影响责任的有无与大小。这种理论将刑罚的目的引进犯罪构成理论之中,使得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反观我国刑法理论,虽然并没有提出类似期待可能性与答责性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对此没有相应的规定。《刑法》第13条中的“但书”部分指出,“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犯罪情节”不仅包含客观的情节,而且还包括动机、目的等主观的情节,换言之,“情节”是整体性判断的要素,期待可能性理论和行为人答责性理论中所含的内容事实上都可以被 “犯罪情节”所囊括。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但书”部分仅有出罪而无减罪的功能,但是从条文的逻辑来看,情节轻微的犯罪应该有别于情节严重的犯罪,需要从轻处罚。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行为人答责性理论归根结底是在表明,刑事责任的启动需要考虑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必要性。边沁曾经指出不得适用刑罚的四种情况:一是不存在现实之罪时(无根据),不得适用刑罚;二是刑罚的适用不会产生好的效果时 (无效果),不得适用刑罚;三是当通过更温和的手段——指导、示范、请求、缓期、褒奖可以获得同样效果时(无必要),适用刑罚就是过分的;四是刑罚之恶超过罪行之恶时(太昂贵),该刑罚便是不必要的。[24]其中第二点就是在强调预防在定罪方面的重要性。在本文看来,对行为人的归责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行为人必须具备与构成要件相关的心理事实,即有故意或过失;其次,法彦曰:法不为人所难,如果法律的要求在行为人行为时是违反人性的,刑法就不应该介入,因为在行为人在面对同一场合时,行为人基于人性势必会作出同样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中,刑法并不具备特殊预防的意义;最后,刑法在适用的时候不能自我陶醉,得出来结论需要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这就意味着刑事判决必须得考虑社会主流的观念。当然,社会主流观念并不一定符合理性的价值观,但将社会观念引导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刑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刑事判决应该做有限度的顺从,确保一般预防的有效性。在婚内强奸的案件中,丈夫显然具备被谴责的必要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家庭观,这种观念的矫正非一日之功,亦非刑法之力所能及,如果刑事判决漠视这种现实,强行将所谓的理性观念灌输给大众势必会带来社会的反抗,因此,刑法适用过程中应关注社会主流观念对刑法一般预防效果的影响,换言之,刑法在给婚内强奸中的丈夫科以罪责时,应该正视社会当下的观念做适当的从轻的处理,以此来区别普通强奸罪。
[1]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的诱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9.
[2]冯准,狄小华.婚内强奸行为的刑法分析 [J].天津法学,2012,(4):70.
[3]邱灵.再议“婚内强奸”是否成立强奸罪[J].中国检察官,2013,(7):21-22.
[4]马玉海.“婚内强奸”法律问题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11,(5):18.
[5]曹雪辉.婚内强奸问题刍议——基于对婚内强奸之概念、理论基础、法律价值定位的考量[J].西部法学评论,2010.,(6):79.
[6]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6-417.
[7]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90-191.
[8]宁从越,毕婷婷.论婚内强奸 [EBOL].(2010-07-19) [2014-08-25].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100 7/19/418844.shtml.
[9]Hale,History of Pleas of the Crown,Gale Ecco,Print Editions,2012,p.629.
[10][美]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M].潘允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07.
[11]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M].王秀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53.
[12]徐久生,译.瑞士联邦刑法典(1996年修订)[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69.
[13]周悦丽.配偶权、忠实义务与隐私权保护[J].政法论丛,2005,(6):38.
[1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52.
[15]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事审判指南[M].1999,(3):25;李邦友.性犯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23.
[16]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犯罪案例丛书编委会.刑事犯罪案例丛书·强奸罪·奸淫幼女罪[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152.
[17]周崎,胡志国.“王卫明强奸案”[J].判例与研究,2000,(2):20.
[18]张贤钰.评“婚内无奸”[J].法学,2000,.(3):56.
[19]张明楷.刑法研究中的十关系论[J].2006,(2):3.
[20]劳东燕.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7.
[21]刘宪权.“婚内定’强奸’不妥”[J].法学,2000,(3):58.
[22]刘一夫.我国“婚内强奸”的定罪与预防[J].法律适用,2012,(5):121.
[23]刘宪权.刑法学(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75.
[24]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李贵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66.
责任编辑:黄永强
D924.34
A
2095-2031(2014)06-0072-06
2014-09-16
江奥立(1990-),男,浙江瑞安人,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刑法、比较刑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