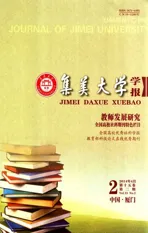地方理工院校国学教育的困思与探索
2014-04-15刘晓艳
刘晓艳
(厦门理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福建 厦门 361024)
作为高等院校人文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国学教育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关注国学、重视国学、开展各种形式的国学教育逐渐成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趋势,一些大学已经将国学教育纳入通识教育体系。面对这一趋势,人文教育本来就相对薄弱的理工院校特别是那些刚刚完成从职业技术教育向全日制本科教育升级转型的地方理工院校如何扬长补短,探索适合自身学科特点和培养目标的国学教育方式和方法,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教改课题。
一
理工院校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开展国学教育吗?这个问题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理工院校人文教育意义的讨论一样,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这样的疑惑在当前一些理工院校师生中确实并不鲜见。在不少人的眼中,理工院校的教育目标和主要社会责任自然是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所以在理工院校开展国学教育这种更加精深的人文教育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但是人才培养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尤其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未来发展和社会长期进步培养优秀创新科技人才,却是包括理工院校在内的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艰巨的现实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几年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以振聋发聩的方式在社会上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和持久讨论。客观地讲,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在数十年内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和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根深蒂固的体制性弊端和瓶颈性难题也越来越暴露出其消极性。而学界在批评和反思这些体制性弊端和瓶颈性难题时,往往不得不直面一个诡谲的困惑——当代大学大学精神的失落。正如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所指出的:
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 (博而且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较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照搬苏联模式,加上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使得大学分科化和系科单面化的模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今天全社会的功利化与实用化的导向,强调所谓专业对口,科系与课程设置更为单一、片面、直接,乃至有大学传统的大学在现行评价体系下沦为职业培训学校,大量不具备大学资质的学校又纷纷升格为大学,于是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而目前推行的所谓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指标体系,日益把大学变成中等专业学校,完全无视大学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视之若工具,把教育活动变成简单刻板的机械运动,阉割了大学精神。[1]19
大学就应当是大学,大学就应当有大学精神。可大学精神不是实用主义的狂欢,也不是科学精神的独奏,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犹如大学精神的两翼,只有两翼健全平衡,大学精神才能完善,大学才能健康发展,大学教育也才能演绎出完美和谐的乐章。而现实的情况是,重科技知识灌输、轻人文素质修养是当前大多数高校共同的偏失,理工院校于兹为甚。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以华中理工大学 (现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理工院校掀起的那场“人文风暴”是针对当时理工院校人文教育缺失弊端的自觉而有力的矫正的话,那么,近年来高校“国学教育”的积极推进则是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人文回归的进一步深化。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精粹,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精神的命脉。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的核心,而“国学”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石。《人民日报》2004年5月13日《人文之光照耀科学摇篮华中科技大学》一文载称:
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讲学的杨叔子见到一位华裔科学家。这位科学家说:“你们培养的大学生ABC很好,也懂美元、英镑,就是不了解长城、黄河,不了解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人能为中华民族服务吗?”[2]
很显然,忽视“国学”,数典忘祖,则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重塑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前高校的国学教育改革,正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回归和继承发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精神的共振。重视国学教育,振兴人文传统,是大学回归大学之道的重要内容。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而现代化“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重要推进力量而促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不断提高的过程。”[3]只有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国学教育之于理工院校的长远意义。
二
国学教育对于广大理工学子的现实意义究竟如何?
在大学生的成才之路上,知识结构是影响和决定大学生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和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应试教育的极重难返,当前大学生“知识跛足”的现象是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的。这一消极现象虽然不能归咎于学生本身,而是教育大环境使然,但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必然成为大学生成才路上不可避免的瓶颈:
由于揠苗助长式的幼儿教育、小中学教育片面地膨胀技术知识与过早的分科,使大学教育对象的东西方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之修养十分欠缺。中学文理分科太早,病患尤大,目前文、理、工、医、农科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中,人文与科学素养双重贫乏,特别是使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生源的水平下降了很多。从中学到大学,长期累层叠加的分科式教育与灌输的方法,使大学生的素养更加贫弱化或单面化,尤其是变得不会思考,没有思想和反思的本领与能力。这当然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养的国民,或平民化的公众知识分子。[1]19
单就理工科学生而言,长期以来中学教育的应试化和理工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难免造成理工学子的人文隔膜或缺失。著名教育家、机械工程专家杨叔子院士曾经发挥教育家梁思成的“半个人”之说来讨论理工人才的培养问题:
教育家梁思成早在1948年就提出,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意思是说,当时的文理分科,使得搞文的不懂理,搞理的不懂文,只能培养出半个人来。可是时至今天,文理分科不但没有变,而且分得更细,学工的不懂理,更不懂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当年所说的半个人,到现在已经是1/4人,甚至是1/8人。[3]
针对这样的人才培养弊端,杨叔子院士倡导,学理科的要读一读《论语》、《老子》,增加“文人气”,让思维发散;学人文的也要学一点理科知识,防止“不着边际”,“文理兼修,并不会有冲突。”[4]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交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5]51,像达·芬奇、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就是科学与人文完美融合的生动例证;另一方面,“国学”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文化浓缩的精髓,包蕴着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在其浸润濡染之下,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了相当辉煌的技术文明和无以计数的科技奇迹,同时,只要我们稍微梳理一下那些在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和人文学术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代表人物如詹天佑、钱学森、竺可桢、华罗庚、苏步青、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胡适、鲁迅、赵元任等等,便不难发现这些人物的成功往往都得益于“国学”与“西学”的共同造就,良好的国学修养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在这些杰出人才的成功道路上不可或缺、相得益彰。
大学以育人为本,理工院校也不是“制器”的作坊,不是生产“科学技术人才工具”的车间和流水线。广大理工学子在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自觉学习国学知识,提高人文修养,贯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既是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也是真正的成才之道、成功之道。杨叔子院士指出:
科技成果能否正确应用?科技成果能否迅速掌握?科技成果能否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能力超前研发,以压倒对方?能否以“高屋建瓴,洞察全局”的能力,异军突起,开拓崭新的科技领域,夺取主导科技潮流的科技成果?这绝不仅仅取决于科技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科学与人文如何结合,取决于研究科技的人及相关者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5]47
所以说,理工院校开展国学教育、理工学子修习国学不仅不是舍本趋末,恰恰相反,通过这种人文教育的积极介入和国学修习的自觉努力,理工学子的知识结构、技术能力、道德修养和文化境界可以齐头并进、全面发展,有补人文之短、扬科技之长的事半功倍的意义。
三
“国学”至今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学术话题,国学教育进入高教改革还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现象,即便是一些知名综合性大学的国学教育也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改进,所以,理工院校开展国学教育必然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许多地方理工院校是在新世纪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影响下由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或专科职业技术学院升级转型而成的,这种快速的升级转型既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转型期的特殊困境。就国学教育而言,与综合性大学以及那些相对资深的理工院校相比,地方理工院校一般都不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浓厚的人文氛围、齐全的学科体系和充足的国学师资,而且这些先天不足之处根本无法一蹴而就,即便是最基本的国学师资问题也不可能短期就补充齐备、立竿见影。如何在现有格局和条件下利用有限的资源迎难而上将是大多数地方理工院校国学教育实践之路上的普遍情形。
从现实出发,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资源并挖掘潜能,国学教育工作者们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实践和探索,其中,关于地方理工院校国学教育与思政教育适当结合的探索尝试日益引起关注。根据我们自己的实践心得,并参考学界同行的探索经验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国学教育与思政教育适当结合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中也具有可行性。
首先,尽管国学教育与思政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上自成体系,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彼此替代,但国学教育和思政教育在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国学渊雅深厚,其所包含的诸如爱国亲民、积极进取、社会和谐、仁义诚信等等知识内容和价值观都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和强调的,国学的这些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恰是思政教育所要努力发掘和发扬光大的。而且,许多国学典籍如《论语》等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通行教材,其中的教育理念、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自强不息”、“明德止善”、“知行合一”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教育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教育史上的硕果。这些教育理念、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对我们的当代思政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其次,人文教育至今仍是大多数理工院校的教育短板,人文教育资源欠缺是理工院校的普遍现状。这也是相当一部分理工院校目前有效开展国学教育的现实瓶颈。而大学思政教育经过这几十年的重视和发展,即便地方理工院校也是较为齐备充实的。思政教育系统涉及历史、哲学、政治、法律、文艺等众多学科门类,其中具有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学科背景的思政课教师若经有效整合,是可以胜任一般性的国学教学工作的。我们知道,虽然国学包罗万象,但其主体部分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大致对应现代学科体系下的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因此,从师资知识结构方面看,思政教师兼任适当的国学教育课程有两大便利和益处:一是学科对应,无需另起炉灶,重置资源;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情教育是思政教育的重点,这样的背景有利于国学教育活动中的“古为今用”和“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可以在思政教育与国学教育适当结合的探索实践中激荡互动。
在具体的国学教育实践中,联系现在一般地方理工院校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现行学科体系下的课程结构和理工学子的国学基础,我们认为,当前理工院校的国学教育课程设置以较为自由的选修课为宜,在引导广大理工学子关注国学、了解国学的同时,积极营造国学教育和学习的浓郁氛围,为下一步更加系统深入的国学教育打下基础、积累经验。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我们认为,尤其应当注重“点”、“面”结合,对文科学生,自然可以要求他们哪怕花上一个学期的时间去潜心钻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类任何一部单独的国学典籍,由点到面,日积月累而至于博雅;而对于国学基础本来就薄弱许多的理工学子来说,则宜于先从整体的“面”上引导学生了解国学总体面貌和基本知识,再落实到具体的典籍中去,这样才不致于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茫然无所措手。
国学的复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国学修养和人文素质的提高不可能朝发夕至,也不可能因一两门国学课程的开设而毕其功于一役。教育最忌浮躁冒进,应当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循序渐进,根据各自学校和学科的实际情况,努力探索最适合自身特点和条件的国学教育方式和方法。
[1]郭齐勇.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读书,2006(4):33-36.
[2]龚达发.人文之光照耀科学摇篮华中科技大学[N].人民日报,2004-05-13(01).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4]朱姝.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要求博士生必须会背《论语》[N].扬子晚报,2008-11-16(01).
[5]汪青松,査昌国,张国定,编.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